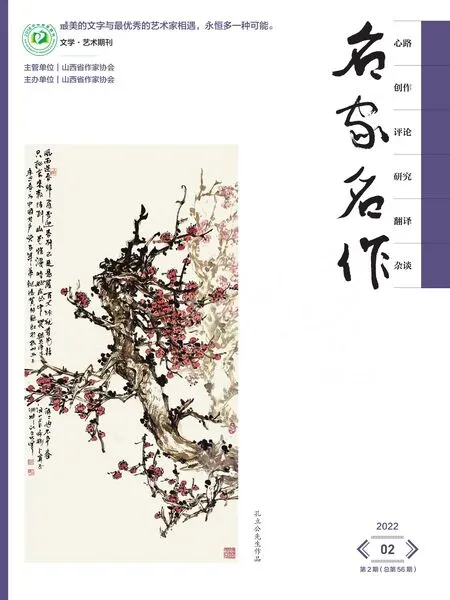现代戏中的母亲形象分析
——以《山村母亲》《土炕上的女人》《挑山女人》为例
2022-11-11姚瑶
姚 瑶
纵观国内外的文艺作品,对于母亲形象的赞美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之一。中华文化中早在诗经时代就开始了对母亲形象塑造的尝试。但提起具体的母亲形象,中国古代文学的相关叙述中塑造的母亲形象总是处于神圣、母性的一极,如三迁的孟母、刺字的岳母和为游子缝制身上衣的慈母。而在中国古典戏曲的领域中,母亲形象在剧中以主角出现的情况较少,大多数情况处于配角位置。母亲唱词、念白少有浓墨重彩,大多也只是零星点缀。总体而言,母亲形象在戏曲文本中基本上都是起辅助作用,凸显的只是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功能而没有明显的个人特征。从这一维度上来说,母亲复杂多义的本质属性与在戏曲叙事传统中单一的形象塑造似乎有着比较深刻的矛盾。戏曲文本在近几十年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涌现出一批与之前或相同或不同的母亲形象。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补充了戏曲文学传统中相关叙事的某些不足,同时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戏曲现代戏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可能。
母亲形象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其形象内涵一直随社会文化场域的变化而处于演变之中——她已经从单纯家庭内部的一种伦理角色逐步走向了带有公共领域意味的社会文化符号象征。因此,本文尝试以《山村母亲》《土炕上的女人》《挑山女人》为例,对新时期戏曲现代戏中的母亲形象做一番梳理,探讨其发展中的文化语境及其形象价值。
一、新时期戏曲现代戏中母亲形象的历时性发展特征
回溯五四时期,那是一个不孝不肖的时代,父子关系在这一节点处于两大历史断代的两端,它表现出一种压抑与反压抑的对立关系。父与子的对立是当时文艺作品表述的一贯母题。母女关系则相反,常常会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母女纽带,母与女分享着情感上的同一。她们的关系甚至时常密切到不容第三者插足的地步,不仅父亲的形象在文本中往往缺席,就是爱情也不能间离之。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对母亲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母亲代表了历史中的弱者。出于对强暴专制的封建父权秩序的逆反,作家们倾向于向历尽苦难的母亲形象的价值回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虽然举步维艰,但毋庸置疑,每一次社会转型都会让国民的人格经历一次重塑。奉儒道文化为圭臬的中华民族文化也常常因此而逐渐浮现出怀疑与反叛精神。“十七年”期间的文艺创作被赋予书写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时期是革命文化针对过去的一切文化成果而进行的一次大清洗的阶段。从表面上看,它是非常彻底的子文化的权力反篡。与五四时期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处处浸润着一种权力意识——女性作为父之子的精神同盟并不具有独立的话语空间,她只是男性的追随者,是被解放了的“娜拉”。直到中国迈入新时期,中华文化在更广阔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视阈里,女性的突围表演才变得理性而激越,女性话语才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而响亮。这时的女性不仅参与到子文化对父文化的批判之中,更主要的是它肩负了对整个男权文化的审视与反思的功能。新时期的戏曲现代戏也是这庞大文化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土炕上的女人》(原著《土炕》)创作于1981年,这一时期无论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史还是文化史上,都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时期。在《土炕上的女人》中,传统秩序中的女性角色,既包括母亲形象,也同时包括女儿和妻子的形象。但在剧中,杨三妞结婚当天即救下临盆的女战士,妻子的角色甚至不存在任何缓冲地直接过渡到母亲角色中。这样一来妻子的角色全部让位于母亲形象的塑造。通过这种关注力的倾斜,将被呵护的新时期改革的三代主力女性包裹在内,表现出了对历史中的个人命运的关注。这种人道主义的诉求,这种永远无限包容、永远等待救赎别人的母亲形象,不仅是一种拯救社会的想象性尝试,更是一种潜在的自我辩护与自我拯救的渴望。
蒲剧现代戏《山村母亲》,自1992年开始创作,2004年于山西省运城市青年蒲剧实验团首演。《山村母亲》几经易稿,经过了王辉、贾璐、杨焕育、田泓伟等编剧对剧作文本的反复打磨,经历了马肇录、张曼君、王乃兴等导演的数次排演,后又迎来了文华奖、梅花奖的获得者景雪变的精彩演绎,编、导、演三方面的通力合作才最终打造出这部成功之作。《山村母亲》多次获奖,迄今为止历经了四次改版,全国巡演超1400场,观剧人次逾百万。它的剧本还被一些其他地方性剧种移植搬演,如豫剧、曲剧、眉户等,在戏曲界形成了“《山村母亲》现象”。这一剧目同2012年首演的沪剧《挑山女人》一样,没有那么宏大的叙事动机与背景。《山村母亲》在蒲剧现代戏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带给古老的蒲剧艺术以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舞台戏曲到电影大银幕再到微电影媒介,《山村母亲》无疑是蒲剧现代戏多元发展的杰出代表。
纵观这三部成功的戏曲现代戏,其中母亲形象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特征和脉络。《土炕上的女人》中采用了宏大叙事的手法,将母亲形象更多地塑造成为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符号,以亲情、以母性缝合时代伤痛。在当时政治文化诉求下,母亲形象的最大变化是借助于政治力量摆脱了一向弱势的历史地位,突破个体形象的局限演变成为农民的整体象征,由单纯的母亲转化为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人民母亲。这样的转变突显了她们身上极富于奉献与牺牲精神的突出特征。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这种处理,在突出了母性内涵的同时也取消了母亲的差异性。在非历史的现实陈述中, 由于要迎合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的诉求, 原本复杂的生活被刻意设置为公与私、集体与个人、先进与落后的对立冲突, 普遍运用的二元对立的文学模式在遮蔽了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的同时, 母亲的形象也被简单机械地设置为进步抑或是落后, 使得在革命历史叙述中就已经简单化的母亲的形象越发陷入单一化和模式化的创作之中。到《山村母亲》中,主人公豆花在两个家庭之间穿梭,又在无意识中担负起了弥合乡村与城市二元结构之间巨大差距的功能。再到苦而不苦、坚守内核、实现母亲价值的《挑山女人》王美红。值得一提的是,在王美红身上有个尤其需要重视的细节,那就是她的感情线的铺设。虽然王美红的感情问题最终在婆婆以及女儿的干涉之下以失败告终,但这绝对是一次不能否认的质的突破——这体现了母亲形象超越了传统伦理纲常中的家庭秩序而走向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秩序。戏曲中的母亲形象终于不再只是从头贯穿到尾的母亲角色,她其实可以是一个女儿、一个妻子,更重要的是,她可以是一个女人。
二、母亲形象的塑造与父亲形象的缺席问题
按照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的观点来说,父亲作为孩子的主要抚养者,往往是孩子早年最佳的理想化对象。但是在今天所要讨论的三部现代戏中,代表父亲权威的文化秩序却发生了断层,父亲不再是家庭的维护者,剧中的孩子成长过程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父亲的缺位。这种父亲形象的缺席所传递出的信息十分微妙。
(一)对男女性别的无意识要求与社会期待
谈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及同类型剧作中的父亲形象塑造——在塑造传统意义上伟大无私的父亲形象时,母亲是可以存在的,只是相对来说比较隐形,而在塑造母亲形象时,父亲却是绝对不能在场,表现在戏剧中通常都是死亡的状态。这一个小小的区别可以追根溯源到自古以来对男女性别的无意识要求与社会期待,即女性肩负起家庭重担的前提必须是男性的缺席,否则,这样的责任就会自然而然地落到男人的肩上。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从戏剧文本来看,那就是女性若要发挥其情感价值与奉献价值,潜在前提必须是主流逻辑陷入危机也即男性缺位之时。
(二)中国儿童成长的历史遗留问题
中国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父亲缺位现象自古以来屡见不鲜——从孟子、欧阳修到鲁迅、林培源、池莉再到改革开放至今依然未解决的留守儿童问题。父亲在抚育孩子过程中的缺席现象虽不能说是一种传统,也足够称得上是一种常态。这些现代戏中的父亲缺位现象也许可以看作是中国儿童成长的历史遗留问题的侧面体现。作为文艺作品的创作人员,虽然没有承接问题剧的传统来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发散和控诉,但这三部剧作中渗透的共识与默契程度也可见一斑。
(三)文化惯性
针对这一点,笔者想要探讨关于“父亲死亡”这一设定的一个细节——为何父亲缺席的直接原因全都是父亲的死亡,而不能是离异或是母亲被抛弃等其他的原因?笔者以为,这个小小的问题牵涉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对于“秩序”的执着。如果我们再次回到中国古典戏曲中去寻找线索就会发现,“进入秩序” 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必定结局,是不论遭受多少艰难险阻,最终都必定要达到的一种叙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完整性。正如遭到始乱终弃的崔莺莺没有选择死亡一样,对那样一个逾越礼法的女性而言,死不能带来任何秩序所认可的意义。因而为了秩序及心理上的完满,她的命运最好也就是于始乱终弃之后,以嫁人方式重新安顿于“某妻”之位。
如果带着这样的逻辑再来思考父亲死亡结局的必然性,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在中华文化的潜意识中,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有资格做出牺牲和奉献的姿态的。她必须首先经过秩序的承认,这之后才有资格去牺牲。换句话说,她如果要成为一个被歌颂的伟大母亲,就绝不可能带着被抛弃的妻子身份、不可能处于被秩序排除的位置。从这个层面上讲,父亲的状态除了死亡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三、母亲形象的背后
中国人的母亲观是分裂的,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制度也往往让母亲们无所适从。这些年来,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读到许许多多颂扬母性的感人作品。那其中有忍受所有苦难、甘心情愿为家庭牺牲一切的伟大母亲,也有追求自我完善,同时能够兼顾家庭的完美母亲。无数感人故事所呈现的理想母亲大多以家庭为中心。然而,百年来的思想和社会制度,不仅反复教导妇女解放和独立,也同时不断动员和推动妇女走上革命、战争和生产劳动的第一线。在家庭、国家和可能的自我之间,被各种期望撕裂的女性,如何扮演母亲的角色、如何面对自己的母性,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女性面临的最大难题。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女性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表面”也不过是五四运动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历史只是男性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历史。女性这一性别作为群体可谓没有历史,她们仿佛来自虚无。因此,歌颂高大全的母亲形象、歌颂亲密而又沉重的母子抑或母女之情,事实上泄露了我们的理想之母形象的匮乏,这是一种性别历史传统的匮乏。这种尴尬的地位反映了女性在成长为性别主体道路上一个不可逾越的结构性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