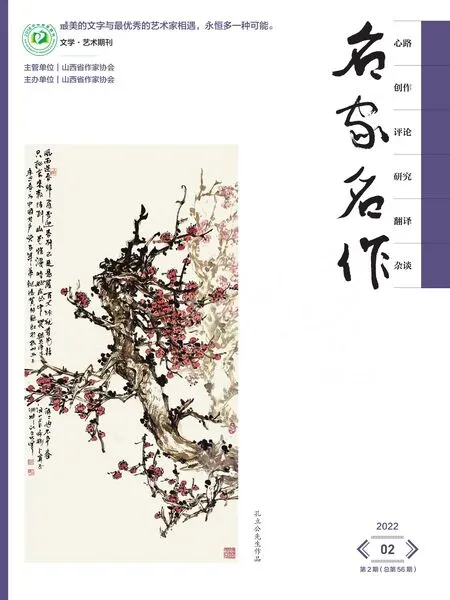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花凋》《倾城之恋》与女性成长
2022-11-11尹璐
尹 璐
作者单位:伦敦大学学院
当我们说孩子气的时候,可能会联想到任性、不自立等特质。而这些特质在成年女性身上也时有体现。成年女性的成长有时是通过对自我进行反思和剖析实现的。本文以《花凋》与《倾城之恋》为例,探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角色从孩子气到成熟的成长过程,看看在这一成长过程中女主角摒弃了哪些特质,以及在这一成长过程中的悲剧基调。
一、《花凋》:花也凋零人也没
《花凋》的开篇就已经申明女主角川嫦的离世,因此本篇是以倒叙的手法进行书写的,而川嫦悲剧性的成长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川嫦的一生就如文题所表达的那样,是一朵凋零的鲜花。她出生的家庭表面阔绰,实际上却要举债度日。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父母与诸位姐姐又都不甚在意她。直到她的姐姐们纷纷出嫁后,她才悄然绽放,开始享受爱情的滋润。然而,她却因中途不得不缠绵病榻被所爱的人抛弃,郁郁寡欢,最终黯然凋零。可以说,从一开始张爱玲就已经用死亡表达了川嫦悲剧的结局。作为张爱玲第一部也是非常重要的中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的一篇,相比于小说集中的其他篇章而言,《花凋》的研究体量逊色太多。比如在《张爱玲研究资料》中,它只是被简略提及,也鲜少有分析。但从女性成长的角度而言,文中所书写的川嫦短暂的一生所面对的主要命题,也是现实中年轻女性要面对的命题:自我与爱情。
从一开始,她就是不引人注目的,甚至朴素的,但是张爱玲很巧妙地以川嫦在姐姐们出嫁之后突然漂亮起来书写川嫦对得到关注的渴望:被压制的欲望终于得到了释放。同时,这也是对姐妹之情的讽刺:姐妹之间并没有友爱,而是明争暗斗。川嫦因为年纪最小则是被欺负的。她仍带着少女心态的贪妄:
她痴心想等爹有了钱,送她进大学,好好的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
但是,现实却是:
非得有很多的钱,多得满了出来,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
也就是说,她父亲郑先生作为一个遗少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思想:女儿的学业是最不重要、最不应该浪费钱的。而川嫦认为上大学并非是为了学习,而是“玩两年”,然后再嫁人。就像波伏娃所说:“她认为没有必要对自己提出许多要求,因为她的命运最终将不取决于她本人的努力。”川嫦把大学看作是一种让自己松一口气的手段:门第限制下,家里就像是一所新娘学校。在姐姐们都出嫁离开之后,川嫦终于可以坦然地美丽着。尽管她深知上大学的可能性极低,却仍旧怀抱憧憬。此时的川嫦尚带有孩童般的贪玩,对爱情、婚姻懵懂,并且视阈单纯。
在和章云藩相识之初,她仍旧是对爱情和未来充满希望的,她自觉值得更好的人,并且内心对章云藩是“纯粹不满”的。然而却在几次相处后爱上了这个人,因为章云藩是“第一个有可能性的男人”。也就是说,此时,面对异性,川嫦首先看重的并不是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而是结为姻亲的可能性,也就是所谓的“合适”。这也反映了在这期间,川嫦经历的心绪回落的过程:从有所幻想到肯定现实。
尽管回落到现实之中,但是川嫦对未来仍旧抱有希望:对爱情的希冀和对脱离原生家庭的希望。川嫦厌倦了总是吵吵闹闹、受到约束的原生家庭,以“开着无线电睡觉”作为拥有独立空间的标准。此时,川嫦已经意识到了她在家中被压抑的自我:既不独立,又不自由。然而她的爱情,也就是她结婚的希望,同样也是她脱离原生家庭的希望,却因为疾病被遏止,最终破灭。因为在病中得知章云藩有了新女友,她自觉无望:
以后预期着还有十年的美,十年的风头,二十年的荣华富贵,难道就此完了么?
而在见过章云藩的新女友,兼之她的父母因为都不想花钱给她买药而闹别扭最终不得不托章云藩代买药物之后,她生出了自贬的想法:
总之,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世界,她是个拖累。
因为曾经怀抱希望,在见到章云藩新女友之前尚还有疑问,在见过后则证实了无论是物质上的富足还是自我的彰显从此都已经无望。她的精神因为希望破灭和自怨自艾而“一寸一寸死亡”。而她没有最终找到自我的独立空间或者说“自己的房间”并不是因为她精神脆弱或者自我认识浅薄,而是被生病这一客观事实阻隔。也就是说她的成长受困于现实:从前受困于家庭,而可能性又被疾病抹杀。
同样是生病的状态下,丁玲笔下的莎菲却是主动的,无论是爱还是放弃,都是自主选择的。但是川嫦则是被动的:爱上只是因为刚好合适,而结束也是因病耽搁,最终被对方抛弃。同样是写自我意识觉醒的成长过程,可以说,莎菲的成长是完成了这个过程,而川嫦则是被迫中断。也就是说,病情并不是阻碍成长的决定性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爱玲小说中传统思想对角色的桎梏更加明显。张爱玲也曾在读圣玛利亚女校期间在校刊上公开发表评论,称赞过《莎菲女士的日记》,“写得极好,可以代表五四时期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莎菲的身上更多的是新思想的烙印,而川嫦则是旧思想的延续。如果说莎菲是破茧成蝶式的成长,那么川嫦则仿佛是作茧自缚。
尽管《花凋》的故事发生在上海,但是张爱玲并没有刻意提及地域。文中对传统的刻画是完全依赖于女主人公的家庭背景的,而她面对的则是原生家庭和留洋归来的(可能的)结婚对象所代表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而冲突的核心则是川嫦自己,一方面她厌烦原生家庭,另一方面又因为生病而被代表着现代的章云藩抛弃,最终不得不守着传统郁郁而终。她已经在心智上成熟,并且具有对“自己的房间”的渴望,但是她的成长受制于现实,因此并没有突围成功。她被迫压抑地成长,就是她一生悲凉的底色。
二、《倾城之恋》:任是无情也动人
对于成长小说而言,《倾城之恋》相对特殊的一点就是,故事的开篇女主人公就是一个离婚女性的状态。但是这不代表女主角白流苏缺乏成长性。白流苏作为上海白公馆的小姐,传统却又现代。故事主要发生在香港,白流苏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身无分文回到家中,备受冷嘲热讽。偶然认识了圆滑世故的单身汉范柳原,白流苏便远赴香港,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原本白流苏几近放弃,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香港遭受日军轰炸,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由此可见,白流苏一生中有几次转折:离婚,和范柳原相遇、斗法,放弃,战争中重逢。因此,可以想见,白流苏的成长是借由爱情之手的在成年之后的一种自我完善式的成长。
故事的开篇,白流苏与旧式婚姻进行彻底的告别:她的前夫因为肺炎死了。但是,尽管她已经离婚七八年了,她的兄长仍然劝说她回去奔丧、守寡。目的不仅仅与金钱有关,也是因为固化的传统,甚至连已经颁发的法律都不在意。因为在当时的传统语境下,离婚是违反天理人情的,甚至如白流苏的三哥所言“拆散人家夫妻是绝子绝孙的事儿”,白流苏这个离婚女性在白家是晦气的。而白流苏从决议离婚那一刻就是一个反传统的“新女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经挣脱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作为离婚女性,她对自己的定位是:没活路。因为她没上过两年学,所以不能出去工作,又没办法再嫁人。所以此刻她感到无路可走,内心是绝望的。新式婚姻中对于离婚的宽容给了她逃出旧式婚姻的出路,但是传统依然是使她痛苦的枷锁,而她的家人都是这副枷锁的帮凶。但是作为这个传统家庭中的一员,她畏惧苍老,对年龄敏感,也畏惧改变,所以面对媒人给她介绍其他人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同时,她的传统也表现在对男性的依赖上。范柳原原本是媒人介绍给白流苏的妹妹宝络的,在第一次见过范柳原的时候,白流苏的内心反而是:
可是她(白流苏)知道宝络恨虽恨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
也就是说,白流苏在与女性竞争男性资源中得到了胜利的快感。而她依赖男性的想法本身也是她把自己他者化的体现。
白流苏是聪明的,她从一开始就看透了范柳原的本性——花言巧语而自私。但是和同样看清楚男性追求者本性的苏菲相比,苏菲选择了离开,而白流苏的选择则是赌一赌。所以白流苏离开了上海,远赴香港。这也意味着她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告别了传统的、压抑的家庭。在香港,从原生家庭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白流苏对婚姻生活仍旧是抱着渴望与期待的,或者说,这一次出走,激活了这种感情。所以她才会愿意和范柳原在爱情中交锋。因为“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
但是,由于范柳原拒绝结婚,白流苏也拒绝做情妇,所以白流苏又一次回到了上海。这也可以看作白流苏的一种清醒的坚持。她在传统中现代,却又在开放中保守。她依然把男性和婚姻当作是生活的保障,她指望着范柳原带着较优的议和条件来和她走进婚姻。但是范柳原并没有,反而只是拍了个电报就使得白流苏被传统又保守的白家赶去了香港。而白流苏内心也因家庭压力而煎熬。但是她又清醒地明白“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也就是说,爱情只是附加价值,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经济安全。因此可以说,白流苏的爱功利甚至自私。
虽然她没有婚姻的保障却仍旧回到了范柳原身边,但是她拥有了川嫦梦寐以求的独立空间。她有了一个自己的住处。但是这却让她迷茫:她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她不是妻子,不必持家;不是母亲,不必照顾孩子,她只是情妇,避不见人,连社交都不必。她的房子和她的心灵一样空。但是,落在香港的炸弹却打破了这种空荡的平静。一场轰炸,白流苏反而在心里放下了钱财,因为她终于明白: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与其说残酷的现实让她们幻灭,不如说,人命的脆弱使她们看清。白流苏不再执着于用婚姻作为天长地久的保障,也不再把经济条件作为看重的因素。她所仰赖的是动荡之中的相互陪伴和依赖。她终于和自己也和对方达成了一种对于家的默契:在乱世中相互依存。或许,这看起来甚至有些皆大欢喜,但是张爱玲却在文章的末尾处写道:
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也就是说,白流苏的婚后生活是存有悲剧的隐喻的。她或许仍然被一些传统观念挟持着,无法抓住快乐。同时,这种压抑也是作者给她的生活埋下的隐患,是她从传统走出来后所存留的痕迹。她终于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但是只是怅惘。好在她终于完成了她的成长,相比起川嫦来说终究是幸运得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川嫦和白流苏的悲剧都与她们的另一半有关,也与她们传统的家庭背景相关。川嫦的成长因病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而白流苏的完成式却也依然怅惘。她们都没有足够自立地去面对这个世界,婚姻对她们而言也只是生存的一种手段。她们尽管摆脱了年轻时的天真与贪妄,但是在精神上却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脱。川嫦的病抹杀了希望,而白流苏终于走进了婚姻却也无法得到内心的富足。也就是说,她们的成长都受制于传统,充满了遗憾与怅然若失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