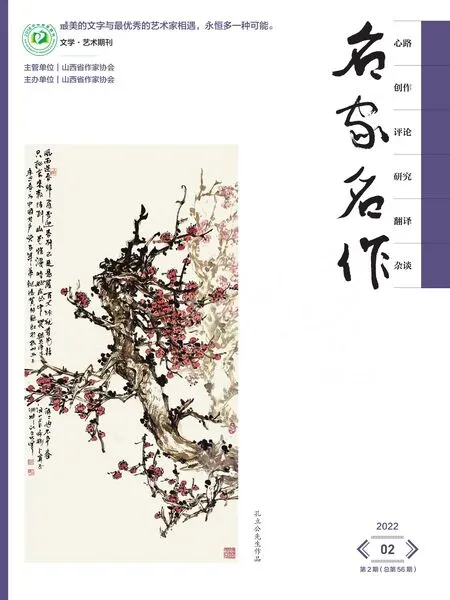论《雷雨》中隐形人物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2022-11-11张子佩
张子佩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雷雨》作为曹禺先生的处女作,同时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成熟而优美的收获”,从20世纪30年代问世以来就广受人们的喜爱与追捧,剧本多次重印出版,话剧上演经久不衰,甚至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将其从剧场搬至银幕。数十年来,也有许多文艺工作者对《雷雨》进行了剖析、深挖与再创作,但大多是站在一个理性的、学术的角度,带着宏观的、社会学的眼光去看待这部作品。然而,曹禺先生在《雷雨》序中写道:“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人,谈自己的作品恐怕也不会例外”。我们不妨以一个更为细腻柔软的视角,跟随作者“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的情怀,尝试去探寻与理解《雷雨》。
《雷雨》讲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周朴园与鲁侍萍两个旧情人在机缘巧合下相遇,促使周、鲁两家人如雷雨时密集的雨点一般,急促地聚集在一起,汇成洼地里的一滩积水,其中的恩怨纠葛难以平复理清;而周蘩漪等具有像雷雨夜中激烈的电光一样性格的人物,在雷电交加的夜晚彻底激化了这场积蓄三十余年的矛盾,使两个家庭成为被闪电击中的树木,最终酿成一场年轻的新叶永远逝去、苟延残喘的树干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生机的悲剧。我认为造成悲剧的主要导火索是三场三角恋,即周朴园、鲁侍萍与周蘩漪的“封建之恋”;周萍、鲁四凤与周蘩漪的“乱伦之恋”;鲁四凤、周萍与周冲的“荒唐之恋”。
虽然看似是这三场复杂的感情将两个家族推向了家破人亡的深渊,但仔细品读后发现,在剧中暗含的两个隐形人物,即赶走鲁侍萍后周家迎娶的“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和侍萍在鲁贵之前的第一个丈夫。尽管在全剧只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近乎隐形,但他们却像木偶背后的提线一般,对整个话剧情节发展与人物形象塑造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在人物设置方面,周朴园和鲁侍萍分开后,两人都分别另结了两次婚。我认为,不论是“有钱有门第”的小姐,或是鲁侍萍离开周家后所嫁的第一个丈夫,都可以从周蘩漪和鲁贵身上找到他们的影子。从周朴园迎娶的“有钱有门第”的小姐来说,在匆忙赶走鲁侍萍后,她被迫嫁入周家,可知这是一场由父母包办的家族联姻,看中的是她“有钱有门第”,这位小姐只是利益间一枚无辜的棋子罢了。周朴园对她是毫无感情的,甚至会将他与鲁侍萍爱情的不幸归宿以及传言中鲁侍萍“投水自尽”的惨死结局都归结于她、迁怒于她。而这位出身高贵的小姐可能同周蘩漪一样是受过教育的,也是对爱情有着美好追求和向往的女性。一个弱小的女子在森严的封建大家庭中,孤立无援又得不到丈夫的关爱,自己也无力反抗,境遇可想而知。这些猜测在《雷雨》中也得到了一些证实。例如,周公馆里一直摆放着鲁侍萍的相片,她在时的一切家具和习惯都按原样保留了下来。上到周蘩漪、少爷,下至家里的仆人都知道侍萍的存在,而这位小姐却从未被提起。另外,我认为造成这位小姐的悲惨命运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她没有孩子。开篇的人物列表中,周家的少爷只有鲁侍萍所生的周萍和周蘩漪所生的周冲。与此呼应的是,鲁侍萍说过,她曾被逼将亲生的两个孩子留在周家,说明周家对子嗣的重视。在这样的家庭中,即便善良贤惠、家世优越,但没有孩子是无法立足的。“有钱有门第”的小姐的命运让我想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梅珊和颂莲,她们只是有钱人家随意更换的玩物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没有子女,被强大的封建势力与残酷的人生现实所压垮后或死或疯。当别人谈论起她们时,一个草草敷衍的微笑或一句轻描淡写的“疯了”就概括了她们渺小的一生。不久,同样年轻单纯的五太太便嫁进老宅,步了后尘。“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如此,周蘩漪亦是如此。
鲁侍萍提及离开周家后所嫁的第一个丈夫时,她说到“是很下等的人,遇人都很不如意”。两个“很”字,一个点破了现实,一个诉尽了命运。“很下等”侧面反映了鲁侍萍的地位,她作为贫苦人家的女儿,带着没有来历的孩子背井离乡。她在世俗的眼光中是下等的,所以也只有“很下等”的男人愿意娶她。曾经年轻貌美的鲁侍萍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让人不禁为之心痛。“很不如意”则是与鲁侍萍的悲惨命运所关联的,倘若她在离开周朴园后遇到一个老实本分的男人,也可安稳度过余生,她却偏偏遇人不淑。鲁侍萍如同《神女》中阮玲玉饰演的带着孩子的妓女,母子二人误入流氓的住所,从此饱受流氓的欺凌和敲诈。想必她的上一任丈夫大抵如此,有着自私势利的嘴脸,染上底层人普遍的赌博恶习,对年幼的鲁大海打骂斥责,挥霍鲁侍萍辛苦赚来的钱去吃喝玩乐……大概鲁侍萍不堪忍受,逃出了那个家庭,却不曾想到后来又遇到了鲁贵这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始终难逃悲剧的命运。
这两个隐形人物为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犹如作者提供的两个已勾勒好的轮廓,其中的内容需要读者去填充、描摹。可看似无关大局的人物是否就不重要?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和鲁侍萍嫁给的“很下等的人”与剧中的人物是互相映衬的。小姐与周蘩漪,“下等人”与鲁贵。纵然结婚的时间点不同,但是周朴园和鲁侍萍的身份地位是没有改变的,在这种固化的背景下,通过读者对隐形人物的性格、命运的猜测,也就更能深化对话剧中实在的人物的了解。因为他们只是两个隐形人物后来的替代品,有不同的姓名,但具有相同的性质。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周朴园与那位小姐以及鲁侍萍和那个“下等人”的结局都是破碎凋零的,因此我觉得这也是对第四幕中两个家庭都鸡犬不宁、家破人亡的一个暗示。其次,隐形人物的设置间接地引导了话剧情节的发展。如果他们可以分别与周、鲁二人相守一生,那么就不会有周蘩漪和鲁贵的出现,之后的一切紧张集中的情节也无从继续,所以看似无足轻重的人物却对往后的情节有重要的影响。最后,我认为隐形人物可以帮助传达悲剧的深刻意义。曹禺先生说过,“《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近代的人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诚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专门探讨过悲剧的含义。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我想这也是曹禺先生创作《雷雨》时所赋予它的更深层的悲剧意义。
从话剧结构情节的角度来看,隐形人物的存在也是合情合理、十分必要的。在戏剧结构方面,《雷雨》采用了封闭式戏剧结构,同时遵循了戏剧的“三一律”原则。即单一讲述了周、鲁两家人的恩怨情仇,最后矛盾像雷雨般狂躁肆虐地爆发出来;情节大都发生在周公馆的客厅,这也是矛盾的始发地;主要情节从第一幕到第四幕,时间从早晨持续到当天半夜两点钟,恰好是一昼夜以内,一切在那个风雨交加的雷雨夜里有了定数。曹禺先生巧妙地将戏剧叙事的顺叙和倒叙结合在一起,封闭回溯式的结构有助于凸显矛盾,使其爆发得更加集中,更加震撼读者的心灵,但美中不足的是,在一个昼夜内让八个主要人物中三人死、两人疯未免太过局促,除去序幕和尾声的舒缓作用,不如利用话剧的回溯式结构,安排“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和鲁侍萍离开周家后所嫁的第一个丈夫这两个隐形人物穿插其中,增强话剧的空白感,从而缓解过度集中带来的紧张感。还有整部话剧的结构是短小精炼的,作者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设置冲突矛盾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需要对人物进行精心的设计,保证剧本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所以,对于与主要情节关联性不强的人物进行隐藏化处理也是合理、必要的。
在戏剧性情节方面,巧合在《雷雨》中体现得格外明显,使话剧情节曲折离奇。在第二幕鲁侍萍与周朴园的对话中,周朴园问其不再找周家的原因,鲁侍萍回答道自己为了孩子嫁过两次。若是没有鲁侍萍的第一个丈夫,即隐形人物的及时出现,可能她会找回周家,也就没有了后来强烈的冲突与曲折的情节。当年周家人以为鲁侍萍已“投水自尽”,但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了下来,是一个巧合,最后在“不公平的命的指使”下来到周公馆,这又是一个巧合。两个巧合叠加在一起,在周朴园眼里,鲁侍萍成了“死而复生”的人。“死而复生”的巧合的情节设置,与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苏斯的复活经历有着相通之处,是有代表性的戏剧性情节。
在戏剧冲突的设置上,两个隐形人物更是发挥了其独有的作用。隐形人物中那个“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再加上鲁侍萍,周蘩漪明白周朴园在她之前有过两段婚姻,聪明的她自然也知道,她与周朴园之间不会有真正的爱情存在,从嫁入周家那天起,她便预料到自己未来生活的无奈和悲惨。但有着“雷雨”般火热性格的她不甘于这样的处境,与周萍开始了一段乱伦的恋情。周萍恰好从小缺乏生母的照顾,再加上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恋母情结”。这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都有体现。这段为人不齿的感情为往后周萍移情四凤埋下了冲突的种子。此外,在鲁侍萍知道女儿四凤与周家少爷恋爱后,除去他们是兄妹的原因,她在离开周家后接连两段婚姻的不如意与遇人不淑尝到的苦头,包括其中鲁侍萍的前一个丈夫作为反面的隐形人物的作用,更加促使了她为了避免女儿重蹈覆辙而对周萍与四凤的感情的阻拦反对。而这又是一个戏剧冲突,一个个矛盾冲突像一根根导线一般,最终在雷雨之夜仿佛一触即发。
《雷雨》作为中国话剧史上有着里程碑式意义的作品,对后世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后来,话剧爱好者不再满足于对剧本进行单纯的描摹与复现,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将《雷雨》改编成舞剧、电视剧和电影等。尽管具体的事件和人物由于改编的需求变得不尽相同,但其中都有《雷雨》的影子,成为中国现当代文艺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因此,“雷雨式”的戏剧结构与“雷雨式”的人物形象,正是这部划时代意义的话剧作品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