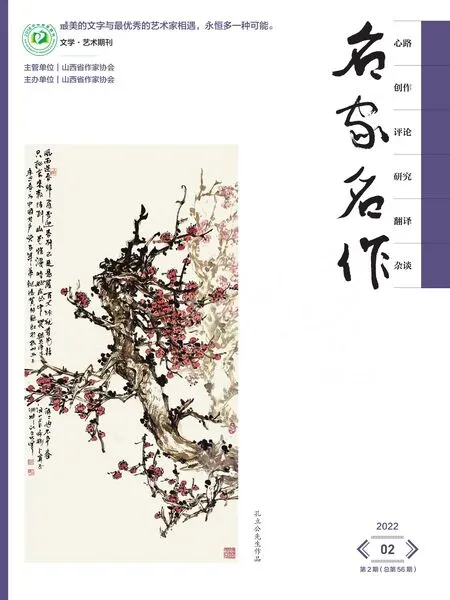论《庄子·人间世》的“返真”
2022-11-11周鹏
周 鹏
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在《人间世》中被分为三类,即士人、异人、无用者。且其虽分属三类,但所追求的进路历程都是一种“返真”,或者说都是在世俗社会这一视域中完成人—天机制的转换,进而达到一种“真人”的境界。
一、士人的“不伪”
士人的“不伪”是在“入世”(政治生活)中展开的。一来,“不伪”是由身向心、由形向神、由外向内的一种修养方法。待到其坐忘自身的存在,进入一种空明虚静的境界。也只有做到这样,才算达到无用而感化万物的境界。并且,这种“不伪”也是“禹、舜之所鈕也,伏戏、几蘧之所行终”。因之,《庄子》的“心斋”更多是一种以积极的态度应人世的“静”的修养方法,只是其更强调“不伪”。
二来,“不伪”是为人臣子对“命”与“义”的应尽便须尽。其“不伪”是在使身心置于虚静状态下,调养心性随境流转、事与时宜。再则,这里还提出“养中”的修养方法,一方面可以说是对颜回“心斋”的另一种解法;另一方面也是从“动”的角度,“顺着老子的‘守中’之义发展而来的”。其将“虚静”状态的人置于世间“乘物以游心”,心神在顺任外物的自然流淌时不忘观照外事。因而其“‘游心’是一种以艺术精神而入世的心态”。
三来,“不伪”是为师者的“虚己用”,即:“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这里的“不伪”是对上两类“虚静”修养方法的小结,且从师者的视角提出的“虚己用”,更是“顺”与“达”对“动”与“静”的调和而形成的一种“颐”。《易经·颐卦》有言:“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因为双方关系的和谐与形式的稳定,一则是以为师者在主动一方保持积极主动为前提的;二则需要善用客体的良好素质。但是作为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为师者,其虽立身为“此”,但仍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并主动处置好动与静、顺与达的平衡。
质言之,士人的“不伪”,是于救世与保身之两难中对“间”的一种把握。士人的“返真”可以说是一种对生存间隙的探寻,或者说是一种“即离”,即入世(救世)与求虚静其心、坐忘其身的一种“离”的超越。因之,士人的“不伪”是忘我至“虚心集道、游心养道、和心达道”,进而以与世俗处。如明朝学者陈治安云:“《人间世》篇,于人情世故极是委屈周旋,世法不疏也。”总的来说,士人的“不伪”虽然在主观上占了主动,但仍需通过更多对己身之修行来缓和、疏导客体制约的因素以达到间世的“无用”,其在“返真”的进路上仍需要多加修持。
二、异人的“不材”
相对士人的“不伪”,异人(以树喻人)的“不材”则是“无所可用”。一来,“不材”是栎树的“无功用而大用”。栎树既然本身无功用,也就不需要含藏锋芒,因而连“虚己用”这一层修养功夫都可以省去,可以说是紧挨着对士人“不伪”作再一次推进。但是,其“以义誉之,不亦远乎!”成玄英疏:“而社神寄托,以成诟厉,更以社义赞誉,失之弥远。”宣云:“‘义,常理。’案:彼非托社神以自荣,而以常理称之,于情事远也。”简言之,其相较常理的“无功用”,多了一层“忘”讥讽之言的功夫。
二来,“不材”是商丘树的“不祥”。商丘树不仅没有功用价值,还被世人憎为“不祥”,但也正因之而“大祥”。相较而言,商丘树的“异材”又是对栎树“不材”的一种更进。因其非但“不材”,还为人所“憎恶”,与“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一般。因之,商丘树兼而无功用与“不祥”,全性保真于人间世得享吉祥。
简言之,异人之“不材”只需要持守自己的本真,就可以不为人事所伤损,亦不为世俗的道德价值所束缚。并且,异人对士人的超越还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否定,是将人事的功用还原为最本真的自然之性与天之“材”。换言之,异人持真、无伪而超越人世功用,在“返真”进程上较士人行得更远。
三、无用者的“离德”
相对于士人、异人,无用者更是将“人”的身份性剔除,进而提出“返真”之“离德”。其“离德”一来是通过对身形的支离达到对身的“忘”,进而上升为对“德”的支离。且无用者既不要像士人那样需要“虚静”其心、“虚己用”,也不需要如异人之寄身社中、为世人憎恶等。其只需忘身而端德,不因身形的缺陷而卑怯,就可以“于传统道德价值之外寻求心灵的自适与自由”。再则,《德充符》中对支离疏者的忘形作了更进一步的补充,即“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也就是说,其在“持真忘形”基础上的“端德自充”,不仅会使形体上的缺陷被主体遗忘,更会在充实的过程中被客体遗忘。
二来是“离德”即离德无得。圣人之“离德”是在“离形端德”的基础上,将“真”递推至最高处,以至“吾行郤曲,无伤吾足”。而在《德充符》中,亦有对圣人之形、德支离的总结,其认为圣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圣人的形貌与常情也一般,只是没有对情感的偏好。无用者离德而无得是因为“道是人和物的最后的物质基础。得到了‘道’的人,就会‘四肢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因之,正如《庄子·逍遥游》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用者只得一“方今之世,仅免刑焉”的喟叹,但这声喟叹传达的非是《庄子》之无情。相反,正如清代学者胡文英所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无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无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简言之,无用者“离德”而得,类似一种“自我回返的退隐,其实是主体返归虚空,或是回到混沌,接近海德格尔所谓的听其自然或泰然任之的经验,即让意识与自我从中解脱出来,而事物在身体的世界内自行运作”。借用明朝学者钱澄之言:“《易》之道尽于时,庄之学尽于游。时者入世之事也,游者出世之事也。惟能入世,即使入世,仍是出世。”
四、小结
总的来说,《庄子》的“返真”是应对乱世而提。当然,其在有道之世也有其意义与价值,因为有道之世亦有无道之时与失德之事。继而,《庄子》追求的虽然是人间世的“返真”,但这并非厌世、弃世,而是一种于浊世的积极求生。因而《庄子》的处世之道被扣以“滑头”“混世”“消极避世”等都是很有问题的。诚如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应该对之持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从境界论的角度来看,无用者的“返真”,即“让人自身内在于自然之中或与自然同在”。“返真”成了一种自心、自性的自然流淌,“人间世”的泯绝无迹,更是一种随境流转的“心行”。因为“到了《庄子》,更偏向于对‘人’的内在精神超越和自由境界的探寻”。而人之“无用”是经困顿与修行功夫之后归返的一种“真”的境界状态。且其“无用”的观点“既包含确认‘用’的相对性:虽‘无用’于彼,却可‘有用’于此;也强调了‘用’的内在意义体现于人的存在‘无用’之‘大用’,即表现为对人的存在的肯定”。
另外,从处世哲学的角度来看,《庄子》的“返真”亦可以说是“自全而全人之妙术”,而其所追求的则是一种无为、无情之“真”的玄妙状态。如其《德充符》所述:“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同样,张岱年先生也有相类似的论述:“人的有思虑,有知识,有情欲,有作为,实都是自然而然。有为本是人类生活之自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返真”也就是《庄子》的“达生”,即“寻找个人对生命的完成和精神对生命的超越”。方东美先生对《庄子》之“达生”所达到的“忘”作解为:“不滞,常住。”进言之,《庄子》之无用者不仅没有因精神上超越而带来的优越感,有的反而只是平等感。
质言之,《人间世》的“返真”在“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境遇中即形而忘形,“离形”而德有所长,“离德”而超越“得”。《道德经》有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故以无德。”无用者不仅有对无德的“离”,也有对有德的“离”。且其作为一种对生命的超越,所有归返之修养工夫都在与道同游的“真”中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