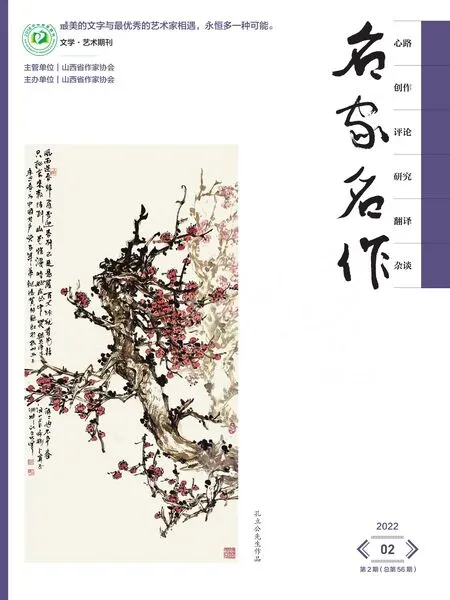诗歌·王位·太阳
2022-11-11赵嘉程
赵嘉程
海子,1964年3月24日生于安徽怀宁,1989年3月26日卒于山海铁轨。
——题记
1984年的秋天深倦难耐,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火车飞驰,车厢末节,他临窗而坐,启程返乡。车窗外火红的叶成为肃秋最炙热的迸裂,多像初恋女友与他相遇时娇艳的面容,热恋如花绽放,如收获之果,充盈而美好,而如今花已开在高高的树上,可果却结在了深深的地下,当年的恋人分离相别,她已在异乡组建了家庭。
他不时整理蓬乱的头发,来回摸索短胡,食指反复揉搓微微泛红的鼻尖,再颤巍地抬起右臂,侧身轻靠在冰冷的车窗上。
双膝如木,视线所及之处都是河流杂草幽幽的眼睛,呼吸之间,沉默的是车下的土地,也是曾郁郁葱葱的心灵。窗外,树上数不尽的枫叶织成一张红棕色的大网,撒满了他的面颊,难以挣脱,也不再挣脱。耳边人声沥沥,切断了他的思绪,他划破密网,获得短暂喘息。
车上两个孩童追逐着、吵闹着,孩子母亲对着内坐的他投来歉意的目光。他注视着孩子,真真切切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月夜,独自躺在屋前的麦地里,借着微弱的星光,望着连夜种麦的父亲。父亲微微曲驼的背上,仿佛流淌着流金般的美好。故乡的风,家乡的云,也曾收聚成最轻柔的翅膀,安恬地睡在他的双肩,对他无限赠予。
渐渐地,车厢里,孩童的嬉闹声寂了,偶有男人此起彼伏的鼾声。他摘下黑框眼镜放在衣服右边的口袋里,闭眼静思。五年前,他站在村头的包谷地旁,无比笃定。告别故乡的木屋与清水、星月与羊群、鲜花与麦地。带着远方的梦,一路向北。
从小城怀宁到首都北京,他像巨树一般,向往着高处的阳光。可他的根却伸向了黑暗的地底。远方的梦在孤寂中成了野花一片,岁月在时间里已尘埃无边。想到这里,我渐合上了书页,叹息不已。
1984年,才二十岁的他,就写出了《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轰动全国。后来更是一发不可收,在七年的时间里竟然创作了近两百万字的诗歌。每一首诗中都藏着他对人生的思考和灵魂深处的疯狂,而这些思考和疯狂也不断折磨着他,使他走向了人生的另外一个极端。现实像一把闪闪发亮的斧子,血刃着孤独的灵魂;或许它就是那一辆拉着被囚禁且失明的诗人的车,携带着他奔向最后的法场,那时的他已暗惨得可怕。
因为练气功“走火入魔”,他已经长时间地处在精神错乱的崩溃中,经常出现幻听。1989年初春,大地在张裂的痛苦中哀鸣,空气中弥散着空虚和寒冷。那个黑夜的儿子,早已来不及触摸春的诗花,他多愿冲破浓密,像春光像火焰,奔向太阳。可他确信要走,在三月的诗尾,火把燃烧的最后一夜。
老人们在巨大的悲痛中再没有任何话语,木然地捧着他曾来到人间的证据回到查湾。有人来访,老人时而不发一言,时而语无伦次:“害在气功上,害在气功上,当初要是去海南可能就不会这样。”偶有几个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前来探望,老人紧紧盯着,再不舍得松下眼眶,脸上多了几十年的苍老,撕心裂肺的痛苦,需要时间才能慢慢释放出它的毒性。最后,无人打扰的,他睡在了松林掩映的山坡上。
他的一生早已是一坛发了酵的老酒,随着岁月的流逝,灵魂的浓度越酿越陈,陈酒味弥漫,让每一位知道他一生的人在扼腕长叹之外,感受着自己青春时代相同的梦想和不同的命运结局。泪水涟涟中,我似乎又看到他复活了,诗歌之魂陪伴着他,他静静地躺在高高堆起的谷堆旁,望着父亲,浅浅哼唱;时而,他发出低低的怒吼,在黯淡的道路上疯狂奔驰,尘世扯乱了他的发,漆黑无光。最后他毅然再次点起火把,燃烧了自己,熔铸成了太阳,身骨葬于山顶,灵魂沉睡麦乡。
“你为何无法走出灵魂的苦井?”
“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透过窗外模糊的暗影,我仿佛听到他这样凄然地答道。
查湾的农舍被加固成了他儿时梦寐以求的书屋,三间平瓦房守卫着他生前一一碰触抚摸过的书册,瓦屋木门、绿树映日,年年岁岁,探访的人络绎不绝,来来往往间总能给予老人些许的安慰,总还有人记得他们珍爱的孩子,对诗歌的眷恋,诗歌之魂在人来人往中延续着。他们在唇齿与心灵的律动中体会着诗歌带给他们最初的悸动,无数低回的倾诉汇成声浪,成了查湾屋舍前新芽破土时清脆爽朗的声响。
耳边的磕哒声时显时隐,车身渐趋平缓,我慢慢收起思绪。
“山海关将要到达,请各位旅客带好随身行李。”火车里传来播音声,车站内阳光炽烈。我郑重地合上诗集,携着他的文字,启程前往山海关,试图抵达他那颗沉睡在春天里永远年轻着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