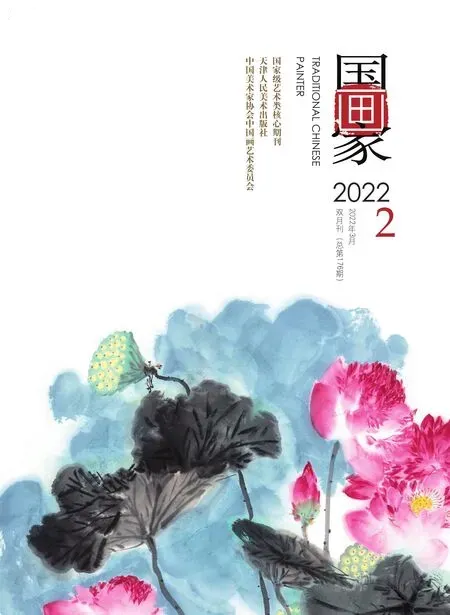浅谈中国早期壁画与盛唐白画的“凹凸风格”
2022-11-06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蔺洁青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蔺洁青
书画鉴定家谢稚柳曾评价北宋画家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说:“最前的一段,对‘人影在地’作了突出的描写,这一种题材的表现,除在中唐以前的壁画上有过外,其他的图绘中是从未见过的。”的确,中国古代绘画中鲜有直接表现“光影”的作品,但不乏一些利用光影明暗呈现出相对立体的“凹凸”画风,这种风格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的壁画上。
近年来有许多针对敦煌壁画及各地的早期墓室壁画资料的研究,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线描本身就可以通过粗细、浓淡的变化来表现物象的量感,这是本土绘画语言原本就有的技法和能力,所谓外来的“凹凸法”或“阴影法”的传入只是刺激了中国画家对表现“光影”画法的兴趣,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东汉的墓室壁画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由宽粗的线条勾勒的人物形象,这些较粗的线条并没有很好地表达出衣服与躯体的结构关系,更像是一种对衣褶阴影的平面化概括,极具装饰意味,并与身上及脸部其他较细的线条,形成了整体的装饰风格。画家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肆意地组织着线条,有些暗示着物象的轮廓结构、有些则是阴影结构,它们之间随意的交替组合形成了极具律动感和平面性的画风。
研究发现,这些东汉时期墓室壁画的笔描与敦煌早期的壁画技法又有着天差地别。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输入,大量的佛教绘画技法也随之引入,张僧繇受到了阿旃陀石窟壁画的“天竺凹凸花”技法的影响,画出了立体感十足的“凹凸花”。北凉时期敦煌二七五洞里所绘的《尸毗王本生》里明显与传统的线描画法有所区别,例如,人物的胸部与腹部以粗宽的色线概括出胸腹的肌肉结构,据研究表明,这些浓重的线条原本是肉色,但由于年代久远原本的肉色便氧化为暗黑色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画家当时是用宽粗色线描绘阴影来交代人物肌肉结构的意图。此外,人物脸部如眼眶及下眼睑部分也用了相似的手法,将结构的凹凸变化以模板化地概括了出来。这些技法与本土笔描传统技法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足以说明外来的风格对其有一定的影响。
这种风格来自古印度的犍陀罗艺术,但经过了中亚诸国的传递,印度佛画中充分的凹凸晕染技法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被削弱和改造,到了中国已然成为一种模板化的形式。新疆克孜尔石窟的“雕像窟”壁画中的人物风格与敦煌二七五洞的画法相似,都利用有颜色的粗线条来表现阴影增加体积感,但不同的是克孜尔壁画中代表人物结构的色晕浓淡层次更加丰富、有渐变,而敦煌壁画里则没有这种变化。这说明了当面临一种新的风格时,中国画家们在接纳的同时又由于不够了解,而以本土的绘画方式来模仿这种新技法。
无论是从克孜尔石窟还是敦煌石窟的早期壁画,我们都能看到外来风格与本土艺术传统是可以和谐并存与融合的,在当时的画家们眼里,这只是可供选择的两种绘画方式,当绘制佛像题材这种外来的人物形象时,自然多取宽色带的绘画技法,当遇到俗世的题材时,画家们又回归到了原有的笔描传统,抛弃了代表阴影的色带而选择了纯粹的线条。当然,中国线描经历了与外来凹凸风格共存的漫长时期,其表达形体结构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因为当时画家在对凹凸法造成的光影立体效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后,在重新审视物象的有机立体结构时便有了更为理性的分析与归纳。换言之,中国的笔描开始了对归纳凹凸色晕表象下有机立体结构的潜力的挖掘。
总而言之,在早期的壁画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作者试图突破二维空间、寻求三维立体逼真幻象的动机,他们的不懈尝试为盛唐时期两种白画风格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唐代是中国人物画的鼎盛时期,“画圣”吴道子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他把物象的复杂结构及受光之后的凹凸面、阴阳面归纳成了唯一合法性的线,再结合书法创作意念所传达的运动感和韵律感,创造了新的画风,被后世的画家们所效仿和借鉴。北宋画家李公麟的“白描”画法深得吴道子的旨趣。唐代的壁画或纸本作品与当时其他色彩艳丽的画作对比,显得清淡得多,这也许是唐人将之称为“白画”的原因。
唐代文献里的“白画”有别于我们熟知的“白描”。前者指的是以线描为主,再施以墨色及色彩晕染的画作,后者指仅以淡墨勾勒轮廓,不再另施色彩。因此,白画的表现范围要比白描广泛得多,不仅能表现物象的外在轮廓,还能表现体积及质感。在白画的观念里,线条只是勾勒出物象的轮廓以及轮廓内表现结构的纹理,线条本身并不能表现出物象结构的受光现象,但通过墨或色彩晕染的深浅变化光影的效能便显现了出来,也就具备了体现量感的能力。
段成式在评吴道子于长乐坊赵景公寺中所绘的地狱变时说:“惨淡十堵内,吴生纵狂迹;风云将逼人,鬼神如脱壁。”此种“脱壁”的效果正是利用光影绘制出量感而产生的逼真立体的视觉体验。
石守谦在《盛唐白画之成立与笔描能力之扩展》一文中论述了中国画线描能力的提升表现,他指出中国画将西来的色彩凹凸法转换成了两种绘画技巧,一种是将浓淡层次的色彩晕染转换为见笔踪的墨晕,另一种就是利用线条的组织来体现形体结构实现传神的造型,概括之为——墨晕式与笔描式,这两种途径虽有不同,但同样体现了物象的结构与立体感。
我们可以试举两例来对比这两种画法的相似与区别之处。韩幹的《照夜白图》中马的形体用流畅的线条勾勒而成,造型结构清晰细致,形体内部的结构关系则通过墨色晕染出阴影来表现,线条在其中担任了辅助性的角色,在一些肌肉体块与肌理如眼周、胸部肌肉等地方则靠墨色来晕染,此时的线条与墨晕相融合成为了阴影的边界线。敦煌103窟中的壁画《维摩诘经变图》则是另外一种靠线条组织来表达形体结构的方法。人物身上的凹凸效果不同于墨色晕染的方法,而是依靠线条的粗细疏密、浓淡虚实的变化来呈现出光影效果,例如,在表现维摩诘的右肩、手臂与身体的关系时,以不同浓淡粗细的密集线条做放射状组织出来,一方面体现了形体结构关系,一方面也将受光情况传译出来。人物通体没有浓重的墨晕,但衣纹的凹凸感十足,这种靠线条的组合方式呈现出亮暗的变化是对于阴影法的一种成功转换。在人物脸部的刻画上,充分体现出了光影对于结构形态的影响。中国人物画自东晋顾恺之以来特别注重“传神”,《维摩诘经变图》中人物的下眼睑用双弧线勾勒,极似西方素描中暗部的轮廓,巧妙地体现了眼球凸起的结构。外眼角的浓淡粗细不同的线条直接形成了相对的阴影变化。鼻翼处用浓线勾出,暗示了与脸颊相邻所产生的阴影等等。这些对于光影变化的细致把握,不但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肌肉结构,达到了“传神”的目的,也大大地加强了线描的表现力。
盛唐“白画”里线描的结构较之两汉魏晋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一转变无疑离不开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绘画从西域传入中土的巨大影响。中国虽然很早就发展出了偏重线条的艺术,如彩陶、青铜器上的纹饰及书法艺术,但就绘画而言,线条的作用仅仅是为了画出物象的轮廓及各区域的界限,对于形体的结构及体积感并不是画家们所追求的目的,他们是为了追求形体及线条的优美律动。可以说,白画里的线描对归纳和表达复杂结构的能力的提升,正是吸收和借鉴了外来的凹凸法或阴影法之后对本土的线描传统丰富和扩展的结果。
结论
纵观汉代至唐代的线描作品,从线条形式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就线条所能表现物象结构的能力方面确是一个不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画家们在接受了外来的“凹凸法”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本土的线描传统,而将之加以融合,使得唐代的笔描作品形成了有别于汉晋时期的独特风格,奠定了宋、元、明、清各代的笔描绘画根基。即使明清时期亦真亦幻的西方绘画再次冲击中国画坛,激起了中国画家对本土绘画传统的再思考,但古典主义的典型模式依然在其中扮演着有力角色,中国绘画仍然保持着自身传统与外来“凹凸法”融合后的“凹凸风格”,又一次完成了内在自足的渐变。
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还与中国的轴心文明、哲思传统、绘画理论中的观看之道和评判体系,以及材料工具等息息相关。不过,对一种风格的“归本溯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也避免不了片面化和局限性,我们要尽可能地深入复杂而丰富的文化景观,才能把握最核心的脉动,为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襄助。
[1]郑重,《谢稚柳系年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2][唐]许嵩,《建康实录》,中华书局,2015年版。
[3]苏莹辉,《敦煌及施奇利亚壁画所用凹凸法渊源于印度略论》,《故宫季刊》,1970年4卷第4期,第13—18页。
[4]石守谦,《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7—38页。
[5]饶宗颐,《敦煌白画》,饶宗颐学术馆,2010年,第5页。
[6]段成式,《寺塔记》(上),第6—7页。
[7]石守谦,《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