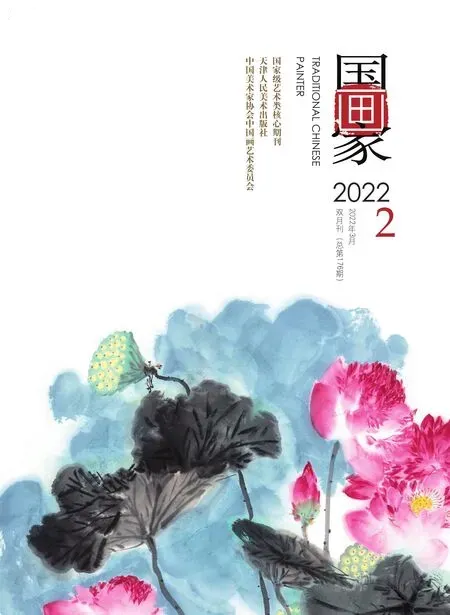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
——“渔隐”中国文艺创作之一洞天
2022-11-06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高群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高可心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高群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高可心
“渔隐”是中国文艺创作中一个特殊的题材,也是中国隐逸文化一个突出的热点,中国文人惯常取用“渔隐”题材抒发自己闲适旷达的心境。“渔隐”能够成为历代诗文书画中常见的题材,得力于它是文人最乐于表现的一类。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左右着一代又一代士子学者的人生追求。入仕,一般来说是当时文人完美体现自我价值最理想的途径;但每人生活状态的不同造成经历也不尽相同:渴望入仕的人,却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排斥在外,郁郁不得志,最终也要慢慢释怀;决心不仕的人,不随流俗以坚守节操,反而避祸全身,安闲自适;身处仕途的人,在功名利禄的紧密束缚中参悟,煎熬却也幻想摆脱羁绊;所以,不论入仕与否,中国文人始终梦想以“隐”的方式脱离烦乱的世俗。这种渴望归隐的心态长久地影响着他们的情志,变成他们的创作契机,文人仕宦能够将自己隐逸的态度抒写进入文艺作品,成为他们寻求心灵抒发的唯一途径,所以才有“古之渔隐,大概感时愤事,胸中有大不得已焉者,岂在渔哉。”之说。
在文艺作品中,“渔隐”题材一般以渔父形象作为具象表达出现。在中华文化里,渔父的形象早已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完全生活在自然当中,既是在自然中劳作的普通人,亦超脱于社会之外,因此能够以洒脱的态度对待人生中的各种事件,渔父的形象代表着智慧与潇洒。文人在文艺作品中借用渔父遁匿山林,烟波渔乐的形象,彰显自身淡泊洒脱的品格,细细品读可知文人其实是借渔父这一具象来阐述自己对“隐”更深层的理解。渔父“身隐”于山林,折射出文人乃“心隐”于市井,透过文艺作品便能窥探其内心安和自在的“一洞天”。
先秦典籍《庄子》是较早以“渔隐”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庄子·渔父》中的渔父形象代表的是超然避世的隐逸者,向心有抱负的“孔子”宣扬“隐”的思想和蕴藏的高深智慧。该文采用夸张、浪漫的手法深刻、完美地塑造了渔父形象,成为书中相当精彩的一部分,此形象根植在人们心中,使渔父作为“隐”的具体形象由此定型。
庄子是中国隐逸文化的灵魂。庄子的学说重在救人而非救世,人在世间生存就注定要遭受世俗的侵染,仕途政治、功名利禄、富贵生死哪一样不是束缚人精神自由的枷锁?在庄子看来世间人“以物易性”的行径根本是本末倒置,“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尽力去苛求名、利、公、私这些身外之物哪一样不是伤生害性呢?庄子讲这些“心外之物”都是人精神上的累赘,要想摆脱在社会中遇到的烦恼和痛苦,要达到“隐”的状态:不受到外在的功名利禄的诱导,也不依赖内在欲望的驱使,摒除一切人为的干扰,以顺其自然的态度调和人在社会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在《缮性》中庄子对“隐”的境界作出阐释:“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所谓的“隐”不在“身隐”而指“心隐”,是个人精神的自由和超越,是心灵的放逸。以超越世俗生活中一切的“心外之物”,达到心灵的完全自由为旨,既要求世人在身处世俗闹事时,内心也要时刻保持淡泊潇洒。《庄子》典籍中多篇涉及“隐”的概念,为阐明“隐”的内涵,庄子以“渔”为具象,以“隐”为内核,讲述隐士的居处、志向、真心、道德等多方面特征,努力塑造出理想的隐士形象。
《刻意》中道出隐士理想的安身之地:“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
隐士栖身江湖而不在朝野,他们隐逸在湖泽草野之间,居住于静谧荒野之处,终日钓鱼闲处,求的是自在安然,而不是功名与权势。此文中表示隐士喜渔,但志趣并非渔猎的收获。
《外物》中任国公子以巨钩牛饵垂钓的故事,言说出隐士在安心渔乐的表现下胸中蕴藏的广大志向:“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
拿着细小的竹竿,在沟渠守候着小鱼,这样的准备若还梦想着钓到大鱼,则是绝对的妄想。愚钝平庸的人期求近效,终是粉饰浅陋,真正的隐士往往具备大的风度,即便在乡野浅水处存身,也具有营谋天下的眼光,所以绝不会迫切地苛求眼前的功利。
《田子方》中陈说隐士渔乐的真心:“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
老者有心持竿实际无心钓鱼,这是顺应自然的表现。文王预给予其国政,老者接受但并没有对国家的典章法规做出一点改变,即便这样国家也能渐渐安稳祥和。由此说,老者接受文王协理国政的要求不过是顺应时势,文王举荐老者辅佐目的在顺应众人的情感以博取众人的信任。钓鱼人手中把持鱼竿实际无心钓鱼,真正的隐士内心时刻清醒,即便身处名利场也不会失陷真心,本无心于名利,收获名利也只是顺应而已。
《渔父》中讲述隐士遵循的道德:“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纯真是贵重的美德,隐士将真诚蕴含在内,精神表露于外,以真为可贵,不拘世俗礼节,不随从世俗变化,不被虚伪熏染,以保持道德的完美。
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刻的哲学意义“渔隐”在历代文人心中挥之不去。以诗词的形式或赞或喻更是其济世宣泄的一种手段。唐代诗人张志和创作了“渔歌子”的词牌。“西塞山前白鹭飞”这首词作者勾画出了一幅清雅秀丽的水乡画面,优美至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表达了苏轼的归隐心境和人生低谷时对世事的态度。杜牧的《赠渔人》以诗喻己,谓之“渔者”高人也,已深悟归隐之道。“渔隐”题材能表达出文人的闲逸、放达和对强权不畏之精神。“渔”这一行当被赋予了深厚的内涵。故此,“渔父”的形象也就成了文人、士子追求隐逸的典型。
“渔隐”题材主要言说的是隐逸思想。经由庄子塑造的“渔隐”意象率先在哲学与文学中确立,成为后世文人寄托理想的载体。经由他们的推动,“渔隐”题材逐渐从文学过渡并落实到绘画领域,以此为题的绘画作品逐渐丰富。可以这样说,“渔父”这一形象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程式,也是中国画发展的见证。
如李唐《清溪渔隐图》,此幅为南渡之后所作,与之前开合大张的风格相比在章法上已有所改变,变全景式为边角式,笔墨变工为写,变雄浑为雅逸,变程式为性情,在经历国家战乱后内心逐渐归于平淡,以绘画释放自我的内心世界寻求慰藉。
如唐寅《溪山渔隐图》,仕途不畅使他没能实现身为文人的人生理想,却成就了他的艺术生命。渔隐的主题融合了他坎坷的人生经历,此幅画作清逸淡寂,画中渔父静坐垂钓,取意于唐寅对于功名利禄的淡泊心境,此时笔下的人生畅快之事已经成为他精神上的安抚。
吴镇代表作品《渔父图》一反传统山水画之程式,画面大面积留水于近景,渔父小舟置其上。这样的处理正是他性情孤绝自洽的体现和其对道家思想的诠释。“舟行水上,不范土地,不赖封邑,犹之浮游天地之间。”吴镇《渔父图》中的渔者为钓者听其自然,顺盈实势,可仕则仕,可止则止。隐者、智者,亦在虚实之间。所以吴镇的渔隐作品恬淡超脱更为彻底,正如词云:“洞庭湖上晚风生,风触湖心一叶横,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
中国画家受秦汉前诸子学术的影响,尤以老庄一派为崇尚。国画作品中出现的庄学形象厚于其他学说。他们始终遵循着“客观规律”之道家哲学,这一点在中国文人画中最能得以体现。其“程式化”是其重要的一笔。所以,庄子的“中国艺术之父”一说,不为过之。
总之,庄学的隐逸思想通过“渔父”这一形象得到充分体现,孕育了中国渔父词、渔父图的萌芽,文人借助笔墨促其发展,最终对中国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庄子“心隐”的人生哲学起到的作用纯粹是精神方面的,而并非具体行为上的指示,但却为文人提供了一条“如何从人世的泥沼中寻求心灵上的自我救赎之道”,正是这种追求精神解放的方式,才更适应文人在社会中的真实生活,所以后世文人多借助文艺创作表达自己处世的“心隐”态度,成为文人纾解心灵与在世间安身立命互不相妨碍的最佳方式。
实际上,“文人”身份在封建社会本就不能独立,它注定对统治阶级存在着极强的依附性,因此中国文人自然将他们个体的人生价值依附于功名,这是古代的知识阶层实现人生理想最重要的途径。每每遇到当仕途受阻,或难以处理的政事时,中国文人的追求、失落与痛苦都在这条大道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撕裂性的痛苦存在文人的内心深处。理想的执着与黯淡的现实之间往往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此一来“渔隐”的人生哲学恰好给予中国文人以生命超越——人生贵贱,荣辱无常,旨在息伪还真,顺应自然。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渔父”渐行渐远,“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隐约传来,依旧……
[1][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
[2]方勇译注,《庄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6页。
[3]同上,第253页。
[4]同上,第247页。
[5]同上,第458-459页。
[6]同上,第350页。
[7]同上,第539页。
[8]Dimitri Kotsifakos(迪米),《吴镇《〈渔父图〉(沪本)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9]林家骊译注,《楚辞》,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