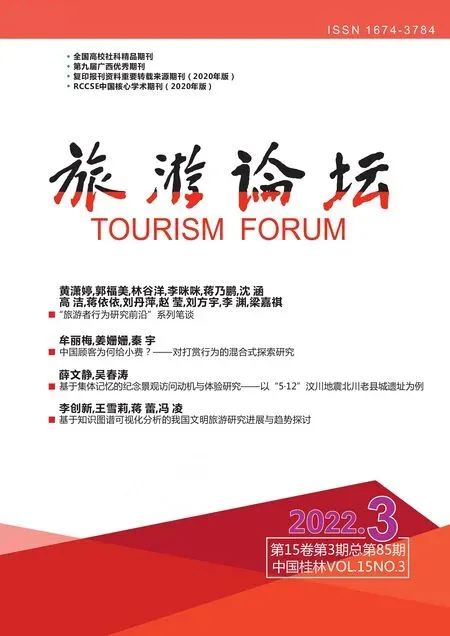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研究述评
2022-11-03梁嘉祺
李 渊,梁嘉祺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物质遗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着中华文化基因。对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已经受到各级政府、学术界乃至广大国民的重视。在遗产保护方面,国际上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系列公约,以及我国相继通过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确定了遗产保护的原则和实施途径。在遗产传承方面,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使人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国家加强文化自信与软实力建设,遗产旅游成为遗产活化、价值传承、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突出方向。遗产价值不再只是专家和政府主导的“小众价值”,而逐步发展成为人民认同、保护、传播的“大众价值”;各方主体身份也从“旁观者”“学习者”逐渐转变为“保护者”“参与者”和“传播者”。
在过去的遗产旅游中,旅游者在遗产地随意刻画、破坏古迹等不负责任行为的事件被媒体频繁曝光,旅游者的素质素养也因此遭到质疑。教育旅游者了解自己的责任,并在旅行中做出相应的行为,是可持续旅游发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出于对旅游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关切,《旅游目的地负责任旅游的开普敦宣言》(以下简称《开普敦宣言》)对负责任旅游(responsible tourism)做出要求:最小化旅游负面影响;为当地社区创造经济利益;让当地居民参与决策;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使旅游者和当地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无障碍及文化敏感性。可见,负责任旅游倡导一切减轻旅游业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负面影响的努力和行动,不仅关注旅游的影响,而且强调利益相关者在可持续旅游发展中的责任。
1 负责任旅游与遗产责任
在遗产领域,国际文献中有关遗产的负责任旅游概念不一,例如遗产地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 at heritage sites)、负责任遗产旅游(responsible heritage tourism),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概念是遗产地的环境责任行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尽管研究情境限定在遗产旅游下,环境责任行为的主要关注对象依然是自然环境;而对于遗产地这类特殊的旅游目的地,正如《开普敦宣言》所强调的,遗产地的负责任旅游还需要保护文化遗产,重视居民、旅游者、当地人等多方主体,考虑文化敏感性等。遗产地负责任旅游的责任对象应当为一切遗产资源,包括自然与人文资源、物质与非物质资源、资源承载主体。尽管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对于遗产地负责任旅游,更为准确的认识仍需要以旅游者与遗产为特定测量对象进行具体考察,而这正是当前研究所缺乏的。
为回应学术界关于旅游研究范式转型中提出的旅游研究应更关注的公平与权利、道德与责任问题,张朝枝以国际宪章与法规中关于遗产责任的表述为出发点,根据遗产与遗产旅游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借鉴企业社会责任和负责任旅游,提出“遗产责任(heritage responsibility)”概念并界定为“个体或组织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是指个体或组织在遗产价值认知、解释与再现过程中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经济、道德与慈善等方面的责任”,指出 “什么是遗产责任”“谁的遗产责任”“遗产责任行动对遗产价值再现和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三大核心议题。此后,张朝枝和王雄志根据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责任观哲学进行反思,将“个体或组织”改为“行动者”,将“相应的法律、经济、道德与慈善等方面的责任”抽象归纳为“伦理道德责任”,并进一步指出“主体对客体和主体间的责任”“为己责任和为他责任”,明确了责任的指向与逻辑。
在遗产责任概念提出后,国内外均有学者对遗产地遗产责任进行量表开发与检验,但研究视角与对象不同,或是从旅游者与居民的对比视角出发,或是针对文化遗产对象。国内研究发现经济支持与遗产认知是旅游者区别于居民遗产价值的两个独特维度,这体现了随着遗产旅游的发展与文化认同的提高,旅游者的责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唤醒,表现出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倾向。国外研究提出文化遗产的负责任旅游包含文化遗产收益与体验、环境可持续性态度、环境责任行为态度、文化遗产尊重与保护意愿、负责任旅游意愿5个核心因素。于是也有研究者关注到旅游者在遗产地的责任感知,但这种道德层面的关切意识是否能够转化为实际行为仍未可知。因此,从旅游者行为视角探讨遗产责任话题是十分必要的。
2 负责任行为与遗产责任行为
旅游者在遗产地的负责任行为,即遗产责任行为(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HRB)是如何形成、发生并产生后续影响的,对遗产旅游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旅游者的遗产责任行为是协调旅游发展和遗产保护关系的重要途径,旅游者对遗产保护的态度和行为、旅游者在旅游环境中的责任感、旅游者对自身责任与义务的认知等对遗产保护和发展都至关重要。在遗产责任行为的研究中,受到关注的不应只是遗产地的环境,更应当包括多种遗产资源、多元文化主体、多方利益相关者,探索旅游者行为在其间发挥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后续影响。
当前国内外聚焦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的研究较为有限,但国内仅有的数篇研究对遗产责任行为的概念界定、测量标准、实践检验进行了有益探索,如对遗产责任概念的探讨、对遗产责任量表的探索、对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机制的探究等,初步形成了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体系。具体而言,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 Theory,VBN)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被用于解释遗产责任行为的成因,即旅游者的遗产责任行为可以通过遗产认知、责任归因、道德规范、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间的复杂关系来预测,其最终目标是在保护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和欣赏”遗产。
在对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的形成条件、内容测度做出积极尝试后,旅游者的遗产责任行为究竟对遗产地产生何种影响需要更为长期的观察与实践检验。这将包括积极与消极的两种影响,即当旅游者未履行遗产责任时,其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而这又回到了遗产责任被提出的初衷,“出于对旅游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关切”。学界与业界当共同努力,为增强旅游者的遗产责任意识、积极促进旅游者的遗产责任行为做出贡献。一方面,出于理性行为与经济效益视角,应当保障遗产地的经济发展与旅游者所能获得的遗产旅游服务;另一方面,出于计划行为与心理认知视角,旅游者如何感知与认知遗产价值、遗产地如何更有效地向旅游者阐释价值、旅游者如何通过知识再现积极影响他人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3 遗产责任行为与感知测度
现有的少量国内外研究主要采用建立假设模型与开展问卷测量的方式探索旅游者在负责任遗产旅游中的行为感知、行为内容与行为影响,这对于结合实证检验丰富遗产责任行为研究的理论模型与概念内容上具有积极意义。但正如借助心理学理论解释行为成因的方式,旅游者的遗产责任行为研究应当具备更为开放的交叉学科视角。例如,当前旅游者行为研究在借鉴心理实验的基础上,从人因视角提供了更为精细的技术手段,能够为微观尺度下深层次地理解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在旅游者与旅游环境的交互中,行为地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理论、方法也能够为中观、宏观尺度的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此外,近期有国外研究基于负责任旅游行为的理论框架和虚拟旅游技术实践开展遗产地的实证研究,指出了遗产数字化在负责任旅游中成为替代方案的可选性。根据相关研究结果,遗产旅游者的负责任行为围绕其“专注(mindful)”方式展开,旅游者通过体验和对信息的心理处理积极建立与遗产的精神联系,获得“信息”并“感知”遗产。在数字化时代,在全球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形下,遗产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虚拟旅游实践或能为“教育旅游者理解自己的责任”提供良好的契机,以提供替代方案或体验拓展的方式建立起旅游者参与遗产保护的责任。同时,遗产地的利益相关者也能够借助虚拟旅游方式或数字技术应用拓展产品类型、营销渠道、口碑推广,进而实现经济效益。因此,虚拟旅游与遗产数字化技术如何与旅游者实现功能交互、体验交互、知识交互,进而建立生理、心理或精神联系,达到更负责任的感知、认知、行为效果,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议题。
综上,笔者尝试对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的研究述评,主要想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旅游者的遗产责任行为进行再思考,呼吁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研究的跨学科探索与技术实践,旨在更好地理解和促进旅游者遗产责任行为,从行为视角为遗产保护与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助力。旅游者遗产责任意识的唤醒与遗产责任行为习惯的养成非一朝一夕,这也使得这项任重道远的工作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相信旅游者思维的转变将会带来我国乃至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