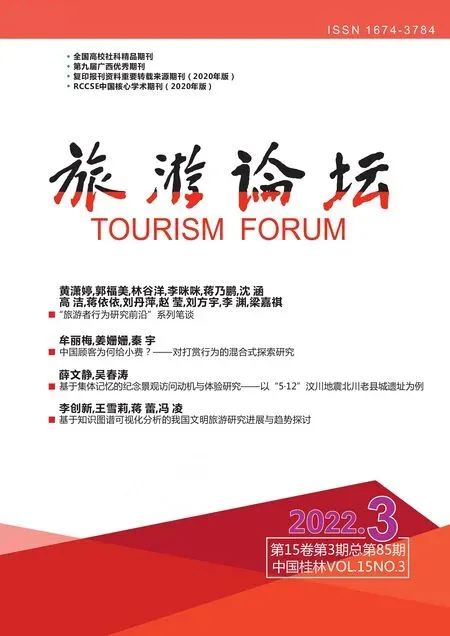感官营销实验在旅游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
2022-11-03蒋乃鹏
蒋乃鹏,沈 涵
近年来,心理学、社会学中的实验研究方法逐渐渗透到旅游学科中,旅游情境下的眼动实验、声音实验等研究的数量也在近年迅速增加,以感观营销(sensory marketing)为代表的营销理论被引入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大有同各类感官实验结合发展的趋势。
感官营销的心理学基础是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在感观营销中引入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之前,具身性已是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等领域内的热门研究主题。具身认知理论将人的身体地位提高到了本体论高度,认为人借助身体体验周遭世界并生成了心智,各类感官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感官营销、具身认知等理论的介入,旅游学科中的实验方法开始从对现象的描述性研究转向理论验证、甚至理论建构的研究,相关研究结论的应用和预测效果不断增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感官营销实验在具身认知理论的支撑下展开。然而,在这一趋势背后,仍有一些与感官实验相关的方法论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既反映了学界中存在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亦昭示着实验方法在未来旅游行为研究中的发展趋势。本文列举了部分感官营销实验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并试图揭示出一些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问题一:支撑感官实验假设的理论基础尚不完善
具身认知理论是感官营销理论背后的心理学基础,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较为一致的认可。作为一个因反对传统认知科学而兴起的心理学理论,具身认知思想的哲学源头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哲学。借着这股具身认知思潮而起,现象学 “身心一体”的观点对于笛卡尔“主客二元论”的批判也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身体研究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学科中得到了广泛重视,成为各学科的主流话题,随之发展出了各类分支理论。尽管具身性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不同学者对于什么是身体、“具身”的含义、研究身体的方法、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还存在很多争论,不同学科、同一学科的不同理论之间针对具身性的研究视角可能都不相同。
目前的具身认知研究还远未形成范式,而只能描述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其中,神经生理学的发展为具身认知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生理学参考,尤其是在恒河猴大脑的前运动皮层中发现的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让许多认知心理学家兴奋不已,该神经构成了动作理解和行为模仿的基础,他们进而推测人的大脑皮层当中也有对应的镜像神经元,从而解释了语言、心智解读和共情等人类能力,为具身认知理论强调的身体之间的沟通奠定了生理学的基础。一时间,各学科关于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蜂起,语言进化、美学欣赏、心理疾病甚至心灵感应等问题都开始借助这一发现得到阐发,镜像神经元变成了“认知科学的圣杯”[1]。有学者在将感官营销理论引入旅游行为研究的同时,也将其建构在了以镜像神经元为生理基础的具身认知心理学之上,认为正是镜像神经元的存在才使得游客的感官体验最终转化成了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这一理论构建为旅游神经实验的合法性构筑了理论依据,然而,限于伦理和技术手段,目前学界仍对人脑中是否存在镜像神经元还有很大争议。在获得确凿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将之假设性地视为具身认知心理学的生理基础,如果这一前提假设无法得到检验,那么从中得到的实验研究结论也都只能是基于假设的推论。同理,如果没有成熟理论作为支撑,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皮肤电测试仪等设备获得的客观数据也并不能真正解释实验参与者的行为。
问题二:具身认知理论要求的实验条件不易达成
具身认知论发源于现象学的一元论,强调人的认知是一个嵌入(embedded in)了身体当中的动态整体,而身体同样嵌入了周围环境当中,同当下的具体情境不断进行动态互动。这样的哲学背景使得具身认知论在根源上无法赞同单独割裂某种感官予以研究的实验方法。这并不是说具身认知论在发端处就与感官实验研究方法格格不入,而是要强调被研究的主体必须是植根于具体情景中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像行为主义心理学那样割裂人与环境的关系,将人视作一个针对刺激做出不同反应的机器。
具身认知论的这一观点对旅游感官实验研究提出了很高的挑战,它要求实验设计者能够尽可能地复现要研究的旅游情景,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情景中的各种无关变量,定向地通过操纵某些要素检验游客的某些生理变化以佐证理论假设。田野实验无疑是较好的选择,但因外部要素控制难度较大导致实验内部效度较低;虚拟现实(VR)技术的发展为在实验室中模拟真实情景提供了新的途径,研究者能够在尽量还原相关场景的前提下准确控制各个变量。当然,限于目前的技术水平,参与者完全沉浸于虚拟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但研究者理应重视参与者与设备的磨合过程,最大限度地让他们参与到实验中去。
问题三:无意识行为的测量与感官联动问题
具身认知论认为,身体行为会和个体的某些特定记忆或认知相关联,形成无意识的具身隐喻联结,在特定的情景下这种隐喻被触发后,个体就会无意识地做出某些动作或者产生某种情绪,并且人的身体和心理活动大多都是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的。著名的“李贝特实验”及其相关实验也都表明,人的很多看似有意识的决定,实则都是来自无意识的大脑活动。基于无意识的巨大开发潜力,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一些广告商已经开始通过训练观众的无意识行为的方式来传播信息。还有一些广告公司在营销时另辟蹊径,把传播的重点放在了听觉、嗅觉、触觉甚至多感官联动的“通感”或者“代偿”上,从而绕开了当下的受众视觉信息过载的问题。
然而,同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发展不匹配的是,许多实验研究现在仍然靠问卷、访谈等方式获得参与者有意识的那部分知觉信息,对于无意识领域则无能为力;大部分实验仍然只聚焦于某个感官上,尚不能实现对“通感”或者“代偿”现象的研究。皮肤电、脑电等检测技术能够为实验研究提供工具性的帮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一则这种客观数据的采集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表征主观感受;二则有些感官的感官属性较为复杂多变,如声音就有声强、声响、音色、声长、频率等属性,当改变某一属性时就会导致其他属性随之被改变,给实验方法带来很大困难;三则“通感”或者“代偿”现象往往能实现1+1>2的效果,仅依靠单维度的测量无法反映出真实的体验变化。要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还应当在实验设计中加入感官民族志、自我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式,将实验表征同主观的内感知描述相结合。
问题四:研究对象中缺乏对非健全身体的关注
近年来,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福利的价值突显,无障碍旅游也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但从感官实验角度来看,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残障群体的研究。感官实验研究者应该关注这一群体的原因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几点:第一,我国是世界上残疾人口最多的国家,从公平角度来讲,这部分群体的权益应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通过相关研究推动政策和公众态度的转变;第二,相较于健全身体,有时非健全身体反而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具身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概念的提出者、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正是在对各类神经损伤患者、被截肢的病人等非健全身体的研究中揭示出了身体的具身性存在;第三,视觉受损者往往听觉、触觉都较常人更发达,听觉受损者的观察力常常更敏锐。这些特殊群体在生活中发展出的优异感官能力往往对感官实验的反应更为灵敏,实验控制效果更显著,感官实验的发现也有助于制定决策,提升这一群体的旅游感受。
未来发展趋势
从以上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感官营销实验在未来旅游行为研究中的几个发展趋势:第一,从单一实验方法发展到多种研究方法配合使用,从多个维度刻画游客行为;第二,从单一感官研究发展到多感官之间的联结研究,揭示这种联结背后带来的体验变化机制;第三,从有意识领域的感官实验发展到对无意识行为的研究,在行为研究层面上检验、补充既有的具身认知理论;第四,从对健全身体的研究发展到关注非健全身体,通过研究推动无障碍旅游的发展、减少社会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