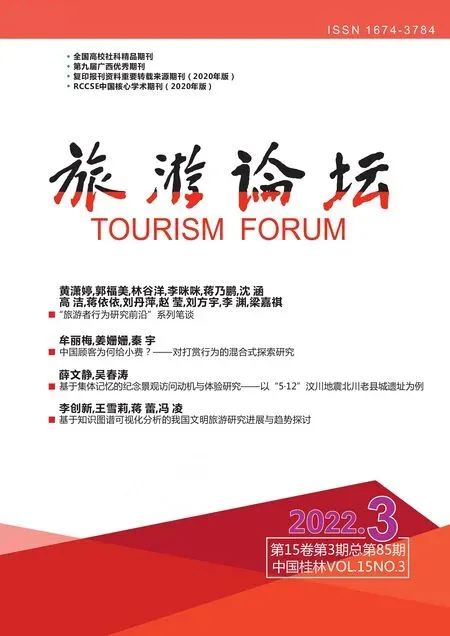旅游者自拍现象从何而来?
2022-11-03刘丹萍
刘丹萍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生产与生活方式。2013年,牛津词典将自拍(selfie)评选为年度词语并收录,明确其基本定义为“由智能手机或其他网络摄像镜头拍摄并上传到社交网络的自拍照片”[1]。自拍不是新鲜事,旅游者自拍有何独特性? 本文的目的不是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就“旅游者自拍现象从何而来”这个话题与同行交流,想用发生学的思维去追根溯源。笔者以为,若想认知旅游者自拍行为,至少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始:
第一,镜子
英语“mirror”一词出自中世纪英语“mirour”,词根是拉丁语“mirari”(诧异,惊叹),后派生出意大利语“mirare”(凝视) 。镜子与人类借以视觉经验认知自己的实践密切相关,有丰富的文化隐喻。西方传统文化中,镜子是主体沟通自我、理想形象和社会形象的重要依据,这种文化心理是实证精神下对于“真”的追求和探索。而中国传统文化里,镜子指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为,“镜”是主体心境的喻示,它远离社会生活,具有主观内悟的色彩。
面对镜子,人们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能够清晰地让人反观自己的容颜,不禁产生舞台表演欲望和自我创造的冲动;另一方面,镜中影像那么不真实,常激发虚幻和想象;更进一步地,通过镜子,现实被不断神秘地复制或再现,引发莫名的不安和恐惧感。进入现代社会,人们更加无法摆脱镜子的诱惑与魔力,过度重视镜像带来主体地位的下降,为此不停地改变自己、加强对自身身份的寻求。因此,镜子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历史的两张面孔,一张是理性,是科学、探索与无限的世界;另一张是想象,是神秘、旖旎与内向的灵魂。我们在镜子中能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把什么带到镜子跟前。
第二,自画像(self-portrait)
达芬奇说,镜子是画家之师。在没有摄影术、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自画像是人们完成视觉性自我表征的主要方式,通过镜子完成。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艺术家们表现自身形象的诉求已然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越来越强,于是呈现出由签名到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一般人物形象、再到写实性的肖像,最终发展到以自我表现为绘画主题的独立自画像。这里面,艺术家增强使自身“留名”与“在场”的意识是非常显著的,从最初追求绘画作品与对象的相似性,到后来艺术家主体意识的觉醒,进而引发自我表现的欲望。同一时期,中国明代也产生了由文人画家完成的自画像热,它明显不同于之前中国绘画求“真”、对“自我”关注较少的特点。这些距今六七百年之前的中国“古人自拍”多由文人画家完成,多配以诗文和题跋(是否与我们现在的微信朋友圈里九宫格美图加文案类似呢?),讲究文字和绘画相融的文化意境,表达出创作者“仕”与“隐”的矛盾心理。应该说,自画像的兴盛体现出时代变革下自我意识的觉醒。由照镜子到创作自画像,人类凝视自我、反思自我的视觉体验变得更加实体化,也从私密的个人空间转到可随时观看、保存和传播的空间。
第三,摄影术(photography)
(1)照相机平民化及快速一瞥
1839年,法国人路易斯·达盖尔发明了银版照相法(daguerreotype),从此人类记录影像的手段就不再仅依赖于绘画。同一年,美国摄影师罗伯特·科尼利厄斯完成人类第一张自拍照。而真正让摄影走进百姓寻常生活的,始于1900年2月柯达“盒子布朗尼”相机的问世。随后,一系列小型、轻便的照相机投入市场,技术的突破直接促成20世纪50年代中期“快照”风格(snapshot)和“决定性瞬间”之大众摄影美学风靡一时。此时,摄影已不再只是摄影师才能做的事,普通个体也能拿起相机去观察生活,制造出海量的,充满了自由、民主和轻松随意之生活气息的快照。
(2)大画幅相机及凝视端详
时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摄影界掀起一股关于小型照相机的“快速一瞥”与大画幅照相机“凝视端详”的讨论。前者“碎片”一样的影像被批评缺乏意义上的深度和广度;后者则被赞许为既可仔细研究被摄体,又能适合观者驻足面对。摄影师当然满意这样的影像思考——意味着专业水准而非大众流行文化。于是,他们随后采取一系列行动去捍卫摄影作为一种艺术的存在。但无论如何,精英艺术与大众消费文化之间经过几轮的此消彼长,摄影越来越有了群众基础。
(3)摄影性、数码摄影与图像流
时间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摄影史上又有了新的重要事件。那就是,摄影在理论上终于被接纳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非绘画的补充),并于90年代后逐渐成为当代艺术的中心。1995年,民用的相机数字化拉开了序幕,一个新的摄影美学主张被提出来,即“摄影性”(photographicité,法语)。具体而言,就是为了适应艺术馆、博物馆等艺术场所大型空间展示的效果,更是为了适应艺术市场运作需要,一方面,当代摄影常以大作品、大展览的面貌出现,“大画幅+彩色”成为主流摄影美学;另一方面,人们开始强调“创作进程”(work in progress),关注点由注重照片本身是否好看而转变为注重艺术品形成过程是否“漂亮”。后者包括摄影行为、摄影活动、未完结的创作以及照片的展示、流通与接受等整个操作,需要多个主体的个性化投入。后来有学者将其命名为摄影美学的“行动判断”路径,即与作品的“存在”时间以及被凝视的时间相比,作品的创作时间占了优势地位。
2000年,数码摄影(digital photography)开始受欢迎,并在互联网和数字通信技术等加持下进一步具象化和提升了“摄影性”概念:数码矩阵一旦完成,创作者不仅可对其进行永无止境的探索与修改,而且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这些图片;其他人接收到图片后也同样能够不断地使用、修改和传播它,摄影图像本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图像的用途、制作、完成、传播、接受和流通。当人们真正发现数码摄影这种独特的运行密码后都惊叹不已,评价这是整个摄影范式的彻底变化。此时,摄影作为艺术的门槛被再次降低,普通民众被一步步技术赋权,摄影的娱乐性进一步得到加强。
第四,智能手机时代的自拍
自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问世开始,人类就开启了数字技术的爆发式增长,智能手机是典型代表之一。智能手机出厂前就为化身成自拍神器而努力:像素无限制提高的前置摄像头完全就是一枚无比清晰的“数字化镜子”;内置的各种滤镜、加光、美图推荐模板等如同完成自画像的必备工具,允许人们通过美颜算法(beauty algorithms)获得自己想要的那张脸;身体和肢体语言表达受人工智能审美标准之形塑;触摸屏的轻巧和灵活让一键分享流畅顺滑,让点赞和评价充满了仪式感。同时,加装在手机里的Android和IOS 两大操作系统,也是在运行管理和系统平台的功能扩展方面做足了准备,允许使用者根据自己的偏好随时下载、安装以及卸载各类第三方应用程序,进而实现对自我影像的电子编辑。更重要的是,自拍的秘密在于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他人,这才是自拍的真正意义。于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功能强大的社交媒体进一步与智能手机实现联姻,它们共同延长摄影行为,将上文提及的摄影性和图像流强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摄影术到这一阶段已需重新书写。由轻巧的智能手机主导的自拍时代,自拍就是一种技术手段制约的自我形象生产和网络围观形成的“情感动员”[17],自拍的目的不是创造可供凝视的永恒性作品,而在于制造暴露自我的、用于流通与消费的图像流。对此,学者评价的原话是“2010年后,自拍占领了世界并动摇了摄影”。
至此,我们初步完成认识旅游者自拍现象的知识储备。若考虑其内在规定性,首先,它是自拍的一种,有自拍的基本特征,例如记录、见证、自我叙事、技术赋权、社交属性和主体建构等。其次,它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完成的自拍。有国外学者发现,自拍存在“景点遮蔽效应”(attraction-shading effect),即游客本人居于游客照中心地位,旅游地是自我影像创作的背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关于这点的讨论目前并不多,需要予以持续关注。即,数字社会里视觉消费文化的浸淫,使得部分游客认为旅游就是换一个地方完成可以在社交媒体炫耀的自拍照,旅游自拍与日常生活自拍之间的界限已愈发不明显。这可能是旅游与非惯常环境之二分法理论再一次受到挑战的鲜活案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旅游凝视(tourist gaze)理论面对旅游者自拍现象应该做出怎样的修正甚至重新建构。笔者提出的四个知识储备未涉及旅游凝视,并非遗忘,实在是因为它需要好好做一番文章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