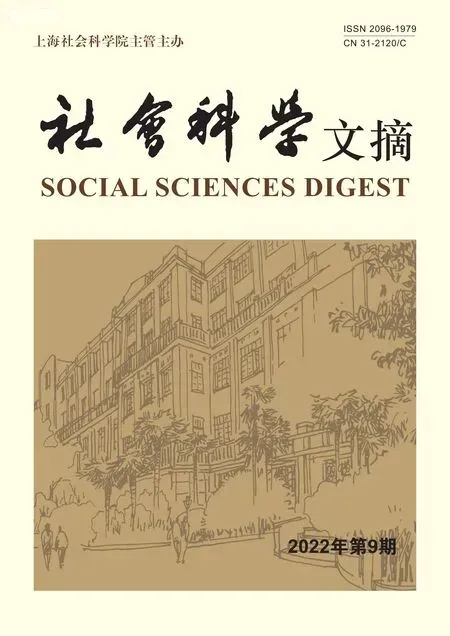国际关系中的身份政治:内涵、运行逻辑与互动困境
2022-10-29姚璐邢亚杰
文/姚璐 邢亚杰
作为一种因身份认同的差异性解释而产生的现代群体性政治观念与行动,身份政治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流行之势。不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追寻叙事表达权力的“文化政治”,现今的身份政治已经成为具备政治动员意义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其诱发的“政治正确”“政治极化”威胁着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稳定。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无论是为维护国家内部稳定还是维护国家权力优势,树立共同敌人、建构调动群体认同成为国家常用手段。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全面理解国家间的身份政治成为把握国际关系动态变迁的关键。
身份政治的跨层次分析
身份政治是特定主体通过确定身份,建构具有归属意义的认同,并以结成群体的形式实现特定目标与诉求的政治实践。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存在两大共同点:第一,二者同属群体认同模式,都以群体形式进行利益的表达、寻求与维持;第二,二者同属差异政治,都是在区分与排斥的逻辑上形成的。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国内层次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政治抗争与政治运动,国际层次通常表现为权力优势国家主导的对异质国家的合围。之所以出现区分,根源在于逻辑起点与逻辑条件的不同。
(一)人、国家两主体带来不同的逻辑起点
在国内层次,人是身份政治的主体。从认知维度看,人认识自我的过程依托同化对象、获得对象的承认而实现,身份政治本身就是人进行自我实现的过程。在现实维度中,阶级政治固化着个人在社会角色中的分配,在强权—资本场里,主流—边缘位置的存在明确着个体的身份,在特定的肤色、性别、性取向等可识别的标签作用下,个体间的边界确立,建构着彼此的认同,形成各自的群体。
虽然国家能够成为身份政治的主体是研究者们将其拟人化的结果,但国际社会的社会人国家与国内社会的个人存在不同之处。从起源上看,国家是个人权利让渡的结果,是基于契约结成的政治共同体,这使得个体对共同体的要求与利益有着更强的自觉,“我群”与“他群”的界限更为明晰甚至被绝对化。从目的上看,由于权力的限制,没有获得完全承认与尊重的非中心位置国家是被动的,当面临异质国家组成群体就独立与领土完整对其进行围攻性的质疑、指责甚至攻击时,此类国家很难有能力主动发起类似国内的群体运动。
回归到国家间的交往过程,国家遵守“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相较于个人对利益的重视,国家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视是被强化的,强化的结果是国家之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身份政治其实是国家获取、维持国家利益的手段。而当以“我群”与“他群”的视角对待国家间利益冲突时,经过文明或意识形态透镜折射后,该利益冲突可以放大很多倍。国家对利益的追寻驱动着身份政治的发生,身份政治也放大了利益对国家的重要性。
(二)不同的逻辑条件:有政府与无政府
是否存在政府这一逻辑条件塑造着不同层次的身份政治。就国内层次而言,政府是国内共同权威体现,它的合法性来自民众的意愿,尊重并实现不同群体的意愿成为政府维持稳定的途径。同时,政府是强调维持秩序的机构和法律的存在,其具备强制力和规制力,在不同群体表达政治诉求、进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约束与调节的作用,这使得身份政治具备一定的可控性。
而在国际层次,无政府状态成为核心背景条件。无政府状态有两层含义:一是缺乏秩序,二是缺乏政府。秩序缺乏带来频发的冲突与战争,国家的敌友观因此鲜明,围绕共同敌人而达成群体合作成为国家间身份政治的出发点,无休止的战争与冲突也会使得群际敌友身份固化。而共同的中央权威与统一的政府制度的缺乏意味着强制力与约束力欠缺,这极大增加了互为敌手的国家之间长期存在难以解决的意识形态冲突和不受控制的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国家间的身份政治会有着更强的烈度与破坏力。
无政府状态虽然不存在世界政府这一公共权威,但每一个主权实体有着不同的实力与影响力,形成着“有序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拥有压倒性实力优势的霸权国占据中心位置,对其来讲,权力转移的出现意味着原有权力优势与制度优势的双重下滑甚至丧失,其本体安全也会受到威胁。面对这种情况,霸权国会调动内群体认同融合,与附庸集团展现空前一致的敌意与群体性的合围压制,以应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身份政治其实是权力政治的一种补充,是寻求或维持权力的工具。
国际层次身份政治的运行逻辑
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兼具差异属性与工具属性,其运行逻辑遵循如下机理:
(一)确定边界:依据国家特性与话语表达进行的分类
在身份政治中,“我群”与“他群”的确立关键在于群体边界的确定,分类是确定边界的基础。依据国家特性(意识形态、情感、偏好、实力强弱及利益需求等)而产生的国家类型成为国家产生他者判断的基础,也成为国家间产生群体划分与群际差异的起点。在确定为某种国家类型的过程中,国家获得了在权力、意识形态和地位上彼此相关的社会类别中的某种群体特征,其成为一国与其他国家比较异同的参照。此外,分类主体越是认同某个类别,就越愿意在他们的自我定义中使用该类别。在“各说各好”的环境下,对意识形态划分类别的坚持与强调加剧了国家间的紧张关系。
在依据国家特性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话语也发挥着明确分类的功能。诸如美国称苏联为“红色殖民主义”、称古巴为“流氓国家”,这些富有敌意色彩的话语使得国家之间分类显性化。同时,在实践层面,话语以叙事的形式发挥着工具属性。叙事深层结构秉持的是二元对立原则,好与坏、善与恶、强与弱这些叙事范畴使叙事产生意义。二元对立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差异政治,更是差异转化而成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使得国家区分异质者,与同质国家结成群体,以实现对自身安全的维护。
(二)建构认同:依据共同命运与最佳区分明确动机
分类确定了群体之间的边界,而国家间的共同命运与最佳区分明确了建构认同的动机。
共同命运为国家间形成认同结成群体带来动力。共同命运是由同一外部力量或同一规则导致的,外在威胁、民族、宗教、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等可以产生同一规则或规范的要素,均可以让两个或多个个体间产生共同命运。在群体认同形成后,共同命运依然发挥作用,有助于区域意识从单纯的地理层面的归属意识向更高层次的合作意识和共同体意识演进。共同命运的延续性使得拥有共同命运的内群体国家呈现康德文化下的朋友关系,国家的归属意识会得到巩固,进而提升整个群体的内部凝聚力。相应地,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也会突出,甚至呈现出更强烈的排斥态势。
最佳区分成为群体排他性与内群体认同走向融合的来源。个体有两种强烈的社会动机:一种是包容性的需求,即自身能够成为一个团体的成员;另一种是分化性需求,即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在这两种动机假定下,一个排他性的群体远比一个高度包容的群体有更强的吸引力与认同感,因为前者同时满足了两种需求。对受身份政治影响的国家而言,本体安全驱动着国家的包容性需求,区分差异思维驱动着分化性需求,主导或者加入一个排他性群体成为必然。当国家两种需求的平衡受到威胁时,会通过调动内群体的认同融合去应对威胁。而无论个体哪一种需求得到高度满足,结果都会呈现内群体认同的强化。
(三)诉诸实践:调动认同融合进行的国家间互动
认同融合是个体发自内心的与群体的合一感,当群体认同成为个体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就意味着认同融合的发生,达到所谓的“群体即我,我即群体”状态。在认同融合作用下,国家间明确了合作、对立与冲突的互动方式。首先,对内群体国家而言,彼此间更易选择合作式互动。在内群体中,认同融合不仅使国家与群体产生了休戚与共感,还强化了内群体国家间的朋友角色,随着亲群体行为的发生,与其他内群体国家达成合作互助。
而对处于不同群体的国家而言,达成合作与维持合作较难,彼此间更易陷入对立式甚至冲突式互动。当国家与群体的合一感出现并逐步加深时,国家以群体身份认知他国时,与外群体国家的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这种被放大的差异很容易使国家出现认知误区,道不同不相为谋,也会影响国家的话语表达,形成自说自话的无效沟通局面。基于放大差异的群际国家互动底色是消极的,国家间想要达成合作需要投入更多成本。而认同高度融合本身就会带来群际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当面对竞争关系的外群体时,内群体的高度融合会强化敌友认知,在极端亲群体行为下,一个内群体国家面对的威胁会变成整个群体共同面对的威胁,国家为群体做出牺牲是正义的,在群情激愤与为之一战的非理性调动下,两个异质国家间的摩擦矛盾很容易转化为冲突。
身份政治作用下的国家间互动困境
(一)差异、排斥思维塑造的消极互动底色
作为一种差异政治,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遵循的差异逻辑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它是实现“自我”合法化的途径,国家依托与“他者”的差异进行着自我实现,将基于自身关照的利益、价值观、规范等进行普遍化。在“自我”合法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与“他者”的区分与一较高低;同时,寻求普遍主义意义的转变并非一家独有,在竞相谋求普遍意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相互比较、指责以突出己身优越。这种“自我”合法化的实现过程为国家间的互动蒙上阴云。
另一方面,由于过度强调与夸张想象,差异可能转变为某种“我们”对“他者”的排斥甚至暴力,成为一种固定陷阱,被永恒化为绝对的、二元对立的。当群体之间秉持着二元对立思想,群体的界限与排斥会被强化。从学理上看,二元对立是秩序的一种表达,“肮脏”意味着失序,“洁净”意味着有序,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创设国而言,以制度、规则进行预防是维持“洁净”秩序的重要手段,根本是寻求同化或排除“肮脏”源头,建立“洁净”的同质群体。在现实政治中,世界文明结构呈现东方—西方的二元结构,二元之间是不断发生接触、矛盾、冲撞乃至战争的动态过程,尤其在西方图景中,这种二元对立思想根深蒂固。
(二)认同之殇、群体之分限制着国家间的互动方式
第一,深陷国内层次身份政治的国家对外互动方式呈现内敛性与集中性。就内敛性而言,当身份政治造成国内社会分裂、给国内政治带来冲击时,国家往往呈现对外政策的收缩,以求维持国内政治的稳定。就集中性而言,当国内出现由多元认同群体、国内矛盾激化带来的“裂缝”时,政府集中力量渲染、树立国家的外部敌人,制造对“他者”的恐惧和仇恨,以强化国家认同、转移国内矛盾。
第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之争造成国家间互动缺乏稳定性与延续性。当国家间出现由价值观、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认同缺失时,对不同群体的国家而言,达成合作式互动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强。以中美两国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走向正常化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摩擦冲突影响着两国合作的开展。而后美国以人权之名对中国进行批评反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摩擦阻碍了中美合作。2017年后,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再度兴起,中国成为美国口中的“邪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凸显。
第三,群际互动模式制约着国家间合作式、自主式的互动。当国家以某一身份、某种认同为口号逐渐向群体、阵营演变时,就跌入了身份政治的陷阱,“唯阵营论”“对立冲突注定论”等论调使国家间互动方式受限,处于不同群体的异质国家合作的空间与可能性被压缩。而拥有某一群体身份也会使得国家做出互动选择的自主性下降,呈现出对中心位置国家互动的从属性。
(三)权力政治笼罩下黯淡的互动前景
作为权力政治的一种补充,现行的身份政治未能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框架。对国家而言,敌友观不仅是国家寻求权力累积的方式,也是国家树立权力合法性的手段。由于缺乏有力的规范与协调,敌友的划分成为一种简化的思维框架,有益于国家团结己方、明确与敌对方界限的作用。敌友观的重要性使其强化有着合理性与必然性,而伴随着国家间权力转移的发生,国家间敌友观也会被持续巩固,进而固化着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此外,权力的不对称性会诱发国家间螺旋上升的敌意。由于奉行二元对立思维与国家间强化的敌友观,处于权力结构中心位置的国家往往难以尊重不同国家对承认、安全和认同的需求,而处于不同位置的国家间容易出现系统性的错误感知。因此,一旦出现异质国家或异质群体对抗的情境,将很难摆脱螺旋上升敌意的桎梏。最后,异质群体发生对抗具有必然性。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斗争中,秉持增加自己的权力或者防止敌对国权力增加的目标,国家往往进行联盟,围绕政治安全、意识形态等结成群体。这个过程的逻辑起点就是通过维持或增强自身权力以应对既有的威胁,这决定了敌对、对抗思维存在的先验性。
是否每个国家都难以逃脱陷入身份政治陷阱的结局呢?中国或许是一个否定式的答案。当代中国坚持的是辩证的“共同体思维”,这种基于相互尊重、协商合作,实现共存共赢共享价值目标的思维方式是避免中国陷入二元对立式、群体对抗式身份政治陷阱的关键。在角色身份上,中国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走向权力结构的中心不是中国矢志不渝的追求,以认同为手段进行权力斗争也并非中国的基本遵循。中国这一“反例”的存在正是对身份政治适用于每个国家的有力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