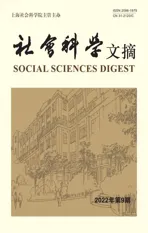“初选”与“重评”:当代文学批评的两种路向
——兼谈批评的“历史化”问题
2022-10-29吴秀明
文/吴秀明
批评“结构性变化”与历史化问题的提出
当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突出之处,就是批评的强大与强大的批评,它在当代文学领域风光无限,一度甚至独步天下,并将思维理念辐射到包括文学史在内的整个研究领域。有意思的是,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专业目录、学科目录分类中,却对之做了不同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处理:后者被命名为“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而前者则被称作“当代文学批评”。也就是说,在这些带有权威性的、指令性的专业或学科分类中,当代文学似乎被认为是不太成熟的一种文学,它不宜或不应被称作“史”的。
这是学术上的谨慎持重,还是学科的偏见,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再进一步,是否像有学者提出的“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文学)如此苛刻”?这是可以讨论,甚至不妨是可以质疑的。自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及当代文学学科及其批评和研究者的“自尊心”。顺便一提,这种对于当代文学的认知,在如今的中文传统学科那里,仍有相当的市场。这大概是所有新兴学科的一种宿命吧,也许与文学教育相对保守有关,也许与中国自汉以来形成的强大而带体系性的朴学传统有关。上述这种崇古之风,在“五四”时期的现代大学仍处于执牛耳的强势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得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持,现当代文学一跃成为并进入现代大学文学教育的核心课程行列。自此之后,在研究路径与方法上,擅长语义分析的理论批评开始取代传统实证占据绝对主导位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教育界和学术界在扭转这一崇古之风的同时,却又过犹不及,走向了“以论代(带)史”的另一种极端。这种极端,自20世纪50年代批判《红楼梦》研究开始,逐步被放大,延至80年代以降,与引进的现代西方理论及逐渐兴起的量化、项目化学术生产机制杂糅相融,它使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从原来的崇古传统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催生了新的问题,造成了学风的空疏、浮夸和浮躁。于是,文坛学界在反思时再次作了带有“一代之学术”意味的“结构性变化”。
这里所说的“结构性变化”,首先,指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从单一的批评向批评和研究(包括文学史书写)并重推进,原来从宁静大学校园跑到喧闹广场的许多学人,到了21世纪以后,因广场的沉寂,又返回校园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促成了当代文学的一次重要转型。其次,从研究角度审察,所谓的“结构性变化”,是指出现带有某种思潮性质的“史料和历史化研究”,并得到了国家学术制度的支持。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一种变化。
怎样看待上述“结构性变化”,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尤其是从事批评工作的学者会有些担忧和质疑。如果换个角度,就常态的发展规律来看,一个学科推进到一定阶段,需要进一步提升时,都会出现文献史料跟进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来理解它,历史地、辩证地去看待它所出现的变化,包括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总之,在批评经历四分之三世纪的当下,如何历史化,对自己过往所沉醉执迷的纯文学理路进行凝视反思,有效地丰富其内涵,提升其质量,这个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历史化,就是将其看成在多元复杂语境下,有别于文学批评的一种学术化、学科化的理性实践活动。它除了揭示生活真相和时代本质外,还经由反复不断的筛选,沙里淘金地将相对客观的作家作品沉淀为共识性表述,并使之进入文学史。
“新人新作初选”:浩瀚数量与文体拓展带来的新问题
当代文学不同于已经“完成态”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新人新作层出不穷是其基本特点。因此,对这些新涌现的新人新作进行评论即我们所说的“初选”,为后来的经典作家作品“重评”提供基础支撑,不仅成为批评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成为衡量批评功能价值及其解释力的重要标准。显然,这里所谓的“初选”,属于审美感知的艺术评判范畴。就历史化角度来看,它主要借助于不无残酷的文学史“压抑机制”,对海量存在的新人新作进行筛选,而成为历史化的“第一道环节”。如果将其置于当下语境考察,就会发现批评对象十分丰富复杂,它早已走出了柄谷行人所说的“文学的时代”框限。
这里所说的丰富复杂,最显见,也是人们讲得较多的,是它的令人咂舌的庞大数量。以长篇小说为例,据统计,最近一些年来年产量有5000部之多,这还不包括网络小说。而在“十七年”,它的总产量也不过170部左右。面对如此浩瀚的存在,任何精力旺盛的批评家都会感到力不胜逮。于是,批评家们只能根据自己个性、心性的实际情况,“别无选择”地从中选择有限部分进行阅读评价。
当然,数量上的浩瀚存在只是一方面,并且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更主要且更棘手的是:面对上述因秩序重组和媒体转型带来的从文体、形式、内容等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批评还没有找到一种与之相适的致思路径与方法,甚至还未形成带有共识性的批评标准,包括价值表述、理性原则、话语模式。简言之,面对批评对象的新变与新变的批评对象,我们还是操持和使用原有固化的思维、观念与方法,批评主体跟进乏力,它与变化了的批评对象之间出现了不应有的脱榫和错位。我们现有的现当代文学史基本按照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四分法,即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种体裁“文学史观”来进行书写,少数的再添加评论,也有的再增加影视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这可以说是至今所有文学史普遍的,似乎也是不容置疑的基本框架。近20多年来出现的网络文学、非虚构文学和科幻文学被排除在外,并未“入史”。现有的理论批评也缺乏跟进,未对之作出卓有成效的阐释。这里的原因,分析起来,当然与当代文学历史太短,还没有充分历史化有关。但从更深层次角度考察,主要还是源于其跟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体制产生抵牾、不对接。
如何看待上述现象?限于篇幅,我只想约略地指出两点。其一,这些新人新作新现象,也许存在某种偏执或追逐时尚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将其置于百年之变的长时段和大视野中给予同情的理解。这需要有开放豁达的胸襟,也需要有丰富健全的知识结构。其二,为使批评经得起历史化的考验,有必要走出狭隘的“审美城”,注意它与理论、史料之间的互动对话,以便形成和建立“批评—理论—史料”正三角的结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提出“批评的研究性”(毕光明)和“学理性批评”(刘艳)的主要原因。
“经典作家作品重评”:代际问题与实践主体及其他
与“新人新作初选”密切相关而又不尽相同的是“经典作家作品重评”。某种意义上,它们之间的互动互融,才有可能使当代文学批评既生动幽微又凝重开阔,具有诗、史兼备的双重品格。这也是我们对已走过两倍多于现代文学历程的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期待。如果说“新人新作初选”是在“零距离”情况下,从当时审美感知出发对新鲜出炉的作家作品所作的一种“即时批评”,为下一步重评或文学史书写进行把关,是构成历史化的“第一道环节”,那么“经典作家作品重评”就是在此基础上,对经当时审美感知初选的作家作品所作的重新审察,它是一种“超时批评”,或可称作是对批评的批评,是构成历史化的“第二道环节”。
从时间范围来看,“经典作家作品重评”主要集中在“前三十年”,以及八九十年代即“后二十年”。21世纪以降的20多年,为了沉淀与稳定的需要,暂不列入。而从“作家形象”角度考察,按照程光炜的设想,在现有的当代“五代作家”中,重点是放在赵树理、孙犁、柳青、马烽等带有跨代性质的第一代作家,以及王蒙、茹志鹃、陆文夫、张贤亮、高晓声等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二代作家身上,对这两代历史化条件相对成熟的作家先试行。第三代作家如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张承志、路遥等,可以适当开展一些工作。至于后面还有两代相对年轻作家或更年轻作家,即60后、70后等第四代作家,80后、90后等第五代作家,可暂且搁置。这里的“重评”,除对作品进行深读细研,即继续作文本批评或文学性解读外,主要是借鉴古典文学治学方法,作超文本研究,对有关史料进行抢救性整理,包括撰写作家传记、年谱、家世、交游,以及对佚文和佚事的调查、发掘、考订等。
当然,对于程光炜有关代际之说,不能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因为作为精神和审美活动现象,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越代际框范。事实上,有的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作家,已经启动了历史化和经典化工作。古今中外大量事实表明,作家作品历史化和经典化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它离不开实践主体的参与。当代文学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因处在频变不断的当下而与时代处于同构状态,故而经典“重评”的节奏和频率更为短促,问题似乎更突出,直到90年代才逐步走向沉稳。这里所说的实践主体,宽泛地理解,包括作家本人及其与之具有特殊关系的他人两层含义。前者,也就是作家本人,主要是指他利用名人身份、地位、影响力等资源优势,通过自传、回忆录和请人撰写评论文章,编写年谱、传记,进行访谈,召开作品研讨会等各种方式,甚至频繁地出入于媒体,为自己造势,将自我经典化。后者,主要是指作家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有师承关系的学生乃至特别密切的友人,通过追忆的方式,来对作家作品进行诠释。这种情况在作家本人去世之后,表现尤甚,它似乎成为实践主体的主要方式。
与实践主体相关而又不尽相同的,是“经典作家作品重评”语境化问题,这也有必要引起重视。不能因讲经典的超俗性或脱俗性,就将其从具体切实的特定语境中剥离出来作非历史或脱历史的解读。此所谓的语境化,首先,是指对象的语境化,其意是强调重评的历史还原,尤其是历史情景的还原。须知,对于柳青们来说,他们不仅将自己看成是一个作家,同时也将自己视作是一名党员、干部。政策、生活、文学之间的差别和距离,并没有今天我们所认为的有那样大,它们交融、交汇的地方要远大于它们的差异。所以在重评时不妨像福柯那样将文学与政治看成一种“结构关系”,这或许更接近历史化的本义。其次,所谓的语境化,是指主体语境化,主要是就今天接受主体的阅读欣赏而言。无论我们对经典抱着怎样致敬和历史还原的态度,它都不可能不受当下时代精神风尚的影响,并需要面向新一代读者,融入当代元素。面对同样的历史化和经典化对象,时代变迁及其接受者所处语境不同,也有可能影响到效果。我们应该用开放、发展与对话的观点,来看待“经典作家作品重评”。
最后追问:从“经典作家作品重评”入手还原历史,来铺展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对当代文学来说,有什么问题需引起重视?这当然比较复杂,不可能有什么结论,但略去个别现象不计,我认为不妨可作两点观瞻把握。一是从大的历史逻辑来看,应要看到当代文学本身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历史局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留在观念层面,艺术创作程度不同地成为社会革命表演性的替代,无法完成经典所要求的宏富的历史叙述与修辞,以致有人不无“顽固”地宣称:“我绝不去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某一位作家,更不要专门研究一部当代的作品。因为我认定当下没有一位值得你专门去研究的作家和值得专门研究的作品。”二是在讲这些历史局限的同时,要警惕滑落先入为主的当代文学“附庸论”的陷阱,以及单面化和简单化的思维理念。作为一种理性的评判活动,我们在进行历史化和经典化时,同样也要看到当代文学在历经曲折坎坷之后并没有沉沦,相反积聚了令人叹服的能量,并且因了历史给予的转型机缘,释放出了常态下不可能有的激情与创造力,“在文学写作的实绩上,在其文本构造的复杂性上,在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建构上,都有着独步的东西,其‘中国经验’的生动敏感的程度,其复杂丰富的含量,等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一点,在当代文学由80年代进入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经过40多年的时间逻辑运演,我们似乎看得更为清晰。尽管在世俗消费大潮冲击下受到压抑,但就其总体而论,仍可称得上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值得纪念的且为数不多的时期之一。
这也再次表明:学术价值固然与选择对象有关,但并不等同于对象所谓的“等级”,当代文学仰望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并且自愧弗如、充满自卑感的时代应该结束,亦到了需要结束的时候。从批评和研究历史化的角度讲,“经典作家作品重评”如何及能否做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思想、有史料,并借助于问题将其连接,求得动态平衡,在于我们是否有新时代的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给予批评对象“一览众山小”的审察。由此来看,尽管当代文学批评不甚理想,存在不少问题,但仍有可以开发和拓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