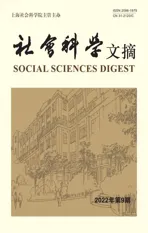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必要
2022-10-29邓安庆
文/邓安庆
伦理觉悟之难,难在伦理是道义高地,是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面子,因而谁都想拔高自己的伦理信念;同时伦理也是制度和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检验某种伦理信念的真伪,因为真信念以规范的有效性证明自身之实存,而假信念仅仅是高喊的价值,不具有规范的有效性。伦理学思想做不到“道德中立”,它要立文明之基,行共存之道,守实存之义,但“道”与“义”具有“存在论差异”,形上之道只有落实为实存之义,才具有善恶之属性,才由价值转化为规范。因而伦理学研究只有伴随着道义实存的历史谱系学考察,才能让人觉悟到伦理之为形而上学之道与作为实存之义相生相克的文明进程。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正是在道义实存的文明进程中,考察一种价值论思维规范的有效性路径,让道德哲学史本身成为一种哲学并成为一面镜子,既防止单纯主观思维因追求超世俗之道的高度而陷入空洞幻相,也防止特殊主义思维因过度追求义之实,而让道义失去普遍性根据。
伦理觉悟之艰难
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先生在其《伦理的觉悟》一文中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以来,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觉悟之最后觉悟。”
当然,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还只能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觉悟之最后觉悟”,而且不只是“吾人”,整个人类全都陷入“伦理”迷雾中。在如此感叹觉悟之艰难时,我们能做的,无非是“分析”其原因。
“觉悟”一词,通常含义是由感知性的“觉”(如感觉、知觉、觉察等)和理解性的“悟”(如“开悟”“领悟”“彻悟”等)两部分构成,但在汉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中是取其一义:“觉,悟也。”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是注重“觉”的“悟性”功能:“佛”不是“神”,而是人生智慧和真相的“觉悟者”。“觉悟”就是对迷糊、蒙昧东西的“清晰洞彻”,既可能是当下顿悟,也可能是由迷糊转而清醒的“觉悟”过程。因此,这种觉悟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理智直观,是对智慧、天道的直觉性把握,是“智性”之“清明状态”的洞见。对于伦理,我们需要具有这样一种觉悟。
但是,“觉悟”的一义化也导致一个问题,化“觉”为“悟”,使得“觉”的感知性前提消隐不见,就有可能让“悟”脱离“感觉”之根本而入迷离之境。“伦理觉悟”,其所感知者都是具体可感的伦理性东西,“悟”是要从这些具体的伦理性东西中,“领会”出自身——伦理性东西——的造化机制、“立己”之本,从而是使物成为物,人成为人,使具体礼节成为普遍礼义的机制和机理。所“感”者为具体的特殊东西,是礼俗规条;所“悟”者却必须是抽象的普遍理则、道义。“伦理觉悟”之艰难,根本原因在于不懂得二者其实是具有存在论差异的,一为现象之“实存”,一为本体之“存在”。现象界的善心善意的复杂性也因此表现在这里。有没有本体论上的善心、心体问题,不是关键;善心、心体之“发用”在现象界的规范有效性问题方为关键。作为本体之存在的善或善心只是一个价值理念,而作为现象界发用的善心却是规范之有效性问题。价值理念是先天之“道”,其作用在于“引导”,是超善恶的“善”,而作为规范性的善心才是真正的“属人之善”。价值与善的区别就在这里,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淆。把先天的形上之“道”这种超善恶之价值直接等同于形下之“义”,是伦理不能觉悟的一个根本原因。
道与义的混淆,属于道义存在论差异的混淆,这种混淆的实质在于不能“觉悟”到属天之善与属人之善的区别。伦理的觉悟就是要觉悟到伦理之善是“属人之善”,形上之道却无善无恶。因此,形而上之道只有落实为实存关系中的“相生之义”,才由价值转化为规范。道与义的结合才把伦理的先天立法原则体现为伦理生活中的历史的规范原则,从而使“道”在伦理生活中实存,并转化为伦常之“义”。
没有从高处而来的道德形上学,就容易把各种特殊的规矩当“义”,这是日常的伦理偏见;但有了从高处而来的道德形上学,却又容易导致另一种伦理偏见,把无善无恶的形上之道直接设定为“善”,从而把一个观念或形上价值直接等同于实存的“属人之善”。善恶之动,由心发轫,但要从行动原则究竟是相生还是相害来判断。“为仁由己”,己欲善,斯善而至,善恶因而有“自由意志”(由己)之根。习俗的伦理偏见往往不懂此理,认为“伦理”是外在的礼节规条,以为只要是先王之法、圣贤之道,就必然有理,这是最为常见的伦理之蔽。我们平时说人要懂“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各个特殊世界认同的“理”。但伦理的“理”不能等同于“规矩”,不是道德上的“地方主义”,不能是外在权威的命令。伦理觉悟的核心,需要基于自由意志与普遍法则之关系的考量。儿童随着长大成人而有“伦理的觉悟”,关键有两点:一是懂得如何区别外在纪律、法律与伦理法则;二是要有作为一个人的自觉。
在成人的习俗伦理水平上,不能觉悟者,常常是错误地把自己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当作是人本身。这时的伦理偏见从道德心理学上讲,就是把行动的“对”或“正当”理解为扮演一个“好角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都是人的角色,而不是人本身。如果一种“伦理”仅仅把人作为“角色”,而不把“角色”当人看,就会失去伦理的根本之义——人义。这就是我们说,“角色伦理”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伦理觉悟”的原因。
在有了对人的觉悟之后,伦理就会进入“后习俗水平”的道德意识层面。科尔伯格称“后习俗”最高水平上的伦理觉悟,是对“普遍的伦理原则阶段”的觉悟。这个普遍的伦理原则是判断一个伦理共同体一切规范与制度对错善恶的标准,被称之为“正义”,它是引领人类文明上升的永恒伦理。人类文明需要永恒伦理的引领才能上升到高贵、高雅的高度,人也只有在崇高的伦理原则的引领和规范之下,才能活出生命的高贵与高雅。因为伦理的高度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德性的高度。
伦理学通史之阙如
对伦理的觉悟不可一蹴而就,伦理伴随着人生,因而也伴随着人类历史之进程。它让人脱离动物性和“匪性”而让人性向神性超越;它让人类生活摆脱丛林法则而自觉顺从礼法正义引导的自由法则,并凭借着这种自由法则的进步而让人类具有了“历史”。所以,伦理的觉悟也就是对作为伦理生活世界之基础的自由与正义之生成性原则的领悟,它必然会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始终。只要历史尚未“终结”,伦理的觉悟就不可能是“最后之觉悟”。伦理学史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是描述伦理的发生史,属于“描述伦理学”的范畴,但作为哲学,它不可能是无反思、无建构的单纯“描述”,而是通过对伦理自身演进的“觉悟”中呈现出的自由与正义法则来塑造人类生活的实存进程。这种“觉悟”渗透着研究者的主观反思和理论建构而最终渗入实存的思想进程中。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只有西方哲学通史,却无西方伦理学通史。
国外一般哲学史著作早已汗牛充栋。自从黑格尔使哲学史变成了哲学,即在治哲学史中“做哲学”之后,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通过对哲学史的学术梳理而得以表达,从而在哲学史中把握世界及其精神走向。但是,伦理学思想史或道德哲学史,由于是从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一般只有简史,而从未见有通史。
我们见到的伦理学简史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伦理学家写的,如麦金泰尔的《西方伦理学简史》、赫费的《西方伦理学简史》、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史》等。这类著作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作者的主观性强;其二,往往选择最能表达本人道德哲学观念的伦理学家或时代,对其他的则不顾。第二类是一些不太知名的伦理学者撰写的简史。这类著作能够比较客观地介绍伦理学的简要知识,如劳伦斯·贝克尔和夏洛特·贝克尔的《西方伦理史》、特鲁尔斯·怀勒的《伦理学史——系统性的导论》等。第三类是重要的伦理学家写的相对比较完整的伦理学史。例如,德国伦理学家弗里德里希·约德尔写的两卷本《伦理学史》、瑞士伦理学家安娜玛丽·皮珀主编的《现代伦理史》、英国伦理学家哈德森主编的以“伦理学新研究”冠名的系列丛书等。
相比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研究更加不够。国内最早的研究著作,应首推张东荪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道德哲学》。新中国成立后,西方伦理学研究一度进入沉潜期。从这个时期甚至一直延续到2000年之后的几年,中国的西方伦理学研究都受惠于北京大学的周辅成提供的重要译作。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有两本“西方伦理学史”著作影响深远:一是由中山大学章海山编写的《西方伦理学史》;二是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的罗国杰、宋希仁编著的教材《西方伦理思想史》。1997年,万俊人出版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龚群则于2010年出版了《现代伦理学》一书。
国内学术界在伦理学史上取得了不少成就,对不同时期的伦理学思想、不同类型的伦理哲学,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有益探索,推动了国人对西方文明尤其是伦理学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但总体而言,在哲学性和历史性两方面的推进都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伦理学哲学的通史依然付之阙如,这就昭示了一个重要使命。
伦理学通史研究的必要性
大自然所有的生灵中只有人类有历史。伦理学哲学事关天与人、自然与伦理、理性与信仰之关系,但更核心的是在人与人性、己与人、福与祸、利与义、公与私等问题上思考人类生存的伦理机制,思考如何才能让人活出人性的光辉,活出人的德性之卓越。人不仅存在于当下,更存在于历史中。因此,对人的理解,需要理解人的历史。伦理学本身研究“应该如何”。“应该”的意向性是未来的,但“应该”要为现在之当下的行动决断提供规范有效性的命令,其理由却必须具有历史的渊源。如此一来,伦理学提供的知识视野,不仅是哲学的,而且是历史的;不仅是普通的一般历史,而且是通史,即“贯通于”人类伦理生活中的人性的道义法则的历史。这种通史的必要性,是从哲学“认识你自己”的需要中产生的。
苏格拉底作为西方伦理之父,把“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的首要问题提出来。由此我们知道,“知人”内在地包含“知己”,但“知己”比“知人”更难,或者说,“知人”的核心是“知己”。“人”“己”关系是人的个体性与人的社会性之关系,每个人身上既体现了个体性也体现了社会性。而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需要放置于历史进程中去认识,伦理学通史内在地包含对人己关系的历史认知的维度。不懂得这一历史,就不可能真实地认识你自己、认识人的人性。
但对伦理的理解不能停留于单个的人性,单个人性之体面的虚荣,属于个人对人性的主观伦理自觉。伦理学对道义的自觉,不光是单个人对主观伦理自觉的把握,而且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伦理共同体共同的伦理自觉,是一种文化的体面要求。因而,伦理学的道义通过落实在具体历史中的人的德性,形成某个时代的伦理精神、某种历史阶段的普遍道德规范。这样就出现了伦理学要求作为普遍道义与某个时代、民族和某种文化共同体所自觉形成的道德规范之间的张力。体面是个人的,但其体现的又是文化的、时代的,最终是某个民族的体面。伦理的普遍统一性就与道德的具体多样性构成了一对矛盾,而对这一矛盾的化解,只有通过伦理学通史的把握才有可能。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伦理学通史的研究,意味着我们可能永远只能达到对某个历史时代、某种文化的伦理自觉,而不能觉悟到人类普遍的伦理法则。当前流行的“中西古今”问题之所以变成对抗性的、撕裂性的意识形态之争,原因就在于没有“通史”概念,从而不懂得普遍的伦理道义与具体道德要求之间的张力与合力。强调其张力,把古代描绘为“黄金盛世”以贬低现代之不堪,或者把现代描绘为进步的高峰而蔑视古代的落后,这就导致两种不可调和的立场。如果没有一种“伦理学通史”的视野,如果没有对伦理的统一性和道德多样性之张力与合力关系的自觉,就跳不出特殊性立场,问题就永远无解。
伦理学通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以哲学追本溯源的固有方式,追溯到特殊性的伦理道德根源,回到每一种文明最初发源时的伦理觉悟,发掘人类原初伦理觉悟的经验,洞察本原伦理道义的存在论机制,这样才能跳出“中西古今”的特殊性,回到伦理之本家——实存之道义。通过本原伦理的实存谱系的考察,我们就能够具有一种超越的视野,见识每一种本原文化自身具有的伦理之“体面”。同时,伦理学通史的历史学特征,更能让我们看清,伦理道义的观念史与伦理社会的经验史之间具有非同一性,以观念代替实在,或以实在臧否观念,都无法达到伦理的真正自觉。伦理既有观念的理想性,因为它是“应该”,同时又具有规范的有效性,即规范现实。尼采正是因为重视道德的谱系史考察,才发现人类迄今还根本不知善恶是什么,所以只有从一般的历史学考察走向伦理学通史的研究,我们才能知道,伦理观念与伦理生活之间存在复杂而多样的斗争。在现实的伦理生活中,善与恶没有绝对的界限,假善为恶或亦善亦恶实为常态。只有透过伦理学通史,我们才能把握道义实存的方向性与现实的艰苦性;只有在伦理学通史的视野中,我们才能做到“同之与异,不屑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