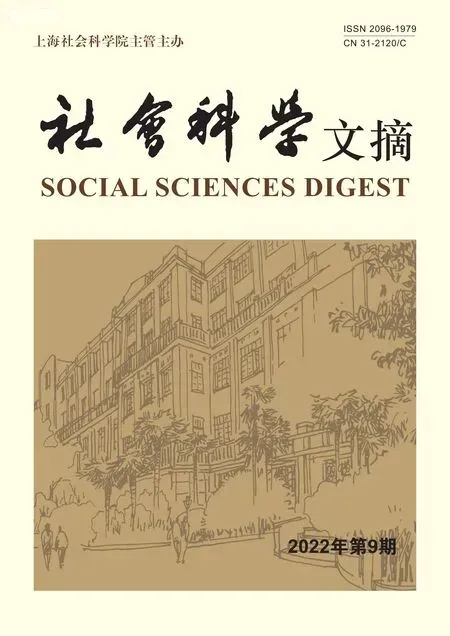论章太炎的文体学
2022-10-29谢琰
文/谢琰
文体,指“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章太炎是近代罕有的体系性思想家,同时也是集大成的古典学术宗师。他对诸多古典文体的理解与评述,一方面构成其庞大思想、学术体系的一部分,一方面又成为该体系的其他部分乃至整个体系的一个立足点或刺激源。他始终坚持从语言文字出发继承与弘扬古典文化,决定了其文体学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家所理解的文体学的独特学理依据、分类标准、评价体系。
正名:章太炎文体学的思想基础
作为清代朴学的殿军,章太炎的正名思想以“对汉语言文字的名实关系、名实源流、名实规范的深入思考”为中心。他高度重视从语言文字规范角度理解和诠释文体;具体而言,体现在正字例和正文例两个方面。
首先,正字例即建立基础性、普遍性的语言文字规范。章太炎始终将“造词”之规范放在“放言”之规范的前面,也就是“训诂”先于“体裁”。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古文、骈文、韵文这些最基本的文体现象,都根基于特定的语言文字规范。比如他认为单行散体不足以界定古文,古文必须在“词气”“训诂”上符合先秦两汉文献所确立的语言文字规范。也就是说,古文是一套内在的应用程序,而不只是外在的形式特征。同样道理,骈文也不是只在形式上寻求偶对的文体现象,它的产生原因是汉语词义“多支别而乏中央”的特点,具体而言就是“一训数文”。骈文的本质是对汉语复杂字例的一种密集性的强化安排,以弥补散体之古文在表达上的单调缺陷,正所谓“孑句无施,势不可已”。
其次,章太炎又立正文例之说,进一步诠释具体文体的语言文字规范。就《文例杂论》所述而言,正文例包括正习俗之名与正文体之名两个方面。每种文体都包含关键性的习俗用语,其名实关系需要厘清源流、折衷古今。同样道理,文体命名也与习俗息息相关。从习俗出发考察文体命名,并且厚古薄今,主张以古正今,这是章太炎的文体命名学的核心特点。在《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中,正习俗之名与正文体之名这两方面工作都得到更全面、更深刻、更系统的推进;有些论点和看法,会比早期的《文例杂论》所论更为激进,同时也更能展现其“正文例”思想的归宿及特质。
综上所述,章太炎的正名思想以建立语言文字规范为中心,由此奠定了其文体学的思想基础,使其获得独特的学理依据。如果说正字例代表了对于语言文字规范性的严格追求,那么正文例则代表了调和规范性与约定性的努力。章太炎的文体学始终具有坚定的历史主义倾向。这使得他一方面强调文体的规范性,主张以源正流,另一方面又拒绝承认抽象的、机械的规范性,而总是从具象中提炼规范性。此种历史主义倾向,与其穷极高明的一元论哲学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张力。章太炎的文体分类学、文体流变论乃至全部文学思想,就在此张力之网中展开。
二分与一元:章太炎的文体分类学
章太炎在1906年的讲演录《论文学》中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文学各科”分类表,并作出了周严的解释,从而建立了涵盖一切载籍文献的文体分类体系。细绎《正名杂义》《论文学》《国故论衡》《论诸子学》《国学十讲》等不同时期著述,会发现“二分法”事实上成为章太炎进行文体分类的一贯性、枢纽性原则。
一是文辞、口说之二分。《正名杂义》认为,《尚书》中“商周誓诰,语多磔格”,就是因为“直录其语”,而“帝典荡荡,乃反易知”,则因为“此乃裁成有韵之史者也”。这个分判已经显示出崇文辞而去口说的倾向。降及战国,“纵横出自行人,短长诸策实多口语”,而“名家出自礼官,墨师史角,固清庙之守也”。尽管两家都留下文辞,但纵横之言近于口说,名家之言则“与演说有殊”。文辞有稳定的规范性(有法),而口说只有当下的实效性(无法)。在章太炎看来,尽管口说本身没有成为历史性的存在,但口说的影响却在文辞中常常浮现。此种影响主要是负面的,需要警惕乃至祛除。他将文字记录所带来的规范性抬到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所以崇文辞而去口说。
二是无句读文、有句读文之二分。《论文学》认为,无句读文如图画、表谱、簿录、算草之类,只是用文字符号记录信息,无法被言说,故代表的是文字的特性,而有句读文既是记录,也可被言说,故代表文字与语言的共性。他用这样的对比表明立场:“文”的根本特质是准确记录,越是接近无句读文就越容易做到准确记录,所以典章、疏证等文体最为优越。换句话说,他希望在观念层面用无句读文的特质来规范有句读文。
三是名家之文、纵横之文之二分,实是从文辞、口说之二分引申而来,但又具有新的内涵。《国故论衡·论式》云:“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在他看来,名家之文所采用的是更优等的表达方式,即建立在充分的小学功底和博洽学问基础上的质朴谨严的名实之论。将名与实准确对应,本来是语言文字的最基本功能,但在章太炎看来,此项工作乃是最不易企及的最高境界。从核准名实出发,既可考清事实,也可说清道理。相形之下,“诗”“纵横”“文士”皆为“浮辞”所困。
四是客观之文、主观之文之二分。他反对今文经学的一大理由是,此种说经方式混淆了客观之文与主观之文的界线,用主观性的“文辞义理”去比附客观性的“典章行事”。在《论诸子学》中,他将此种二分法更明确地表述出来:记事之书遵循客观之学,故可称客观之文;诸子之书遵循主观之学,故可称主观之文。在晚年的《国学十讲》中,他将“集内文”分为“记事文”和“论议文”两大类,亦可见客观、主观之二分法。他认为主观之文并不能依仗个体的主观性,而必须依赖群体的知识基础。他极重高明之学,但又始终不离朴学本色,试图建立主观性思考的客观性基础。
综上所述,在章太炎的文体分类学中,虽然文体细目驳杂且多变,但是二分法思维贯穿始终。他将二分法作为权宜之计,以便归类丛杂的文体现象;将一元论作为根本原则,用来建立文体的正确规范。他始终强调以文辞为本,以无句读文为本,以名家之文为本,以客观之文为本,而力图克服口说、有句读文、纵横之文、主观之文的种种丧本失源、多歧多变的弊端,这就用一元论模式统摄了二分法思维。归根结底,他希望用文体的最原始、最客观的特质来规范一切文体,故最终坚定地将“有文字著于竹帛”作为“文”的定义。换句话说,“记录”这种社会行为,在他的阐释下具有了形而上学内涵:记录,就是将意义彻底客观化的一种人类理性能力;文体,就是客观规范本身。
名实、质文、气势:章太炎的文体流变论
章太炎的文体学整体上围绕建立语言文字规范而展开,其文体分类学又以强调规范的绝对客观性为根本依据,因此,其文体流变论本质上是基于客观规范而对一系列失范事实进行严厉批判的产物。具体而言,失范事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例失范,主要体现在文体之名与文体之实的不相符;二是字例失范,即文体书写由质而趋文;三是作者失范,即时代风气催生了不合格的作者,从而造成文体势衰。
章太炎从习俗出发考察文体命名,主张厘清古今源流,所以他对文例失范现象的批判,包括古今增减、古今缩放、古今淆乱等多方面。文体之名,无论增减、缩放、淆乱,都是因为“事”的变化,也就是习俗衍变。文体增减、文体缩放现象,如能以古正今,当然最好;如能明其源流,也不妨随波从俗;如果不识源流,妄加规定,甚至以今律古,则会造成文体淆乱现象。在《国故论衡·正赍送》中,他对诸种“送死之文”在后世流变中的名实淆乱现象条分缕析,提出“刊剟殊名,言从其本”“慎终追远,贵其朴质”的总原则,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变通之法。
如果说章太炎对待文例失范现象尚容许变通之术,那么他对待字例失范现象则极为严苛。在《正名杂义》中,他用“表象主义”概念分析中国文化,认为汉字假借、《易》学、文章修辞是“表象主义”的三大表征。文章写作中的“表象主义”则主要有两种:一是文人不明文字孳乳之源流,“习用旧文而怠更新体”;二是文人滥用比喻、借代、用典等修辞手法。在章太炎看来,只有建立在正字例基础上的造辞才是合理的,这叫“言而有物”;违反字例而胡乱造语,这叫“破碎妄作,其名不经”;而绕过语言文字的直接表意功能,用修辞之效果取代用字之精确,即便“原本经纬”、无一字无来处,也不合理。此种奇特的反修辞倾向,“其实是严格至极的修辞学要求”,也就是强调基础性、普遍性的语言文字规范。
章太炎的文体流变论的第三个方面,是对作者失范的批判。章太炎并不对作者进行独立且平允的研究,而是常在文体流变史中刻画作者的面目并评估其价值。他每好言“势尽”“泯绝”,其笔下之诗赋史就是一部退化史。他以武力、兵气解释韵文作者的情感盛衰。他甚至将“词气”、情感与“体气”也就是身体强健程度直接挂钩。令人深思的是,章太炎虽然感慨后世作者的体气之衰、性情之衰,但并不主张在情感层面重建民族心理或民族文学,而是寄希望于理智层面的激发与重构。
综上所述,章太炎的文体流变论着眼于文例、字例、作者,描述了文体发展史中名实不符、由质趋文、气势渐衰的失范现象。整体来看,其文体流变论是其正名思想和文体分类学的附庸,是以否定性的方式强调并验证了“规范”的绝对客观性。他将一般文学批评家所津津乐道的高贵、优美、情感丰沛、技艺精致、高度个性化、充满不定项的那样一些文学特质,统统予以唾弃。因此,他的文学论述中几乎看不到系统的作家论和作品论,而是处处以文体学为视角、为框架,显示出高度客观化的学术取径。他的既武断又高明的种种论点,及其背后质朴而幽邃的学理基础,也都应该从文体学角度予以理解和阐发。
存真的焦虑:从文体学理解章太炎的文学思想
郭英德认为:“文体的基本结构应由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构成。”章太炎的文体学,主要落脚于语体和体式,而相对忽视体制和体性。在文体四层次中,体制是已然固化的外在形貌,体性中则包含抽象化、主观化的内在精神,只有不内不外、既偏于客观同时又没有固化的两个层次即语体和体式,可以高度契合章太炎的语言文字规范思想,故成为其文体学体系的枢纽;与此同时,他又将体性中有关表现对象的部分,降低至习俗乃至物质层面,作为其文体学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建构起一套拥有充分客观基础,以建立语言文字规范为中心的文体学体系。章太炎对于自己文体学的独特取径有鲜明的自觉。
在写给曹聚仁的书信中,章太炎反对从“精神”和“工拙”来判定“诗”,坚持只能从客观性的“形式”着眼。在《论文学》中,他有更详细的阐释。他倡导以“形式”“轨则”“雅俗”为本,而反对以“精神”“才调”“工拙”“兴会神味”为本,终究是为了确立“无句读文”在其文体学体系中的基原地位。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将“修辞立诚”这一古训上升到“第一文学原理”的高度,意味着他极力维护“记录”作为一种理性能力的崇高价值,由此也凸显了他对于“记录”能否实现绝对客观化目的的深刻焦虑,不妨称之为“存真的焦虑”。
章太炎之所以抱有“存真的焦虑”,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缘由。第一,他一向认为历史是民族之根,所以准确记录历史事实就是民族存亡之命脉,意义极为重大。文人笔下的文学,往往会对“识往事”产生严重动摇,所以章太炎向来不赞同周氏兄弟式的文艺救国。第二,他将“小学”和“名学”视作结构相似的精神过程,力求捍卫主观表达的客观基础。逻辑的失范与语言的失范是一体之两面,都需要高度警惕。而思想的准确阐释,与历史的真实还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第三,他认为古典文学传统中长期存在虚假的“规范”,会反噬真正的“规范”。在他看来,宋代以降“文章学”所讲之“体制”,实际上是以偏概全的主观之论,继则由主观化而趋于机械化,生出种种间架结构、起伏照应之说,但此种“体制”不是规范,真正的规范乃是依据不同习俗、不同文体特点而自然产生的“学”;既然名之曰“学”,意味着写作者必须具备系统化、习俗化、客观化的知识与能力。“学”的存续与否,在章太炎看来是“记录”能否实现绝对客观化的最关键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学”“文体”“文学”这三个概念是同义词,它们的内涵都可以被概括为:记录的规范。章太炎所理解的“规范”,是经验的历史集成,而非理念的逻辑演绎或偶然示现。
综上所述,章太炎的文体学以正名为思想基础,以建立语言文字规范为核心诉求,包含独具特色的文体分类学与文体流变论,对纷繁复杂的文体现象提出了独断而统一的规范性意见,显示出高度客观化、理性化的学术进路。作为一个坚守一元论思维的思想家,他用刻意的片面态度来强调语言文字的主导性,以求建立文体运行的内在规范性。在中国文明遭受西方文明强烈冲撞的时代大背景下,章太炎慧眼独具地揭示出汉语自身所包含的“规则系统的力量”,由此推动古典文学传统之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