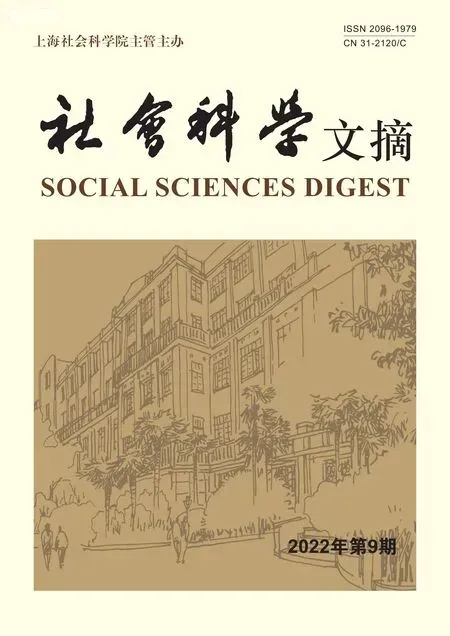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体系建构与发展面向
2022-10-29杨博超李丹
文/杨博超 李丹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与商事争端解决
我国经济贸易总量的持续增加和商事争端数量的上升,使得从法律角度应对商事争端问题产生两方面发展趋势:一方面,对内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提升治理效能;另一方面,积极批准或加入相关国际公约,并同时探索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新模式。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跨地域范围内改善区域合作和实现互通互联”目标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认同,倡议框架下投资额度和经济贸易总额逐年上升,与此同时,涉及商业交易、项目建设、环境保护、劳工关系等法律争端日趋增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呼声日益高涨。因此,厘清商事争端解决涉及的理论问题,梳理我国涉外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历程和“一带一路”框架下商事争端解决的体系建构,探讨仲裁、调解、仲裁在实践中的价值、互动模式和挑战,或将对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未来发展作出有所裨益的尝试。
涉外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和体系建构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探索设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模式,主要涉及以下四个理论问题:
第一是管辖权。涉外商事仲裁管辖权指司法或仲裁机构对某一特定领土范围内的特定主题事项和特定人员作出决定,其中包含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或调解解决争端的能力。实践中虽然很多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在设立时考虑到了领土管辖权的概念,但由于这些机制的目的在于处理更多的国际诉讼,管辖权通常经同意后被扩大,从而呈现“去领土化”的状态。此外,在国家内部设计的争端解决法律网络(legal hub)通常具有“次国家”特质,而非传统国际法意义上的完全主权,从而使争端解决网络摆脱了类似国家体系内部的官僚性羁绊,程序也更灵活,进而能够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变化作出更迅速的反应。但其仍存在两方面潜在风险:一是从规范性方面看,次国家管辖权很难独立于国家,从而可能产生法律程序正当性和结果公平性不足的风险;二是从实践方面看,管辖权的潜在拓展可能造成与东道国关系的紧张。
第二是法律地位。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地位,可以将其假设为一个法人实体,并由政府使用类似公司运作模式来建立机制,通常表现为国家通过建立一个中央机构来控制和监督解决机制的运行和活动。这种法人实体的模式通过公司式的运行而推动利用提供法律服务来创造收入。这种理论也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争端解决机制所有权和争端方对机制公正性的疑惑,特别是在争端涉及政府实体或国有企业的情况下。
第三是法律适用。涉外争端解决机制一般被视为复杂贸易和投资关系的连接点,主要涉及民事和商业问题,具有一定分散性,法律适用也不局限于东道国法律。从国际实践看,机制支持当事人自由选择实体法订设合同。这种自由同时体现在争端解决条款所选择的准据法方面,即当事人并不一定选择争端机制的默认实体法,而选择其所偏好的法律。从这个角度看,争端解决机制的运作或被视作跨国法律的节点,同时也具有使分散法律系统内部形成一种平衡状态的功能。
第四是“一站式”争端解决机制建构。“一站式服务”(one-stop shop)的核心是,在争议前和争议阶段,争端解决机制可以提供相关的几乎所有法律服务,包括争议解决。这与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满足争端当事方的多元争端解决需求,提高处理效率,而提出创立“诉讼—仲裁—调解”三位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路颇为契合。它的优势在于结合了诉讼和非诉讼机制,破除了替代争端解决机制(ADR)中的“非此即彼”的逻辑障碍,并可在仲裁庭和商事法庭之间建立互动联系,最终发展出满足当事人需求和市场偏好的跨机构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立兼具功能性和象征性。因此,在考虑机构和规则的设定时,应以促进国际当事方灵活选择跨国法律来解决争端为原则。从管理的角度看,争端机制除了扩大影响并提高专业性以寻求创造利润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使自身在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东道国中呈现效用最大化。
“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多元发展
“一带一路”涉及的贸易和经济领域争端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主权国家间因中国投资的有关项目产生的纠纷;二是投资者与投资目标国之间的投资争端,即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争端,包括沿线国家之间可能产生的争端;三是由商业行为带来投资者(平等主体)间的争端,其中可能存在同一个项目下涉及不同的合同文本和法律事实。从国际习惯看,一般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争端通常通过既定的国际机构和协议,如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各种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但由于该机制面临“停摆”的尴尬局面,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一般由国际投资协定设定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立替代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以迅速有效地解决涉及私人和政府主体的经济和商事交易争端显得十分必要。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与其他成立较早的、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业)法院(庭)可以从三方面进行比较。一是审判语言。中国商事法庭不接受将英语作为出庭语言,但可以经当事人要求提供翻译;在当事方接受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提交英文证据。而除法国外的其他国家商事法庭均接受英语作为诉讼语言。二是法官选择。中国商事法庭不允许选择外籍法官,而新加坡和伦敦可以根据案件涉及民法或普通法来选任相应的法官。三是判决执行。国际商事法庭对域外判决的执行几乎均通过签订或加入有关判决承认和执行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以及本国立法等予以确认。而中国商事法庭建设起步较晚,加之司法惯例中对域外判决的执行持保守态度,这种体系显得较为单薄,但可预见,随着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加深,这种情况将会好转。
为充分发挥司法审判和仲裁机制的优势作用,我国开创性地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中引入“一站式”商事争端解决平台,形成了“诉—调—仲”三位一体的争端解决模式,其具有五个特点。第一,为了解决中国暂不能聘请非中国籍法官的问题,并体现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性特点,商事法庭创造性地聘请不同法系的法律背景专家成立了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第二,在管辖权方面进行创新,国际商事法庭的判决为“一审终审”,案件管辖可以通过当事人协议确认,但其并不享有普遍或广泛案件的管辖权,而被限制在国际商业和民事事项有关的争端中。第三,建立了调解和诉讼之间的有机联系,将调解作为解决争端的首要方式,从而可有效利用财政和司法资源,提高争端解决效率。第四,建立了便捷和快速的域外法律查明体系,并可接受互联网技术等其他合理方式。第五,通过“互联网+”建设双语网站和电子诉讼服务平台等,以支持在线案件登记、诉讼、证据交换和其他法律服务,营造对当事人友好的环境。
中国涉外商事审判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创新性发展,但因创设时间短,规则和制度设置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从而实现“一站式”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影响力拓界。
一是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性质和工作流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包括为司法审判提供咨询意见、域外法查明以及进行商事调解。但对于其开展商事调解工作的身份应当进一步明确,即是否可以既受法庭委托开展,又能基于当事人申请而直接开展调解工作。同时,应对专家委员会的中立性、监督机制、任命和退出、内部讨论流程、具体案件中的委员会成员遴选标准等问题作出具体和细化的规定。
二是管辖权的明确性。法庭对标的超过3亿元人民币与中国实际产生联系的争端,基于当事人书面同意可以提起管辖。同时,对上级法院移交的案件或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移交可以行使管辖权。从司法实践看,仍不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如何行使管辖权移交的司法裁量权。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商事法庭成立前,当事人不能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事纠纷,因此当前的管辖权设定对当事方是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在当事方倾向于将争端提交中国法院,或案件已经在中国法院管辖的情况下。
三是“一站式”平台各争端解决程序之间的融通性。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文件均提出要建立调解、仲裁和诉讼有效衔接的争端解决平台,但三种程序如何协调和衔接尚需要制定更明确的程序规则。当前,纳入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平台的调解和仲裁机构的选择标准尚不清晰,并且对于在“一站式”框架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可以纳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也缺乏明确的法律性质指引。调解协议在国际层面的法律效力问题,可能直接影响当事人选择使用“一站式”平台的决定。
四是应对争端的灵活性和可调试性。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力核心在于信誉、公正、程序灵活和判决(裁决)的执行力。当前,具有影响力的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都在努力塑造品牌,并向机构客户宣传“最先进”的服务,而各中心之间则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虽然每个机制几乎都主要适用所在国法律,但也会考虑参考或适用其他机制的判决或裁决。由此,调试性显得更为重要,在没有全面适用的相互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国际条约的情况下,各机制或可依靠“软法”性质的文件,如谅解备忘录或机制间协议来进行联系,同时跨国法律精英(具有多国律师职业资格的人士,中国司法制度暂不支持非中国籍人士以律师身份出庭)亦可成为机制间的沟通桥梁。同时,可考虑发挥仲裁程序灵活的优势,如2021年9月16日,“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与日内瓦国际争端解决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或是一次有益尝试。
“一带一路”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面向
国际商事法庭可以被视为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真正的体系创新,但其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在结合国内和国际情况的情况下,可从四个方面考虑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面向。
(一)可调试性:“互联网+”赋能“一站式”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法院系统在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理念的指引下,在建设“智慧法院”的总目标下,初步实现了“互联网+”与涉外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嵌入式发展,并为传统理念上的“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融入“中国特征”,形成了中国化的“线上纠纷解决机制”。对于“一站式”争端解决机制的顺畅和融通问题,亦可通过“互联网+”赋能解决。如仲裁在机制中处于较为尴尬地位,即若当事人有意通过仲裁解决争议,则根据规定只能委托其他仲裁机构进行审理,由此则使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在仲裁中“难有用武之地”;而若考虑使专家介入仲裁,则需要赋予专家委员会以特别仲裁的职权,但因涉及《仲裁法》的修订,恐较难实现。对此,可以考虑在“智慧法院”框架下,纳入“大仲裁”概念,为仲裁机构提供入驻平台机会,并逐步探索发挥专家委员会在仲裁中的“智囊”地位,从而最终实现调解、仲裁、诉讼“三位一体”的有效衔接。
(二)可预见性:持续发挥指导性案例在商事争端解决中的作用
涉外商事诉讼的定位应当考虑破除当事方对基于东道国司法体系和司法主权的畏惧,而指导性案例则可明宣司法连贯性和整体性,有效避免此种风险。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发布多批涉“一带一路”典型和指导案例,对于处理类似法律争端具有指导作用,并将提升司法专业性,提高跨司法区域和地理边界裁决的一致性。但从实践中看,法官虽认为指导性案例可以作为后续类似案件裁判说理和援引依据,但在援引案例时却部分抽离了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所应起到的明示作用,同时“似用非用”又使得法官借用指导性案例作为跳板,规避了裁决真实的说理过程,违背了裁判的信诺。但不可否认,对于“一带一路”所出现的新型涉外案件数量增多、法律事实复杂多样的趋势,指导性案例在为法官探求说理方向上具有重要作用。
(三)智力储备:稳步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建设
不论“智慧化”或“类案建设”,核心都应是人,而且是熟谙国内和国际商事法律的专业人才。所以,稳步推进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储备是首要之务。一方面应当针对性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的研究者;另一方面应当培养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的法律人才。培养复合型国际法人才,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在海牙国际私法协会等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阐明中国法治观点,并最终推动国际规则、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的形成。此外,在法官层面,可考虑任命国际商事法庭专任法官,以彰显法官专业性。
(四)跨国执法:衡量评估国际条约,推进域外执行
判决和裁定的域外执行是所有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理想状态下,中国可考虑推动国际层面上建立外国法院判决执行公约,但现实中因涉及司法主权问题,可能较为艰难。当前中国司法审判所依照的“互惠式”判决承认机制,可能会使当事人无把握预测域外司法管辖区域能否给予这种“互惠”待遇而产生不安,并一定程度限制商事法庭的发展。未来中国一方面可以持续评估已签署的《海牙公约》,并考虑适时批准;另一方面可以参考《互惠执行英联邦判决法案》《相互执行外国判决法案》等经验,积极开展区域性法院判决互认磋商。但要坚持公约适用的国际性和统一性,慎重对待双边条款,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