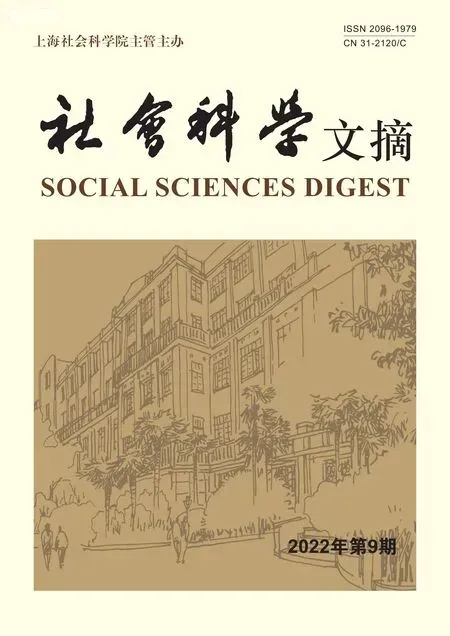结构、行动与历史:社会学视野下革命研究的源流
2022-10-24马学军应星
文/马学军 应星
中国革命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主题。然而,革命研究在1979年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中长期不被重视。近年来,国内兴起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趋向,革命也日益受到中国社会学的重视,涌现了一些关于革命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尽管如此,革命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依然处于边缘位置,人们对革命的社会学研究仍然存有疑虑。
实际上,“革命”不仅是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以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的革命研究包含了结构与行动、现实与历史、社会与政治、民情与观念等多个面向,把现代革命既理解为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同步转变,又视为与具体行动者的能动性紧密相关的历史进程。20世纪欧美历史社会学的革命研究或偏于结构分析,或偏于文化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学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研究,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组织行动和思想观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结构、行动和历史的维度,重返经典社会学的革命研究传统,辨析欧美历史社会学中革命研究的流变,梳理当代中国社会学革命研究的成果,强化革命主题对拓展社会学想象力的意义。
西方经典社会学的革命研究传统
“革命”是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经典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就单独列出一章“社会学家和1848年革命”,讨论孔德、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态度和观点。与孔德不同,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不仅参加了欧洲革命,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分别形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样的经典著作。因此,经典社会学的革命研究传统首先要回溯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革命研究思想。
1.马克思的革命研究传统
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论断不仅指出了革命的结构性特征,也指出了革命与阶级行动、革命与历史变迁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对革命分析的总体性观点。马克思研究中的革命包含了结构、行动与历史三个基本面向。
首先,马克思笔下的革命是与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直接相连的。这一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表达过,也更鲜明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中。其次,马克思的革命分析又是与阶级行动与人物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更是开创了将结构、局势和行动者三个要素折叠在同一时段的事件分析的方法。行动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构成历史转折的关键要素——这种行动者远不止波拿巴,而是包含了1848—1851年法国政坛几乎所有重要的当事者。最后,马克思的革命分析还是历史性的,与其历史唯物主义密不可分。这是马克思不同于庸俗唯物论和唯心主义的地方,也是不同于既往革命分析的结构视角和行动视角的关键。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是以辩证唯物史观的总体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即将社会现象置于社会与历史的总体过程中来确定它们的性质和意义,考察它们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认为,方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这一方法既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又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
2.托克维尔的革命研究传统
出身于法国旧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曾经是七月王朝众议院的代表,还参加过制宪会议并出任外交部长,亲历了共和国的覆灭和路易·波拿巴的上台,可谓法国大革命的见证者。作为孟德斯鸠的信徒,托克维尔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现代民主和法国大革命,完成了《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两本经典著作,分析了大革命发生的长期性因素,讨论了革命前后的政制变化,同时还注重“民情”在革命进程以及民主运行中的作用。这些思想使他成为经典社会学的大师之一,也足以让我们去重视他的革命观。
首先,托克维尔的革命分析,其思想主旨是关心现代民主问题。《论美国的民主》旨在回答为什么美国的民主社会是最自由的民主社会,《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想回答“为什么法国在朝民主演变、保持自由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中,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其次,托克维尔的革命分析既注重长时期政治结构的变动,也重视短时期个人行动。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纯粹的偶然事件,应从长时段内旧制度的崩溃入手分析。同时,他对大革命中人们的行为、激情和态度都作了极为细腻的分析。革命的发生是结构性的,但革命一旦发生,革命的力量和走向就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行动者的意图、情感、态度密切关联。最后,托克维尔受孟德斯鸠提出的“民情”概念的深刻影响,分析了“民情”对理解美国和法国不同民主样态的影响。他认为美国民主政体之所以是自由的,有三个原因:独特的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其中,习俗和信仰是影响人的自由的重要条件,习俗的决定因素则是宗教。与之相比,法国在大革命爆发前,身份平等已产生了革命性的效应,但法国社会的“民情”并没有产生相应变化,缺乏可以减少民主盲目本能的弊端,使得法国大革命出现了动荡,走向了专制。托克维尔从“民情”角度分析大革命,既不同于革命的经济社会结构分析,也不同革命的政治制度分析,而是开创出一条非常独特的革命研究路径。如果不了解支撑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民情”基础,我们就难以深入理解世界各国的革命类型以及革命运行和波动的底色及潜层基础。
欧美当代历史社会学中的革命研究
美国历史社会学自20世纪60年代主要经历了三波思潮。第一波发生于60年代至70年代,关注宏大的政治结构及其历史变迁;第二波发生于70年代至80年代,关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差异性,侧重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分析诸如革命爆发、国家建构、资本主义形态的不同历史演化轨迹;第三波发生于80年代至90年代,侧重对文化、符号、意义以及行动者能动性的分析。本文以斯考切波和林恩·亨特为代表,分别分析美国历史社会学第二波革命研究的结构分析和第三波革命研究的文化视角。
1.斯考切波所代表的结构分析取向
斯考切波在其代表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革命是到来的,而不是制造的”(Revolution comes,not made)。她认为,当代社会科学中几种主要的革命研究理论对革命总体进程的分析从根本上是一样的,即“大约都将这种普遍性的革命进程模式视为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或者是由意识的目标所引导的运动”。为了超越既有革命的研究理论,也为了解释她所谓的“社会革命”,她认为要采用一种结构性视角,而非意志性视角。她断言革命是在客观的社会结构下发生的,而非由某些群体、个人有意识或有目标发动或制造的。
斯考切波借鉴马克思的思想,从结构性视角分析社会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也被视为关于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然而,这样的结构性分析视角后来也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和争议。如果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是由结构性的关系所决定,那么如何理解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革命中的作用?如何理解精神或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实际上,马克思分析革命的行动视角和历史视角在斯考切波这里被完全忽视了。尽管她在文中也用“接合”(conjuncture)一词来处理革命的结构与行动的张力,但她终归还是坚持结构分析是根本的。可以说,斯考切波对马克思革命分析中的结构、行动和历史的总体视角作了中层化的理论改造,将其改造为强结构分析,而行动分析和历史分析在其中丧失了重要性位置。
2.林恩·亨特所代表的文化分析取向
林恩·亨特所代表的新文化史分析试图突破革命的结构分析,倡导革命的文化分析。她在其代表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中,既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从经济—社会的维度解释法国大革命,也不同意政治史学家从政治维度解释法国大革命,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政治文化上。在她看来,法国大革命主要不是新生产方式或经济现代化的出现,而是革命政治文化的出现:政体结构在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和民众大动员的影响下改变,政治语言、政治仪式和政治组织都呈现出新形式、新意义;革命者通过语言、意象与日常的政治活动,致力于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和社会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作为一种不同以往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在全球史学中开始流行,也对中国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产生影响。新文化史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引导我们关注人的内在经验、关注符号的意义,由此可以为我们理解历史现象提供新的视角。新文化史承认托克维尔是其范式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然而,在托克维尔所开创的革命的“民情”分析中,是将政治分析和行动分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非单独割裂出来文化因素。新文化史的革命研究往往过于执着于仪式、符号和意义等文化要素的分析,脱离了与结构史、制度史的结合,这样就很容易落入碎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窠臼。
当代中国社会学中的革命研究
中国20世纪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其规模的宏大性和影响的深远性来说,堪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相比。中国革命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主题。然而,革命研究在1979年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曾长期不被重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在中国社会学视野中就完全消失了,只是它被打散、消融在其他分支领域里,被人们视而不见。而最近十多年来,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革命研究的意义日渐引起社会学界的重视。
本文以“中国共产主义文明”为线索,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初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期”“21世纪初期以来”三个时段来评述与中共革命相关的研究范式、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试图将国内散落在各分支领域的革命研究成果“打捞”并整理出来,以引起学界对这个主题的重视。
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在第一个时段主要借用现代化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以及中国近代社会转变,其特点是偏重结构分析,偏重从宏观上把握不同时段社会结构的形态和变化趋势。孙立平是这一时期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20世纪革命的代表人物。在第二个时段,中国社会学一方面引入国家—社会、法团主义等西方理论范式,周雪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张静主编的《国家与社会》以及《法团主义》是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要深刻理解当下的社会变革,离不开对传统特别是中共革命传统的研究,路风以及李猛、周飞舟和李康对单位制的研究、孙立平从1994年开始的中国农村土改口述史研究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论著。在第三个时段,中国社会学在继续关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已经越来越重视历史的视野,呈现出“历史社会学的转向”,并进一步提出了“把革命带回(到社会学视野中)来”。本文扼要从“中共政治文化及军事组织的源流研究”“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历史变迁研究”“群众路线及群众团体形成和变迁的历史分析”“思想改造及道德重塑的历史分析”这四个类别来梳理并简评这个阶段的研究。应星对中共大革命时期和苏维埃时期民主集中制的若干研究以及对中共军队的专门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长时期理解“中共政治文化和军事组织”的源流。冯仕政、周雪光、渠敬东、王星、贾文娟等人的研究,共同推进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历史变迁研究。张静、孟庆延、李里峰、卢晖临、张乐天等人的研究,共同聚焦分析中共成立以来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和农村集体化的实践。游正林、马学军等人的研究聚焦分析中共成立以来工人运动的实践和工会组织的变迁。丛小平、王颖等人的研究聚焦分析中共成立以来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困境和变化。周晓虹、刘亚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人物的口述史访谈和研究、李放春对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考察等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展历史资料,记录普通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深化对集体记忆、思想改造等议题的研究。这四类研究成果有助于从社会学的视角深化和丰富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认识,也有助于拓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边界和主题。
结语
米尔斯对具备“社会学想象力”心智品质的研究者有一个基本判断标准——在面对任何一个社会现实时,都会坚持不懈地追问三组问题:这个特定的社会作为整体的结构是什么?不同的人在这个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个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米尔斯的这三组问题,恰恰包含了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即结构、行动和历史。本文选择从这三个维度入手来梳理西方经典社会学、欧美历史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也正是希望能紧扣社会学的基本视角,来勾勒社会学革命研究的基本脉络,明确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的意义和地位。
西方经典社会学、欧美历史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在结构、行动和历史分析上表现出了不同的样态。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最初散布在其他领域研究中,侧重宏观结构分析,而在最近十多年来开始呈现出“历史社会学的转向”和“把革命带回来”的热潮,并在行动分析和历史分析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在将其如何与结构分析进一步结合上尚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