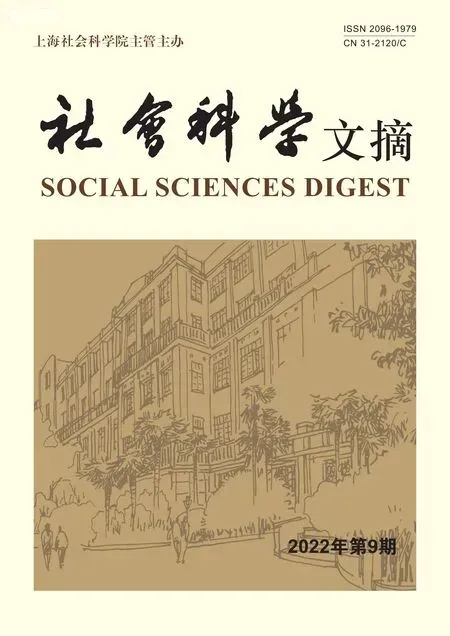观念的“割席”
——当代中国互联网空间的群内区隔
2022-10-24陈云松
文/陈云松
背景、问题和基本概念
随着互联网逐渐成为各类信息的来源与传播平台,信息开始变得更有非连续性和自选择性的特点,使得公众对许多观念议题,尤其是和“文化主体性”相关的议题出现集体认知和记忆的叠加、更新、断裂与分化,最终演变为互联网上的观念之争和个体观念的固化,使得具有同质性特征的基础性社会结构单位之内出现普遍的观念的“割席”。之所以使用“割席”这个词,是为了体现原本同一社会群体内的系统性共识和倾向被裂解分化了,如同东汉末年管宁与华歆这对友人因理念不合而割席断交一样。本文将这种同质性社会群体内部因观念之争而导致的异质性称为“群内区隔”。在微观层面,本文所讨论的“群”,指的是个体在互联网新媒体社交平台上有联系的基础社会结构单位成员;在宏观层面,我们讨论的“群”实际上代表了家庭、单位、学校等具有同质性特征的社会基础结构。
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中多主体现代性的形成与“双向脱嵌”所导致的“时空折叠”,为中国当代互联网空间中的观念的“群内区隔”提供了宏观理论诠释。接着,本文引入戈夫曼的剧场理论,强调了其催生的“强义务”特征,使得互联网社交媒体形成分裂的“关系剧场”,以此为“群内区隔”提供微观层面的理论框架。据此,本文初步构建了当代中国互联网空间中的社会观念与现实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总体图景以及宏观—微观理论框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当代中国互联网社会心态的理解,提升治理能力。
“群内区隔”的宏观背景:“时空折叠”与多中心现代性
当代中国互联网空间围绕文化本土性观念所形成的“群内区隔”及其日益强化的趋势,其宏观背景恰恰来源于吉登斯所说的“综合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于社会系统时空变迁的总体秩序”。基于此,吉登斯提出了“远距化”到“时空分离”路径。制度结构所包含的规则和资源具有延续复制能力,形成了时空的“远距化”,对应着现代性。而“远距化”可以导致“时空分离”,使得具有现代性的社会系统“脱嵌”并在其他时空进行复制。“先发”社会的制度系统以“脱嵌”的时空分离方式延伸复制到“后发”社会,形成跨越地表的全球社会结构。显然,吉登斯所讨论的“脱嵌”暗喻了一种社会系统的体制势能或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边缘”假设。只是当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规则和资源进行时空延伸之际,吉登斯和福山心目中的严整的全球秩序并不会保持某种超稳定的静态结构。一方面,真正触及深层制度的社会系统的脱嵌、复制往往是非常困难和不稳定的,甚至会出现原有社会系统的回流。另一方面,在一些看似成功的吉登斯心目中的现代性扩散案例中,其时空延伸过程中会出现经济系统甚至政治和文化系统“反向脱嵌”的张力:完成了政治系统嵌入的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其经济系统的崛起对西方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完成了市场经济系统嵌入的当代中国,其基于文化传统和政治系统的输出性力量,形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多中心现代性”。忽略了这种“多中心现代性”便是吉登斯“时空分离”理论的薄弱之处。
因此,我们在吉登斯的“时空远距化”——“时空分离”概念路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对应着全球化多中心阶段的“时空折叠”的概念。所谓“折叠”,指的是在现代化“后发”社会这一“地点”,不同的“制度时间”在同一个空间里形成了叠加。“时空折叠”的后果是,在宏观上使得现代化“后发”社会,特别是成功汲取了全球化资源的“后发”社会通过对外来系统的片段移植,同样具有了“时空分离”能力和反向进行“脱嵌”的传播能力,进而形成现代性的“多中心特征”和“双向脱嵌”的社会张力。在微观上,“时空折叠”使得现代化“后发”社会的人群同时面对着历史悠久的原生系统记忆和新生的外来系统记忆,催生了社会不同群体内的观念分化,最终导致类似“北京折叠”那样共同占据集体记忆,但在时间里此消彼长、分享空间的记忆割裂。投射到文化主体性层面,就形成了本文所说的社会观念的“群内区隔”及其强化。
具体而言,在全球化的单中心阶段,来自西方的社会系统片段,从西方“脱嵌”并植入到非西方的社会系统之中,完成了单向度的“时空分离”。在整合的过程中,其原生“制度时间”的结构层不会消失,而是被新“制度时间”的结构层遮盖。一旦新的社会系统在规则与资源上成功地积蓄了足够的势能,原生“制度时间”及其载体深层“记忆痕迹”就总是会试图上升,成为和当年外来社会系统一样的主体不在场的新结构,具有同样的“时空分离”和“双向脱嵌”的集体意识。此时,被外来现代系统所定义和发现的原生的、传统的社会系统,经过结构化重新定义了自身和整个世界,并把外来系统重新发现和定义为远方的原生传统。这个过程体现了原生性与现代性的相互定义和现代性的多中心、多主体流动特征,前文提到的中国的崛起和实质性系统输出的能力就是典型案例。
此外,对不同世代的群体,时空折叠带来的记忆组合呈现出不同的人群权重搭配。“60后”“70后”“80后”“90后”对于家、国、世界的认知以及对文化主体性的理解是高度差异化的。这种分化表现为同质性的社会群体却会对同一件事物、同一个过程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同世代的社会群体也会有类似的观念鸿沟。以上因素相互掺杂互动,进一步形成社会观念的分裂对峙。
“群内区隔”的微观机制:媒体、关系和剧场
要构成对社会群体在文化主体性观念方面较为普遍的割裂以及强化,则离不开互联网新媒体的信息强化语境。
(一)互联网新媒体的“信息负压”
当代中国互联网新媒体的两大信息特征在个体层面催生并不断强化着互联网观念的“群内区隔”。第一大特征是互联网新媒体的信息高通量,指的是个体获取的信息流量大、更新速度快。第二大特征是互联网新媒体的信息自选择。公众可以选择使自己愉悦的内容,但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封闭信息空间之中,形成桑斯坦所说的“信息茧房”。这两大特征最终形成了社会观念体系中的“信息负压”效应。“茧房”彼此间相互挤压对峙,并向外输出信息以试图同化更多的人群,最后以“信息负压”的形式构成社会群体的内部张力。而“茧房”内部的公众逐步被自己所选择的信息遮蔽,慢慢丧失反思能力与动机,最终导致“群体极化”,即团体成员一开始有某些观念偏向,在群体讨论后会进一步强化偏向甚至形成极端的观点。
(二)互联网新媒体的“关系剧场”
除此之外,互联网新媒体和关系网络的嵌合形成了具有特定时空和关系特征的虚拟空间——“关系剧场”,加剧了观念分裂。
(1)剧场的时空特征——“强化表演”
具体表现为在场的时空分离性和延续性。前者指的是在社交平台上,人们既可以进行实时互动,又可以通过调整信息传递的节奏来改变互动的时空分布。它使得各类行动者(例如“群主”“潜水者”)在剧场中既可以对自己的言行深思熟虑,又可以通过各类方法使社交空间变得更具有戈夫曼所说的“表演性”,进而加剧观念对峙。而在场的时空延续性指的是网络上的互动会随着“群”的存在而持续不断,它使得行动者在表演的过程中的观念必须始终如一,否则或失去面子,或失去他人的信任,而信任是戈夫曼提出的表演行为的前提与核心。基于此,社交媒体中人们所表演出的观念执着和对峙甚至比真实生活中更为激烈和持久。
(2)剧场的关系特征——“强义务”在场
大量的社会义务形成了新媒体的两个关系特征,使得人们形成一种“强义务”在场。第一个特征是陌生人的快速强关系。即便是素未谋面的人,例如“博主”和“粉丝”,在公开场合的社会关联一旦建立起来,就因信息互动的持续性和全天候而形成强关系,而不需要现实生活中长期的互动培育。第二个特征是熟人的退出压力。在社交媒体上,在知晓彼此身份的情况下长期“潜水”,很快就会面临同侪压力。“拉黑”甚至退“群”更是一种艰难的决定。这些举动会被解读为对熟人特别是“群主”或邀约者的友谊和信任的背叛。
显然,“强化表演”和“强义务”在场,会使得“关系剧场”中的主体不得不长期坚持自我观念并加以巩固维护,最终形成互联网新媒体的平台“规训”。我们以微信为例,来描绘“规训”的方式。首先,人们可通过微信相互设置对方的查阅权限和建“群”等方式来形成各类私密、半私密或公开的前台,完成对虚拟空间的分配。在这种强制序列中,参与者不断被分类并获得了在网络空间中的不同定位。其次,再来看话题节奏的控制。“微信”也完全可以实现福柯总结出的“规训”三部曲:对活动节奏的安排,对日常事务的强制确定和周期调节,让个体在生产(话语)过程中被形塑为“规训”客体。再次,从创生活动的时间组织来看,“微信”平台能够如同监狱组织放风一样,通过发“红包”、统一“点赞”等近乎全员参与的形式,以连续活动的序列化让个人的时间变成一种集体的、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并指向一个稳定的活动终点。最后来看力量的编构。经过这样的“规训”,在“微信”群中,个体成为福柯所谓的经过精确命令系统的力量组合所能摆布、移动和构建的要素。例如,“微信”群中看似没有公开发布的纪律,但实际上在冒犯性的语言后,“群主”或“骨干”会通过施加微妙的控制进行惩罚,从轻微的尴尬“表情包”、到语言劝诫、再到踢出群。这一过程使得社交平台上的所有人实质上都处于一种永远可见的福柯引述的“完美圆形监狱”状态。
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对峙性观念的此起彼伏,让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上的时间和空间获得了线性的方向和话语活动的意义,也让参与者各自获得了自己的社会空间位置,并为维持这种意义而乐此不疲。也因此,观念的“割席”,“群内”的“区隔”,实际上已从人际交往中的观念碰撞,内化和升华为一种经过惯习化后的个体“时空分离”的自我存在载体,是自我建构的定期与不定期组合的生活洗礼方式。每个人的异质性细节恰恰构成了“群”中的自我,并必须通过观念“割席”而维持下去。这个时候,制造区隔和协调观念分裂一样,都成为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上人的存在的特征。人们在异见中争论,但也在异见中达成社会结构的彼此判定。因此,社会结构形成观念、行动的舞台,同时又被观念和行动所结构化与定义。“群内区隔”遂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熵增式的均衡——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在自我的牢笼中不可避免地朝观念对峙的方向走去。
讨论和结语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时空折叠”理论跳出中国的价值和“群内区隔”这一互联网现象在现实社会的扩散。
“时空折叠”现象并非仅局限于当代中国,2020年美国社会也因政治偏向而产生严重的观念分裂。其中的案例包括围绕时任总统特朗普、美国大选和“Black Lives Matter”(即“黑人命也是命运动”)等热点人物、事件产生的争论。实际上,当代美国的观念分裂的宏观背景可以理解为美式中产家庭的记忆折叠,这是二战后的美国记忆对今日城市空心化、产业衰退、政治正确愈演愈烈的“时空叠加”。从这个角度,本文提出的“时空折叠”或可在抽离出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后仍具有理论解释力和一般性价值。
“群内区隔”是否已经扩散到网络之外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为此,本文使用非互联网数据来进行统计检验,我们发现,“中西VS.西医”之争,不仅在互联网中形成了“群内区隔”,而且在线下现实社会中也在发酵,打破了阶层与观念之间的对应。不过,互联网空间中“洋节VS.土节”和“计划VS.市场”的群内区隔并没有规模性、实质性地弥散传播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并影响阶层结构。因此,网络上与此相关的看似撕裂的声音,或许并未真正造成社会的撕裂。尽管“群内区隔”或许尚未全面、实质性地影响现实社会互动,但如果不加引导纾解,也可能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消极的后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体心态的极端化。观念对峙容易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群体中对持有不同观念的人形成一种简单化和极端化的失望甚至敌视、鄙视的态度。
第二,社会撕裂的弥散化。互联网上的个体极端化心态不但会在虚拟空间中不断蔓延,而且会向现实社会互动中延伸。这一方面会让互联网公共话语出现裂痕,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现实社会中思潮的高度情绪化和对立公开化。
第三,交往结构的封闭化。观念分裂,特别是线下的“群内区隔”会对中国传统由家庭、亲属、朋友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造成一定的改变。新的“差序格局”将是混合关系网络和观念同质性的梯次结构。在关系的束缚下,“道不同不相为谋”式的自我隔离可能在一定时段内出现。这样一来,观念“割席”将会使社会交往结构进一步封闭化。
第四,意识形态的隐喻化。观念之争的背后潜藏着意识形态的倾向和潜移默化。互联网空间中观念的多元化和差异化是一个健康社会和健康互联网空间文化繁荣与百花齐放的表现。但如果观念形成强烈的难以兼容的对峙、分裂甚至缠斗,此时的“群内区隔”就会成为社会治理特别是互联网治理的暗面,需要决策者和治理者发出坚定宽厚的主流声音,让网络上无谓的争论减弱,让触及治理根基的互联网话语具有明确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