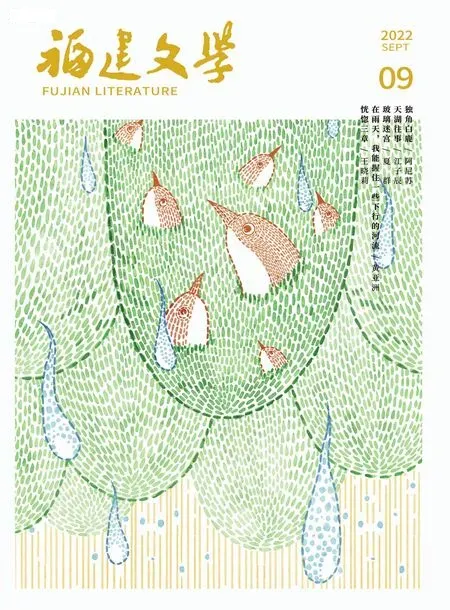《闽韵乡风》的地理文学书写
2022-10-23苏少伟
苏少伟
地理环境、地理空间,是作家们审美视野、文学视界的基础性的生成背景;而地理文化、地理现象则更为深刻,对作家的深层意识结构的影响更显著,它是一种多元素的综合作用,包括传统文化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历史、风俗、方言等)。由此可言,“地理”,显性地构成了作家们的创作因子。具体到八闽大地,它蕴含着丰富的地理信息、地理文化,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地理环境,相似又存异的地理空间,丰富而又精致的地理文化,这些引起了很多作家的注意。近些年来,在关注八闽大地的闽籍作家中,林彬是较为出色的一位。他的散文集《闽韵乡风》对闽地的“地理性”进行了综合浓缩,以文学性的话语将闽地的典型风格呈现出来,建构了闽地的地理文化特征。
地理文学书写的一个要点是文本中的语言、材料,需要从生活、历史中去发掘。鲜活的生活图景、活泼的历史感受,构成了作家个人体验中的两个活跃因素。这就是说,对很多地理文学书写来讲,站在当代生活角度省思,从历史厚重感中挖掘地理信息,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叙事方法。《闽韵乡风》也有这方面的特点,它的叙述内容、呈现方式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当代体验感和深厚的历史情怀。这两种因素的获得,首要是借重于丰富的历史文献,并以此为叙述的基点,来铺陈对闽地的观察、书写。
事实上,闽省历经千百年岁月,积累了厚实的典章文献。舆地、民俗、工艺、饮食、建筑……不一而足。要对这些“国故”做出整理、进行呈现,首先靠的是遍览相关材料。这在《闽韵乡风》中具有鲜明的体现,它的内容涵盖了闽地的名山武夷山、戴云山、太姥山、冠豸山等,名江闽江、晋江、九龙江等,文化事业如方言、诗歌、绘画、工艺、刻书、菜肴,等等。在对这些叙事对象的呈现中,作家援引了丰富的历史素材进行加工。以“漫说泉州之‘多’”这一章节为剖析对象,我们见到了一种多角度、丰富的呈现:
泉州古建筑中最有地方特色的是泉州民居建筑,尤其是贵族、官僚、富豪、士大夫阶层中的文人和画家,他们的宅第规模可观,形式讲究,其造型、格局、技艺、用材等都蕴含着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气质。其中,有三开间或五开间红砖白石双坡曲燕尾脊的汉式古大厝,有“手巾寮”的纵向住宅,有骑楼式的商住合一的建筑,还有与山村环境十分协调的“吊脚楼”(木楼),就地取材,十分简朴,却独具风格。还有一种是外围护有高大坚固防御墙体,适应大家族集居特殊形式的土楼建筑。中西合璧的住宅称“洋楼、番仔楼”。千百年来,民风民俗的传承衍化,使泉州民居建筑自成一派天然风韵。
短短的文字,对泉州的民居建筑进行了一番有声有色的介绍,注重历史传承、历史之变的同时,也抓住了它的特点,显示了泉州民居的独一价值。其实,在论述泉州的“多”时,《闽韵乡风》还聚焦了它的“小八景”、“十八景”、南音、百戏、木雕、彩塑等,涉及社会、历史生活中的多个方面,显示出异常的丰富性。余者,如福州的“脉”、厦门的“开”、漳州的“精神”,漫说“八姓入闽”、方言、诗歌、绘画、工艺、刻书、菜肴等,均带有这种叙事倾向。通概而言,《闽韵乡风》的全部文本内容都明显具备这一种写作特色。也基于此,我们说《闽韵乡风》的内容多且实、繁且精,材料基础扎实。在多方面的叙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作家对多样态生活的接受和开放性视界的呈现。
从丰富的历史文献里,《闽韵乡风》还生发出一个非常显性的特点:识见,即不黏着于材料本身,而从历史材料中生出自己的见解,从而使材料逻辑化。说到这种识见,《闽韵乡风》一书经常以一个字来捕获各地的独特性,把住了一乡一地最核心的精神内涵。譬如福州是“脉”,厦门是“开”,嵩口是“境”,双溪是“慧”……这种历史识见,是本书地理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价值。
看一看《闽韵乡风》是如何有识见性地凝练、挖掘出鼓浪屿的独特之处。在“漫说鼓浪屿之‘聚’”时,文本道出鼓浪屿的生成乃是“聚”的力量结果:
“聚落”文化的独特呈现——“更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为鼓浪屿贡献了新颖独特的‘聚落’文化元素,最终促成了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面貌,这方面集中体现在从华侨洋楼宅院的演进变化,最终产生独特的厦门装饰风格建筑。”
“聚合”文化的独到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鼓浪屿在整体上是以‘聚落’文化的形态展示在世人面前,那么鼓浪屿在微观上则以‘聚合’文化的形态供世人欣赏。”
“聚荟”文化的独辟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讲,鼓浪屿可以说是一个百花汇聚的园林,是中西合璧式园林‘聚荟’文化的呈现。”
“聚声”文化的独一呈现——“为此,鼓浪屿天然的‘聚声’环境和后天形成的独有的音乐文化底蕴,成就了鼓浪屿‘琴岛’‘音乐之岛’的雅称。”
“聚心”文化的独树呈现——“这种魅力、气质是在鼓浪屿特有的人文生态环境中形成的,也只有这种独树一帜的人文生态环境才能铸就别有风韵的鼓浪屿文化。”
这些从历史材料中凝练出的理性认识,丰富了我们的认知。所以,我们说《闽韵乡风》的历史感、生活性是十分明白的。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地理文学书写也非常注重语言的独具匠心的运用,语言部件、语言表达是地理文学书写的“外壳”。“审美对象化”这个理论研究式的表述,从一定程度上说,也包含着地理文学语言的独特运用。
语言,灵动地决定了作家的地理创作特色、文学含义、艺术高度。具体到《闽韵乡风》,它将个人的语言习惯、文化气质,与闽地丰富的材料进行有效融合。可以说,论到“语言”,触及的就是《闽韵乡风》的鲜明的文本特点。有三种语言风格深刻地体现在这本书中:精练、整饬、细密。
论“精练”,一段时间以来的闽地地理文学书写,似乎均不及《闽韵乡风》。这个文本,全篇都重在以精练的词汇(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字)来抓住一地的地理个性、一地的文化精髓。就以“漫说武夷山”这个篇章为例,武夷山是有代表性的,因为武夷山之美、武夷山之韵,闽地的人大多眼见耳闻,但能对之进行概括、提炼,而又提炼到何种程度,大概也是作家们的一个写作挑战。在这方面,《闽韵乡风》详细地提炼出武夷山的几个“然”。它先讲出武夷山的地形、地势、关口等“自然”,此为介绍自然地理风光:
东坡舒缓,有层级地形发育;西坡陡峻,断崖显著。在武夷山脉中有许多与山脉走向相直交或斜交的垭口,古称“关”“隘”“口”,是重要的交通通道和军事要冲,如浦城与江山之间的枫岭关、武夷山市与铅山之间的分水关、光泽与资溪之间的铁牛关、建宁与广昌之间的甘家隘、长汀与瑞金之间的古城口和武平与寻乌之间的树岩隘等。
武夷山这种“简单”的地理景观背后,是一种深刻的“地理精神”。因此,《闽韵乡风》继续发挥出武夷山的另外几个“然”:傲然、沛然、天然、悠然、肃然。“傲然”这一点,主要讲出武夷山“傲”的缘由:无诸、朱熹,以及吟咏武夷的历代文人,为武夷山增加了文化底蕴的“傲气”——“历代文人骚客偏爱武夷山的情致总是跃然于笔端,流传于山水之间,不仅给武夷山留下了一份份弥足珍贵的瑰丽篇章,而且使武夷山汇集的众多之美更加‘傲然’于世。”
“漫说武夷山”的最后点出了武夷山的“肃然”,详细介绍了武夷是儒释道的“三教名山”,以此增添“肃然”的气氛,足见武夷山的历史文化之厚重。至此,我们看到的“自然、傲然、沛然、天然、悠然、肃然”,都是以简洁精练的词汇对一个地方(武夷山)做整体上的价值提炼,并恰当地抓住了其社会、历史、生活寄寓在地理上的精髓。
在《闽韵乡风》中,这种写作风格很强烈,很容易再现。如,莆田的“化”是“兴化而名”“教化而厚”“神化而安”“文化而润”“造化而达”;嵩口之“境”是一种丰富的“场境”“语境”“化境”……这些都是精练的词汇表达,都有简洁明了的特点。然而,再细细品味,我们还可以看出作者对一种语言习惯的偏好,即擅长运用整饬的语汇结构来进行表述。
其实,这种语言风格并不是突然出现,作者的上一本作品《脉动乡土福州》中就已显露出他对这种语言结构的熟练运用。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水脉”闽江为赞叹对象时,特别强调了它“之于福州是‘源远流长’的”“之于福州是‘生生不息’的”“之于福州是‘母爱绵绵’的”“之于福州是‘广泽福祉’的”“之于福州是‘文化使命’的”;“文脉”这一章中说三坊七巷“神”之所在时,指出它具有“神明的文脉”“神奇的文化”“神妙的文物”“神韵的文教”“神采的文豪”“神往的文雅”“神品的文墨”……
《闽韵乡风》是对这种语言风格的继续深化。我们可认为,这种整饬的话语结构是一种有意为之且充满审美个性的文学行为。在遣词造句之间,整齐的句式之用,构造出浩荡的文气,也体现出多重的文字张力、情感张力。
在精练、整饬的语言风格之下,《闽韵乡风》没有使人形成一种抽象甚至缥缈的阅读观感,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文本还有一个特别的语言建构手段——“细密”,即反复吟咏、多重论述,造成一种绵密、优美的表达效果。仍以“漫说武夷山”中的“悠然”这一点为例:
人坐筏上,全方位地沉浸在碧水丹山之中,无噪音、无污染,抬头可见山景,俯首可观水色,侧耳能听溪声,伸手能触清波,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刚柔相济,悄然间就会生出“悠然见南山”的憧憬与梦幻。坐筏观山,极目皆图画,丹山、碧水、绿树、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呈现出武夷山大自然五彩缤纷的色彩美。沿途看到奇峰相叠、嵌空而立,那高低相错的山峦,如旌旗招展,那气势磅礴的岩峰,如万马奔腾,展示了大自然中极富韵味的参差美……
短短文字中,就有细致的景观铺陈、细腻的心理感受、细微的景物辨别,更写出了山、水、石各自的特点。其文学审美趣味,极素雅、极自然,整体上看来又展露出强烈的文学艺术色彩:凝练、传神,时而雄浑,时而又冲淡。所以,我们阅读后,能得到一种细腻的审美感受。
通篇而言,《闽韵乡风》以独特的语言系统,精细地呈现了闽地的百态生活,挖掘了闽地的千年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形塑了闽地的地方个性,让我们品味到了闽地的乡土之美好、历史之厚重和文化之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