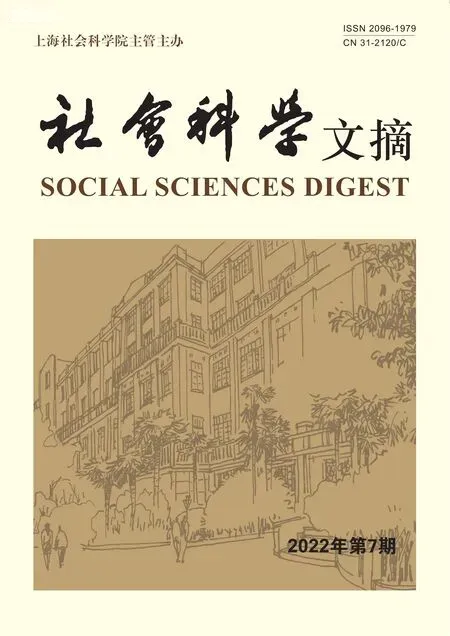规划中国、制度中国与真实中国:发展与治理的政治逻辑
2022-10-22张树平
文/张树平
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历史政治学视野中的发展与治理问题
若从古今之变的视角来看,传统中国或者古典中国在国家形态上呈现为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治理型国家”,即“传统治理型国家”。围绕着政治主体与政治制度之关系,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在平陂往复的历史循环和王朝兴替中展开传统国家治理的实践历程,这种实践既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留下了若干经验和启示,又留下了若干重要的治理困局需要现代政治加以彻底解决。作为“传统治理型国家”,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留给后世最大的警示在于,“以治理求治理终不得治理”,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欲求解决政治问题,是不能跳出“王朝周期率”的。
自近代以降,包括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发展问题的介入,彻底改变了传统治理型国家的运转轨迹,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程。一切现代国家建设方案归根结底是以制度为表征的现代国家治理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发展之间的互动问题。自近代以来,正是这种互动产生了中国的现代性诉求,现代性诉求产生了解放诉求,解放诉求产生了革命诉求。当针对传统国家形态与传统制度形态之突破与解放的方向指向现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个政治逻辑就开始发生,这就是“向解放寻求现代”。
解放必须由革命行动来完成,自近代中国以来,革命浪潮此起彼伏、新旧相替,种种不同的革命主张和革命行动分化合流,最终逐渐汇集为两种主要的革命:那就是中国国民党所主张的以“民国”为目标的民主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以“人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民主革命。历史将这种前后相续的革命运动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定性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将“解放”放在革命的首要位置,并且确立了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类型发展,确立了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到个体解放的过程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向解放寻求现代”的政治逻辑中诞生的。
从发展与治理到规划与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年来,围绕着发展与治理这两大主题展开的现代国家建设先后相续地形成了“向解放寻求现代”“向发展寻求解放”“向治理寻求发展”的政治逻辑。在现代国家建设框架内,由发展主题衍生出国家的规划体系建设,由治理主题衍生出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两大战略任务。73年来中国国家建设历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政治形态,深刻规定着这两大战略的实施形态及其相互关系。
第一,解放型政治形态下的“全能型计划”与第一波国家制度建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但却绝非是截断历史众流的产物。新国家形态是前后相续的革命的产物,就革命指向的新国家形态而言,则以“解放型政治”为基本特征,新中国前三十年可以被视为“解放型政治形态”的延续,此一阶段中国满怀信心地推进其规模宏大的发展计划。“解放型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既然呈现为一种“全能主义”国家,“解放型政治形态”下的国家规划就不能不呈现为一种“全能型计划”。此一阶段的国家计划一方面可以在资源贫薄条件下完成难以想象的重大生产力布局和项目建设,另一方面也因为“全能型计划”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不能不受到政治运动的条件和政治气候转移的影响而削弱其计划的连贯性。
国家制度体系建设在此一阶段中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度建设的第一波——即立国制度的建设。“解放型政治形态”下的国家制度建设,重在确立新生国家之规模与大体。现代中国国体、政体和国家性质的确立,都依赖于立国制度建设。我们后来称之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这一波制度建设的成果;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之奠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成果。不过,从制度与规划的关系来说,此一时期制度建设与规划建设呈现一种较为疏离的状态。
第二,发展型政治形态下的“中心规划”与第二波国家制度建设。改革开放盘活了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打通了现代中国政治发展逻辑中滞碍不通的关节点,既接续了革命和解放的传统,又将这种传统导向或者折向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之转折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开始于对前三十年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而成功于“向发展寻求解放”这一政治逻辑的生成。发展的本质是以“生产力解放”为核心的经济解放,“向发展寻求解放”,亦即向经济解放寻求政治解放,或者说将政治解放奠基于经济解放的基础之上,由此形成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中国“发展型国家”政治形态。
这一时期的国家规划体系发生了若干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在“发展型政治”形态下,国家规划体现为一种“中心规划”的形式,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布局规划,从国家层面到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各级各类规划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此一时期的国家规划,其出发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此来布局相关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经济建设是触发点,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客观地来讲,“中心规划”有力地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另一方面,这种规划形态不能不造成事实上的“多中心化”——从地方发展规划到部门专项规划各自为政、“自我循环”的现象,这最终将损害国家的整体规划能力。自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规划体制改革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国家规划“体系化”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此一时期在国家制度建设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1992年南方谈话等,已经成为指导现代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不朽篇章。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建设战略指导下,现代中国进行了第二波国家制度建设。这一波制度建设与第一波立国制度建设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既继承了立国制度的基本制度框架,又通过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领域大量的制度和法律建设、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在制度建设中引入主体行为动机考量,特别是通过容纳经济、社会、政治主体的利益取向而将制度的有效运行建筑于人性的现实基础之上。通过第二波制度建设,第一波立国制度也逐渐被盘活。从此一轮制度建设的重点来说,前期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领域以及与此相关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随着21世纪“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也逐渐加速。根据此一轮制度建设和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表现形式,我们将第二波制度建设称之为“关联性”制度建设。在“向发展寻求解放”的政治逻辑规定下,国家规划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国家制度建设服务于国家规划能力建设,因此,此一时期规划体系建设与制度体系建设的关系侧重于以制度体系建设支撑规划体系建设。
第三,“基于发展的新治理型国家”形态下的“全面规划”与第三波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迅速形成了“向治理寻求发展”的国家建设逻辑,中国改革的协同性、系统性、关联性极大增强,中国超越“发展型国家”的未来之路呼之欲出:那就是——超越“发展型国家”,走向“基于发展的新治理型国家”。从大历史的视角看,这种“新治理型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呈现出一种“复归”和超越的双重取向,亦即同时存在对传统治理型国家的某种借鉴与对传统国家的现代超越。
在“向治理寻求发展”的政治逻辑下,包括人的发展在内的国家全面发展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国家全面发展的持久动力。在“向治理寻求发展”的政治逻辑下生成的“基于发展的新治理型国家”形态,决定了国家规划在形态上必须是“全面规划”,国家制度建设在形态上必须是“全面制度”建设,从而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国家规划必须实现从“中心规划”向“全面规划”的形态演进,国家制度建设必须实现从“重点”或“相关”制度建设向全面制度建设的战略演进。
从实践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包括“多规合一”改革在内的国家规划体制改革进入顶层设计和国家推动期。此一时期国家规划体制改革聚焦于发挥国家规划特别是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国家规划同国家战略、国家政策的关联性、整体性不断增强。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波”制度建设发生于此一时期,并呈现为“全面制度”建设形态。“向治理寻求发展”的政治逻辑决定了“第三波”制度建设的战略、重点和特征:此一轮制度建设重在实现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建设走向绵密化和体系化,“制度间性”成为与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考量,制度建设的主动性、自主性、系统性不断增强。除经济制度建设之外,制度建设遍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党的建设制度、党的领导制度等国家治理的全领域。
此一时期国家规划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亦发生了深刻调整,二者之间呈现一种相互支持同时相互约束的双重双向关系——国家规划作为一种政治行为逐步被纳入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相关制度和法律对于国家规划行为既是一种支撑,也是一种约束;同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发展被纳入绵密的规划网络之中,上述各领域制度与法治建设也通过国家规划的方式得以推进,这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建设和迈向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选择。
规划中国、制度中国与真实中国
发展和治理是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两大主题,由此决定了国家规划行动与国家制度建设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70余年来中国国家建设政治逻辑的转换,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治形态的演转,因而也决定了不同政治形态下国家规划形态和国家制度建设形态的演转,即从“全能型计划”到“中心规划”再到“全面规划”的三种国家规划形态,从“立国制度”到“关联性制度”再到“全面制度”建设的三波国家制度建设形态的演化和转进。时至今日,无论是国家规划还是国家制度都烙上了与“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相关的“全面”建设的时代印记,“全面”意味着全覆盖、全领域、全链条、全流程。因此,当下中国国家规划行动与国家制度建设对中国发展与治理的影响就不再是局域的,而是全方位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规划中国”与“制度中国”的概念表达由国家规划和国家制度建设的形态转化所引起的“国家特征”。
如何理解规划中国与制度中国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从国家能力的视角看,国家的规划能力与制度能力同属国家政治能力的重要构成。在“基于发展的新治理型国家”形态下,国家规划能力是国家政治结构以及作为其制度表达的国家制度水平的函数。“制度中国”建设就是要解决国家制度水平的问题。“规划中国”与“制度中国”的深度交织与密切互动,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现实。二者的交织与互动共同提出了一个新的现实问题,那就是“真实中国”建设的时代命题。国家规划是否有效、如何评估、如何改进,首先依赖于真实信息的获取、整合和加工;国家制度是否有效、如何评价、如何完善,首先依赖于制度绩效的真实呈现和反馈。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基于发展的新治理型国家”建设时代,“真实中国”已经成为“规划中国”与“制度中国”深入发展的内在需求,成为“规划中国”与“制度中国”建设的前提。所谓“真实中国”,既包括信息的真实,这是最基本的层次;也包括逻辑的真实,比如中国全面发展的政治逻辑,这是一种需要理解、构建和展示的真实。只有在真实信息和真实逻辑基础上才能形成中国发展与治理的认知共识,也只有这种认知共识才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才是持续的和颠扑不破的,才能为国家规划与国家制度建设提供真实的数据基础、逻辑基础和认知基础。
党和国家如何发现和建构“真实中国”,并将“规划中国”和“制度中国”建筑于“真实中国”的基础之上,关键在于确保国家(特别是作为国家之领导者与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握和生成有关中国发展与治理的真实信息和真实逻辑。有效的国家规划与国家制度建设以“真实中国”的建构为前提,而“真实中国”的建构既需要国家规划能力和国家规划行动的支撑,也需要国家制度与法治建设的支撑,这就是“规划中国”“制度中国”与“真实中国”的辩证法。
在“向治理寻求发展”的政治逻辑和“基于发展的新治理型国家”形态下,国家规划形态和国家制度建设形态的更进一步发展使得“真实中国”建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前所未有地上升,这不仅关乎国家规划的有效性,而且关乎国家制度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因而在整体上关乎新时代中国发展与治理的有效性。而“真实中国”的呈现与建构,同样依托于国家与政党作为政治主体之规划体系与规划能力的现代化,依托于中国国家制度与法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规划中国”与“制度中国”的密切互动之外,“规划中国”“制度中国”与“真实中国”的互动将进一步增强,因为只有有效释读和有效建构“真实中国”的规划体系与完整、有效呈现和塑造“真实中国”的国家制度,才能为中国的发展与治理赢得真实信息与真实逻辑的基础,从而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