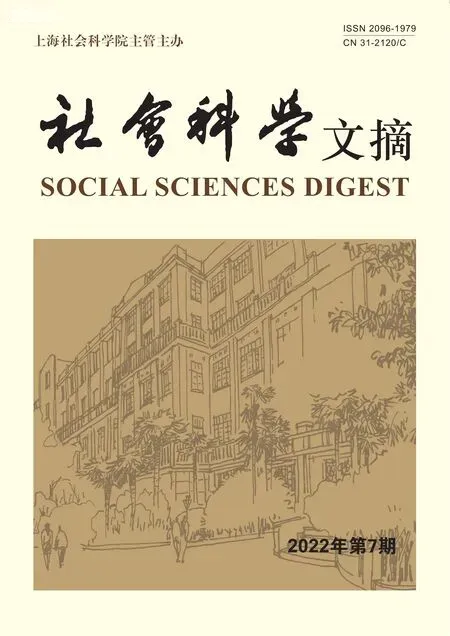身体法益的刑法保护
2022-08-30张明楷
文/张明楷
基本观点
与国外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相比,我国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比较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伤害的范围来说,只将器质性精神障碍认定为伤害,没有将反应性精神障碍认定为伤害;二是从伤害的程度来说,对轻伤的认定标准过高;三是在刑法没有规定暴行罪的立法例下,司法机关也不认定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导致故意伤害的未遂犯要么无罪,要么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等侵犯公法益的犯罪。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应当适当扩大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第一,故意伤害罪是针对人的身体的犯罪。“身体的安全是仅次于生命的安全的重大法益。”既然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就不能过于限制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第二,与侵犯财产罪相比,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不仅比较窄,而且处罚程度较轻,形成了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例如,使用暴力或者胁迫手段抢劫他人几十元或者几百元的财物,即使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也应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使用暴力造成被害人轻微伤,被害人花几十元或者几百元治疗费用的,反而不成立犯罪。第三,故意伤害罪的发案率高,因而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大,不宜限制其成立范围。“身体(与财产相并列)是最容易受攻击的法益。”行为人针对被害人一拳一脚可能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并不是行为人可以完全控制的。要预防轻伤害与重伤害,首先必须禁止造成轻微伤的行为乃至一切非法暴行,否则,对轻伤害与重伤害的预防效果就极为有限。第四,故意伤害罪一般属于暴力犯罪。“人们对无情的暴力犯罪的恐惧超过了其他任何形式的犯罪行为……暴力犯罪使人恐慌,也因此左右着公共政策。”在暴力伤害他人身体的案件频繁发生的环境中,国民不能安心地从事社会生活,因而也特别期待刑法保护个人的身体法益。
总之,在我国当下,虽然刑事立法不必提高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刑事司法也不应提升对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幅度,但需要适当扩大故意伤害罪的成立范围。首先,应当将故意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其次,应当将故意造成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最后,应当承认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
精神伤害
所谓精神伤害,是指使他人产生反应性精神障碍,如使他人神经衰弱、抑郁、长期处于不安的状态、长期处于惊恐的状态、产生应激反应障碍、长期失眠等。故意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是否成立故意伤害罪,首先取决于如何理解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
可以肯定的是,人的生理机能的健全是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问题是,如何理解人的生理机能(生理机能的健全性)与精神状态的健康(精神的健全性)的关系?
《德国刑法》第223条规定的普通伤害罪(伤害身体罪)的保护法益是否包括精神的健全性,存在争议。通说认为,普通伤害罪的保护法益及行为造成的伤害结果,仅限于身体的内容,而不包括精神的内容(身体症状限定说)。少数说则认为,普通伤害罪包括精神虐待(精神症状包含说)。《意大利刑法》第582条与《西班牙刑法》第147条明文规定伤害罪包括对“身体和精神”的伤害。《法国刑法》中广义的伤害罪包括了精神伤害。在奥地利,侵害健康不需要区分身体与精神;造成身体的被害与精神的被害,都属于对健康造成侵害。例如,职场中的骚扰行为,导致他人精神疲惫、产生重度睡眠障碍或者产生自杀念头的,都属于造成伤害,甚至可能构成重伤害。在瑞士,健康和疾病是相反的概念,人的健康包括身体的健康与精神的健康。《日本刑法》第204条没有明文规定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构成伤害罪,但“根据判例与通说,作为伤害内容的生理机能的障碍也包含精神机能的障碍”。英国《1861年侵犯人身犯罪法》规定了“身体伤害”的犯罪。“上议院确认,‘身体伤害’包括所有公认的精神伤害。”
综上可知,有的国家刑法明文规定了故意伤害包括精神伤害;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精神伤害的部分国家,虽然在德国只有少数说认为伤害包括精神伤害,但奥地利、瑞士、日本以及英国的通说与判例均认为伤害包括精神伤害。
在我国,《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没有将反应性精神障碍归入伤害。不过,这不是刑法的明文规定,只是司法上的判断。因此,即使不修改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刑事司法也可能将精神伤害包含在伤害概念中。
肉体伤害与精神伤害未必具有明显的界限。例如,在德国,“长期对被害人进行跟踪和骚扰,导致被害人情绪抑郁,无法入睡和集中注意力”的,被认定为身体伤害罪。德国的通说认为:“如果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进而造成了对其身体健康的消极影响,则应当肯定符合身体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例如,告知被害人令其感到极为恐惧的信息,持续通过电话恐吓、骚扰被害人或者制造被害人无法回避的、使其身体耗弱的敌对气氛,从而损害被害人身体健康的,均成立身体伤害罪。”完全可以认为,使被害人无法入睡和不能集中注意力,以及使被害人极为恐惧,是典型的精神伤害。既然如此,不如直接承认精神伤害也成立故意伤害罪。
我国有学者认为,精神伤害作为民事赔偿责任问题提出是可以的,但在刑法上,精神伤害并没有实质上损害身体健康,因而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然而,这一观点可能受到以下质疑。其一,精神伤害能够成为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当然也能成为刑法上的危害结果。因为严重的侵权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其二,精神伤害对人的危害并不轻于对人的肉体伤害。许多精神伤害的时间持续长,甚至基本上不可能或者难以逆转,因而比肉体上的伤害更为严重。其三,精神对肉体具有支配作用,对精神的伤害也会直接影响人的肉体行动,乃至会因为精神伤害而进一步形成肉体伤害。
承认精神伤害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解释论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笔者持否定回答。没有理由认为,“身体”与肉体(躯体)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可以认为,“身体”一词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身体是指肉体,广义的身体则包括精神在内。即使认为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是人的生理机能的健全性,其中的“生理”也不必然排除精神。并且,“精神机能的障碍,是基于大脑机能的障碍,在人的器官的机能障碍这一点上,可以说与通常的身体机能的障碍没有本质区别”。
承认精神伤害所遇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是否存在精神机能的障碍,以及行为与该障碍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确,因而认定起来是困难的”,在司法实务上,将精神伤害认定为对身体的伤害是否具有可行性。笔者认为具有可行性。其一,对精神伤害的鉴定并非不可能。例如,在国外,“医学能够令人满意地证实精神伤害的存在、它的严重程度及其后果”。国内早就有学者提出了精神伤害中的重伤害与轻伤害的鉴定标准。其二,如果在具体个案中不能鉴定出精神伤害程度及其因果关系,当然适用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其三,将故意造成他人精神伤害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并不意味着任何与精神伤害具有因果关系的行为均成立故意伤害罪,也不意味着对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也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轻微伤害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将伤害程度分为重伤、轻伤与轻微伤,其中的轻微伤是指达到一定程度的伤害但不构成轻伤的情形。《刑法》第234条第2款规定了重伤,人们似乎可以据此认为,《刑法》第234条第1款规定的是轻伤。可是,《刑法》第234条第1款并没有使用轻伤概念,其中的“伤害”,完全可能是单纯伤害或者普通伤害,而非《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所称的“轻伤”。换言之,没有理由认为,《刑法》第234条第2款规定的是重伤,第1款规定的就是轻伤,轻伤就是指《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的轻伤。因为这个推理并不符合逻辑。况且,《刑法》第234条第1款是故意伤害罪的基本法条,而不能简单地认为该款规定的就是轻伤。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的轻微伤,是达到一定程度的伤害。只不过轻微伤这个概念给一般国民的印象是,伤害很轻微因而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轻微伤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伤害,也不是不需要治疗就可以自然痊愈的轻微伤害。即使与其他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相比,也应将故意造成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例如,与《刑法》第247条规定的暴力取证罪相比,故意造成他人轻微伤的行为的不法程度更为严重。与国外的学说、判例认定的伤害相比,我国《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所规定的轻微伤并不轻微,而是比较严重。我国司法实践虽然没有将故意造成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但与此同时,司法解释已经将轻微伤作为认定一些犯罪的重要标准。这说明,轻微伤是提升不法程度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在法定刑最低刑为管制的立法例之下,将故意造成他人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也无不妥之处。
此外,《刑法》第236条与第237条将奸淫幼女“造成幼女伤害”、猥亵儿童“造成儿童伤害”的,规定为结果加重犯;其中的伤害显然不要求达到重伤程度。既然轻伤害可以成为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就有理由将故意造成他人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基本犯。
在暴力行为致一人轻微伤的场合,如果否认该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反而会导致对这种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适用更重的法定刑。倘若将暴力致一人轻微伤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则可以避免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在暴力行为致多人轻微伤的场合,如果否认该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会导致对这种行为均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也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身体法益。
伤害未遂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以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定罪量刑的判例。刑法理论对故意伤害罪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存在不同观点。笔者主张《刑法》第234条第1款存在可能构成犯罪的未遂犯。换言之,对轻伤害未遂但存在具体危险、情节严重的,也应以未遂犯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并没有采取主观主义立场,需要肯定未遂犯处罚的例外性。所以,必须实质性考察各种具体故意犯罪的未遂形态的可罚性:罪质严重的未遂应当以犯罪未遂论处,如故意杀人未遂、抢劫未遂、强奸未遂等;罪质一般的未遂,只有情节严重时,才能以犯罪未遂论处,如盗窃未遂、诈骗未遂等;罪质轻微的未遂不以犯罪论处,如非法侵入住宅未遂、侵犯通信自由未遂等。
与盗窃罪、诈骗罪相比,故意伤害罪的罪质更为严重。一方面,从总体上说,故意伤害罪的不法程度并不轻于盗窃罪、诈骗罪。另一方面,就侵犯个人法益犯罪的不法程度而言,故意伤害罪是仅次于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倘若让一般人在身受重伤与财产损失数额巨大之间选择,恐怕更多的人会选择后者。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仅处罚盗窃罪、诈骗罪的未遂犯,而不处罚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
我国刑法虽然没有将暴行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但不能一概认为我国刑法不处罚暴行,而应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了特殊的暴行罪。在与暴行罪的关联性上,承认故意轻伤的未遂犯,是完全协调一致的。易言之,仅处罚特定情形下的暴行罪,会导致处罚的不公平。如果要实现处罚的公平性,就必须将故意轻伤害且存在具体危险、情节严重的未遂犯认定为犯罪。
从近几年来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随意殴打他人没有造成轻伤的,大多会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导致处罚过于严厉。反之,如果承认故意轻伤的未遂犯,对行为以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处罚,同时适用未遂犯的规定,才更为合适。
将故意轻伤未遂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其实是将对个人法益的犯罪认定为对社会法益的犯罪。通过将某种行为认定为侵害公法益的犯罪来保护个人法益,并不是可行的路径。因为这种路径常常导致行为侵害数人的个人法益才成立犯罪,这便不利于保护公民的身体法益与其他个人法益。并且,这种做法必然侵害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利,也不利于附带民事诉讼。
或许有人认为,如果认为故意轻伤的未遂犯也成立犯罪,就明显扩大了处罚范围。然而,犯罪的成立范围并非越窄越好,而是越合理越好。从前面与盗窃未遂、诈骗未遂的比较可以看出,肯定故意轻伤的未遂犯,并没有明显地扩大处罚范围。如果只有造成了伤害结果才成立犯罪,就会导致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实施伤害行为,难以预防犯罪。肯定故意致人轻伤的未遂成立犯罪,则能有效地规制一般人的暴力行为,进而保护被害人的身体法益。
当然,主张对故意致人轻伤的未遂成立故意伤害罪,并非没有任何限定。成立故意轻伤的未遂犯,首先要求行为人所实施的客观行为足以给他人造成伤害结果(具体危险),其次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造成伤害结果的故意。
在具备上述要素的前提下,还要求未遂行为本身情节严重。在笔者看来,故意伤害他人未遂,除以重伤为目的的情形以外,具备下述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进而以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犯论处:(1)携带或者使用凶器或者其他危险工具伤害他人的;(2)使用毒药或者其他危险物质伤害他人的;(3)对被害人身体的重要部位(如头部、胸部、腹部)实施伤害行为的;(4)暴力行为强度大或者连续反复使用暴力的;(5)以阴险的袭击方式实施伤害行为的;(6)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伤害行为的;(7)多次对同一人实施伤害行为的;(8)行为具有造成重伤害的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