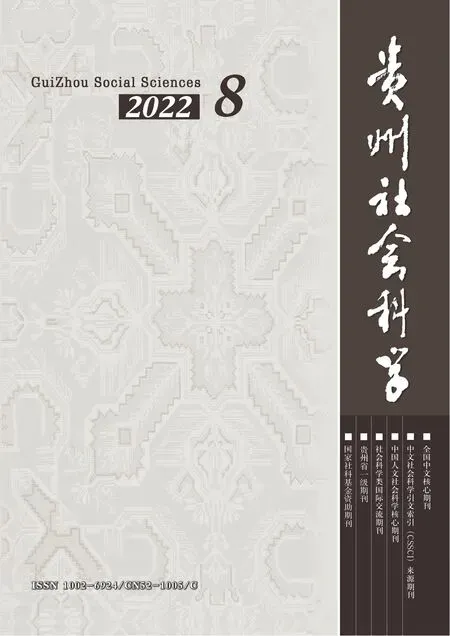《伊尹》入“道家者流”索解
2022-10-12郭泓志
郭泓志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伊尹》五十一篇”[1]1729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诸子略道家类的第一部。尽管此书已经亡佚,然据诸子书名往往与诸子本人相关(一如《孟子》《庄子》与孟子、庄子本人相关)的规律,《伊尹》亦当与伊尹本人有关。孟、庄本人各为儒、道两家大师,故《汉志》以《孟子》《庄子》入“儒家者流”“道家者流”自是无待多言。然古史传说中的伊尹乃夏末早商之际起于庖厨、佐汤灭夏、放逐太甲、以德治国的开国宰相,其时并无诸子百家,其事亦与以“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为“君人南面之术”[1]1732的道家有一定距离,那么,为何《伊尹》入“道家者流”?
扬榷而论,前人对此问题的讨论有两种思路:一是指认《伊尹》乃包含“治国用兵,取威定霸之术”[2]86的权谋之书,甚至是教人“以间谍欺诈取人”[3]的阴谋之书;二是据出土文献指认《伊尹》“具有浓厚的黄老思想”,伊尹天道化身的“帝师身份”普遍见于黄老文献[4]。此二种思路皆具一定合理性,然一则在《伊尹》性质的确认上尚存在抵牾,故需厘清辨析;二则重于内容分析,故在《汉志》分类标准和《伊尹》文体形式的探索上留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由于《伊尹》是《汉志》道家类的“排头书”[2]84,对《伊尹》性质的全面把握关乎今人对“道家”概念的分析和阐释,故《伊尹》入“道家者流”的原因仍值得系统考察和深入索解。
一、甲金史载与诸子作品中的伊尹形象
(一)甲金史载中的伊尹形象

历史记载中的伊尹有四种形象。第一,为汤间夏的间谍。《国语·晋语一》:“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7]250《古本竹书纪年》:“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8]14第二,商汤的佐臣。《尚书·君奭》:“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9]520《咸有一德》(1)《咸有一德》虽为伪古文《尚书》,然其中“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见于清华简《尹诰》,又见于《礼记》、郭店楚简及上博简《缁衣》,故此二句当为先秦文献。:“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9]257第三,放逐太甲的重臣。《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10]《国语》晋语四:“伊尹放大甲,而卒以为明王。”[7]347《尚书·太甲》(2)今见《尚书·太甲》三篇为伪古文《尚书》。诸多文献的征引保留了真古文《尚书·太甲》的只言片语,如“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礼记·表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缁衣》)、“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缁衣》)、“顾諟天之明命”(《大学》)、“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缁衣》,又见《孟子·公孙丑上、离娄上》《说苑·敬慎》)。中有伊尹对太甲的谆谆教诲。第四,废君自立的国王。《古本竹书纪年》:“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广弘明集》卷十一引《汲冢书》径直用“篡”来形容伊尹自立:“伊尹自篡立后,大甲潜出,亲杀伊尹而用其子。”[8]17概而言之,甲金史载中伊尹重臣、间谍、君王的三种形象,与道家并无多大关系。
(二)诸子作品中的伊尹形象
诸子作品虽大体继承了甲金史载中的伊尹形象,但在描述的侧重点上却有明显转移。诸子作品强调伊尹之贤,并以其事迹论证君主重贤的重要性。
孔子与子夏将伊尹塑造为商汤拣拔的贤者:“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速矣。”(《论语·颜渊》)[11]墨子则强调伊尹本是“天下之贱人”(《墨子·贵义》)[12]441:“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墨子·尚贤下》)[12]67-68为强调举人唯贤,墨子开始刻意强调伊尹贤者身份地位的低贱。
孟子坚决否认伊尹负鼎干汤的传说,并以伊尹为耕于有莘之野的处士。他通过对伊尹教汤的强调,塑造了伊尹崇高的王师形象:“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公孙丑下》)[16]281-282“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万章上》)[16]705
与孟子思路相反,韩非子以伊尹的“七十说”、干商汤为贤德仁义的表现:“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故伊尹以中国为乱,道为宰于汤;百里奚以秦为乱,道为虏于穆公。皆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辞卑辱,故谓之仁义。”(《难一》)[17]387在韩非子看来,贤臣的仁义在于心忧天下,然其心忧天下须以守礼尊君为前提;由于君主的主动求贤会损害君主的威严,故只需坐等伊尹等贤者到来。
概而论之,诸子书中之伊尹比甲金史载中多出“贱人”或“处士”的卑贱者形象,然此种形象却与道家关系不大。尽管如此,诸子书中的伊尹材料,却透露出两个重要讯息:其一,就内容方面而言,结合《孟子》中孟子对伊尹干汤的否认及疑为孟子所增伊尹自陈心迹的细节来看,诸子时代应当流传着不少生动具体乃至彼此抵牾的伊尹故事;其二,就形式方面而言,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往往会借用伊尹的古史传说来申说己意。而此两方面,皆与《汉志》“道家者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汉志》“道家”的内容特征及与《伊尹》之关联
(一)《汉志》诸子略道家类小序的“道家”特征
《汉志》道家类著录书目多已亡佚,故相形而论,《汉志》道家类小序要远比今见道家类书目更能从整体上反映《汉志》的“道家”观念。(3)《汉志》著录的道家著作,仅残存《太公》《筦子》《文子》《庄子》《鹖冠子》《列子》,及《说苑·敬慎》《孔子家语·观周》中疑属《黄帝铭》的几则材料。此外,今见传世文献中刘向、刘歆父子时已有的道家类著作仅有《老子河上公章句》及《老子指归》(残)。(参见孙显斌《东汉之前的道书叙录》,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五辑)故可资以分析其中“道家”概念的传世典籍未出以《老》《庄》《文》《列》为核心的传统范围。因此,仅据今见道家传世文献恐难以准确全面地把握《汉志》的“道家”概念。
就小序而言,“道家”非老、庄平列,“老”比“庄”更宜居于道家正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1]1732老子本人是“周守藏室之史”(《老子韩非列传》)[18]2589,可谓“出于史官”;《老子》一书,充满令人惊警的格言韵语,可谓“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强调“道”“啬”[19]155“大象”[19]87等核心理念之于治理的意义,可谓“秉要执本”;重视“虚”“静”等范畴之于个人修养的作用,可谓“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频频提到“天下”“圣人”“治国”,更说明它饱含“君人南面之术”。可见《汉志》道家小序更像是为《老子》量身定做。而小序中所称“绝去礼学,兼弃仁义”的“放者”,似指“退仁义,宾(摈)礼乐”(《天道》)[14]489-490的庄子学派。由是观之,《汉志》道家小序阐述的“道家”概念与《老子》思想更为切近。
班固《汉志》虽是东汉著作,然由于整体承袭刘向、刘歆父子确立的框架,故其中的“道家”概念实则反映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的思想。(4)《汉志》在大小序写作上极有可能以《七略》为基础进行增删。《汉志》序言中有一严重破例,即诗赋略无小序,设若班固出于整齐的需要对《汉志》各略类重新作序,则何故独弃诗赋略不顾?《汉志》道家类无班固“出”“入”之自注,可见对《七略》道家书目未有增删,故班固亦可径直采用刘歆道家类小序。退一步说,即便《汉志》道家类小序确实经过班固修饰,亦说明班固对小序的改动未溢出刘歆的框架。故《汉志》道家所收书目和小序,均可视作刘向、刘歆父子“道家”观念的反映。而刘向、刘歆父子对“道家”的理解也非独出机杼,其“道家”概念一是延续了《庄子·天下》篇对关尹、老聃学派“人皆取实,己独取虚”[14]1089的描述,二是继承了《论六家要旨》“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18]3969的道家观念,并在对二者进行综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中的外王色彩。因此,相比于《天下》篇与《论六家要旨》,刘向、刘歆父子之特色有二:一是在“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中,视“内圣”为手段、“外王”为目的,进而将清虚、贵柔、守雌、养身统摄于“君人南面之术”;二是在“圣人”与“隐士”的关系中,强化“圣人”在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继而将不利于君长统治的思想(似指“独与天地精神往来”[14]1091的庄子学派)斥为异端。
水在渠中流动,单位时间内流动的距离,叫做流速,它的单位是米/秒,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横断面水的体积,叫做流量,单位是米3/秒或公升/秒。若某渠观测地点的过水横断面积是1平方米,水每秒流动1米,则通过流量为1米3/秒(1米3/秒=1000公升/秒),通常称为“一个水”。
刘向、刘歆父子的此种外王学观念,自会体现于“道家”目次。今见文献中可见的伊尹故事,也正透露出此种“道家”的外王学观念。
(二)伊尹传说中的“道家”外王学色彩
尽管《伊尹》一书已经亡佚,具体细节无从得知,然如上所述,诸子时代应当流传着不少生动具体的伊尹故事。据诸子书名与诸子本人相关之原则,这些伊尹故事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伊尹》与“道家者流”的关系。
事实上,某些伊尹故事的确体现出君主以节制私欲的“内圣”手段达到平治天下目的的道家“外王”观念。《吕氏春秋·先己》有一则伊尹说商汤以“治身”来“取天下”的故事:“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20]69-70故事中的伊尹认为,“取天下”的前提是“身将先取”,据《吕氏春秋》的解说,“身将先取”即“啬其大宝”(高诱注云:“大宝,身也。”[20]70),即君主本人节制自己的小私小欲。
同样的思路复见于《吕氏春秋·本味》中伊尹说汤通过“成己”而“为天子”、通过“为天子”而享“至味”的故事:“汤得伊尹……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对而为乎?’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圣人之道要矣,岂越越多业哉!”[20]312-321故事中伊尹所举肉、鱼、菜各类食材需“为天子”才能获得,而“天子成”的前提在于行“在己”之“道”,即通过节制私欲、躬行仁义而“己成”,“己成”即“天下成”。
上举两则故事中的伊尹所以要求商汤节制个人私欲,其目的乃在于“取天下”。体现此种观念的伊尹传说又见于马王堆帛书《九主》及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等。易言之,上述故事中的伊尹,都不同程度地论及君主通过“治其身”之手段以成“天下治”之目的的观念,这就正符合君主以节制一己之小私小欲来平治天下的道家外王学。
(三)《伊尹》的“兵权谋”属性及与道家外王学之关系
尽管有称《吕氏春秋·先己》中伊尹数句“当是出于《伊尹》五十一篇之中”[21]的说法,亦有谓马王堆帛书《九主》为“《伊尹·九主》”[22]的判断,然大量伊尹传说与《伊尹》的关系仍难以确定。例如,古史系统及诸子系统中都有伊尹使用权谋乃至阴谋的传说,如《孙子兵法·用间》称“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业,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23]300-301,显是目伊尹为具有“上智”的间者;《孟子·告子下》谓“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16]892,此行为似可解作间谍的通风报信;更为直接的证据,是《说苑·权谋》录有伊尹在商汤灭夏前夜提出“请阻乏(之)贡职,以观夏动”[24]的策谋。那么,此类伊尹传说是否与《伊尹》有关?这就难以仅据《汉志》“道家”类小序判断,而需另辟蹊径。
值得注意的是,《汉志》中的班固自注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尽管《伊尹》已经亡佚,然班注却透露出《伊尹》在《七略》中兼具二重属性的重要讯息。《七略》与《汉志》将诸书分作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班固在兵书略兵权谋小计后标注“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1]1757,换言之,《伊尹》与同入“道家者流”的《太公》《管子》《鹖冠子》一样,在《七略》框架中兼具道书、兵书二重属性。此种目录分类上的二重性表明,《伊尹》不但具有节私欲以成王业的道家观念,甚至具有比节私欲以成王业更深更甚的外王思想。
首先,早在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编订《别录》和《七略》前,道家观念就往往被从权谋乃至阴谋方面进行理解,从而使与权谋相关的外王学内容为“道家”概念所涵摄。《韩非子·喻老》对《老子》第三十六章有一段解说:“越王入宦于吴,而观(劝)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17]170-171无论是勾践以“劝吴”而“弊吴”,还是晋君、知伯以“遗之”而“取之”,皆是以讨好的手段达到讨伐的目的,其权谋色彩毋庸赘言。《史记》将老子与韩非合传、将道家与法家并举的写法,也表明史公承认具有权谋乃至阴谋色彩的法家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有学理上的因袭关系。由于伊尹传说有明显的权谋色彩,而“道家”又往往被从权谋乃至阴谋角度进行解读,再辅以班注提供的《伊尹》于《七略》中亦属“兵权谋”的讯息,综合来看,指认《伊尹》因颇具权谋、阴谋的外王学内容而入“道家者流”,不失为一种合理推定。

最后,因重而省《伊尹》的“兵权谋”,在小序中体现出所收著述以道用兵的思想。《汉志》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兵权谋小序为“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1]1758,其特点在于以计算融贯形势、阴阳、技巧。而从《汉志》“兵形势”“兵阴阳”的小序来看,此二类正可视作道家哲学观念在用兵上的直接运用。
就兵权谋“兼形势”而言,《汉志》兵形势小序称“形势者,靁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1]1759,其中“后发而先至”“变化无常”皆与《老子》“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十四章)[19]31-32、“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第二十一章)[19]52、“道常无名”(三十二章)[19]81、“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四十一章)[19]113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兵权谋“包阴阳”而论,《汉志》兵阴阳小序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也”[1]1760,强调顺应自然之道以用兵。此小序中“顺时而发”与《论六家要旨》所述道家“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有法无法,因时为业”“圣人不朽,时变是守”[18]3969相合,“推刑德”与《鹖冠子》“纪以度数,宰以刑德”(《王鈇》)[15]181、“牧以刑德”(《泰鸿》)[15]219及同样兼有道书、兵书二重性的《管子》“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四时》)[26]相合,“假鬼神而为助”则与疑为《太公》中兵书的银雀山汉简《六韬》“大兵无创,与鬼神通”(见于传本《武韬·发启》)[25]113相合。可见,兵阴阳小序确与道家思想相通。其实,“阴阳”本身就与《老子》第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19]117及马王堆汉墓《黄老帛书》中屡屡提到的“阴阳”扣合。还需注意的是,以阴阳用兵的观念其来有自,《国语·越语下》范蠡对勾践即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后无阴蔽,先无阳察……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7]585,而《范蠡》二篇同《伊尹》一样正著录于《七略》兵书略兵权谋中。由是观之,包括《伊尹》《范蠡》在内的兵权谋著述在“包阴阳”方面都与道家有亲密联系。
可见,《汉志》兵权谋小序径直引用《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16]149可谓有理有据、毫不含糊。《汉志》兵权谋不到三十字的小序,十分精粹地揭示出兵权谋一类的二重属性:一方面,兵权谋是兵书略的集大成者,“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另一方面,兵权谋是道观念的生动实践,“先计而后战”,“道”“天”“地”“将”“法”[23]2-3五事并举。前者从形而下层面保证了用兵的“百战不殆”,后者从形而上层面保证了用兵的“师直为壮”;前者是精良的“武备”,后者是正义的“王官”。就此意义而言,《汉志》兵书略大序“王官之武备”[1]1762的表述,可谓是对兵权谋最好的注脚。因此,《伊尹》在《七略》中的兵权谋属性,便从目录学角度有力证明了佚著《伊尹》所应包含的以道用兵思想。
三、《汉志》“道家”的形式特征及与《伊尹》之关联
今见伊尹传说体现出节私欲以成王业的道家外王学理念,此正与《汉志》道家类小序体现出的以“外王”统摄“内圣”的“道家”内容特征相符。班固自注透露出的《伊尹》在《七略》中兼具“道家”和“兵权谋”两类属性的重要讯息,则从目录学角度证实了《伊尹》确有相当浓厚的外王学理念。故从内容方面来看,《伊尹》入“道家者流”,是因为它具有符合“道家”概念的内容特征。然而,仅从内容角度进行的把握尚不够全面,因为根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基本原理,《伊尹》及所属“道家”的内容特征必然要在形式方面有所体现。
(一)“说”:《伊尹》与《伊尹说》的呼应
翻检《汉志》,其中以“伊尹”为名的著作,除道家《伊尹》外,还有“小说家”之《伊尹说》。此种现象并非巧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伊尹》《鬻子》著录于“道家”,与之对应的《伊尹说》《鬻子说》著录于“小说家”;《黄帝四经》《黄帝铭》著录于道家,与之对应的《黄帝说》著录于小说家。可见,《汉志》道家与小说家间的确存在某种形式上的呼应。
那么,此种呼应关系该如何理解?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汉志》“小说家”兼具浅显性与故事性的形式特征。《汉志》“小说家”小序称“小说”为“街谈巷语,道听塗说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1745,故“小说家”在诸子略中的浅显性一望即知。有说法指出,此小序与《文选》注引桓谭《新论》“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27]的“小说家”定义“同条共贯,可以互相发明也”[28]。桓谭论“短书”,又见于《太平御览》所引《新论》之“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29]。由此可推知,“小说”一方面“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30],另一方面则颇具传奇性和故事性。
《汉志》“小说家”浅显性与故事性的形式特征,恰恰是“道家”支流的一个特点。“道家”尤其是“老系”道家尽管在思想内容上玄奥精深,但由于主要是为“君人”打造,曲高和寡,故往往因“没有大众的基础”而“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31];相反,“道家”支流却因其行气导引的日用之术和生动迂曲的寓言故事而具有更广泛的受众。曾有说法强调小说与“武帝时方士”的联系[32];现结合简帛材料来看,小说与方士的关联可进一步溯源至先秦时期,易言之,掌握道家行气导引之术的先秦方士也往往编造“小说”。
因此,方士就构成了“道家”“小说家”的中介环节。《汉志》“道家”“小说家”著述的呼应关系,一定程度上是方士兼通“道家”之术及“小说家”寓言这一现象的目录遗存。故《伊尹》入“道家者流”,可通过“小说家”有《伊尹说》与之对应而得以说明。
(二)“托”:《伊尹说》的“依托”手法
《伊尹》与《伊尹说》的近密,除见之于《汉志》“道家”与“小说家”著述称名的彼此呼应上,还体现于《伊尹说》所使用的依托手法上。《汉志》“小说家”类“《伊尹说》二十七篇”下有班固自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1]1744,说明班固业已辨认出《伊尹说》在形式上有“依托”的特征。
《汉志》著录诸书中,班注明确怀疑作人或作时的著作有《文子》《力牧》《盘盂》《大禹》《神农》《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封胡》《风后》《力牧》《鬼容区》,其中除《神农》入农家、《盘盂》及《大禹》入杂家外(5)杂家著述往往具有兼合包含道家在内之诸家的特点,且中有《吕氏春秋》《淮南内》《淮南外》等与道家关系颇近之著述。农家亦与道家关系密切,《庄子·山木》将“物物而不物于物”视作“神农、黄帝之法则”,便是神农、黄帝并举。,余者尽皆著录于“道家”“小说家”“兵阴阳”三类。有趣的是,班注在除《盘盂》《大禹》外的以上著作时皆使用“托”或“依托”字样,此现象既使上文揭橥的“道家”“兵权谋”“兵阴阳”的内容联系(6)“道家”“兵权谋”“兵阴阳”的内容联系除体现在上文所说各类小序中,还在《汉志》目次上有形式上的反映:一、“《伊尹》五十一篇”、“《鬻子》二十二篇”著录于道家,与之对应的“《伊尹说》二十八篇”、“《鬻子说》十九篇”著录于小说家;二、“《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著录于道家,与之对应的“《黄帝说》四十篇”著录于小说家、“《黄帝》十六篇”著录于兵阴阳;三、“《力牧》二十二篇”著录于道家,与之对应的“《力牧》十五篇”著录于兵阴阳,据班固自注,力牧是“黄帝臣”,而同样以“黄帝臣”之名为书名的“《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鬼容区》三篇”见载于兵阴阳;四、“《师旷》六篇”著录于小说家,与之同名的“《师旷》八篇”著录于兵阴阳。针对此种现象,有说法已注意到《汉志》小说家著作与道家、黄老、方士乃至道教的关系。可参见,蔡铁鹰《〈汉志〉“小说家”试释》,《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卢世华、楚永桥《黄老之学与〈汉志〉小说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有了形式上的依据,又使上文所说“道家”“小说家”的形式呼应得到进一步确认。
所谓“依托”,即藉他人之口道自己之语。此与我国重视历史的传统相关。《尚书》《国语》《左传》中说理者征引先王之迹、古人之训以立己意的做法,极大拓展了古人之言的意义。诸子出于立论或争鸣需要,在借古人之言以申一己之意的基础上,发展出以一己之意等同于古人之言的形式,从而形成“依托”手法。战国是个大“依托”的时代,《汉志》著录著述中也多有“依托”现象,但为班固所辨识者,除《神农》一部属“农家”外(7)神农与道家亦有密切关系。《庄子·山木》将“物物而不物于物”视作“神农、黄帝之法则”,《淮南子·修务》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皆以神农、黄帝并举。,余者皆属“道家”“小说家”“兵阴阳”,这说明,“道家”对“依托”的使用可谓轻车熟路、驾轻就熟,中如庄子学派甚至托之于动物、植物、影子乃至抽象概念来道己之语。由于他们之中很多人本不冀望受众相信他们所说为实,故而在“依托”的使用上显得从容烂漫、自由洒脱。因此,指认“依托”为道家的主要手法,可谓实至名归。故《伊尹说》“似依托也”[1]1744的手法,可为与之呼应的《伊尹》入“道家者流”之原因提供一有力旁证。
四、结语,兼论道家“阴谋说”
综上所述,《伊尹》弁于《汉志》道家类之首可从如下四方面得到解释:
一、甲金史载中的伊尹具有重臣、间谍、君王三种形象。其中重臣、间谍的形象对诸子系统中伊尹高士形象的塑造影响甚大。此为《伊尹》入“道家者流”的历史依据。
二、《汉书·艺文志》之“道家”概念具有浓厚的外王学特点,诸子系统中伊尹的某些传说,体现出道家节制君人私欲以成王霸之业的道家外王学理念。此为《伊尹》入“道家者流”的观念前提。
三、据班固自注,《伊尹》在《七略》中兼属“道家”“兵权谋”两类,“兵权谋”小序所概括“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的特点可与“道家”相结合。同样具有此种二重身份的《太公》《管子》皆有合道用兵的观念,故《伊尹》亦当有此“道家”外王学观念。此为《伊尹》入“道家者流”的内容原因。
四、班固谓与《伊尹》相呼应的《伊尹说》使用“依托”,《汉志》中班固辨识且注为“托”或“依托”的著述主要集中于“道家”“小说家”“兵阴阳”三类。“小说家”“兵阴阳”从《汉志》小序和目次两方面来看,均与“道家”相关。“依托”是道家的主要手法。故《伊尹说》用“托”,实乃《伊尹》入“道家者流”在形式上的反映。此为《伊尹》入“道家者流”的形式原因。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伊尹》的性质及道家“阴谋说”的问题。首先,尽管《老子》在后世被从权谋乃至阴谋角度进行理解[33],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子》本身就是阴谋书,王弼本《老子》三十六章的相互对待“绝非老子心怀叵测的表现,而是事物运动本身的辩证法”[34]。其次,“道家”重“谋”,此由《汉志》“道家”所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中含“《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1]1729一望即知,毋庸赘言。再次,“道家”主流并不推重“阴谋”,《国语·越语下》记载与道家关系较密的范蠡有谏言曰“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7]576,《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好黄帝、老子之术”的陈平曾对自己的一生发出“我多阴谋,则道家之所禁”的感慨[18]2491,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大经·顺道》明确提出“不阴谋”,则道家并不推重阴谋明矣。故佚著《伊尹》中或有阴谋之术,然不当占据是书之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