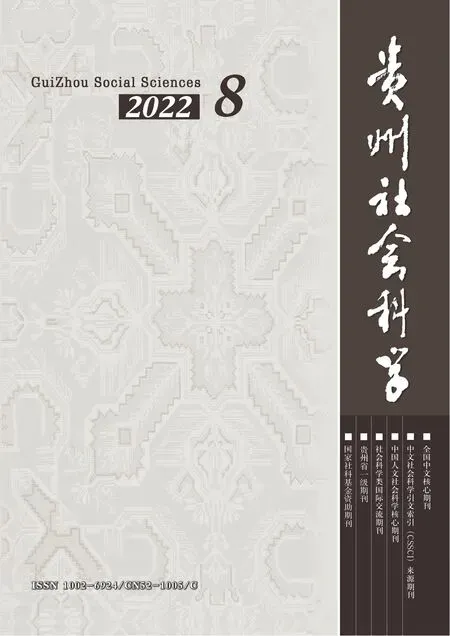西方犯罪史研究的视域与趋势
——以英国犯罪史为中心的学术史考察
2022-11-27许志强
许志强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西方犯罪史研究的兴起有其特殊的现实背景。“二战”之后,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相继掀起了大众文化研究热潮,受此影响,长期被忽视的底层社会、边缘群体及其日常生活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欧美国家普遍出现了亚文化抬头的现象,引起普遍忧惧。对此,学术界开始从历史维度上寻根溯源,以至于出现了集中研究犯罪、下层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前所未有的高涨局面”,并使这一领域成为“社会史研究中一朵盛开的花朵”。①
犯罪史研究在西方社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多方面的促因。首先,“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的法庭档案和地方文献逐步开放,并经历了系统的数字化处理,这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方便获取的新史料。其次,整个历史学研究旨趣由宏大叙事转向新社会史,新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小人物”,劳工史以及后来的底层社会史研究是这一转向的结果。再者,社会学、人类学、犯罪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融合为犯罪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和诠释路径,打破了传统的主要囿于史学本身的研究范式,这成为其方法论上的重要驱动力。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涌现出大量犯罪史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犯罪史发轫于史学思潮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它的成长见证了整个史学视域的演变、拓展与深化。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基本研究概况特别是一些代表性成果作了一定梳理,②但还缺乏对主导性观念、视角和路径的动态性考察,企望以下梳理与分析能使学界对西方犯罪史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更深入的探究。
一、社会变迁视域中的“犯罪”
犯罪史着重考察的是历史语境之中的犯罪现象以及此种现象与特定群体、社会环境、大众观念、政府机制等诸方面的互动关系,其探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犯罪群体及其行为,而是囊括了与之相关的社区、阶层、警制、法律、法庭、刑罚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在英文语境中,“犯罪史”经常被表述为“crime history”或“history of criminal justice system”,后一表述本身便包括各种犯罪治理制度。
整体来看,西方史学家对犯罪的考察主要集中在16—19世纪。在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大转型时期,经济、社会、文化的嬗变影响着人们“看待”犯罪的视角,法律、司法、刑罚机制的变革则进一步改变着国家“对待”犯罪的方式。比如,在近代早期的手工业生产中,劳动者“占用”少量生产材料或产品是被雇主默认的一种惯例,到19世纪,随着私有财产观念的渗透以及财产保护法案的制定,“占用现象”则成为一种违法犯罪。③再如,英国传统社会对少年儿童犯罪普遍较为宽容,他们极少成为被起诉的对象,但是,维多利亚时期少年教管制度确立后,遭到起诉与关押的儿童也空前增加。可见,“犯罪”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对犯罪现象及其治理机制的准确理解离不开对具体历史情境的深刻体认。
在现代法律主导社会治理之前,西方社会对犯罪的认知深受宗教与道德观念的影响。“犯罪”与“罪过”(sin)没有明显的分野,道德上的失范或信仰上的动摇,都可能招致非常严重的惩罚。当时欧洲社会对巫术的严格管控和对“女巫”的大肆迫害证实了这种非理性的犯罪认知模式。法史学者辛西娅·赫鲁普认为,17世纪英国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宗教,亦受约于宗教,当时的法庭手册明确强调:法律的作用在于通过规定、限制和规范的方式将人们引向上帝。④当然,无论是世俗语境中的“犯罪”,还是宗教意义上的“罪过”,都有着共同性的“边界”或标准,即这种行为是否为既定社会所接受和容忍。盗窃、通奸、酗酒等行为不仅有悖于摩西律法,损害上帝的荣耀,同时,也有违世俗法规,有损政府和社区的形象,为教俗两界所不容。无论如何,宗教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主导着对“犯罪”的界定和惩罚。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转型,经济、社会方面的世俗纠纷日益增多,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得以凸显。“犯罪”越来越成为立法的产物,宗教、道德、风习等传统因素的约制则渐趋式微。犯罪史学家们发现,18、19世纪,英国的财物犯罪逐渐代替道德犯罪成为政府管控的重点对象。这一时期的“血腥法典”便主要针对侵犯财物的违法活动。根据学者麦克莱恩的解释,之所以称之为“血腥法典”,因为在“长18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的近百余年中,英国刑法体系中的死刑条目从不足50项增加到了220余项,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犯罪类型。新增的死刑法条尤其针对一些看似轻微的财物犯罪活动,如扒手盗窃、入室行窃、商店盗窃超过一定数额,偷盗牛羊、砍伐树木、毁坏鱼塘等,这些都可能被判死刑(公开绞刑)。⑤而在此之前,死刑主要集中于叛国、谋杀、强奸和纵火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在工业革命的特殊背景下,英国政府强化了对财物犯罪的惩治力度,体现出对私人财产权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
近代早期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如刑法与民法尚未分野),难以对“犯罪”予以明晰的分类。法史学界对犯罪活动的划分也主要基于研究的便宜性,比如普通法中经常被提及的重罪与轻罪、财物犯罪与暴力犯罪等。很多情况下,叛国、谋杀、强奸、纵火等被归类为“真正的犯罪”(real crimes),因为这些在当时皆被列为重罪,必须经司法程序的审判并在很多情况下被判极刑。⑥还有一些违法行为,如斗殴、欺诈、毁坏财物等,经常通过非正式途径化解,多被看作日常纠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不过,詹姆斯·夏普教授强调,“真正的犯罪”这一术语压缩了犯罪史的研究范畴,虽然严重的犯罪更容易引起关注,但轻罪类的违法行为更加普遍和典型,更能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更具探究价值。⑦“真正的犯罪”被认为应该具有“反社会性”的特征,即此类违法活动造成了较大负面的社会影响,带有一定的恶意动机,不被当时的社会所容忍。⑧
与“真正的犯罪”或“反社会性犯罪”相对的则是经常被犯罪史学家援引、使用的所谓“社会性犯罪”(social crime)。⑨“社会性犯罪”主要发生于社会大转型时期,是指那些在法律上被界定为非法但在地方社会获得广泛认同或支持的行为活动,比如英国18世纪普遍存在的盗猎、走私、私造货币、哄抢沉船货物以及从圈地上拾穗、拣木柴、挖泥煤等。在时人看来,盗猎是农村贫民应对生计困难和捍卫传统权利的一种体现;走私不仅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便宜、易得的商品,也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私造货币盛行则与皇家铸币成色欠佳、分量不足有关。⑩这些违法活动被阐释为对不公平的法律、不完善的经济体系、僵化的社会制度所做出的反应和纠正。亚当·斯密在谈及走私犯时亦不无同情地指出,倘若国法未将此定为犯罪,他们或许在一切方面皆可视为良好市民。某些“犯罪”则被诠释为资本主义立法的直接结果。比如,圈地立法出台后贫民如果再像过去那样到土地上捡拾物质资料将被定性为“非法侵入”,工厂管理法的严格执行使手工业者占有部分生产资料作为福利的传统做法成了“盗窃”。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莱恩博认为,传统惯例被“犯罪化”的现象是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要之举:“既要保证一支劳动大军自由流动,又要服从工厂纪律,所以,一方面,必须摧毁其传统的习惯性工作和收入——通过将习惯界定为犯罪的方式;另一方面,需要借助法律严厉打击各类不劳而获的偷盗活动”。他认为,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有必要做一番“去罪化”的还原。
这种“去罪化”的呼吁在西方左翼史学家那里得到回应。他们认为,因资本主义立法的相继出台,工业化转型时期普遍出现了劳工阶层被“犯罪化”或“污名化”的现象,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需要被重新评价和认识。E.P. 汤普森在论述“道德经济学”的文章中指出,18世纪英国妇女群体发起的食品骚动(food riots)是对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表示不满和提出挑战。在这些群体行为中普遍存在某种合法化的诉求,即参与者都坚信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传统权利,而不是有意地制造混乱,通常情况下会赢得社会的广泛支持。乔治·卢德在考察英国、法国的民众骚乱背景时也注意到,一个普遍性的诱因是饥荒导致的食品短缺。他认为:“那些走上街头的都是行为审慎的普通市民,而不是处于半疯狂状态的兽类,更不是罪犯。”对英国乡村犯罪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偷盗发生于丰收之前的青黄不接的一段时期内,在19世纪“饥饿的四十年代”,英国的犯罪率几乎达到了最高峰。鉴于此,有些历史学家专门将某些迫于生存的违法活动称之为“生计犯罪”(survival crimes)。不难看出,历史学家的“去罪化”阐释强调了经济社会环境对犯罪活动的刺激作用,体现了“理解之同情”的底层关照倾向,但这种诠释路径在学界尚存有争议。
迪尔凯姆将犯罪视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他认为,界定犯罪主要是为了凸显一个社会对可接受和不可接受行为标准的划分。犯罪现象具有重要的社会预警功能,如同某些病症可提醒生命体做出调整一样,犯罪在引起恐惧和反思的同时也会促进社会的变革与调适。对历史学家而言,“犯罪”有见微知著的意义,透过“犯罪”这个窗口可以发现一个纵横交错的大千世界。梅特兰曾说过,倘若能有幸目睹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社会场景,他会选择观看对杀人犯的审判,认为从中可解读出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实际上,近代转型社会中大多数所谓的“违法之徒”不过是犯轻罪的普通人,与这些轻罪犯人及其犯罪活动相关联的是一个充斥着各种社会角色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有犯人及其亲属或同伴,还有受害者、目击证人、具结证人、法官、警察、狱监、律师等,透过这些脉络关系和制度体系不仅可以还原从犯罪现场到刑罚结果的完整司法过程,亦可重构一个庞大的历史社会场域。
总体来说,对“犯罪”的解析应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以避免“时代错位”(anachronism)所导致的某些误读、误解。同时,“去罪化”的阐释亦不可走得太远,还要充分考虑犯罪的类型、性质和特殊情境。在大转型的时代,不仅犯罪的形式在发生变化,而且社会看待犯罪的观念、应对犯罪的刑罚机制也都经历了重大变迁,理应采用动态的视角来考察和认识这些变化。
二、史学转向中的犯罪史研究
20世纪上半期,主导史学研究的是传统的宏大叙事范式,它强调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中的重要事件和精英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20世纪60、70年代,“新社会史”的出现则将聚焦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特别是底层劳工群体。E.P. 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敏锐地发现,底层劳工在工业化转型时期普遍遭遇了某种被“犯罪化”的经历,即他们对传统权利的诉求在新的法律语境中变成了非法行为,以致“被迫”介入了各种法律纠纷,甚至成为监狱中的囚徒。随着视角的不断下移,劳工史研究逐渐延伸至犯罪史领域。汤普森在1975年出版的《辉格党与狩猎者》开始正式涉及这一主题,并在与他人合著的《阿尔比恩的死亡树》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犯罪化”现象的不同表征。
“新社会史”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底层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流民、窃贼、妓女、拦路大盗等犯罪群体以及学徒、家仆、车夫、家禽商、清洁工、街头少年等所谓的“准犯罪群体”,以从底层社会重新发掘历史。不过,底层视角并非忽略上层或国家因素,而是侧重自下而上地分析历史,重视从底层社会的维度来分析社会问题,从普通民众的立场来看待国家角色及其重大变革和影响。20世纪70、80年代,犯罪史研究主要聚焦于犯罪现象、犯罪类型、犯罪性质以及社会动因等方面,自90年代以降则转向对犯罪治理机制的考察,视角和方法也更加多元化。
在新社会史的影响下,英国犯罪史学家对传统的“辉格史观”展开批判与反思。辉格史学强调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念,批判“旧制度”的诸种弊端,肯定精英群体主导的政治变革。列昂·拉兹诺维奇教授是20世纪英国法史领域的“辉格派”代表,他自诩为托马斯·麦考莱的继承者,曾在其多卷本刑法史序言中写道:“麦考莱将英国史概括为进步的历史是正确的,这也适用于刑法史,因为刑法是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英国18世纪的刑法体系逻辑混乱、缺乏正义,没有执行效力,且充满专制主义,19世纪初,皮尔、塞缪尔·罗米利等人主导的刑法改革扭转了这种困局。犯罪史学家对英国传统的犯罪治理体制作了重新阐释,纠正了过分强调精英人物和时代断裂性的辉格史观。比如,约翰·兰博约分析了18世纪主导法庭裁决的治安法官和陪审团的身份构成,认为这些人并非来自土地贵族,绝大多数是中产阶层。所以,将法律视为贵族统治工具的说法则有失公允。约翰·贝蒂通过考察近代早期英国法律和法庭的具体运作机制也提出了诸多新观点。他认为,传统的法律体系并非是无效的,而是通过威慑性和选择性惩罚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这种执法模式与近代早期英国官僚机制的相对薄弱密切相关。英国社会对“血腥法典”的反思也并非开始于19世纪初的大变革时期,而是在漫长的18世纪有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
犯罪史学家还对国家在犯罪治理中的角色及其转变问题展开了讨论,出现了一度较为盛行的“国家垄断说”。坚持此说的研究者将国家现代化的相关理论融入对犯罪治理制度的阐发之中,强调近代西方的犯罪治理体制普遍经历了由民间向国家、由私权向公权的演进过程,现代犯罪治理体系的特点集中体现为国家垄断了追捕、审判和惩罚的权力,以至于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道格拉斯·海与弗朗西斯·西尼德明确指出,英国新式警察的建立是干预型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这种新的国家权力结构的特征体现在理性规划的指导、公共财政的赞助、科层机构的把控、中央政府的引领,它能触及每一个具有隐秘犯罪和失序问题的社会角落”。大卫·泰勒将19世纪国家权力在司法、执法、刑罚等方面的扩大概括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结果,因为只有权力集中、高效率、理性化的制度体系才能逐步适应这个日益城市化、流动性、非人情化的新型社会形态。
“国家垄断说”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遭到质疑,批评者认为这种理论将犯罪治理机制的演变纳入了简单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中,新旧体制之间被描述为彻底的断裂,一个代表着现代的科层制,另一个则属于前现代的地方自治体系。实际上,二者之间并没有如此明晰的分野。就警察制度而言,新旧警制在很长时期内兼容并存。新式警察作为公共权力对社会治安的介入是有限的。一方面,尽管警察开始扮演公诉人的角色,但在整个19世纪,私讼制度依旧盛行,是否提起诉讼主要取决于受害者的态度。另一方面,时人更倾向于借助非正式手段化解纠纷,比如要求对方公开道歉、经济赔偿或通过第三方协调等。在监狱制度方面,维多利亚时期虽然开始完善国家监狱体系,但一些私人慈善建立的矫正机构,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教管机构(如“reformatory”和“industrial schools”)依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垄断说”使研究者注意到国家权力在近代犯罪治理进程中不断彰显的趋势,但这一角色远非面面俱到,无所不能。
犯罪史研究对传统政治史和制度史虽然有较为明显的路径依赖,但在新社会史的影响下已经不再是就制度而论制度,而是融合了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关注视角开始下移,民众与制度、仪式之间的互动多有呈现。例如,V.A.C.加特尔教授对绞刑制度的研究不仅考察其运行的机制、程序,也从大众文化的立场呈现了普通民众的观感与态度。此种新的研究理路既有制度设计的背后考量,也有执行效果的现实图景,如同呈现戏剧的台前幕后一样,颇具层次性和立体感。犯罪史研究不仅受新社会史的影响,也深受新文化史的启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犯罪”不再被视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客观事实,而是越来越被描述为某种社会文化的建构。不揭开形塑犯罪的各种机理与要素,便很难探知犯罪的本貌。于是,历史语境中的阶级、性别、大众传媒等成为解读“犯罪”如何被形塑的重要视角和维度。
近代英国是一个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主流舆论体现着中上阶层的价值认同,对犯罪的认知亦不例外。底层社会与工人阶级经常被视为“危险阶层”或“犯罪阶级”,而白领人士介入犯罪则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之事。这种认识基于不同阶级之间迥然不同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与道德观念。19世纪弥漫英国社会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主要是中上阶层对底层社会的恐惧,他们极力渲染犯罪问题的严峻性主要是为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进而督促政府出台他们倡导的应对举措,形塑他们所宣扬的道德秩序。中产阶级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改良的主体力量。然而,在历史学家看来,他们主导的改良活动未尝不是将其自身的价值观念渗透于工人阶级,最终实现对后者的社会改造。在中产阶级的道德话语中,底层工人的语言风格、行为习惯、生活环境、健康状况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消极的亚文化色彩,附以种种道德评价的目的在于让公众认识到,底层社会是需要关注、教化甚或“规训”(discipline)的社会群体。实际上,底层社会的暴力或粗犷是一种不自觉的日常表达,他们自身亦难以觉知,其“犯罪标签”在很大程度上是阶级话语的产物。
性别因素也影响着既定社会对犯罪的认知、界定、审判乃至定罪。男性长期在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男性气概(masculinity)、孔武有力、勇于搏击逐渐成为其身份特征,纵然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具有鲜明的男性图腾色彩,但近代西方主流社会对男性特质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男性暴力的非法性。比如,当时贵族男性的公开决斗、底层男性的赤拳较量皆为披着合法外衣的暴力。比较而言,女性则长期被视作社会的弱势群体和犯罪活动的被动参与者,只有个别类型的犯罪如投毒、卖淫、溺婴被视为典型的女性犯罪。此种弱者形象的建构影响了法庭对女性的审判与裁决。研究显示,18世纪英国的法官和陪审团对女性犯人更加宽仁,她们获得缓刑、减刑和赦免的机会明显比男性犯人要更多。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将女性建构为“家庭天使”的形象,大力宣扬家庭美德和家庭伦理,这一方面展示出保护女性的姿态,希望女性远离工业化以来出现的险恶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为女性戴上了道德枷锁,阻碍了女性走向社会独立。因为在当时的主流道德学家看来,“妇女每向独立迈进一步,也便向监狱迈进了一步”。一切与“家庭天使”相悖的言行举止都有可能被贴上“非女性”“非道德”甚至是“准犯罪”的标签。
此外,大众的犯罪认知还深受印刷品和传媒话语的影响。18、19世纪,随着印刷媒介的发达,英国的犯罪文学和出版物日益勃兴。除官方的审判记录和各种民间报道之外,社会上流传着大量以犯罪为题材的小册子、画报、“低俗怪谈”(penny dreadfuls)等通俗读物。为博人眼球和扩大销量,这些作品字里行间充满逸闻趣事般的描述和捕风捉影式的猜测,使一些知名大盗的形象英雄化、浪漫化。道德改良家们认为,这些低俗读物毒害了少年儿童,误导他们向往并模仿犯罪生活。鉴于此,改革者倡导发行价格低廉的健康读物,这些作品被称为“至理雅谈”(penny delightfuls),以抵消犯罪出版物的不良影响。饶有趣味的是,在这些主流作品中,犯罪几乎成为远离现代文明的他者,比如城市底层社会往往被描述为“街头阿拉伯人”“欧陆渣滓”“爱尔兰佬”“印第安人”等。如此,两类出版物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则成为两个阶层、两种价值观的交锋。二者对犯罪的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对公众亦有不同的影响。
三、犯罪史的跨学科趋势
犯罪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研究领域和对象上存在交叉与重叠,他们分享和使用共同的概念和方法。以E.P.汤普森为代表的“华威学派”成功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用于诠释英国18世纪的法律与社会,揭示出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在合法性认同上的紧张关系,这一研究在今天依然有重要影响力。犯罪史学家通过借用社会学或犯罪学的概念提升了理论高度,也促进了学科间的交融,诸如“社会控制”“道德恐慌”“标签理论”等社会学术语已在犯罪史研究中获得共识。鲁滨逊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自觉不自觉地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生命力,以获得自己进步的机会。犯罪史学的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福柯对犯罪史研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规训理论”启发历史学家重新检视18世纪以来主导历史学认识的“启蒙与理性观念”,反思犯罪治理制度研究中出现的绝对进步主义的叙事模式。福柯认为,传统的专制体制强调肉体惩罚来展现权力的运作,而新体制更倾向于经由科层化的专业机构和抽象的知识来形塑和改观人的内在灵魂。因为人的身体开始被视为国家或社会的某种财产形式,所以,监禁取代了各种肉体惩罚,以避免破坏人的身体,目的是维持人体在经济上的生产性。犯罪史学家通过考察监狱、警察、济贫院、感化院、儿童免费学校、教管学校等所谓现代化机制的历史演变,揭示出其普遍担负的社会功能:即实现对底层社会的规训与“再造”,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都与福柯的理论有着密切勾连。例如,加特尔指出,英国建立世界上第一支现代警察队伍是加强社会控制和犯罪治理的重要体现,此后警察开始在“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中扮演核心角色。叶礼廷对近代英国监狱制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规训理论”。他指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政府之所以热衷于打造“模范监狱”与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和建构文明国家形象的考量密不可分,新式监狱融合了惩罚、感化、教育等多学科知识的社会功能。
除福柯的“规训理论”之外,埃利亚斯则为犯罪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文明演进”的考察视角。他认为,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漫长社会转型过程中,欧洲人的话语表达、行为模式发生了深刻转变。国家逐渐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民间暴力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约制。市民的行为模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合拍,为了在商业活动中达成协议、化减成本,认同性而非挑衅性的沟通模式开始流行。受埃利亚斯的影响,约翰·布莱特所著《刑罚与文明》一书以英、美、加、奥等国的案例为论据,考察了近代以来西方刑罚方式的文明化进程与社会行为模式转型的关系。他指出,整个社会对暴力惩罚(如公开绞刑、戴枷示众)不再像过去那样冷漠,而是变得愈加敏感并从情感上将其视为不可接受之事。约翰·伍德的研究揭示了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暴力观念。一种来自中上层社会,他们提倡理性、宽容和克制,谴责各种暴力行为,并力图通过社会改革根除暴力及其来源。另一种来自工人阶层,他们将暴力视为日常的行为、合理的表达。伍德认为,这与底层社会化解纠纷的有限途径以及底层大众文化的熏染有关。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文明观念的普及,秉持后一种暴力观念的人已逐渐成为少数。布莱特和伍德的研究都关注到了刑罚制度、行为模式与社会观念、内在情感的互动关系,从具体的方面对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做了延伸和深化。
犯罪史学家还经常借用心态史的或心理学的理论来解读历史语境中犯罪现象。他们认为,倘若不能对整个社会心态作一番深入考察便不能很好地理解时人如何看待犯罪和如何对待犯罪这一问题。马尔科姆·加斯基尔以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普遍存在的巫术犯罪及诉讼问题为例,强调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巫师、起诉者,还是目击证人、治安法官和陪审员,都无一例外地笃信存在某种给社会带来福祸的超自然力量。伦道夫·罗思则结合心理学的理论诠释了美国历史上的谋杀率的变化及其动因。他强调,当人们不满足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时,暴力犯罪就会增多。这一结论的社会心理学机理在于,有着广泛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容易促进以信任和合作为特征的思想和行为,相反,低水平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则容易衍生厌恶和不满,进而导致怒气、报复和挑衅的发生。不可否认,心理学、心态史、情感史等新的分析视角极大丰富和拓展了犯罪史的研究内容,提升了相关研究的理论性和说服力。
犯罪史研究不仅借用社会学科的相关理论和视角,也经常采用其研究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方法在分析犯罪趋势、类型和性质的研究中已不可或缺。基于档案材料的数据分析便于更直观地呈现某一时期的犯罪状况、各类犯罪所占比例及其变化。尽管有史学家怀疑犯罪统计过程中存在的“黑暗数字”(dark figure)——因各种因素不可能纳入统计的罪案数量,但整体来说,数据依然是重要的分析工具,并为诸多问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新的论据支撑。如前所述,传统的史学观点认为,18世纪的英国法律体系是极为严酷和血腥的,对底层穷人尤为不利,许多人因小偷小摸被判绞刑。新的历史数据则显示,被法庭判为死刑的人数和实际被处决的人数并不等同,因为有近三分之二或更多的死刑犯会因各种因素被减刑。这样,先前历史学家所定性的“血腥法典”便需要重新认识。
随着数字化处理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刑事司法档案的数字化过程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英国学者已经建成的“中央刑事法庭档案”数据库、“1690—1800年伦敦生活”数据库为犯罪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目前,一项受“艺术与人文委员会”(AHRC)资助的项目力图通过系谱学、计量生物学的技术将18、19世纪英国中央刑事法庭档案中涉及9万多人的信息建成数据库,这样便于追踪哪些英国人的祖先在那个时代的英国本土或帝国范围内曾经历过何种法律诉讼或惩罚。这种跨学科的大数据整合不仅可以重构过去的社会场域,还可在今人与古人之间建立起某种纽带联系。
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不断开阔以及不同区域、国家的学者之间的密切交流,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陆续出现,研究者开始尝试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来理解犯罪现象、治理机制及其社会文化语境。目前这方面的探索主要体现在英法之间的或英帝国视野下的比较研究。英国与法国犯罪史学家密切交流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犯罪、历史与社会》英法双语刊物的出现,该刊是国际刑事犯罪史协会的会刊,主要刊登两国犯罪史学领域的相关成果,其首任主编是著名犯罪史学家克里夫·埃姆斯利。跨国别或跨区域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研究者对本国和本区域的相关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有寻找“他者”来强调差异性的客观需求,或将相似者纳入同一研究模型来凸显共同性的规律、背景。特别是当研究对象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性——同异兼存时,比较研究的价值更为明显。比如,在帝国史的视角下,不少研究成果涉及英国本土的警制、法庭、监狱等犯罪治理制度如何被“移植”到加拿大、澳洲、南非、印度等殖民地,以及这些制度经历了何种求同存异的地方化过程。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更广阔的视角下来理解西方现代社会治理制度的生成、传播、接受与调适等问题。
总之,近50年来西方犯罪史(特别是英国犯罪史)研究不断趋于成熟,涌现出大量颇具开创性的成果。通过吸收和融合新社会史、新文化史、计量史、心态史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如犯罪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犯罪史研究颠覆了传统的线性史观和宏大叙事风格,在底层视角下重新界定“犯罪”的内涵,并重新估价与之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大大深化了学界对西方历史的认知。不可否认,随着研究范畴的不断扩延,该领域也出现了选题“碎片化”、部分研究过分倚重理论而轻视史料等趋势,值得警醒和反思。诚然,在这样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中,这未尝不是施展史学优长和影响力的契机。
注 释:
① Leon Radzinowicz and Joan King, The Growth of Crime: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kks,1979, p.15。
② 杨松涛:《近代早期英国犯罪史学述评》,《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郭家宏、许志强:《资本主义发展视野下的英国犯罪史研究》,《学海》2009年第5期。
③ John Styles, “Embezzlement, industry and the law in England 1500-1800”, in Maxine Berg, Pat Hudson and Michael Sonenscher eds., Manufacture in Town and Country before the Fac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83-184。
④ Cynthia Herrup, The Common Pea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Criminal Law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p.4。
⑤ Frank McLyn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xi-xii。
⑥ J.A. Sharpe, “The History of Crime in England 1300-1914” ,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28, No.2, 1988, pp.124-137。
⑦ J.A. Sharp, Crim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Longman,1999, pp.7-10。
⑧ Wilbur Miller, The Social History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merica: An Encyclopedia, vol.4,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12, p.1926。
⑨ 霍布斯鲍姆在两部早期著作中探讨了此类犯罪:Eric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1965; Eric Hobsbawm, Bandi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1969。
⑩ Clive Emsley, Crim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London: Longman,1987,p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