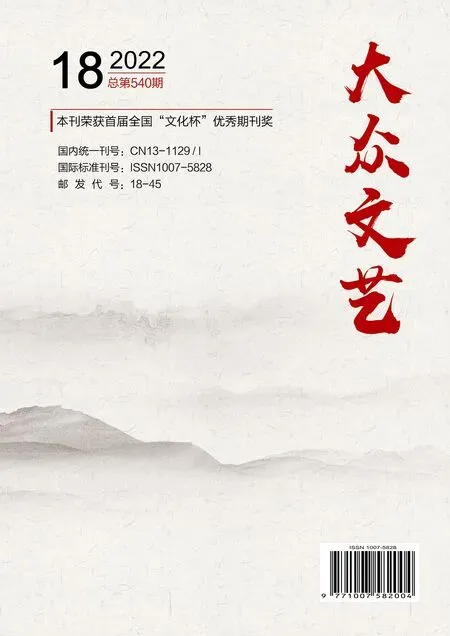玉溪白龙潭传说的三重叙事“公约数”
2022-10-10王志琳
王志琳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海淀 100875)
民间传说在某一地区的老百姓口中流传,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地方性叙事传统,但这一地方性叙事传统的内部也并非完全均质。根据讲述者和听众不同的需要,传说叙事会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之上被增添一些新的元素,而当这些创编和变异的新元素在一定的讲述者群体中固定下来时,就形成了新一层的、范围更小的叙事传统。
林继富在《故事传统与个性叙事——多人一次讲述一个故事的传承考察》一文中曾借用数学上的概念“公约数”,来形容民间故事中稳定的叙事范式和共同的故事内容,并在“公约数”的基础上寻找故事家的个性化叙事。“公约数”这一概念在民间传说中同样适用。传说叙事“公约数”不仅包含了传说在情节结构层面的稳定因素,亦包括讲述语言、观念信仰等层面的共同传统。
笔者基于多人讲述同一则玉溪白龙潭传说的调查,试图研究这一地方传说的叙事传统在不同层面的“公约数”,发掘对传说讲述者和叙事传统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
一、玉溪白龙潭传说概况
清代张泓的《滇南新语》中有关于玉溪白龙潭“上行水”奇景的记录:“新兴田地最饶,赤旱不荒,尽由各龙潭之灌溉也。潭有五,或在山顶之巅,或在山崖之下。最广者曰黑龙潭,而白龙潭之水独奇,潭居崖下,村人引水上行,能盘旋度山顶,顶畦具满,犹余润过岭。诸村落俗曰:彼村有女子,昔为龙所娶。故逆水过岭,以利其土。”
新兴州即为今天的玉溪市红塔区,白龙潭就位玉溪龙马山的西南麓。上山头村是龙马山上的一个自然村,世代以白龙潭为水源。“彼村有女子,昔为龙所娶”指的便是上山头村流传着的白龙潭传说。传说讲述了上山头村女子阮氏娘娘嫁给白龙老爷,从而使村子获得水源的故事,是该村民众记忆中的村落历史叙事。黑龙潭则位于新兴州西部,白龙潭传说中也包含与黑龙潭相关的内容,通常为黑白二龙斗法情节。
过去,白龙潭传说的讲述场景与当地的求雨仪式和庙会紧密相连。据上山头村民说,每年三月初一是白龙老爷请九龙老爷做客,二月十九是九龙老爷请白龙老爷做客,一请客辄风雨大作。《滇南新语》也有关于“龙会亲”的记载,只是具体日期与村民所说不同:“新之三月三日,必风云起白龙潭。大雨雹,至黑龙潭而止。俗云龙会亲。且雹不损禾。”老一辈人说,在农历三月初一和二月十九两个日子里,当地会举办祭祀白龙老爷的庙会活动,民众前来求雨、祭龙,期间举行各种民间文艺娱乐活动,白龙潭传说也多在这样的语境下被讲述。后来,龙王庙在“文革”中被摧毁,庙会祭祀等民俗活动长期中断。如今玉溪城市化发展,上山头村已成为城市近郊,村落时代的庙会和求雨仪式也不再举办。随着村中会讲述白龙潭传说的老一辈人也相继去世,白龙潭传说的讲述语境逐渐消失了。现在的上山头村白龙寺,除了平日提供当地民众上香祈福外,更多地承担了旅游的功能。因此,目前能采集到的活态的白龙潭传说文本相当有限,集中流传于上山头村的老人中。
二、地方、村落、家族叙事传统代表性文本
白龙潭传说虽然以上山头村为核心,但在实际流传中存在着由大到小三个不同的层面的叙事传统:地方、村落和家族。为了直观地感受这三个层面叙事传统的不同,笔者在分析前先将有代表性的文本列出,以供参考。
地方层面的白龙潭传说流传在玉溪 各个不同村落,反映了当地人对白龙潭由来的传说记忆。笔者选择一则上山头村以外的其他村落文本作为代表。在《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云南玉溪·红塔卷》中收录了一则来自小石桥乡的传说《黑龙潭的来历》:
从前,龙马山上住着白龙和黑龙,白龙住得比黑龙高。黑龙对白龙不服气,双方都想把对方赶走,独自占山,因此经常争斗。一次,一个牧羊人在山腰上放羊,走过来一个黑胡子老人对他说:“明天你的白羊和黑羊要打架,你看到了就打白羊。”第二天牧羊人放羊的时候,果然见到黑羊和白羊在打架,但他记不清黑胡子让他打哪只羊了,于是就打了黑羊。黑羊和白羊就是黑龙和白龙变的,黑龙落败,向西逃去,逃到大营街西北边的山下,那儿有一潭水,就在那里住下了,就是现在的黑龙潭。白龙依然住在龙马山,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白龙潭。
村落层面的白龙潭传说以核心村落上山头村为代表。上山头村白龙寺内的官方宣传栏上记载着在整个上山头村落社区内搜集写定的文本,其情节内容可作为上山头村落叙事传统的参考,主要讲述了白龙潭的白龙化作人形与上山头村的姑娘阮氏结亲的故事,情节概括如下:
1.上山头村的阮氏姑娘与双目失明的母亲相依为命,每天挑水照料母亲。2.阮氏姑娘一日在挑水途中与白龙化身的年轻小伙子相遇,小伙子扶了她一把,在交往中二人日渐熟络。3.小伙子在梦中嘱咐姑娘明天若看见一头黑羊和白羊打架,就打黑羊,姑娘照做,赶走了黑羊。4.原来小伙子就是白龙,白龙提出要娶阮氏姑娘,但是姑娘走了就没人给妈妈挑水了。5.白龙于是在迎亲那一天骑着一匹白马,白马的尾巴扫过,出现了一条石沟将水流引向了上山头村。
本次调查中,笔者采访了几位上山头村居民,记录了他们讲述的白龙潭传说。其中,讲述人胡兰芝、段丽芬、李学光是普通的村民,讲述人李进英和阮兆云则是传说中的阮氏家族的后代,在整个白龙信仰体系中有着特殊地位。调查发现村落社区内部的传说讲述也存在差异,核心家族内部有着独特的叙事传统。笔者摘录情节较为丰富的阮兆云讲述文本作为家族层面的白龙潭传说代表:
白龙老爷最初来这里转转玩玩,就看见这个地方;还有黑龙也来到这个地方,两个就可能争执了下。有个小娃娃过来放羊,白龙老爷说:“孩子,明天午时,有两只羊在这里打架。你打黑羊,别打白羊。”第二天两只羊打架,乌风暴雨的,那放羊的就一直按着黑羊打,把黑羊打跑了。那个黑羊就是下郭井的黑龙,所以白龙就得以居住在这儿了。黑羊跑到现在叫“龙爪”那里,杵出个龙爪印来,所以就取名叫“龙爪”。
初初那会儿,阮氏娘娘去很远的地方挑水。白龙老爷的名字叫白海,他就问:“姑娘,你怎么会来到这里挑水?”她说她住在上山头,有个妈,挑水的地方路又远,没人给她挑水,所以来这里。白龙天子就说:“不怕不怕,我担水来给你吃。”他还没显露他是白龙老爷,单说挑水来给她吃。然后日深年久,白龙老爷就去提亲。她妈说:“不会给,我要留着女儿,我挑水吃难。”白龙老爷就说:“不消要您挑水,我修一股沟,把水通到你家门前。”所以他骑着马出去,马尾巴上就顺着带着扫出条沟。然后就看好日子结婚了。
结婚后,晚上睡那会儿要铺床铺,阮氏娘娘就求她嫂嫂说不消要床铺,只要两把簸箕。她嫂嫂就奇怪了,想看看去。睡到半夜,她嫂嫂就去偷偷看。窗户是拿纸裱起来的,她就把手伸进嘴里,吐点唾沫,把纸戳开一个洞。看见两条龙在里面金晃晃地睡着,然后有一只手就没变完,还是人手。
结婚时间长了,他们就生了两个小娃娃,七八岁了。阮氏娘娘说:“你们弟兄两个去喊你外婆过节,路上不准闹架。”喊了之后,他外婆也就去了,去到路上,他外婆说:“孩子,你们两个怎么那么规矩?不说话,也不吵不闹。”他说:“我妈说了,不准闹架,不准喧哗,把您喊了去。”然后他外婆就说:“不怕不怕,你两个搅搅。”他们两个就打起架来,外面立刻就下起棱子来,两个娃娃就变成小龙,住在小龙潭。
三、提取最大“公约数”:地方的叙事传统
白龙在与黑龙的争斗中获胜,从此定居在上山头村附近的白龙潭。之后白龙迎娶了人类女子阮氏,骑着白马用尾巴扫除一条水沟,将水源带给了上山头村。在白龙与阮氏姑娘结婚后的某一天,两人在夜里睡觉的时候被嫂子窥见变化成龙,从此成为上山头水源的守护神。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在山坡上打闹的时候变化成小龙……这一系列关于白龙老爷的情节被玉溪本地人代代相传,但他们每个人的具体讲述又因种种原因而并不完全一致。将所有搜集到的文本拆解到叙事结构层面,可以通过比较提取整个玉溪地方的白龙潭传说叙事结构层面的最大“公约数”,即所有白龙潭传说叙事中的最大重合部分。具体情况如文末表1:

表1
根据表格,可以将所有出现的情节进一步概括为四个事件:①白龙与黑龙争斗;②白龙与阮氏结婚;③白龙与阮氏化龙;④白龙的孩子变成小龙。
在同一地域的村落中共有的传说叙事是事件①“黑龙与白龙争斗”。讲述了若干年前白龙与黑龙都看上了龙马山下的这一处水潭,于是它们变身成为两只羊打架,人类在龙的指点下打跑了黑羊,帮助白羊获胜,白龙于是占有了现在的白龙潭,而黑龙逃到了现在的黑龙潭居住。
这一传说在两个不同村落的流传中发生了叙事层面的分化,上山头村的白龙潭传说以白龙为主角,是白龙指点了人类(牧羊人或阮氏姑娘)驱赶黑羊。而小石桥乡的黑龙潭传说以黑龙为主角,黑龙原本指点牧羊人打白羊,结果牧羊人记不清了,反而打了黑羊,最终结果仍是白羊获胜,白龙获得了龙马山白龙潭的居住权。对比之下,整个地方共同的叙事“公约数”便是黑龙与白龙为了地盘争斗,最终白龙获得胜利这一事件。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是具有玉溪乡土根性和地域标识的地方叙事传统,解释了地方风物白龙潭和黑龙潭的由来,塑造了当地人的地理观念和历史记忆,是当地民众共同享有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四、村落社区的叙事传统
在地方共享叙事传统之下,作为传说核心地的上山头村还分化出了另一层独特的村落叙事传统。在上山头村的叙事传统中,事件②“白龙与阮氏结婚”是白龙潭传说的核心。通过提取几位上山头村讲述人的叙事“公约数”,可以发现上山头村白龙潭传说共同的叙事结构为“提亲被拒——成功娶亲”,这本质上是一个难题娶亲的故事。这一共同的叙事结构在所有上山头村讲述人的口中高度一致,构成了上山头村白龙潭传说的特殊文化场域,也是上山头村民众对传说进行个性化叙事的基础。
阮氏娘娘与龙王爷的异类婚配传说在文化流动的过程中沉淀下来,在上山头村民众的记忆深处被保留,构成了村落共同的叙事传统。这一叙事传统以水源的缺乏开头,又以水源的获得结束,其目的是解释上山头村水源的由来。讲述人们对白龙老爷和阮氏娘娘感情的发展经历往往一笔带过,对于其他细节信息也常有遗漏,但对于水源问题的解决,他们却都能流利地叙述。这恰恰反映出上山头村白龙潭传说的在叙事结构层面的核心就是“提亲被拒——成功娶亲”的难题娶亲,更深层功能结构就是水源的缺乏与获得,反映了当地人农耕灌溉的历史记忆。白龙潭传说对村落水源历史记忆的构建,宣示了上山头村对白龙潭水源的所有权及使用水源的正当性,是村落社区传统化实践的一部分。
在情节内容层面,上山头村白龙潭传说中稳定和不变的“公约数”,还有事件④“白龙的孩子变成小龙”。这一情节虽然在上述核心结构之外,但在阮氏家族内部和外部人员的讲述中均有出现,可以认定为上山头村共享的叙事“公约数”。此外,白龙潭传说的离散情节也是村落叙事的“公约数”,上山头村的讲述者们常常致力于叙述传说与现实的“客观对应物”之间的联系,比如白龙寺柱子上的龙,白龙潭、小龙潭、山上的“龙爪”痕迹等等,而这些都是属于上山头村这一社区内部共享的知识和记忆,被上山头村民众代代相传。
此外,还有一些观念层面的“公约数”,如龙的变形会带来风雨,龙的变形和变形终止都是由于禁忌的打破等等,这些观念在讲述人的口中反复出现,润色了传说的各种细节。
传说与信仰是一体两面的,上山头村叙事传统的背后是龙潭祈雨的民俗仪式和龙王信仰。民间龙王信仰的形成与佛、道两教的影响有关,据学者考证,龙王信仰实际上是隋唐之后,佛、道融合的产物。上山头村白龙寺内的白龙老爷和阮氏娘娘雕塑都是典型的道教神灵形象,白龙寺外的对联中则有“众生救苦救难功德无边”“有求必应”等佛教术语,可见佛、道信仰对上山头村龙王信仰的共同影响。根据学者对民间祈雨仪式的研究,唐宋以后,官方祈雨中雨师的地位逐渐让位于龙。民间祈雨的主要场所也逐渐变成了龙王庙,而龙王庙一般都在水潭、水井等与农业有密切联系的地点附近。上山头村落白龙潭传说的叙事传统反映了农耕文明与水的密切关系,折射了当地人民引水灌溉的劳动历史;白龙潭的传说与龙王庙的祈雨仪式一道,成了上山头村民众归属感的纽带和宝贵的民俗财富。
五、家族内部的叙事传统
虽然同为上山头村居民,但几位讲述人之间也是有身份差异的,这种差异又形成了一层更小的叙事“公约数”——家族内部的叙事传统。从上表中可以发现,阮氏家族的讲述人们在村落叙事传统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新的元素,主要集中在事件③“白龙与阮氏化龙”上。阮氏娘娘向嫂嫂讨要簸箕,嫂嫂好奇,于是半夜捅开窗户纸偷窥,结果看到夫妻二人变成了两条龙睡在簸箕上,其中一条龙的手还没来得及变,依然是人的手。两龙变形的情节只有阮氏家族内部成员李进英和阮兆云在讲述,而且是他们叙述的重点,总是被生动地铺排、详细地描绘。
李进英奶奶是嫁入阮家的,其夫阮明寿正是阮家的后代,她本人一直以阮氏后人自居。在过去上山头村祭祀龙神的祈雨活动中,她也一直担任着重要的主持位置。在村里人的眼中,她是最会讲这个传说的人。在讲述的过程中,她也反复强调“这个传说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以前我家有本书,现在找不着了”等等,以彰显传说的家族传承和权威性。另一名阮氏家族的后代阮兆云讲述的事件是最全面和详细的,他显然比外部人员更加了解整个白龙潭传说的体系,在他的讲述中,也是嫂嫂窥视这一情节最为生动详细。
虽然阮氏家族外部的普通村民们未必不知道这一情节,但讲述人们在有意或无意的选择中形成了这样的叙述差异,很可能与家族身份的认同有关。在所有的白龙潭传说相关事件中,只有白龙与阮氏变形成龙的事件发生在阮氏家族内部的生活空间,其余事件都发生在龙马山等社区公共空间内。阮氏家族的后人作为白龙潭传说最有话语权的叙事传统持有者,不约而同地选择精心渲染和着力讲述窥视变形这一情节,对于他们家族身份的强调和认同是有突出作用的。李进英老人在讲述事件完成后就向笔者介绍和指认了阮氏娘娘曾经生活的住所,说曾经阮氏娘娘与他们家都住在一道大门里。这正是一种对家族身份的强调和确认。可见,嫂嫂半夜窥见两龙变形的情节是一个具有家族内部性的传说叙事“公约数”。讲述者通过这一“公约数”,能够赋予家族讲述传说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凝聚家族内部成员的身份认同,凸显“阮家人”在白龙潭传说叙事传统中的重要性。
结语
传说总是在特定的叙事传统下被讲述,但在具体的讲述过程中,常常会有一些与传统无关的个性化叙事。由于讲述者的记忆和各种现场因素的影响,传说的变异是时时存在的,活跃在每次演述中的个性化因素正是表演理论所关注的重点。但这些变异因素只有在特定群体的重复叙事中被沉淀为固定的“公约数”时,才具有意义,才能成为某一层面的叙事传统。笔者先后采访了李进英老人三次,三次讲述的内容基本一致,主要讲述了白龙与阮氏结婚、嫂嫂窥探到二人变龙两个事件,说明这已经沉淀为她个人固定的叙事模式。家族外部的讲述人段丽芬、胡兰芝,和家族内部的阮兆云的讲述中都提及了两只小龙打闹的故事,可见这一事件也是上山头村民中广泛流传的叙事传统之一。
玉溪白龙潭传说在不同讲述人的口中形成了地方、村落和家族三个层面的叙事“公约数”,家族的叙事“公约数”强化了家族内部的身份认同,村落层面的叙事“公约数”保留了村落获取水源的历史记忆和龙神祈雨信仰,地方层面的叙事“公约数”则标注了当地人的地方感和空间秩序。个人的叙事总会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有所变化,但同时又遵守着某个层面的叙事“公约数”,形成了具有层次差异的白龙潭传说叙事。
①(清)张泓.古今游记丛抄·滇南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36:1.
②(清)张泓.古今游记丛抄·滇南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36:1.
③罗杨总主编.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云南玉溪·红塔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153-154.
④胡兰芝,女,64岁,原非本地人,嫁入上山头村,共讲述两次。
⑤段丽芬,女,65岁,上山头村人,共讲述两次。
⑥李学光,男,67岁,段丽芬的丈夫,上山头村人,共讲述一次。
⑦李进英,女,78岁,其夫阮明寿是阮氏后人,共讲述三次。
⑧阮兆云,男,80岁,阮氏后人,共讲述一次。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