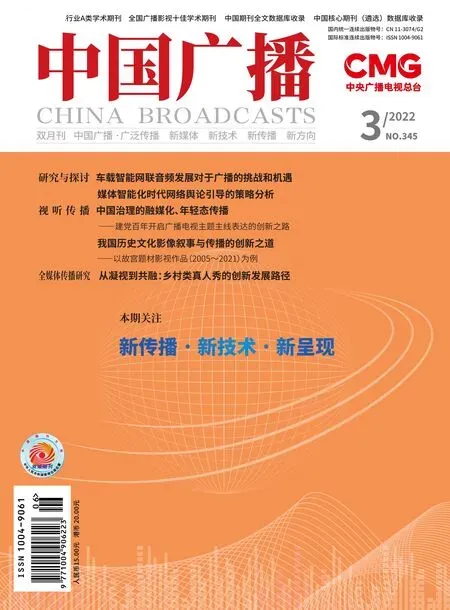新媒体技术赋权下健康传播研究
2022-08-20徐艺萌吴世文
☉徐艺萌 吴世文
第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拥有10.32 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为73%。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5G、云计算等新技术快速更迭,塑造着当代社会和日常生活。技术与健康在数字时代的融合,改变了健康传播的内容、方式与影响,并且能够赋权公众的健康生活和公共健康治理。但与此同时,技术对健康领域的嵌入也带来了新问题。例如,社交媒体诱致伪健康信息泛滥,新媒体技术导致侵害健康隐私的风险大为增加,等等。当下,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状态,迫切要求我们检视技术对健康传播的影响。
一、健康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现代意义上的健康传播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彼时,美国传播学者与心脏科医生尝试将传播理论应用到公共卫生的宣传之中,开启了斯坦福大学的“心脏病防治计划”,这被认为是健康传播研究的起点。在国内,健康传播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起步,但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该研究多以实践为导向,研究内容局限于医疗卫生、健康教育与健康宣传等。进入新世纪,我国健康传播的发展受到“非典”、口蹄疫、禽流感、H1N1 等公共卫生事件的推动,逐渐成为一个热门领域。随着新媒体与健康议题越来越多地结合在一起,基于新媒体或面向新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引起关注,也推动着健康传播研究不断拓展。当前,健康传播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社会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学、新闻传播学、信息管理科学等学科都从自身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出发关注健康议题。
健康传播在全球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当下中国,健康传播的地位显现。这主要受到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一是顶层设计对“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度重视,推动开展健康传播成为谋划与落实战略和政策的必要一环。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6年)与《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出台,“健康中国”正在加快推动中国进入“大健康时代”。为落实这些战略和政策,开展健康传播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二是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总体的健康需求增加,并且对健康传播提出了新要求。三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健康传播问题突出,包括伪健康信息在社交媒体中泛滥等,激发了研究共同体的兴趣和热情。四是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现实冲击和长远影响,需要开展持续的健康干预和健康传播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历史的分水岭”,如何解决疫情期间的健康危机和健康问题,如何应对心理健康等问题,需要持续的健康干预,并基于科学的健康传播研究开展综合的健康治理。
随着健康传播地位的凸显,人们更加重视健康问题,相关研究也得到快速发展。而新技术对健康传播领域的现实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命题。技术与健康是健康传播领域的六大分支之一,相关议题包括社交媒体对健康促进的影响、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健康素养的提升以及纠正伪健康信息、消除数字鸿沟、保护健康隐私,等等。据孙少晶等的观察,2013年以来,“微信”“网络媒体”“新媒体”等成为高频关键词,这一现象折射出健康传播研究者对新媒体技术的关注。
二、健康传播中的新媒体技术赋权

从Web1.0 到Web2.0 再到移动互联网,媒介技术的发展引起一系列变化,新媒体技术改变了健康传播的内容、方式与影响。在内容上,技术催生了多样化的健康内容生产,多元的内容生产者进入了健康内容生产领域,网络空间中的健康内容膨胀,健康话语多元而复杂。在方式上,技术改变了健康传播过去自上而下的、单向的流动方式,转向双向的、互动的传播过程。互联网重构了社会关系,去中心化的社会网络可以为公众开辟处理、加工、转化健康知识的空间,能够形成多元对话的格局,从而拓宽了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在影响上,新媒体技术可以打破健康传播的时空限制,实现信息的高速流动,创造了基于健康议题的社会新连接。从传播赋权的角度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在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实现对健康传播的赋权。
(一)个人层面
个人层面的影响体现在信息、关系和行动三个维度。在信息维度,公众能够利用新媒体技术获取丰富的健康资讯,获得个性化的健康服务,更新健康观念,做出健康抉择。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互联网是公众监测环境动态、感知外部风险的重要渠道。在关系维度,新媒体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公众开展信息生产以及获取信息的便利性持续提升,成本不断降低,因此公众能够提升自己在健康议题中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进而增强自我健康效能感。特别是利用在线问医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医患沟通的难题,推动患者与医生之间的有效沟通。在行动维度,新媒体技术为公众提供了表达自我的机会与空间,公众可以开展在线健康信息搜寻、健康话题讨论、健康自测、寻医问药等活动,并利用诸如“养生圈”“运动圈”等新型趣缘社区开展与健康有关的活动,新媒体技术可以推动用户自发组织并实现社会动员。值得强调的是,技术在实现社会的健康平等层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成为健康特殊群体(如某些病患群体)的健康“赋权器”。美国传播学者E.M 罗杰斯(Everett M.Rogers)认为,赋权是“一种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来自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面对结构性的困境,健康特殊群体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获得健康信息支持,并寻找情感支持与认同,从而提高自我的健康效能感。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新媒体技术之外,智能应用、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也可以帮助健康特殊群体实现健康赋权。如“盲人高空避障眼镜”“健康监测床垫”“AI 语音交互式助起沙发”等新产品,可以帮助健康特殊群体获得更多的健康平权机会。
(二)社会层面
新媒体技术开放、共享、交互的特质给健康公共治理带来了诸多可能性。典型的案例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健康码”。健康码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其创设体现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创新思维,而通信、算法、大数据等技术是其诞生和迭代的基础。健康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已经彰显,得到了普遍的社会认可,实现了精准的健康治理。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技术进步被广泛应用于健康信息领域和健康活动中。区块链与大数据等技术被应用于食品冷链的安全性追踪、流行病学调查、心理疾病筛查、医疗资源分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理等领域。如大数据可以实现心理疾病的有效筛查,并增强诊断的准确性;算法可以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病率、关键节点、规模、周期等做出预测。
新媒体技术可以促进健康领域的社会协同,动员多方力量集中应对健康问题。技术除了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可以整合力量与协同多方,亦可以赋权个体以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技术亦在不断更新和迭代,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如为了满足老年人群的需要,诸多互联网应用积极拓展新功能,朝着无障碍化与适老化方向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方便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小孩出行,多个省份推出静态健康码,一次生成,重复使用;在核酸检测中,现场工作人员可以反向扫码,缓解了老年人群和小孩无法出示健康码的技术困境;一些健康应用程序增加语音识别功能,使用更大的字体图标、更高对比度,实现便捷切换。
三、健康传播中技术赋权的反思与出路
(一)新媒体技术能够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实现健康赋权,同时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
其一,新媒体技术的不当使用,有时会带来侵犯隐私等问题,干扰有序的健康治理。当前,诸多健康类互联网应用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会有意无意地收集用户的健康信息,造成了对用户健康隐私的侵犯,带来健康数据处理和再利用方面的潜在风险。这些不当利用新媒体技术的行为,忽视了新媒体技术使用的公共面向,应当引起重视和警惕。
其二,不同的社会群体使用技术的能力存在差异,技术可以赋权,也会制造数字鸿沟(包括数字接入沟、数字使用沟、数字效果沟)。受到经济、教育程度、地域等因素的制约,一些相对困难的群体无法获得平等的数字媒介使用机会,而且其使用能力也存在差异。数字鸿沟在病患群体中的特殊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影响尤为显著。

其三,网络空间中泛滥的伪健康信息,严重影响网络健康信息的质量,污染网络健康信息环境。简言之,伪健康信息是被“此时”的医学专业共同体据其现有的知识和共识认定为假(非真的、非科学的)的健康信息。网络空间中滋生的大量伪健康信息以虚假健康广告或健康知识、被事后证实是非真的健康谣言、健康流言(或传言)等形式存在,具有非科学性、敏感性、欺骗性、误导性等特征。伪健康信息会使人们产生错误的健康认知,采取不正当的健康行为,其社会危害不容忽视。网络伪健康信息的扩散受到文化语境、社会心理和商业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新媒体技术亦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这提醒我们关注新媒体技术在伪健康信息滋生与传播中的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错误的疫情信息的出现会误导公众,是干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重要因素,也引起了全球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解决新媒体技术健康赋权中的问题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防止新媒体技术在健康领域的过度扩张,主要是防止滥用以及商业利益驱动的扩张。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边界亟待规范。例如,公共机构或商业应用获取用户的健康信息应当遵循“知情同意”以及“最小必要”原则,这需要立法和司法机构做出更细致的回应。
其二,切实解决老年人群和儿童(“一老一小”)等数字特殊群体在使用新媒体技术方面的困难。一方面,需要提升老年人群的媒介素养和健康素养。帮助数字特殊群体适应新媒体技术在健康领域的使用。另一方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怀“一老一小”,通过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解决数字特殊群体使用新媒体技术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注重规避侵犯隐私等问题,实现有序的公共健康治理。
其三,注重纠正和治理网络空间中的伪健康信息,优化网络健康信息质量。研究发现,对于网络伪健康信息,单纯地指出错误或简单地撤回伪信息,并不是有效的方法,无法根除其负面的社会影响。理论研究和健康传播实践都证明,传播相应的纠正性信息进行“反说服”较为有效。因此,需要在甄别网络伪健康信息的基础上求证和纠正它们,从标题、信源、叙事等维度优化健康信息的设计,以抵制伪健康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优化网络健康信息的质量,营造良性的健康信息环境。在社会层面,纠正伪健康信息需要社会力量与专业力量的介入与推动,合力强化纠正性健康信息的供给,创新纠正性信息的传播。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超链接》节目不时会关注伪健康信息纠正的问题,注重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科学的健康信息。主流媒体这种主动纠正伪健康信息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个体层面,针对社交自媒体传播,需要强调个体甄别、求证与纠正伪健康信息的责任与能力。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不断提升个体的媒介素养与健康素养,而不仅仅是“不信谣、不传谣”还需要提到的是,应该注重运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去甄别、求证和纠正伪健康信息,可以利用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等新技术手段与方法,实现对伪健康信息的识别,提供传播预警,并实时开展基于数据库等手段的智能纠正。
总之,新媒体技术可以为健康传播带来革新,实现公众的健康赋权,推动社会的健康治理。但是,健康赋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媒体技术应当以更加平等、更加包容的姿态融入个人健康赋权与社会健康治理的过程之中。对于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始终应当重视,保持警惕。
注释
①第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202/P020220407403488048001.pdf.
②E.M.Rogers: The field of t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Behavioral Scientist,1994,P208~214.
③“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and A.C.―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The New York Times,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7/opinion/coronavirus-trends.html.
④刘瑛:《美国之健康传播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 期。
⑤孙少晶、陈怡蓓:《学科轨迹和议题谱系:中国健康传播研究三十年》,《新闻大学》,2018年第3 期。
⑥Evertt M.Rogers,Arvind Singhal: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03,P67~85.
⑦《老人健康,有了智慧“卫士”》,人民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7655134268561232&wfr=s pider&for=pc.
⑧吴世文、罗一凡、杜莉华:《健康码:行进中的健康传播创新与应急创新》,《传播创新研究》,2021年第12 期。
⑨⑫吴世文:《不对称的“博弈”:伪健康信息的扩散及其纠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第260 页。
⑩U.K.H.Ecker,S.Lewandowsky,B.Swire,D Chang: Correcting False Information in Memory:Manipulating the Strength of Misinformation Encoding and Its Retraction[J].Psychonomic Bulletin Review,2011,P570~578.
⑪E.K.Vraga,L.Bode: I Do Not Believe You: How Providing a Source Corrects Health Misperceptions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formation[J].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8,P1337~1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