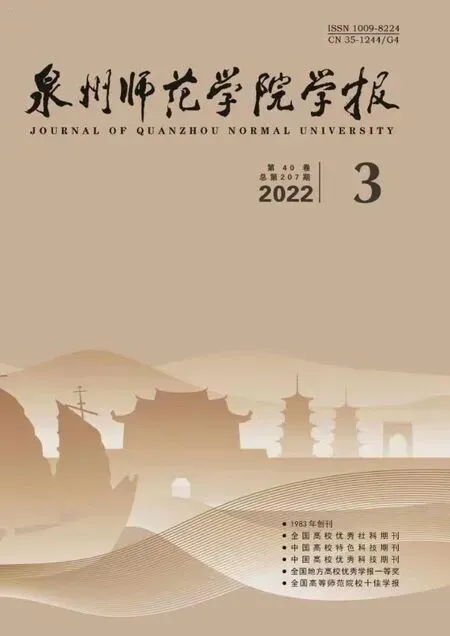父母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能力: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
2022-08-08陈秀丽张燕勤林永乐
陈秀丽,张燕勤,林永乐
(泉州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情绪的识别与表达是人际交流的重要信息与手段,对人类社会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述情障碍(alexithymia)是指个体在情绪识别、表达时出现困难的一种心理特点,主要表现为情绪识别困难、情感描述困难和外部取向思维[1]。研究表明,述情障碍与各种身心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抑郁、精神分裂)、神经症(如焦虑、强迫症)、成瘾行为(如酒精依赖、手机成瘾)以及低自尊、疏离感等负性问题存在一定的联系,它是许多身心疾病和精神障碍的一个重要心理危险因素,在普通人群身上也有体现,受到心理学和临床医学学者广泛的关注[2-3]。述情障碍个体由于自身情绪认知加工和调节的缺陷,无法准确识别情绪图片和情绪词语[4]。这意味着述情障碍者在人际互动时无法准确接收和回应对方的情绪,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也会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健康互动。贺祖辉等研究发现,如果父母存在情感表达困难,子女患抑郁的几率会提高[5];梁宗保研究发现,父母对自我或子女情绪的反应、认知、理解和评估会影响儿童的情绪识别、理解[6]。目前,国内外对述情障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异常心理状态和心理亚健康状态人群。父母作为孩子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自身对情绪的识别、表达能力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社会化。Eisenberg等认为,父母的情绪社会化行为引发儿童在特定情境中的唤醒水平,进而影响情绪相关的社会化结果[7]。因此,述情障碍父母对孩子情绪社会化的影响应受到重视。
共情是儿童情绪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共情又称“同理心”,是指站在对方的角度,感同身受地理解对方的情感、信念和意图。共情在儿童社会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儿童的道德发展、亲社会行为、同伴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认知神经加工机制研究表明,共情包含自下而上的表征共享加工过程和自上而下的执行控制加工过程。表征共享的加工过程需要涉及个体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知觉,如果个体对情绪情感的知觉能力较弱,其共情能力比较低[8]。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结果表明,存在述情障碍或述情障碍倾向的个体共情能力比一般个体低[9]。另外,关于父母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能力的关系还没有直接探讨过,但是个体对情绪情感的知觉还是容易受到父母情感的榜样作用和家庭情感互动经验的影响。从这个层面上讲,父母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能力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亲子依恋指儿童与主要照顾者(一般指父母)之间在情感上建立起的一种特殊连接纽带。依恋与述情障碍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杨红君研究发现,低述情障碍得分与安全依恋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述情障碍是恐惧型个体症状报告的预测因子[10];薛璐璐研究发现,中学生的述情障碍与亲子关系显著负相关,述情障碍可直接预测中学生的人际关系[11];秦金梅对焦虑障碍患者的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亲近、依赖) 与述情障碍显著负相关[12]。综合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国内大部分研究集中在述情障碍与依恋的相互作用方面,偏向个体内部方面研究;而涉及述情障碍与亲子依恋关系的个体间代际方面的研究较少。另外,已有研究发现,亲子依恋具有代际传递[13-15]。因此,关于父母述情障碍与亲子依恋的代际间关系及其相互作用非常值得研究。
亲子依恋与共情的研究表明,高依恋个体的共情能力一般较高[16]。依恋理论认为,个体在与最初抚养者的早期经历中通过发展出对自我和对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式为其人际关系奠定基础,并成为日后自我认知和人际交往的认知模式[17]。依恋的建立从时间上看比共情的形成要早,共情在个体处理自我和他人关系时得以体现。在对他人的反应上,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展现出更多的共情关心和观点采择,不安全依恋的个体有更多的个人悲伤。Goldstein等认为,安全型依恋个体的情感需要在儿时已被充分满足,因此更少沉浸在自己的需要中,更容易与他人产生情感连结[16];Pistole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模式之所以能提供高水平的共情,是因为他们拥有可效仿的高共情的父母[16]。这两个结果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亲子依恋对共情的影响,说明父母对孩子情绪感知和反应具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亲子依恋可能在父母的述情障碍倾向与儿童的共情能力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为了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其中的影响作用机制,本研究对父母的述情障碍、亲子依恋以及儿童的共情能力进行相关调查。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法,选取泉州市450名四年级至六年级小学生及其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儿童问卷共发放450份,父母问卷部分由父亲、母亲分开填写,共发放问卷900份。剔除规律性作答、乱涂乱答后,共回收有效学生问卷348份,回收有效父母问卷603份,回收率分别为77.3%和67%。将这些有效问卷进行名字匹配及异常值筛除后,共获得292份父母与儿童匹配良好的问卷数据(见表1)。

表1 被试基本情况
(二)研究工具
1.多伦多述情障碍20个条目量表中文版(the 20-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20) 用于评估父母的述情障碍倾向。该量表翻译并修订自Taylor的述情障碍量表,是目前国内外应用范围最广的述情障碍测量工具。袁勇贵、蚁金瑶和姚树桥等先后利用该量表对成年人和青少年进行信效度测试,结果发现,TAS-20适用于中国人群述情障碍的评估[18-19]。TAS-20共有20道题目, 由情感识别困难、情感描述困难和外向思维3个子维度组成。该量表采用五点记分的方式,从1至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由父母分别作答,总体Cronbach’sα系数为0.82。
2.基本共情量表(basic empathy scale,BES) 用于评估未成年子女的共情水平,由Darrick等根据情感共情的定义和认知共情的定义于2006年编写。该量表取自恐惧、悲伤、愤怒和开心4种基本情绪,并避免社会赞许性的影响。量表共有 20 道题目,分为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2个维度,采用五点记分方式,从1至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由儿童作答,总体Cronbach’sα系数为0.75。
3.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IPPA) IPPA用于评估子女与父母的依恋程度。该量表由Armsden、Greenberg编制,最开始用于16~20岁青少年的依恋状况评定,后来也用于年龄比较大的儿童。原版IPPA为每个依恋量表(父亲依恋、母亲依恋、同伴依恋)分别设置10个项目。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只采用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2个分量表,共20个项目,每个分量表又包括信任、 沟通和疏离3个维度。量表采用五点记分的方式,从1至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由儿童作答,父亲依恋量表和母亲依恋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72和0.70。
(三)数据收集与统计
确定施测对象后,儿童被试采用班级集体实测方式。在统一指导语下,研究者统一收发基本共情问卷和父母依恋问卷;父母被试利用家长群,在统一指导语下,父母在线上填写述情障碍量表。采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和分析。
二、调查结果
(一)儿童共情能力、亲子依恋、父母述情障碍的描述性统计
对儿童共情能力、亲子依恋、父母述情障碍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中可知,儿童共情量表、亲子依恋问卷的均分为3分左右,处于理论上的中等水平,说明儿童的共情能力水平中等,对母亲和父亲的依恋水平中等;母亲述情障碍量表与父亲述情障碍量表得分分别为2.06和2.04,均低于理论上的中等水平分(3分),说明父母述情障碍的倾向特征比较低。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92)
(二)父母述情障碍、儿童共情、亲子依恋的相关分析
对儿童共情能力、亲子依恋和父母述情障碍进行两两相关分析。其中,由于亲子依恋问卷收集的数据未呈现正态分布,所以先要对其进行正态性转换。相关分析的结果见表3~5。

表3 父母述情障碍、儿童共情各维度与总体的相关分析(N=292)

表4 父母述情障碍、亲子依恋各维度与总体的相关分析(N=292)

表5 儿童共情、亲子依恋各维度与总体的相关分析(N=292)
从表3可知,母亲述情障碍总分、父亲述情障碍总分、父亲情感识别困难维度均与儿童共情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母亲述情障碍各维度与儿童共情各维度的相关均不显著;父亲述情障碍总分、父亲情感识别困难维度与儿童的认知共情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儿童的情感共情维度不相关;父亲情感描述困难、父亲外向思维与儿童共情总分及各维度的相关均不显著。
从表4可知,母亲依恋总分、母亲信任与母亲述情障碍总分具有显著负向相关,与母亲述情障碍各维度相关不显著;母亲沟通、母亲疏离与母亲述情障碍总分及各维度的相关均不显著;父亲依恋总分、父亲信任、父亲疏离与父亲述情障碍总分及各维度具有显著负相关;父亲沟通与父亲述情障碍相关不显著。
从表5可知,儿童共情总分、儿童认知共情与母亲依恋、父亲依恋的总分及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儿童的情感共情与母亲依恋、父亲依恋的总分及各维度相关不显著。
(三)亲子依恋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1.母亲依恋的中介作用分析 从上述相关分析可知,母亲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呈现显著负相关,母亲依恋与儿童共情呈现显著正相关,母亲述情障碍与母亲依恋存在显著负相关,说明母亲依恋可能在母亲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之间起中介作用。为了进一步探索三者的关系,本研究以母亲述情障碍、母亲依恋为自变量,以儿童共情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从表中可知,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F=5.71,P<0.01),两个变量可解释儿童共情3.8%的变异量,调整后可解释儿童共情3.1%的变异量;回归分析模型的容差值大于0.1,方差膨胀系数小于10,说明进入方程的自变量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且回归系数在0.01和0.00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根据温忠麟的中介检验程序[20],在各变量进行标准化情况下,检验母亲依恋在母亲述情障碍和儿童共情的中介作用:第一步,以儿童共情为因变量、以母亲述情障碍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母亲述情障碍可负向预测儿童共情(系数c,β=-0.12,t=-2.02,P<0.05)。第二步,以母亲依恋为因变量、以母亲述情障碍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母亲述情障碍可负向预测母亲依恋(系数a,β=-0.12,t=-2.08,P<0.05)。第三步,以儿童共情为因变量、以母亲述情障碍和母亲依恋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引入变量后母亲依恋可正向预测儿童共情(系数b,β=0.16,t=2.70,P<0.05);母亲述情障碍对儿童共情的直接效应(系数c’)下降,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由0.12降为0.10,且预测效应由原来的显著变为不显著(β=-0.10,t=-1.7,P>0.01)。说明母亲依恋在母亲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见表6,图1)。

表6 母亲依恋的中介作用分析

图1 母亲依恋对母亲述情障碍、儿童共情的中介作用模型 图2 父亲依恋对父亲述情障碍、儿童共情的中介作用模型
2.父亲依恋的中介作用分析 从上述相关分析可知,父亲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具有显著负相关,父亲依恋与儿童共情呈现显著正相关,父亲述情障碍与父亲依恋存在显著负相关。说明父亲依恋可能在父亲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之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以父亲述情障碍、父亲依恋为自变量,以儿童共情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索三者的关系,结果见表7。从表中可知,该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F=5.95,P<0.01),两个变量可解释儿童共情4%的变异量,调整后可解释儿童共情3.3%的变异量。回归分析模型的容差值大于0.1,方差膨胀系数小于10,说明进入方程的自变量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且回归系数在0.01和0.00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表7 父亲依恋的中介作用分析
根据温忠麟的中介检验程序[20],在各变量进行标准化的情况下,检验父亲依恋在父亲述情障碍和儿童共情的中介作用:第一步,以儿童共情为因变量、以父亲述情障碍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父亲述情障碍可负向预测儿童共情(系数c,β=-0.12,t=-2.10,P<0.01)。第二步,以父亲依恋为因变量、以父亲述情障碍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父亲述情障碍可负向预测父亲依恋(系数a,β=-0.21,t=-3.69,P<0.001);第三步,以儿童共情为因变量、以父亲述情障碍和父亲依恋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引入变量后父亲依恋可正向预测儿童共情(系数b,β=0.16,t=2.72,P<0.05);父亲述情障碍对儿童共情的直接效应(系数c’)下降,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由0.12降为0.09,且预测效应由原来的显著变为不显著(β=-0.09,t=-1.50,P>0.01)。结果表明,父亲依恋在父亲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见表7,图2)。
三、讨论
(一)父母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亲子依恋的关系
从上述研究可知,无论父亲述情障碍还是母亲述情障碍均与儿童共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父母述情障碍倾向越高,儿童共情能力越低。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早期场所和持续终身的支持系统,家庭的情感氛围和情绪经验、父母对自己情绪识别与表达的榜样作用以及对儿童的情绪教养直接影响儿童的情绪社会化进程。Krevans J认为,儿童共情能力主要通过观察性学习和模仿得到[21]。所以,当述情障碍父母对子女或他人的情绪表现出不敏感、平淡甚至淡漠的态度时,儿童便会习得这种情绪反应模式。述情障碍父母自身对情绪信息的加工存在缺陷,在与孩子互动过程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进行情绪反应、情绪谈论和情绪表达,孩子就会缺乏情绪信息的精细加工经验,导致在情绪反应的敏感性和情绪处理能力方面存在不足。本研究发现,父亲述情障碍的情感识别困难维度与儿童认知共情呈显著负相关。在家庭教养中,父亲更多强调理性特质。如果父亲情绪识别存在困难、不敏感于人际情绪问题,在情绪调控和处理问题冲突就明显存在不足,自身的观点采择发展就会受限,就不能给孩子更多的影响与支持。
本研究还发现,父母述情障碍与亲子依恋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及本研究假设相同。提高父母的敏感性,特别是提高父母对儿童特定情绪线索的行为反应,可以有效提高儿童的安全依恋水平[22]。Lane 等认为,高述情障碍体现的是躯体感觉与行动倾向这两级情绪意识的低水平,语言加工情绪的能力没有发展完善,其感受也还没有从躯体感觉和行动倾向中转变成言语可以说明的情绪;高述情障碍者存在情绪语言图式(对情绪词汇的评价、再认和回忆)和非语言图式(对情绪图片的感知和识别)缺陷,并且在两种情绪图式之间的参考性链接缺陷,高述情障碍者的情感和认知图式没有很好地结合;热执行功能以情绪情感的卷入为特征,需要对刺激的情感意义做出灵活评价[4]。Ferguson 等研究表明,高述情障碍者对损失的敏感性较低,在任务选择上相较低述情障碍者表现不足,认知决策能力较弱[4]。这些说明高述情障碍者在情绪能力上存在不足,很难对子女进行恰当的情绪反应、示范和指导,直接影响亲子间的情绪经验和情绪氛围。因此,具有高述情障碍倾向的父母较难和儿童形成安全有效的依恋关系。
关于儿童共情与亲子依恋的关系。潘彦谷等认为,安全依恋可以促进共情的发展,且在亲子依恋关系中,父亲主要影响儿童的认知共情,母亲主要影响儿童情感共情[23]。本研究发现,亲子依恋与儿童共情总分、认知共情子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但是,无论父亲依恋还是母亲依恋,均与情感共情子维度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追溯其原因,是个体的共情发展与脑区的发育及成熟密切相关。情绪共情主要是依赖于镜像神经元系统的自发性反应,它与生俱来并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变弱,较少受到父母关系的影响;认知共情则依赖于与高级认知加工有关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等脑区,儿童在10~12岁时,认知共情逐渐成熟,且占据主导地位。本研究的被试对象正好处于该年龄段。儿童较强的认知共情能够调控情绪反应,要成功地追踪他人的情绪这类高级的认知加工仍主要依赖于认知共情[24]。
(二)亲子依恋对父母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的中介作用
从亲子依恋在儿童共情与父母述情障碍中介回归检验上看,引入亲子依恋这个变量时,父亲述情障碍、母亲述情障碍对儿童共情的标准回归系数均下降,且父亲述情障碍、母亲述情障碍对儿童共情的直接效应均不显著。这说明亲子依恋在父母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与研究假设一致。具有高述情障碍倾向的父母往往不利于儿童安全依恋及高共情能力的形成。一般情况下,患有述情障碍的人群较难与他人形成亲密的情感连接。述情障碍者存在较强的孤独感和较低质量的人际关系,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常常处于冷漠、疏离状态[25]。在与家庭成员相处时亦是如此。由于对情绪情感的识别表达困难,高述情障碍父母无法及时满足子女的情感需求,与子女情感关系淡漠。同时,由于情绪交流存在阻碍,这类家庭夫妻双方容易发生争吵,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儿童无法形成正确的榜样示范。生活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孩子与父母双方容易形成不安全依恋。低依恋水平儿童人际信息的加工模式趋向消极、负面,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较弱,容易卷入消极情绪,难以共情同感他人。不安全依恋的儿童更加关注自己的内部世界,较少和他人发生共情体验和行为,儿童共情能力较低[26]。另外,亲子依恋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高质量的父母抚养行为、对孩子需求的敏感性和及时回应。虽然述情障碍父母和子女在情绪交流与互动的质量较低,但并不代表他们的扶养行为和对孩子需求的回应存在问题。高述情障碍者只是在情绪信息的加工时存在缺陷,在一般认知信息的加工与普通人没有差异[4]。情绪表达具有文化差异性。抚养文化中较少强调情绪性,而是强调对儿童的精心养护和照顾。因此,高述情障碍父母并不必然难以与孩子形成依恋。一旦形成一定的亲子依恋,就可以减缓高述情障碍父母对其子女共情能力的消极影响。因此,父母的述情障碍对儿童共情能力的负向影响,也可以经由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而降低。
四、结论
父母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亲子依恋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儿童共情、亲子依恋存在正相关。亲子依恋在父母述情障碍与儿童共情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父母述情障碍通过亲子依恋关系影响儿童共情能力的发展,且述情障碍倾向越高,儿童对其依恋水平越低,儿童共情能力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