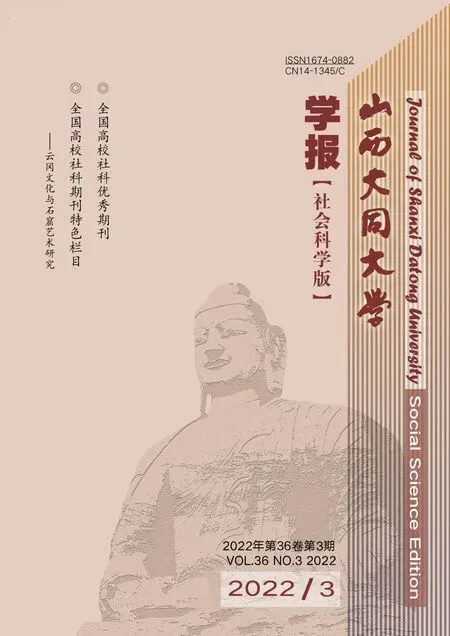“非遗”视角下的广灵八角地木偶戏保护与传承
2022-07-06刘兴利
刘兴利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木偶戏,一种由演员操纵木偶以表演故事的戏剧。在我国,流行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古称“傀儡戏”“傀儡子”“魁子”“窟子”等。[1](P1651)从其表演形式上看,广灵八角地木偶戏属于杖头木偶一类。2017年10月,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本文以文献考证结合田野调查作为方法,本着“记录也是对文化的一种保护”的指导原则,对广灵八角地木偶戏进行考察,在尽可能全面反映该剧种的同时,对其保护传承提出建议。
一、剧种的稀缺性
关于广灵八角地木偶戏,极少见于文献记载,即使在一些权威的戏曲剧种统计资料中,亦难觅其踪影,故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以下略作梳理。
(一)剧种辑录
1.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研究室为了研究山西的戏曲剧种,曾组织编写了《山西剧种概说》一书,共收入山西地方剧种50种。[2]在寒声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中,言道:“皮影戏尚有纸亮子、纱亮子之分;木偶戏有杖头偶、布袋猴(指偶和小杖头结合)之别;过去晋中一带烟火技巧中也曾有药发傀儡。”[2](P1)但书中正文未提及木偶戏。
2.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山西文化艺术志》是一部“穷尽式”志稿,体现出“跨度大、时限长、包罗广、门类全”的特点。该书第五章单列皮影戏、木偶戏:“山西木偶分杖头和提线两种形式。清末民初,浮山、孝义等地木偶兴盛。浮山有许多人以作偶制箱闻名,也出现了许多木偶戏艺人。……现在,全省专业木偶剧团只有孝义县木偶剧团。”[3](P74-75)
3.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正文共收录中国近代以来流布各地的戏曲剧种335个,附录“木偶戏和皮影戏”中关于山西木偶,只介绍了晋南提线木偶。[1](P1654)
4.《中国戏曲志·山西卷》共辑录49个地方戏剧种,无皮影戏和木偶戏。[4]
(二)研究成果 专门就山西木偶戏进行研究的成果,目前只看到安瑞峰、刘超英的《浅谈孝义木偶在民俗风格人物造型中的位置》、[5]张艳红的《山西孝义木偶戏的民俗文化探析》。[6]未见关于广灵八角地木偶戏的相关研究成果问世。
综上,广灵八角地木偶戏既不为文献所记载,亦无相关研究成果,“缺位”使之成为被木偶大家族遗忘的角落。
二、剧种形成时间
戏剧,向被视为“小道”“贱业”。“但以末技,故不备述”,故史料搜求颇为不易。这就导致我们在研究某一剧种时,经常会遇到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那就是剧种的源头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也是治曲者必须釐清的问题。广灵八角地木偶戏的出现时间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1.“汉初说”
此说源自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战”。[7](P38-39)记叙汉高祖刘邦征讨韩信,在大同白登山为匈奴单于围困,后陈平献计,重贿阏氏,助刘邦解围一事。记载中并未言明陈平所用何计。据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傀儡子》条载:“自昔传云:‘起于汉祖,在平城,为冒顿所围。其城一面即冒顿妻阏氏,兵强于三面。壘中绝食。陈平访知阏氏妒忌,即造木偶人,运机关,舞于陴间。阏氏望见,谓是生人,虑下其城,冒顿必纳妓女,遂退军。史家但云陈平以秘计免,盖鄙其策下尔。’后乐家翻为戏。”[8](P62)后人杂附种种,遂为广灵八角地木偶戏之起源一说。
2.“清初说”
广灵本地说法。木偶戏形成于清朝顺治年间,随着发展,在清朝后期木偶戏达到了鼎盛,并经过历代老艺人口传心授,才得以传承至今。因过去班社从业艺人多居于广灵八角地村,故称八角地木偶戏。(见广灵八角地木偶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仪表性项目推荐申报书)
3.“光绪年间说”
广灵本地说法。广灵木偶剧为杖头木偶,清代光绪年间出台。先在河北省蔚县各村流行,嗣后传入广灵。[9](P560)
以上究竟哪一种说法较为可信?试作辨析。
关于木偶戏的起源,主要有“始于周代偃师”观、“始于陈平六奇解围”观、“源于方相氏”观、“源于丧家乐”观等。[10](P73-75)对于木偶戏“始于陈平六奇解围”说,孙楷第先生认为此说不能以为信史,在其《傀儡戏考原》中说:“应劭生汉末,所言如此。知陈平奇计解围,至是已由测想而变成事实。然尚云图美女,不云刻木为美人也。以是言之,则陈平刻木为美人之说,纯属后人传会,羌无故实。”[11](P139)又,除却大同本地流传的汉初“白登之战”外,汉以后之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历代均无有关大同地区傀儡戏的任何文献记载,故广灵八角地木偶戏源自“汉初说”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再看“清初说”。此说主要源出广灵八角地木偶戏传承人对传承谱系的追溯。
按笔者所见传承谱系记载,广灵八角地木偶戏第一代传承人是焦老新(1663-1749年),男,须生。由此可知,焦老新生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卒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享年86岁,其应工须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该木偶戏至迟到焦老新一代,已经能够区分脚色行当进行演出。一个剧种的成熟绝非朝夕之事,必然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照此推理,广灵八角地木偶戏的初创期下限至迟应在清初。此传承谱系完整,信息衍递清晰,至今已历十一代,因此具备相当的可信度。
我们再考察清初广灵本地的戏剧活动状况。据清康熙乙丑年(1685年)《广灵县志》卷之一“风俗”条载:
四月初十日,阖邑士民献戏、设供,祭享城隍,以求福庇。凡三日。
五月十三日,献戏、设供,祭享伏魔大帝。凡三日。
六月十三日,社台山祭赛龙神。凡三日。
乡村二三月春祈,八九月秋报,在神庙前扮乐享赛。[12](P43-45)
清乾隆甲戌年(1754年)《广灵县志》卷二“坛壝·雩祭坛”条载:
在壶山上。是日,置水器、柳枝,用优歌。
春场:在先农坛。至日设春筵,用优歌。[13](P42)
以上文献记载中的“献戏”“祭赛”“扮乐享赛”“优歌”等,虽未明确指出是何具体剧种,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那就是清初广灵本地的戏剧活动已颇为兴盛,而且这种现象绝不是偶发性的,而是常态化的。近人齐如山在其《北京百戏图考·托偶戏》中曾记载,杖头傀儡戏“名曰托吼,有清一代北数省各地皆有之。”[14](P296)可见,清代杖头木偶戏在北方是相当普及的。这些都为“清初说”提供了坚实的注脚。
至于“光绪年间说”,1993年版《广灵县志》只是说“清代光绪年间出台”,是就其演出活动而言,抑或指剧种出现时间?语焉不详。笔者先对存世的不同版本的《蔚州志》《蔚县志》进行检视,结果如下:
据明崇祯八年(1635年)《蔚州志》卷一“风俗·岁时纪”载:
五月十三日,享祭伏魔帝君庙,凡三日,鼓乐不绝。
乡村三月春祈,八月秋报,神庙前扮乐赛享。[15](P347、349)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蔚州志》上卷子集“风俗·岁时纪(附)”载:
五月十三日,享祭伏魔帝君,凡三日,鼓乐不绝。
乡村三月春祈,八月秋报,令优人扮乐赛享,行社会礼。[16]
清乾隆四年刊本(1739年)《察哈尔蔚县志》卷之二十六“风俗”载:
五月十三日,谒关帝庙,鼓乐三日不绝。
当春秋祈报日,里社率钱备牲礼祀神,召优人作乐娱之。[17](P140)
清光绪三年刊本(1877年)《察哈尔省蔚州志》卷十八“风土记”载:
当春秋祈报日,里社备牲礼祀神,召优人作乐娱之。[18](P258)
经遍检蔚州(县)存世文献,并未发现有木偶戏在蔚州活动的踪迹。历史上广灵曾长期属蔚州之地[13](P18),加之天然的近邻地缘关系,两地有清一代的戏剧活动都非常兴盛,互相之间必然有所交流,这与两地文献记载是一致的。但因此说木偶戏“先在河北省蔚县各村流行,嗣后传入广灵”则不能令人信服。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即便确实存在木偶戏的活动,但出于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不屑一顾,当时的文献根本不会记载,以至于付之阙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以传承谱系作为依据的“清初说”是比较准确的。
三、木偶制作及演出形制
木偶戏之基本特性应该理解为“偶性”,即“非人性”。也就是说,但凡称之为“木偶”或“傀儡”的,其首要条件是无生命的偶,而非有生命的人。[19](P144)木偶自身是“非人”的,要完全依靠演员的表演才能让木偶“活”起来。换言之,木偶戏是以木偶为主,演员为辅,以偶人代替演员出现在观众眼前,进行拟人化表演并达到人偶合一的一种特殊的戏剧样式。显然,偶人的制作是木偶戏得以实现表演的必要前提。
广灵八角地木偶戏所用木偶是集泥塑、雕刻、美术等为一体的工艺制作而成,其最初的木偶雏形类似古人照明所用的麻油灯,当地人俗称“灯树子”。木偶头像用纸浆、石膏、腻子粉、染料等原料制作而成,身架用木头和海绵等材料制作,服饰视人物需要而配置,结合钢筋制作的支撑架,从而形成活灵活现的木偶形象。头像制作过程可概括为“三雕七画”。第一步,先用广灵本地产红胶泥塑形木偶头部,需要经过三次雕刻;第二步,上石膏翻成内膜;第三步,把纸打成纸浆,然后将纸浆灌注内膜;第四步,待内膜干透后,取出,粘合木偶头部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第五步,打腻子,用砂纸打磨光滑;第六步,打底子,彩绘;第七步,成型。
木偶制作完毕后,接下来便是如何表演了。关于杖头木偶的演出形制,明·莫是龙《笔麈》云:“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于帐帷之上,则正谓窟儡子矣。”[20](P410)清同治二年(1863年)范祖述则称杖头木偶戏为“木人戏”,其《杭俗遗风》载:“木人约长尺半许,各样脚色衣帽行头均全……台以布幔约五尺高,遮护人身,布幔之上,仅见木人,其桌椅及台上应用之物均令高出,不啻戏台一般。所做戏文与人做等,尤能滚狮子、滚龙灯,但不多得。”[21](P72)近人宗彝在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亦有所记:
其后外间又有大台宫戏班,以应宅邸堂会。其式小于戏台,而高与等,下半截以隔扇围之,内可隐人,与内外隔绝。傀儡人高三尺许,装束与伶人一般,下面以人举而舞之,其举止动作,要与伶人一般,谓之肘搂子。歌者与场面人皆另外齐备,坐于台内,与外不相见,当年所谓关防者也。[22](P93-94)
综合以上三条材料,可知由明至清,杖头木偶戏的表演形制是一致的,即演出时用布幔遮蔽人身,观众和操纵偶人者被分隔开,艺人将木偶举于头上进行表演。观众看不到操纵木偶的艺人,只能看到木偶表演。这种表演形式可称之为“遮挡式”。“遮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木偶戏的神秘感,观众观看演出时,势必会产生期待心理,而这正是木偶戏不同于其它艺术样式的显著标识。
作为杖头木偶之一种,广灵八角地木偶戏的传统表演形式为遮挡式。据《广灵县志》记载:“它不在戏台演唱,而是另搭台表演。台高丈余,木架支撑,外上布围,抬头仰视。”[9](P560)另外,广灵当地还有一种单人玩弄的小木偶戏,当地叫“掇偶子”,[9](P560)其表演类型也属于遮挡式。
早期的木偶戏表演大都为遮挡式。但也有例外。如海南岛临高县就有“人偶同演”的木偶戏,约形成于明末清初。其演出舞台上不设布幛,由经化装的演员手擎半人高的杖头木偶,边唱边念边操纵,人与木偶同演一个角色,以木偶为主,人为辅。[1](P1653)这种“人偶同演”的形式可称之为“开放式”。“开放式”的特点就是人偶同台表演,打破镜框式结构,撤去遮挡物,观众可以直接看见演员操纵木偶当场演出。“开放式”较之“遮挡式”,对木偶戏特有的“陌生化效果”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稀释,观众的观剧期待亦随之弱化,这是其固有的弊端。
2017年,广灵八角地木偶戏代表广灵县赴大同市参加文艺调演,当时在华严寺广场演出,现场应观众要求,改为开放式演出。现在两种演出形制并存,可应观众要求随时切换,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木偶戏最初大概是运用说唱曲调来演唱的。清代以来,由于地方戏曲的兴盛和受到地方观众的热烈欢迎与爱好,各地的木偶戏大多逐渐采用了地方戏声腔来演唱,从而成为各地方剧种的附属,例如京剧、评剧、秦腔、晋剧、闽剧、豫剧、汉剧、湘剧、赣剧、川剧、粤剧等唱腔,都有自己的木偶戏。[23](P210)广灵八角地木偶戏经过多年的演变,借鉴和吸收了广灵秧歌、晋剧、河北梆子、二人台、二人转、豫剧等众多地方剧种,黑、红、生、旦、丑各类偶人脚色齐全,唱腔道白用广灵韵白,演唱采用上下对子句,近乎说唱。乐队分文武场,以二胡、笛子、板鼓、锣、镲等为主。文场简洁明快,武场节奏紧凑。近年来乐队中加入电子琴、小提琴、中阮等现代乐器,丰富了伴奏色彩。
剧目方面,广灵八角地木偶戏基本以传统古装戏为主,如《八蜡庙》《四杰村》《恶虎庄》《三岔口》《打金枝》《大堂见皇姑》《辕门斩子》《回荆州》《斩黄袍》等。其内容、情节、动作、唱腔等均与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相同。
四、传承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非遗”保护的核心是掌握该项技艺的传承人,“非遗”保护的目的是通过传承人的传授,被传承人习得技艺,然后使该项技艺得以传承下去,其外在表现是活态的、富有生命力的。广灵八角地木偶戏于2008年7月,列入广灵县“非遗”保护名录;2014年11月,列入大同市“非遗”保护名录;2017年10月,列入山西省“非遗”保护名录。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非遗”。总体上看,该剧种的传承谱系比较完整,信息嬗递清晰(见表1)。

表1 广灵八角地木偶戏传承谱系
从传承谱系看,其八代以前均为八角地焦氏家族的内部传承,且均为男性,体现出“传男不传女”、传播地域狭窄等特点。自第九代邱贵德开始,八角地木偶戏不仅有了外姓传承人,而且也出现了诸如邱政卿这样的女性,无论在性别上亦或地域上,都有了不小的突破,这对于该剧种的传承是有利的。
据木偶戏老艺人回忆,广灵八角地木偶戏以第五代传承人焦珍明(花脸),第六代传承人焦新远(三花脸)为剧团骨干,曾召集当地木偶戏爱好者20余人,自制木偶人道具、服装、舞台等演出用品,演员黑、红、生、旦、丑齐全,乐队伴奏配板胡、二胡等,动作配锣、鼓、钹等打击乐。排演剧目30多个,如《打金枝》《大堂见皇姑》等。从焦珍明、焦新远的生卒年月推断,二人的活动时间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中华民国,可见广灵八角地木偶戏的传承从未间断。
广灵八角地木偶戏在民国时期逐渐衰退,幸有第七代传承人焦如意仍在艰守传承。新中国成立后重获新生。1961年,第八代传承人焦存发于1961年组织团队,代表广灵县参加雁北地区小剧种汇演,曾获得多个奖项。
第九代传承人邱贵德,从小酷爱戏剧艺术,擅长音乐和舞台艺术表演,对木偶艺术情有独钟。1978年随第八代传人焦存发学习木偶艺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广灵八角地木偶戏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工作。为了传承木偶技艺,他四十多年来共投入60多万元,用于培养木偶戏后继人才。2011年,邱贵德组织成立了广灵县木偶皮影戏剧艺术协会。现有演职人员35名,其中乐队伴奏人员10名,舞台艺术表演人员25名,调音师1名,导演1名。他们自己研制偶架、头像及偶人服饰和道具,排练传统和现代剧目,排演剧目达50多个。
经过多年努力,广灵八角地木偶戏被列入山西省第五批非遗物质文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广灵县木偶皮影戏剧艺术协会被评为大同市AAA级社会组织,2018年被山西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化系列活动组委会评为“基层文化特色团队”。
目前广灵八角地木偶戏在保护、传承过程中,还是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主要是缺少经费支持,严重迟滞甚至阻碍了剧种的发展。
按政策规定,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享有每年3000元的传承经费保障。然而就笔者走访所知,这项经费并不是每年都有。自广灵八角地木偶戏于2017年成功申报省级“非遗”保护项目,至今已过去三年,现在的传承人邱贵德没有领到过一次传承经费。笔者在《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通知》(晋财文〔2019〕29号)中,就没有看到广灵八角地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经费。这样势必对传承人心理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该项技艺的传承。
为了摆脱剧种生存发展的困境,从2000年开始,邱贵德开始招收木偶戏学员,前后大约有30多个学员。起初每人每月收取学费50元,后提高至每月100元,根本无法应付剧团日常消耗,如剧团现在租房一年就得5000元,冬季取暖烧煤也得自己购买。遇到演出,乐队每天就得100元,雇用演员每天200元。遇到参加大型活动,目前主要靠自筹资金,前期基本上都是邱贵德自己垫付。近两年情况略有好转,主要得益于县文化局文化下乡补贴,如2018年共演出20场,2019年共演出17场,每场由文化局补贴2400元。偶有外出演出机会,承办方有时也会负担部分费用,并给予一定的象征性报酬。如2012年,剧团参加大同春节庙会展演,主办方提供食宿,5天共支付了700元。
另外,“非遗”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保护对象存世文献的挖掘、收集、整理。就广灵而言,目前已有《广灵秧歌音乐》《广灵秧歌・音乐卷》《广灵秧歌・剧本卷》(上)等成果问世,但木偶戏至今尚无任何举措,保留在传承人手里的剧目手抄本已残破不堪,亟待抢救保护。
五、保护建议
作为非精英、非主流的“草根艺术”,广灵八角地木偶戏目前面临资金不足、发展乏力的窘境。如何解决其“当下生存”的问题,并回答其未来“应当怎么样”,显得尤为迫切。笔者结合调查走访所获得的资料,试就广灵八角地木偶戏的保护传承提出建议。
(一)建档立册,全面挖掘和继承 尽快完成广灵八角地木偶戏传统资料挖掘和从业人员的建档立册,达到一偶一档,一人一案。以朝代剧目作为分类登记标准,逐人逐偶记录在册,登记存档,做到朝代清晰,人物角色明确。除了向保护传承人学习木偶制作及表演技艺外,还应向剧种原发地的受众,特别是喜爱该剧种艺术的老人们挖掘他们的群体记忆,确保木偶戏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走形,不变味,这也是剧种保持自身特有的规定性所必须注意的。
(二)建立基金制度,借鉴“文物领养”除去部分自筹资金外,可将演出收入按一定比例抽取做为发展基金存入专户,以备不时之需。剧种要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发展不能只靠政府补贴、政府采购送戏下乡。2017年3月11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广灵八角地木偶戏可借鉴此方案,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木偶戏发展的热心人士和企事业单位,多方筹措资金。
(三)文旅结合,“借鸡生蛋”广灵历史悠久,既有传统的六月十八庙会,也有国保单位水神堂、千福山汉墓群、洗马庄汉墓群、汉白玉石林等,加之近几年出现的广灵剪纸艺术博物馆、涧西古民居、殷家庄古民居、广灵湿地文化节等,已经形成了独具塞外特色的优质文化景观群。广灵八角地木偶戏可充分利用当地所具有的文旅优势,将自身发展融入到这个大的语境中,借鸡生蛋,多维度拓展木偶戏生存空间。
(四)联合艺术院校,走共同培养之路“非遗”保护的核心是掌握该项技艺的传承人,传承人的培养并形成稳定的传承机制,是保证“非遗”传承发展的不二法则。广灵八角地木偶戏虽已突破家族封闭式的内部传承模式,但仍局限于广灵一地且从业人员数量较少,受众面不够。就表演而言,尚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显得“戏”味不足。可联合具备条件的艺术院校开办木偶专业培训班,走共同培养之路,以破解剧种传承后继乏人的桎梏。
(五)积极申报“惠民工程”,抓住机遇再发 2020年2月19日,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山西省财政厅下发《关于印发<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该方案已将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列入2020年省政府民生实事,重点实施“五个一批”服务内容。此项文化惠民工程所需资金已列入省财政年度预算,各级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给予适当经费补贴。这对于广灵八角地木偶戏而言,必将是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需要认真准备,积极申报参与。
六、结语
广灵八角地木偶戏,是一门融合雕刻、服装、表演、剧本、音乐等多种元素,通过木偶塑造剧中人物形象、烘托剧情、感染观众的民间艺术形式,极具地方特色。遗憾的是,该剧种至今“养在深闺人未识”。基于“非遗”的不可复制性特征,“人亡艺消”往往就成了“非遗”普遍面临的硬伤。加紧对被传承人的培育,是广灵八角地木偶戏得以生存发展的刚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重要保证。扩大木偶戏的影响力、存续力,固着受众记忆,使之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一种期待,广灵八角地木偶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