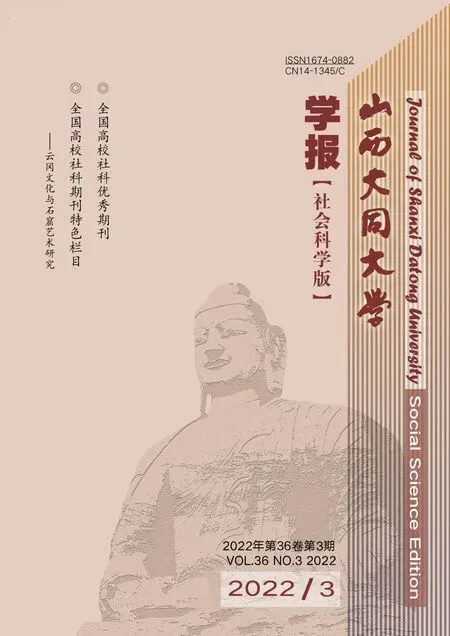“着”的历时音变及在大同方言中的体现
2022-07-06柴敬畏张忠堂
柴敬畏,张忠堂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无论在现代汉语普通话还是各地方言中,“着”字的出现频率都相当高,所以“着”字的音形义及其语法功能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为了避免多音多义字的错用、乱用音义的现象,有必要理清它们在汉语史上的发展脉络和音义关系,促进现代汉语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从而加强人际交往中普通话用语的规范性,为语言文字的汉语教学服务做好工作。最后以山西大同方言为例,分析“着”在大同方言中的表现形式及用法,体现地方方言的文化特色,促进地方方言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着”的历时演变
现代汉语中的多音多义字众多,根据学者的研究考证,其中大部分多音多义字都是上古汉语音变构词的遗迹。音变构词,是指音节中的音素变化来构造出意义有联系的新词,大致包括变调构词、变声构词和变韵构词三类。[1]“着”字声母均为zh[tʂ],未发生变化,但是它的韵母和声调有所变化,发生了音变现象,是典型的音变构词之例。
“着”在现代汉语中是多音多义字,结合《汉语大词典》[2](P168-172)与《现代汉语词典》,整理“着”的四个读音分别为zhe[3](P1661)、zhāo[3](P1654)、zhuó[3](P1730)、zháo[3](P1654-1655),如表1所示:

表1“着”字音义对应表
“着”读“zhe[tʂə]”时,旧同“著”,有4个义项,均依附于其他实词之后。读为轻声的“着”皆作为助词使用。①位于动词后,一种表示动作的持续。如:他们正干着活;另一种表示状态的存在。如:桌子上摆着一个花瓶。②常出现于形容词后,表示程度深,常跟“呢”连用。例如:这花儿香着呢(哩)。“哩”来代替“呢”,是方言中比较常见的口语化形式。③在动词或程度形容词后加强命令式语气。例如:大家都看着。④放在某些词后构成介词。如:为着;朝着;挨着等。例如:为着别人,输了自己。(康进之《李逵负荆》第四折)
“着”读“zhāo[tʂɑu⁵⁵]”时,查阅《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大致有三种词性及用法。①动词,“放,搁进去(放置)”义。例如:着盐。②形容词,在方言里表示同意对方的观点,针对交际对象的话语而作出的回应。例如:着,就这样办。③名词,“手段、办法”,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方法、策略。例如:此一着谁参破,南柯梦绕,梦绕南柯。(刘致《殿前欢·道情》)
“着”读“zhuó[tʂuo³⁵]”时,同“著”,位于词语的开头,有的与表示动作类的词汇义相关。①动词,表示“穿”,着装。例如:脱我战时袍,着(著)我旧时裳。(乐府诗《木兰辞》)②动词,表示“接触”,同《汉语大词典》的意义相同。例如:这衫儿穿的着皮肉。(关汉卿《普天乐》)③名词,表示“着落”。例如:着在经手的身上赔补,这就有了数儿了。(《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四回)再如:吃穿无着。④介词,把、将。例如:莫忧世事兼身事,须着人间比梦间。(韩愈《遣兴》)
“着”读“zháo[tʂɑu³⁵]”时,①动词,表示“接触,挨上”之义,与读“zhuó[tʂuo³⁵]”中意义一致。例如:上不着天,下不着地。②动词,表示燃烧。例如:着火。③动词,指感受、受到。例如:我着凉了。④位于动词后,表示已经达到目的或一种结果。例如:他躺在那儿就睡着了。此外,此读音的还有:着急、着慌、着迷等。
从历时演变来看,“着”属于汉字中的后起字,首见于宋代德清丞方淑与智善撰写的《春秋直音》(简称《直音》),[4]它是作为“著”的俗字出现的,而“著”最初产生是作为“箸”的异体字出现的。“著”的原始词写作“贮”,动词,“贮存、贮藏”之义。张学成《“着”字古今形音义辨略》阐述了“着”字的古今形音义,从形音义角度进行了简要分析演变进程,说明“箸、著、着”字的演变及音义异同。[4]《说文·竹部》:“箸,飯攲也。从竹者声。陟虑切。又遲倨切。”[5](P91)《说文解字》仅收录了“箸”字,艸部未收录“著”字。“箸”,本义为“筷子”,即“吃饭时所用的工具”,名词。早在《荀子·解蔽》中就有此义,即“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集韵》:“箸,或从艸。古作‘’”。[6(]P492“)箸”作为形声字,其异体字有“櫡、筯、著”,“著”出现以后,逐渐从“箸”中分化出来,并分担了“箸”的绝大部分音义。甲骨文时期并未记录“著”字,仅记录有“贮”字,“著”字从金文开始有了记录,字形变化如下。
张忠堂先生《汉语变声构词研究》指出,“著”的变声构词在上古已经发生,原始词“著”,动词“附着”义,上古属端母铎部短入,中古属知母药韵入声三等开口。滋生词“著”字,动词“附着上了”义,上古属定母铎部短入,中古属澄母药韵入声三等开口。宋代以后,“著”和“着”用字分化。[7](P78-82)孙中运《“著”字源流问题》从字本身的源流出发研究了“著”的字形演变发展,分别论说形声、假借、通假的“著”字,提出“著”在古籍中用作代替本有其字现象,这是古人不正常的用字现象。[8]因此,“箸、著、着”同出一源,古人常将它们混用,后来才将其区别。
据《广韵》[9]记载,“著”的音义,如表2所示:

表2 “著”字中古音的音义对应表
“著”字在古代典籍中的声母有澄母和知母,韵摄有遇韵和宕韵。中古汉语中,“著”的音义很复杂,而发展到近代汉语时期,“著”的音义逐渐减少。《现代汉语词典》中“著”主要有三个读音(zhuó、zhe、zhù),包含三个声调(阳平、去声和轻声),其中“zhuó”“zhe”两个读音与“着”字的读音相同,但“著”字读为“chú”时,在古代“著雍”是十干中戊的别称。例如:称戊干年为“著雍敦牂”。[10](P3441)
“着”作为“著”的俗字,它最初是作为“著”的异体字出现的,“着”字出现后,与“著”并行混用了大概一千年,近代才独立使用。例如:表示动作正持续进行时,“躺著、正说著话”也可以写作“躺着、正说着话”;表示动作的存有时,例如:“镶著(着)金边儿、贴著(着)标语”;表示某种情形的程度时,例如:他可厉害著(着)呢;表示命令或嘱咐的语气时,例如:你可要记著(着)。因此,“着”字可以独立使用后,分担了“著”的大部分音义,“著”的常用读音变为“zhù”,常用义项为“显明、著名、著称”。
二、“着”的语法演变
历代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关于“着”的语法化问题,在汉语史上,它从实义动词虚化为一个依附在实词后的虚词成分,即实词虚化。下面将从历时与共时角度分析“着”的语法化演变历程及目前学界对“着”所属范畴的主要观点。
(一)“着”字的历时演变
1.先秦时期
王力先生认为“着”本作“著”,最早提出“着”为不及物动词,表示“附着,放置”义,形尾“着”就是从“附着”的意义演变而来的。[11](P306-309)例如:风行而著于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例中“着”(著)是动词,后面只限跟附着处所名词的宾语。
2.东汉时期
汉末的“着”已经有虚化的迹象,“着”与前面的动词构成使成式结构。[11](P306)例如:忧陀莫亲世业恋着故家。(《中本起经》卷上)例中“恋着”是“想念、思念”义,心理动词“恋”指精神意识活动,表“附着”义的“着”指心理上的“依附”,因“着”与心理动词意义相重合,使“着”的动词性有所减弱。
3.南北朝时期
“着”字开始虚化,又构成“动词+着+处所词”结构,且宾语不限于处所词,“着”字的目的是为了引出这个处所,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到”。例如:王独在舆上,回顾展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着门外。(《世说新语·王子敬骄子》)例中“着”为“到”义,是处所介词,“门外”是动作“送”要达到的位置,也就是目的地。
4.唐朝时期
“着”主要出现在“动词+着+宾语”结构中,与之前相比,“着”已经完全失去了动词“附着”义,而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出现在诗词类作品中。例如:看著闲书睡更多。(王建《江楼对雨寄杜书记》)
5.宋元时期
“着”字表示行为的完成,相当于“了”,主要集中出现在南宋话本和《朱子语类》中,尤其是《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但这种用法的使用还不是很普遍。例如:若不实说,便杀着你。(《三国志平话》卷中)
6.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着”字有很多用例,这一时期多表示完成体,集中出现在明清小说中。例如:大王若肯下去,寻着老龙王。(《西游记》第三回)清朝以后“着”主要用来表示持续体,用法较为普遍。例如:虽然遇着一人,跳过船来,这人是谁呢?(《孽海花》第七回)
(二)“着”字的共时研究
关于“着”的语法化,大部分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的分析研究。张爱民与王媛媛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它的虚化机制与虚化规律,举例分析了它的虚化过程,说明它的虚化过程是渐变过程。[12]吴福祥谈论了关于持续体标记“着”字的语法化,列举“着”字语料来证明典型的持续体是在宋代以后才见到。[13]关于它的语法性质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认为“着”是形尾。王力先生认为“着”与中古时期相当于“在”义的“著”有其渊源,同时他认为“着”在汉末时期有了虚化的迹象。[11](P306)朱德熙先生认为“着”是一个定位黏着语素,属于动词后缀,同时他还认为“着”加在动词后面是表示动作或变化的持续。[14](P28)例如:我正忙着呢!
第二,认为“着”是动态助词,附着于动词的后面,表示时态,而且动词与“着”之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这个观点也是学界普遍认同的。吕叔湘先生提出“着”是助词时,紧接动词、形容词之后,可以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也可表示状态持续。[15](P665-666)邢福义先生认为“着”表示持续的状态,应该轻读。例如:唱着歌儿。这也属于附着在动词后面表示的一种持续状态。他还认为助词的作用是“附加”,“着”主要附着于动词,它像形尾,但是也依附于短语,所以“着”也叫做词尾性助词,同时“着”附着在动词后,可以看作词尾。[16](P203-210)
第三,认为“着”是体标记,汉语仅用体标记就可表示持续态,也可表示完成态。吴福祥认为持续体标记“着”字的语法化,是在宋代以后才可以见到。[13]
三、“着”在大同方言中的体现
大同位于晋冀蒙交界处,大同方言具有游牧民族与汉族融合的语言风格特色。关于大同方言归属问题,就山西境内语言来说,将大同方言归为山西晋语的一类;就所有的晋语来说,将大同方言归为晋语大包片。王力先生认为现代汉语方言属于现代汉语的范围,方言也是由历史发展来的,汉语史与汉语方言学也是有密切关系的。[11](P3)由此可见,方言与汉语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清“着”字在大同方言与历史上的音义对应是极其必要的。
大同方言有五个声调,比普通话多一个入声,且有较为明显的喉塞音[ʔ],调值与普通话也不同,且大同方言调类是源于中古的入声,中古时期的清声母入声字为阴入,浊声母入声字为阳入,而中古方言的阴入和阳入在大同方言中合为入声,且读音极为短促。事实上,20世纪大同方言的阴声韵保留晋方言的特色,但20世纪以后晋方言特色加速磨损,逐渐向普通话靠近,而且整个大同方言的音韵结构也很大程度上受普通话的影响。[17](P207)
马文忠《大同方言志》记录的是城内老居民的口音(属于老大同话),[18](P3-4)与现在年轻人口音存在一定的差异,现将它在大同方言新老两派的音义对应整理如下:

表3 大同方言“着”音义对应表
大同方言中“着”字有入声和阳平,表示不同的意义,而且保留了“着”字部分动词以及从实义动词虚化后的助词用法。大同方言“着”字的常见用法如下:
1.“着”读为“[tʂaʔ³²]”或“[ʦaʔ³²]”,动词,义为“放”或“使、弄”。
(1)“着”,义为“放、搁”时,例如:菜有点儿淡了,再往菜里头着点儿盐。例中“着”读为“[tʂaʔ³²]”或“[ʦaʔ³²]”,口语中读为入声,带有急快短促的喉塞音韵尾,相当于“放、搁”义。宕摄三等入声字普通话读为[tʂɑu⁵⁵]时,早就晋朝《太平御览》就已出现“着”[tʂɑu⁵⁵]的读音,本义为“放置、搁”,与大同方言中读为“[tʂaʔ³²]”或“[ʦaʔ³²]”时意义相同。大同方言中“着[tʂaʔ³²]”是宕摄三等入声韵字,百年前大同方言的江宕摄入声韵已经完全合并,且与山咸摄入声韵合并,形成aʔ和æʔ入声韵。同为宕摄三等入声韵字的“酌”初期是[tʂaʔ],中期[tsaʔ],后期[tsaʔ],[17]它的声母、韵母和“着”字一样都变成了舌尖前音且有入声韵[tsaʔ³²]。
(2)“着”,义为“使,弄”时,例如:帽子让他给着丢了。
2.“着”读为“[tʂaʔ³²]”或“[ʦaʔ³²]”,构成“着套”,有“办法”义。
例如:我看看你有啥着套哩!大同方言中“着套”有“办法、方法”义,可以理解为“我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这种特殊用法相当于普通话的“着数”,在大同方言语境中多为表示一种蔑视的感情色彩,偏贬义。再如:快点哇!你这着套可多哩!此例中明显体现说话者的抱怨与不耐烦,听话者会认为说话人不愿意等他,所以在此语境中可以理解为“快点儿,你事儿真多哩。”
3.“着”读为“[tʂəʔ³²]”或“[ʦəʔ³²]”,助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表示状态持续。
例如:你注意着点,小心把孩子打着。此例中第一个“着”读为“[tʂəʔ³²]”或“[ʦəʔ³²]”时,作为助词,附着于动词后,表示一种加强命令语气,能明显感受到说话者命令式的感情色彩。再如:你看着点儿!你慢着点!第二个“着”读为“[tʂɐo³¹³]”或“[ʦɐo³¹³]”,表示动作的结果,作补语,在方言中“打着”引申为“打坏”义,可以理解为“小心把孩子打坏。”
大同方言口语中还经常用“地”放在动词后,代替“着”的语法意义。例如:听地哩!(表示听的动作正在进行)他们正吃饭着哩!(他们正吃饭地哩!)“着”与“地”用法相同,从大同方言的口语来看,“地”与“着”在语音源流上有一定的联系,“地”相当于“着”表示一种状态的持续。此外,还有“走着[tsəu⁵⁴tʂəʔ³²]或[tsəu⁵⁴ʦəʔ³²]”、“说 着[ʂuaʔ³²tʂəʔ³²]或[suaʔ³²ʦəʔ³²]”等,表示动作正在进行。
4.“着”读为“[tʂɐo³¹³]”或“[ʦɐo³¹³]”,表示“感受、受到”,构成“着慌”“着怕”等,例如:真着怕哩!(因某事感觉到害怕)大同方言“着”读为“[tʂɐo³¹³]”或“[ʦɐo³¹³]”,普通话中读为“[tʂau⁵⁵]”。20世纪的大同方言声母系统未发生剧烈变化,且声母格局在20世纪后期已基本形成,[17](P197)而大同方言的效摄字形成了一套[ɐo]类韵母,入声韵依然保留喉塞音韵尾[ʔ],由于受普通话影响较大,大同方言后期也在向普通话靠拢。
5.“着”读为“[tʂɐo³¹³]”或“[ʦɐo³¹³]”,助词,表示动作的持续态或完成态。例如:他睡着了。此例中“着”表示动作的结果,也就是表已经入睡的完成态,与《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表示“入睡”的义项相同。例如:一挨枕头就着。大同方言“着”读为“[tʂɐo³¹³]”或“[ʦɐo³¹³]”,这里的用法侧重强调结果,但是“他睡着哩”的“着”读为“[tʂəʔ³²]”或“[ʦəʔ³²]”与“他睡着了”的“着”用法不同,此处的“着”与“地”相同,表示动作体入睡的结果和持续性的一种状态,更侧重强调一种持续状态。“地”是“着”向持续体标记过渡的一个助词,比较强调结果的持续性。
因此,“着”在大同方言与普通话中存在差异,但也有相同用法。通过整理“着”在大同方言中的表现形式,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大同方言“着”的独特使用情况,体会方言文化的语言特色和民俗文化的深层积淀。
四、结语
“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多音多义字,在字形、语音、语义等方面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通过考查其来源、形成和发展,理清其脉络源流,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认识“着”的用法,为人际交往提供准确的导向,同时对促进语言文字教学的规范化有着重要作用。最后通过梳理“着”字的发展演变及在大同方言中的表现形式及用法,彰显地方方言的文化特色,促进地方方言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