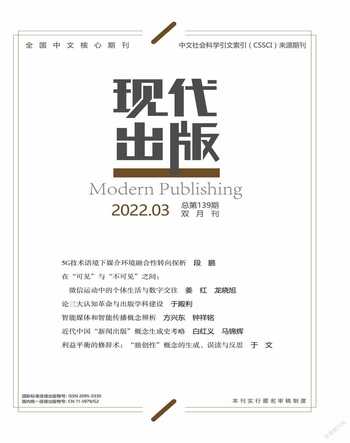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微信运动中的个体生活与数字交往
2022-06-22姜红龙晓旭
姜红 龙晓旭


关键词:微信运动;可见性;运动社交;社交媒体
行走意味着什么?在全民健身的风潮中,行走是一种运动。2021年8月3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传感器技术的应用,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测量和评估个人的运动成果,运动得以在碎片化时间中进行,日常的琐碎行走也能被统计为可见的数据。运动社交App的发展,让运动回归到社交,以此来激励全民运动。2015年上线的微信运动公众号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仅10个月用户就已突破千万。在运动社交产品的逻辑中,行走作为最基础的运动,被技术转化为客观的量化数据。微信运动更是将行走步数作为产品核心,引入排行榜、点赞等竞争互动机制,以打破“一个^运动的孤独”。
然而,行走又不仅仅是运动,计步数据也不只是运动量的体现。“我们挺立身姿,如此与世界产生连接,并在其中感受自我。”行走是人的能力。在真实的行走中,我们与周边环境建立关联、产生交往。在技术的加持下,行走数据成为与人的肉身关系密切的“数字伴生物(digital companiOnspecies)”,并伴随着真实的行走同步更新,暴露了个人的日常活动。自2018年国庆起,微信的数据报告便以微信运动的步数来表现用户的生活状态,“百步青年”更是成为“宅生活”的标签。微信运动在社交平台展现了一种动态的生活轨迹。然而,与微信运动设立之初衷相比,这种动态呈现可能导致更多隐私信息的泄露,社交平臺的相关讨论层出不穷。微信运动在日常交往实践中生成了更为复杂的“可见性”。
一、可见性视野下的媒介研究
“可见”,就字面意思而言,即可以看见,这一意义包含着看见的能力、能见的范围。而“看见”这一动作又涉及两方:看的一方与被看的一方。因此,“可见性”也意味着关系。Brighenti指出,这种关系往往是不对称的,它与权力息息相关。比如,在福柯的观念里,空间的“可见性”可以成为规训的手段,类似“全景敞视”的空间展现了“不对称”的可见性,使得被观察者对观察者“可见”,但被观察者却无法得知观察者是否存在,只能以观察者的目光对自身进行管理,形成新的自我监视机制。
正如我们通过望远镜看远方一般,技术能够改变可见的范围,同时“看见”的实现往往需要以技术作为中介。因而,技术也是可见性研究的一个重点。首先,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带来了更大范围的可见性。在个体层面,电视等媒体的出现使得个体的可见性范围扩大,重构了公私生活的界限。丹尼尔·戴扬进一步发展了媒介的“可见性”概念,将媒介研究与可见性联系起来,并提出可见性是人的一项权利,它包括被看见的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以及给予他人可见的权利。一方面,个体能够利用媒介来行使个人的可见性权利,继而获得社会意义上的“可见”,许多学者将“可见性”看作“公共性”的象征(孙玮、李梦颖,2014;姜红、开薪悦,2017)。与此同时,媒介的可见性也让权力关系发生了改变,相关研究聚焦于媒介实践中的职业可见性(陆晔、赖楚谣,2020)、性别可见性(曾丽红、叶丹盈、李萍,2021)、群体可见性(秦朝森、梁淑莹,2021),探索了媒介对于权力关系的再造,这是媒介可见性研究的核心价值。
就社交媒体而言,可见性的视角为相关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沿着福柯的空间规训理论,技术嵌入后的社会化媒体,除了呈现空间的可见性,同时还呈现了空间关系的可见性,这一语境下的可见性生产,“极大地解放了空间的社会学内涵和公共性特征”,是“对主体性的代替性解放与拯救”。一方面,社交媒体通过聚合用户及其所发布的内容,使得相互之间更加可见,不再是少数人观看多数人的“全景监狱”,而是窥视他人和暴露自己同步的进程。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交媒体带来的泛在的“观看”也引发了人们对隐私问题的担忧,人们希望能够管理并组织自己的可见性,或是利用社交媒体的可编辑性,改变线上空间的自我呈现,或是通过调整功能设置,改变可见的范围。因而,在具体的使用实践中,可见性与可供性密不可分。
在Treem的观点里,传播的可见性是可供性之根(root affordance),他进一步提出了思考“可见性”的三个维度,即聚焦传播者的行为、他人的观看行为以及传播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因素。也有研究认为,可见性是一种可供性,它具有变异性,取决于平台的特定功能以及用户对特定功能的应用。因此,对于媒介可见性的研究,也可以聚焦于平台功能的改变或是用户实践的差异带来的断裂之处。比如,截图的断裂在于,我们的本意是保留当下的可见,截图分享却让可见的传播范围不可控了,截图的潜在可见性影响了青少年的同龄交往。而微信运动的断裂之处在于,可见的信息范围超出了个人原本的预期。微信运动可以为我们思考当下数字时代的“可见性”提供参考。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研究者通过滚雪球抽样及在社交平台公开招募的方式,遵循信息饱和原则,共对15位微信运动长期使用者进行了访谈(编码与个人信息见表1)。访谈对象中13位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访谈中,首先请受访者谈论个人使用微信运动的经历,并进一步深访使用者个人的交往互动体验与具体的可见性管理的方式,主要专注于“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同时,研究者本人是微信运动的深度使用者,对微信运动的交往活动进行了长期的参与式观察。除此之外,研究还使用资料分析方法作为辅助,一是通过媒体报道、行业报告等了解微信运动的发展;二是聚焦于微信运动相关话题中的热门微博评论,展现有关微信运动的讨论。
二、行走之“可见”:微信计步中的“量化自我”
身体如何可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身体感知和认识世界,身体是观看和行动的主体,在哲学意义上,作为主体的身体是不可见的。但当我们需要认识和解读身体时,身体又成了认识的客体,它的可见性被显现出来。在现代医学的话语中,身体的各项机能被视为可以计算的指标,通过指标可以评估身体的健康状态。故而,量化身体成为人们认识身体状态的一种途径,身体成为一种可计算、可统计的物质。身体通过技术被具象化,转化为数字表征,形成一种中介过后的“可见”。具体来说,运动App中的数据和图像就是身体的“可视化”,即可见的身体。当智能传感器技术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身体就成为个人随时随地可以观测的对象,具有了日常的“可见性”。但是这种可见是相对个人化的,观看的主体是我们自己,观看的目的在于控制和管理个人的身体。
行走,是身体的日常活动。德·塞托在论述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时强调了行走的重要性。在技术逻辑下,行走被视为“人们随身的传感设备的加速度变化”。因为装载着传感技术的设备随着行走而发生移动,行走得以被量化,通过计算和统计,生成“可见”的步数。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可见”并不是行走活动的可见,因为我们可以用肉眼观察到身体的移动。它更倾向于表示我们对行走“量”的可见,是随着时间变化积累的记录。使用者基于这种“可见”的“量化自我”,来感知日常的自我活动。在徼信运动中,行走的“可见”便体现在对身体行走的记录中,技术的感知、记录与数据同步成为关键。
感知和记录通过传感技术实现,记录下的数据呈现在微信运动之中。具体来看,微信运动步数的主要呈现方式有两种:一是每晚10点左右会推送排行榜,显示个人今日的步数与排名;二是随时随地可以点开个人主页或是排行榜查看实时数据。两种方式代表了每日总结和实时统计的行走量。在使用者查看时,两种呈现数据都会成为人们感知日常生活的根源。受访者中,大多数人通过排行榜中直观的步数显示都会得出一个对于生活状态的初步感知。在自己步数很多或者排名靠前时,使用者会感受到“有成就感”(访谈对象F05),“它的排名或者是那个步数能肯定一下今天的我”(访谈对象F01);而步数很少时,则会产生“浪费时间的罪恶感”(访谈对象FIO)。同样,在看待他人的计步数据时,使用者也会有类似的解讀:“他的微信运动步数多,你莫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积极、很勤劳的人,感觉很上进。”(访谈对象F01)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计步数据可以被看作个人生活的“数字标签”。除此之外,微信运动还可以查看步数的历史记录,数字的变化图表也为使用者带来了每日行走变化的观察途径,以此来评估生活的变化。
数据的同步则发生在不同的设备之中。一般来说,微信运动自动读取的是手机内置的计步数据,但在设置数据来源时,还可以接入第三方设备或应用。截至2021年,微信运动官方显示,其可接入11个品牌的智能手环的外接设备及6款运动App作为数据来源。在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中,手机成为微信运动数据来源最主要的智能设备,4位受访者有过使用智能手环(2位使用小米手环,2位使用华为手环)的经历,另有1位使用过一般的计步器(没有智能同步功能)。使用外接设备的受访者普遍认为,手环相对手机来说更为“随身”:
“之前给我妈买了个华为手环,用华为的那个‘运动健康’软件来同步到微信运动上……手环的数据还是比手机要准的,计步能多一些,毕竟我也不是随时随地带着手机。”(访谈对象FIO)
“因为手环是随身的,一些不是那种完整时间的步数它也会算进去。”(访谈对象F05)
这些经历再次强调了行走可见的过程中智能设备“在场”的必要性。受访者FOB则表示,买计步器的目的主要是脱离对手机的依赖,“我不想总走路看手机,我觉得我看手机的时间有点多,我就想手机不要在我运动的时候也不离手”,行走时的设备“在场”反过来影响了个人的媒介依赖。
在微信运动“行走”的过程中,媒介技术既充当了中介角色,将不可见的身体转化为可见的数据,又改变了人与身体、媒介技术的关系。一方面,人与身体通过传感技术和设备联结,技术成为身体的解释者,向人们展现出一种可视的“真实”,人通过技术对个人的行走活动进行解读,并对身体活动进行管理,身体被隐藏在技术之后,成为仅保留小部分特征的“数字化个体”。另一方面,智能设备影响了人们对于媒介的选择和依赖。行走过程中,身体与智能设备共同在场,其行动保持一致,二者融合成为“赛博人”。
三、连接之“可见”:微信运动中的社交与展演
如前文所述,若只谈行走之“可见”,过程是相对个人化的。但行走不仅仅是孤独的,它也会与日常的社会交往产生关联。德赛托提出的“行人言说”(pedestrian speech acts)概念,包括当下(the present)、殊异(the discrete)及寒暄(the phatic)三大特性,其中,“寒暄”就指的是步行中的社交动作。人们在日常行走中,与他人相遇,与空间相连,继而产生社会交往。在微信运动中,步行这一状态并未描绘出实体空间的具体样貌,但通过身体的行走与技术的转换,实体空间的步行与手机这一日常生活领域联结,在微信的好友中开展社会互动。
微信运动的功能介绍就写道,“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好友的运动情况”。在王茜对运动健身App的量化研究中,微信运动的受欢迎程度排名第一,并且,“社交互动”是人们使用运动健身App的最大动机。微信运动更具吸引力的一点,就在于它的社交功能。它嵌入在微信这一社交平台之中,建立了基于已有好友圈的社交运动场。当个人行走数据被连接到微信运动的社交网络时,可见的范围扩大了。这种被连接的“可见”让使用者的日常行走成为互相可见的数据,每个人都成为观察者,每个人也都在被观察。
人类天生就喜欢分享。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在线上的社会交往中,也呈现主动分享的趋势,目的在于寻求他者以及自我展示。微信运动的特点在于,人们建立起连接的“可见性”是主动的,但却少有更为主动的分享行为。与其他社交App中运动结束后的结果分享不同,微信运动是自动更新并实时公开的,它强调的是一种“共在”状态,能被看见的不只是步数,也有“当下”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围绕微信运动的社会互动,不是基于特有的分享行为带来的“可见”,而是基于好友间实时步数统计的“可见”,用户的主动性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为排行榜直观反映了个体的步数和排名,排行榜成为微信运动社交最主要的互动空间。在这里,可见的不只是每个人的步数,还有好友的位置排名。为了争夺排行榜的前列位置,人们互相比拼步数,开展竞技,形成了被社交媒体“中介化”的运动竞技景观。在微信运动功能上线的初期,这种“比拼”的氛围甚至超越了运动的氛围,“刷步”屡见不鲜。此外,在平台的技术设计中,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人,还有占领排行榜封面的权力。这一设置赋予了“竞技”优胜者更高的“被看见”的可能性。占领封面,成为个体在与社交好友的比拼中最想达成的目标。
但是,另一方面,排行榜的直观让竞争变得明朗,也让差距变得清晰。微信运动已经走过七年,从访谈结果来看,个人的竞争愿望虽然存在,但已不再如最开始那般“疯狂”。受访者F01和M09都表示,只有和排名前面的人差距很小,才会有想要竞争的意愿,“渐渐地就觉得没有必要去抢榜一了,抢不过”(访谈对象F01)。如今,面对排行榜,人们展现的更多的是“消极竞争”的态度。比起“竞技场”的比喻,排行榜更像是“大荧幕”般的展示列表,供人们互相观看。
竞争的欲望虽然在减弱,但人们的互相观看并未受到影响,受访者都有查看别人步数的经历。在这种看与被看的氛围下,人们将行走步数视为个人的数字化表征,通过微信运动展演自身,借此来展现个人的生活姿态,并通过与朋友的互相点赞,维系个人的社交关系。对于受访者来说,数字的“好看”比起数字的“靠前”更为重要,“至少每天还是要走到2000步吧,不然被别人看起来也太颓废了”(访谈对象F14)。
微信运动将计步数据从设备与使用者之间扩展到社交媒体,并与他人的数据发生连接,“大荧幕”般的排行榜,刺激了竞争,也鼓励了展演。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改变微信运动中的数据,或者说为了修改数据背后的“我”的行走状态,个人的身体活动也发生了变化,受访者F08就表示:“比如说我那天休息,早上起来一直在家里面,我下去拿个陕递再待会可能就一千来步了。如果哪一天休息基本没怎么运动的话,我就会偶尔下午出出门,上附近小区溜达,我都会拿着手机看我走了多少步。”自我管理与他人的视线共同对身体活动产生影响。微信运动中的社交联系使得寻求他者的关注成为可能,而关于步数的身体展演指向的则是一种线上的自我呈现。
四、失控的“可见":成为“日常行踪监视器”的微信运动
在前两个部分的叙述中,“可见性”从数据之于使用者的“自我可见”,转换为微信运动使用者之间的“他者可见”“相互可见”,私人数据变为好友间的公开数据。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数据被更多人看见后,其意义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此,笔者摘录关于步数的一条热门微博下的评论来窥探一二:
“我都不敢开步数,他们会知道我12点后怎么还没睡觉。有时候说在家其实出去玩了也被(拿)捏得明明白白。”
“我奶奶每天看着步数研究全家人都干什么,只要今天走多了,她就会打电话过来问。”
“以前我前任就是通过步数监视我。多了就问我是不是去哪去哪了,很烦。”
类似的发言在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为什么微信运动从运动社交平台变成了人们争相吐槽的“日常行踪监视器”?在这个过程中,“可见”是如何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范围的?个人又如何看待这种失控的“可见”?社交好友之间的交往实践有何变化?伴随着“自我可见”向“他人可见”的转换,这些问题变得愈加重要。
正如前文所述,“可见性”意味着关系,而关系往往又是不对称的。社交平台虽然提供了互相观看的可能,但观看的程度、观看到的信息往往存在个体化的差异。一方面,微信运动的步数随着日常的身体移动自动更新,且实时可见,时间与步数成为相互关联的要素,被同时观测到。因此,从步数在时间维度的动态变化可以推演出个人在某段时间的行动状态,这是微信运动中能够“被看见”的隐藏维度。另一方面,要开发出这种隐藏的“可见”,需要观察者格外注意和关心。毕竟,微信运动并不会向好友展现每个时间的步数动态,只能通过频繁地打开、观看、比较,才能在观看者的思维中留下动态的印象。从这一层面来说,此时“看”与“被看”的双方存在关注程度上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微信平台中现有的社交关系。社交平台的讨论与访谈记录都表明,这类表现主要存在于亲密关系之中。
“因为我小孩在外面读书,怕她作息不规律,有时候也老宅在宿舍不出去,就会看看她微信运动什么时候有步数,早上步数在涨的话说明她已经起来了,其他时间(步数)变化大的话那她肯定在外面走动。”(访谈对象F03)
“我表姐一開始刚做完腿部手术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步数,十几步、几十步,后来她慢慢开始练习走路的时候,她可能有的时候会走一千多步……康复期间我就经常通过她的微信运动来看她恢复得怎么样。”(访谈对象F11)
建立在亲密关系的基础上,观看者对被观看者的近况、生活习惯均有一定的了解,再结合步数的动态变化与每日统计,加入个人的推演和想象。比如,微信步数每日0点之后会清零,F03便可以通过步数监测和想象子女0点之后的夜间行动或早晨起来活动的时间。此时,可见的不只是步数,而是更为细节化的日常行踪。
这种失控的“可见”与充满着矛盾的个体交往实践共生。首先,使用者想要展示的内容与被观察到的内容存在差异,使用者个体已经无法控制“可见”的方式和范围。个体主动公开私人数据,并将其作为社交互动的资源,是出于交往的目的,也是为了在社会化监督下评估个人的生活状态。但是,当碎片化的数据不仅仅被呈现,也被想象、被编织,其背后隐藏的生活细节被暴露,就已经超出个体预期的目的,使用者不再是“用自己的方式被看到”,而是“用他人的方式被看到”。使用者不希望被过度关注的生活细节也成了“可见的”。
“有一次我去北京的时候,去天安门,然后绕着鼓楼大街那一边走,去北海公园,去了一大片(地方),那天走了两万八,我妈说‘干什么去了?走了两万八’。然后我心想,这样我在北京没有好好实习的事,我妈又知道了。这就很过分。”(访谈对象M04)
这种被窥视的感觉让使用者感到不适。然而,让人更感压力的是,窥视往往会在具体的对话中显现。不论是前文的微博评论,抑或受访者M04的描述,这种窥视常常在交往中以直接、公开的方式让被看者知晓。
随之出现了第二重矛盾,即意识到“可见”的信息超出控制之后,使用者面对社交关系的复杂心态。在意识到有人通过微信运动想象个人的行踪时,使用者面临的选择是是否还要继续保持个人步数在社交网络中的“连接”,继续公开个人的微信步数是否意味着同意这种“追踪”?对此,使用者的反应不一。一部分人认为,微信运动的“追踪”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关心;但另一些人认为,它已经上升到了“监视”的程度。受访者F15表示:“我妈每天都会给我的微信步数点赞,看我的步数,用这样的方式不打扰我,关心我的生活,我会觉得挺温暖的。”受访者F06则经历了心态的转变,一开始因为“父母经常性会针对微信运动来问我,我需要对我的日常向别人做出一个解释”,从而将微信运动关闭。但是,当感受到父母因距离与时差(F06目前正在某西部省份工作,与家乡距离很远)无法轻易选择直接的沟通方式时,她又将微信运动看作一种连接的纽带,重新开放该功能。
“他们直接给我发消息的时候少,就是通过看微信运动,然后有时候才会给我发消息,问我的日常。我觉得它已经成为沟通的一个切入点了……有时候我也会去看一下他们的(步数),换一种别的方式去了解他们的日常。”(访谈对象F06)
“寒冬里的刺猬”揭示了人性的矛盾之维,人与人之间既需要互相取暖,也需要保有适当的距离感。在微信运动中,我们希望与好友分享个人的行走数据,开展社交互动,但又不希望过度暴露个人的生活细节;我们渴望“被看见”,将微信运动当作互相关心的入口,却又不愿公开的数据被过度解读,演变为对个人行踪的“日常监视”。
五、编辑“可见”:微信运动中的“断连”与“伪装”
社交媒体大多设置了可见范围的管理功能,如微信朋友圈的“三天可见”、微博的“仅半年可见”。这一设置,并不仅仅是一种隐私保护方式,也包含着个体对自我可见的主动管理。基于不同的因素,微信运动的使用者也选取了差异化的管理策略,对可见的内容与范围进行编辑,力图改变步数的呈现,以隐藏现实生活的具体细节与轨迹。其可行性在于:第一,微信运动有可见性管理的功能,即平台的“可供性”;第二,微信运动中直接可见的是以数字形式展示的“步数”,但“步数”的生产过程其实是不可见的。
因此,使用者采取的编辑策略也存在两种方式。
其一,利用微信平台的隐私设置来进行编辑,切断数据的社交连接或者缩小数据在社交圈的可见范围。微信运动的隐私设置主要有三种,即直接关闭微信运动功能、选择不加入排行榜以及针对部分人设置限制。
直接关闭功能意味着直接退出,受访者中有3位(M04、F05、F12)在使用微信运动一段时间后选择将该功能关闭,他们关闭的原因分别是“点赞是一种压力”“不想被妈妈看到走了多远”“晚上步数多被朋友截图发朋友圈调侃”,反映了使用者的不同心态,其共同特点都是社交网络的压力。
而不加入排行榜,切断的是数据的实时显示。此种策略下,实时步数为0,统计步数只有等到晚上的总结推送中才会显示。但在这种策略下,数据异常也有可能“被看见”。受访者F10就曾设置过不加入排行榜,但这一做法反而让行踪变得“异常”:“我有一次因为要去看一场特别晚的电影,不想让别人看到我那么晚还有步数,所以就试着关了排行榜,结果在电影院接到我妈的电话,因为步数是0,她就很担心我出了什么事。”出于这一原因,F10并未继续采用这种编辑策略。
针对部分人设置限制,则可以在微信运动中对某些好友设置“不与他(她)排行”,也可以针对微信好友设置“仅聊天”的限制,后者让微信运动与朋友圈一起成为个人不可见的状态。这一设置虽然并未直接退出微信运动的社交场域,但关闭了与特定好友的数据连接。相对来说,这一策略考虑的是跟特定好友的社交关系。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没有把我加入排行,还是说他们压根就没有开……我是看不到的。像有些同事,我就设置不让他们加入排行,不太想让他们看到我的排行、运动的情况。……我感觉我不太想同事来了解这些。”(访谈对象FOB)
在技术的帮助下,使用者通过缩小被看见的社交范围,甚至是直接放弃被看见的权利,来管理可见,为自己争取适度的空间,以求从被追踪、被过度观看的压力和焦虑中解放出来。但是,社交关系又反过来会影响相关策略的实施。F10便受到过这种困扰:“之前我因为父母老通过微信步数说我不运动、起得晚,所以设置过‘不与Ta排行’,但是后来就直接接到电话要我打开,没办法又开了。”由此来看,技术虽然提高了我们争取“适度可见”的自主性,但并不能提供对抗社交媒体中“过度可见”的全部力量。
其二,改变数据的生产过程,从而改变微信运动的呈现。在这一策略中,使用者通过改变“不可见”的过程,来改变“可见”的结果。最常用的,就是以“摇动”来代替行走。由于行走是通过技术测算随身的传感设备的加速度变化来实现量化形式的可见,那么改变这种测算结果,只要让设备感知到移动的加速度变化即可。“摇动”能够带来与行走相似的结果。一方面,“摇动”或“抖动”的身体代替了真实的行走,身体移动的部位发生了变化。受访者F10讲述:“我不会因为想竞争什么的去摇手机,但是我会早上醒来摇,因为有时候醒了不想起,摇一摇加点步数看起来就像我已经起床了。”另一方面,还可以借助外在的技术物来实现轻松的“摇动”,如电商平台的“刷步神器”。
另外,暂时“停用”微信运动功能也是一个隐藏真实数据的办法。据受访者F05所述,在停用的当日,微信运动步数会保持已统计的数据不变,一些使用者采取这种策略来隐藏特定时段的个人踪迹。受访者F14表示:“有时候有半夜走超過1000步的情况,就会暂时关闭微信运动,要不然可能会被我妈打电话问。”
正因为行走步数与个人真实的身体活动紧密相关,所以微信运动才能够在社会交往中被开发出隐藏的“被看见”的内容。但若是采用“摇动”或者暂时停用的策略,步数就不再与真实的行走同步。从这一点来说,使用者对行走进行了伪装,数据代替“我”成为可见空间中的表演者,并与真实的自我逐渐脱离。可见的不再是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是被个体使用者编辑、修改、伪装的自我形象。
六、结语
在微信运动的“可见性”实践中,数字技术的“解蔽”与“遮蔽”也同时生成了个体可见性的悖论。我们本希望通过技术的“解蔽”更深入地看见自己,更好地认识和管理自我,以线下的行走连接线上线下的社交生活,追求更健康和更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却因为“可见”在交往中渐渐失控,而被迫切断连接,伪装行走。在抵抗“被过度看见”的过程中,在争取“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过程中,行走的“自我”也渐渐无法真实地“被看见”,不得不放弃“自我可见”以求得不被他人过度看见。数字技术反而带来了新的“遮蔽”。
微信运动呈现的这种可见性的矛盾是今天社交媒体中数字个体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相较于社交媒体兴盛之初人们“360度无死角”式的自我表现,今天,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逃离朋友圈”,在微博小号发言,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摇摆,在不同的账号之间切换,设置分组可见、三天可见……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既能“被看见”,又能在某种程度上“不被看见”,他们在社交分享与自我隐藏之间,在连接与断连之间,在真实与伪装之间苦苦挣扎。
贝克认为,“个体化”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原子化、与世隔绝、形单影只、各种社会的终结或不相连接”,它首先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社会的旧生活方式的抽离(the disembedding),其次意味着再嵌入(re—embedding),在此过程中个^必须自己生产、上演和聚拢自己的生活经历”。
可见性背后,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一技术系统”框架中个体如何数字化生存问题。在拉什看来,第一现代性中,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相互分离,甚至“互斥”,但是,在第二现代性中,社会和技术相互交织,成为非线性的“社会一技术系统”,所以“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是带有浓厚社会一技术性的主体”。随着数字媒介深度嵌入社会和日常生活,个体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也由传统社会中具身交往的远近关系,转化成个体与他者之间数字交往的可见程度问题。
当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多元社会网络的中心点,社会交往成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即使具有亲密关系的亲人朋友,在“社会一技术系统”中,也只是“他者”。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年轻一代更加表现出和他人、社会之间既亲近又疏离的关系,既渴望被社会“看见”,又不希望被置于“数字敞视监狱”之中。他们希望以自己定义的方式被看见,但这种适度可见的需求很难被父母所代表的那一代人所理解。
这一代人的数字化生存之路,也许注定要经历这样一段旅程——在“脱嵌”与“复嵌”之间徘徊,在渴望被看见与拒绝被凝视之间纠结,在勇敢展现自我与隐藏和伪装自我之间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