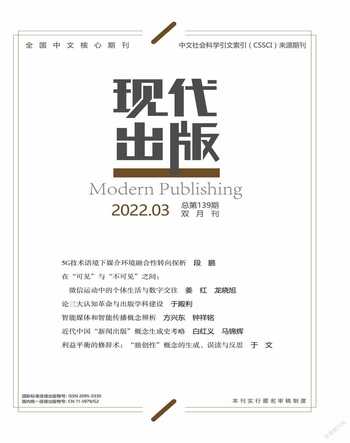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概念生成史考略
2022-06-22白红义马锦辉
白红义 马锦辉



关键词:新闻出版;概念史;新闻;出版;近代中国
“新闻出版”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以及编辑出版学界一个特有的常用词语。一方面,英文文献中并没有与新闻出版相匹配的概念,若以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英文名称(National Press and PublicationAdministration)中的“press and publication”为关键词在搜索引擎和外文数据库里检索,绝大多数结果都与中国有关。另一方面,它在国内又使用得极为广泛,中国知网2012-2021年这十年间所有期刊论文的题目中包含“新闻出版”一词的共有2137条,平均每个月知网上都有将近18篇新的论文题目里包含“新闻出版”四个字,常用程度可见一斑。在深受西方学术和学科体系影响的新闻传播领域里,一个使用如此普遍的词语却难以在西方语境中找到与之匹配的表达,这就使得“新闻出版”一词为何及如何在中国本土生成、反映了中国怎样的特殊语境等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此前有研究者对国内CSSCI论文中关于“新闻出版”的知识图谱分析显示,围绕这一概念形成了五个聚类:法制与道德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与时代背景、战略目标与发展规划、政府职能。由此可见,“新闻出版”一词的运用语境是高度行政导向的,这或许可以为“新闻出版”一词为何是中文特有概念提供部分解释:因为我国在行政层面长期将“新闻出版”作为行政部门名以及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所以“新闻出版”一词有着高度的行政倾向且在中国独有。但是,“新闻出版”一词并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形成的概念,早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就已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概念的意涵是否发生过变化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本文将以概念史的思路,探究近代“新闻出版”一词在中国本土早期生成、流传的过程,以求解决围绕着“新闻出版”—词所产生的疑问。
一、“新闻”与“出版”:一对互相纠缠的概念
要想厘清新闻出版的演变历史,首先得弄清楚“新闻”
“出版”“新闻出版”等概念在中国本土生发过程中的联系与边界。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一词是随着晚清传教士入华而诞生的,传教士马礼逊在1820年前后印行的《华英字典》中就已将英文里的news译作“新闻”。“出版”这个概念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已有研究已证明这是个日文引进词,虽然早在1879年黄遵宪与日本学者龟谷省轩的“笔谈”中就已出现,但直到1914年北洋政府《出版法》出台,“出版”一词才开始得到普遍运用。然而,关于“新闻”和“出版”两个概念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却少有梳理,由于所有对“出版”一词进行概念史梳理的研究都默认“出版”主要指书籍出版,导致过往对于“新闻”与“出版”的概念史讨论彼此孤立。而本文在探索“新闻出版”一词的概念史之前,势必需要将“新闻”与“出版”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词在早期的生成与流传过程中如何彼此交织做一个大致梳理。
从“新闻”和“出版”各自的特性上就不难看出二者的亲密关系:首先,新闻的主要载体——报纸,直到今天仍被定性为出版物的—种,因此广义的出版事业就包含新闻事业在内。其次,新闻和出版两种事业都涉及对纸张、油墨等资源的大量消耗,需要相关部门统一管理,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颁布过新闻出版业节约用纸的管理办法。最后,新闻与出版都面向大众,都能够产生较大的社会舆论效应从而影响政治,这也就使得官方向来重视这两项事业,常常将新闻和出版并置处之。
中国近代的新闻出版法制史进一步展示了中国语境下“新闻”“出版”两个概念的紧密关系。中国早期的新闻出版法规深受日本影响,“大部援据日本之出版法及著作权法”。但是,日本明治时期出台的新闻出版法规与中国清末民初的新闻出版法规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日本的新闻纸法规与普通出版物法规互相独立,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出台的《出版法》第二条还明确规定了新闻纸、杂志不受《出版法》规制,另有《新闻纸条例》约束定期出版物。中国在清末民初虽也和日本一样,单独为新闻行业颁布了《大清报律》《报纸条例》等新闻纸法规,然而无论是《大清印刷物专律》,还是1914年颁布的《出版法》,均对报界有约束力。1914年《出版法》第一条直接照搬了日本《出版法》所规定的管控范围,“用机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书图画出售或散布者,均为出版”,然而却并没有借鉴日本《出版法》第二条将新闻纸杂志划出此法管控范围,其第四条“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管警察官署”更是常常被作为报纸预检的依据。这种以《出版法》统摄新闻出版两界的做法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甚,1930年南京当局出台的《出版法》直接将新闻纸、杂志管控的具体条例写进了条文,彻底使新闻法规和出版法规合二为一。而此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再次修订的《出版法》延续了1930年《出版法》的结构。中国新闻出版法制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不断演变的过程,显示出近代中国官方从未将“新闻”与“出版”完全割裂开来,甚至有统一化、集约化的趋势。
近代官方新闻出版法规从未把“新闻”剥离出“出版”的指涉范围,但“出版”一词从其本身的概念上似乎先天与“新闻”彼此独立。目前查到民国最早收录“出版”一词的汉语词典《辞源》给予“出版”的解释为“用机械或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书图画出售或散布者,均为出版”,与1914年《出版法》及日本1893年《出版法》保持一致。然而在此之后的眾多词典中,“文书图画”多数演变成了“书籍图画”,甚至去掉了“图画”,仅保留“书籍”,新闻纸的出版则从未被特别强调为“出版”事业的一部分(见表1)。
与此同时,“新闻”和“出版”两个概念的相对独立也体现在行业主体的分立之上。尽管报纸一向被视作出版物的一种,但实际上的新闻行业主体主要是报社、通讯社,而出版行业的主体主要是出版社、书店、书局,二者从业态划分来看相对独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出版两行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泾渭分明,当时也有一些报社、期刊社、通讯社在主营报刊之余,下设出版部门进行图书出版,例如申报馆出版部、新评论社、上海通讯社、上海医学通信顾问社等,这些报馆、期刊社、通讯社也是近代图书出版的一类重要主体。此外,当时也有大型报社以“媒介集团”式经营着出版机构,例如申报馆经营着申昌书局、集成书局以及点石斋书局。这些证明了书报刊的生产在民国时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纠缠。
总的来讲,“新闻”和“出版”两个概念,定义上相互独立,却在中国实际的政治实践和行业实践中彼此纠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纠缠越来越显著。从上文民国时期新闻出版法制进程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在这个过程中,官方舆论政策的推动是关键性因素。
二、“新闻出版”最早的意涵:新闻纸出版
目前在中文世界里发现的最早的“新闻出版”字样,出现于1902年由作新社编译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大事记》一书,里面记录道:明治五年(1872年)5月29日,“由司法省,请许新闻出版人在讼廷傍听,且令揭载其记事”。据笔者查证,此处可能是译自1893年出版的指原安三所著《明治政史》,日文原书中就有“新闻出版”的字样,因此可以确定“新闻出版”一词引自日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新闻出版”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表达,意为“新闻纸出版”,而非今天我们熟悉的“新闻+出版”。
事实上,早在晚清时期,类似“新闻纸出版”的表达就已出现。1868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就将“to publish a newspaper”译作“出新闻纸”,将“the publication of a paper”譯作“出新闻纸之事”。然而,在“出版”一词从日文引进中国之后,“出新闻纸”就逐渐演变成了“新闻纸出版”以及“新闻出版”,而“新闻出版”一词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应是受到了日文语境的影响:在日文当中,“新闻”一词的含义与中文有所不同,实际上是中文里的“报纸”“新闻纸”,而“新闻”在日文中表达为英文news的片假名音译“二工一”。考虑到“出版”一词是纯粹的日文外来词,且“新闻出版”一词也是最早从日本流人中国的,因此早期“新闻出版”中的“新闻”含义为“新闻纸”就不难理解了。
民国早期大部分“新闻出版”的表达都是“新闻纸出版”,从英文译著中的“新闻出版”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现象,在笔者查到英文原文的五例译著(译文)中,仅有一例里的“新闻出版”指“新闻+出版”(见表2)。
此外还有部分中文著作出现“新闻出版”字样时标注了其英文表达,笔者共找到两处,其中一处意为“新闻纸出版”,一处意为“新闻+出版”(见表3)。
随着现代语词的流变,“报纸”一词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基本完全替代了“新闻纸”一词,相应地,“新闻纸出版”意涵的“新闻出版”也逐渐消失了。然而,这种表达实际上直到今天仍旧有留存痕迹,只不过“新闻”一词已被“报纸”一词完全取代,彻底演变为“报纸出版”。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还出台了《报纸出版管理规定》,这一规定直到今日仍然有效。
三、并列结构四字词“新闻出版”的形成
与上文中N+V主谓结构的“新闻出版”不同,现代中文常用的“新闻出版”一词是Nl+N2并列结构的词语。在中文世界中,最早将“新闻”“出版”二者并列起来的是1905年清末官学教科书《政治学》,该书由留日学生杜光佑、甯儒瑷根据日本政治学家小野壕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一书以及课程讲义整理编译而来,书中讲道:“舆论成立,有议会、新闻、出版、演说、谈话,各种之举动。”而后的几年时间里,《政治学大纲》出现了几个不同的译本,在此处的翻译均大同小异。类似的表达还在1908年2月5日《申报》刊发的《论说新岁读报律感言》一文中出现,该文言道:“试观欧美各立宪国其所恃以觇舆论者,不外议会新闻出版集会演说诸端。”这是目前发现中文中最早将“新闻”“出版”相并立的两例,可见,“新闻、出版”这样将新闻及出版并列起来的表达在中国的出现,应是西方政治思想引进中国的产物。
晚清民国时期,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引进的同时,中国的现代新闻、出版业也在不断发展,官方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控也在持续,这也就从多方面促成了“新闻”和“出版”两个概念的绑定。而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推动因素促成了“新闻出版”作为一个词语的生成。
(一)近现代汉语四字组合习惯的推动
笔者在中外文各大数据库进行了考证,均未在近代日文中发现并列结构“新闻出版”的表达,也未发现因此,并列结构的“新闻出版”一词应并非从日文直接引进,而是中国本土诞生的。从最初从日文引进的“新闻、出版”演变成复合词“新闻出版”,演变过程应是受到了中文语言规律的影响。
此前已有学者指出,“骈体性和四音节节奏倾向,决定了汉语必然会产生各种类型的并列四字组合,这是汉语的特点”,因此汉语中出现“新闻出版”这样的四字表达并不奇怪。此外,这种“2+2”式的复合词表达习惯,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日本语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相较于19世纪以前的汉语四字词语,日语2+2型四字词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两个二字语素均为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复合构词的抽象名词”,“二是经常以相同的二字语素为中心进行系列性构词”,这类词包括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等,而这些词大量流入中国后影响了中文的造词习惯,使得中国本土衍生出了大量仿造日式2+2式词的复合词。显然,“新闻出版”一词完全符合日式2+2型词语的特点。
中文“新闻出版”作为复合词的表达目前最早见于1929年朱鸿达《刑法新论》一书:“政治犯……凡是为了选举、结社集会和新闻出版等政治事项犯罪都包括在内。”这里的“结社集会”“新闻出版”明显都是复合词,这也证明了“新闻出版”应是语言习惯所推动形成的词语。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1946年1月国共签订的《和平建国纲领》中有一条为“废止战时实施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部分书籍在转载此条文时,将新闻、出版之间的顿号去掉了,直接表述为“废止战时实施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1946年李旭所编《政治协商会议之检讨》和1947年民治出版社所编《中华民国宪法及行宪法规》均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这种正式官方文件的转载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连写情况,可见,将“新闻、出版”直接连写为复合词“新闻出版”,应是中文表达里司空见惯的现象。
(二)官方宣传工作的集约化倾向促成新闻、出版合流
在“新闻”与“出版”两词组成并列词并流传的过程中,国民党新闻出版统制政策的推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新闻、出版两种事业的统一管理取向较之北洋政府更为明显,早在1930年《出版法》颁布前,1929年的《宣传品审查条例》就已规定报纸、通讯稿、定期刊物、书籍、戏曲、电影以及传单、标语等宣传品都必须统一接受中央宣传部的审查,由此促成了空前强劲的文化统制。在1934年1月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国民党政府通过提案要求宣传委员会“今后对全国之新闻界及出版界,应作有效之统制”,随即在当年6月和8月相继颁布了《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和《检查新闻办法大纲》,对《出版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了拓展,“统制新闻出版界”“新闻出版统制”一类的说法开始出现。随着新闻、出版在官方行政事业中的合流,“新闻出版”也小范围地进入了官方话语当中,例如1937年7月10日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提案审查委员分为六组,其中一组便是“新闻出版组”,其他小组包括“电影戏剧组”“美术音乐组”“教育组”等;再如1942年中央文化运动委員会主持的国家总动员文化界宣传周里,2月13日被定为“新闻出版日”。
除此之外,“新闻出版”一词也出现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地公开的经济志、年鉴中,主要是对地方新闻出版事业进行的统计。例如1935年的《中国经济志》在安徽歙县的统计,以及1936年在宁国、泾县的统计,均有一小节为“新闻出版事业”,其中,宁国、泾县仅有报社的统计,全志中并无图书事业的统计;歙县的新闻出版事业统计包括县志修纂,因此可以视作包含了书刊出版事业。1937年的《福建省统计年鉴》中也出现了对“文化与新闻出版事业”的统计,里面对福建省书店、杂志社、印刷所、报馆、通讯社的数量分别进行了统计;1946年的《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党务报告》中也有一小节为“整理衡阳长沙两市新闻出版事业”,对报社、通讯社的运营情况进行了统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志》在安徽休宁以及安徽寿县、霍邱、六安、合肥、舒城、霍山六县合编本中,在相同的位置使用的是“出版事业”一词;在对浙江嘉兴、平湖进行统计时使用的是“新闻事业”一词,而这几个地方的统计情况与宁国、泾县的情况一致,该部分仅有报社的统计,全志并无图书事业的统计。从这些经济志的具体内容看,“新闻事业”“出版事业”“新闻出版事业”三个概念实际上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些地方实际上只有报社和通讯社,没有书局和出版社。例如浙江平湖共有4家日报社和1家通讯社,并不见图书出版;再如安徽寿县、霍邱、六安、合肥、舒城、霍山六县共统计出报纸9种、杂志1种,亦不见图书出版。从这里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基于有限的行政资源,对新闻和出版事业进行了集约化管理,这一点和国家层面新闻与出版的合流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与此同时,显然新闻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脱离了出版事业的指涉范畴,且相比于普通出版事业成了更具普遍性、重要性的事业。
(三)全球新闻自由浪潮的影响
“新闻出版自由”至今仍是一个常用概念。上文中提到的“新闻出版”知识图谱论文,对围绕着“新闻出版”一词的研究进行了高频词分析,“新闻出版自由”也在里面。虽说频次排名较靠后,却是少数的不带有行政导向的高频词汇。或许从这里可以推知,在“新闻出版”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除官方所起的主导作用之外,新闻出版自由浪潮也可能是一个推动因素。
既有的研究已经揭示“出版自由”一词最早出现于1899年梁启超的《自由书》中,此后成为英文“freedom/liberty of the press”的通用翻译;而“新闻自由”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新闻自由”(freedomof information)运动传入国内之后。相比“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两个词,“新闻出版自由”在民国时期的运用要少得多,但是这些零星的“新闻出版自由”的表达展示了“新闻出版”一词形成的又一推动因素。
中文中的“新闻出版自由”目前最早见于1926年出版的《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一书,然而这里的“新闻出版自由”仅被作为一个细分图书门类而存在,没有解释其含义,也无从溯源,很大概率表示的是“新闻纸出版自由”的意思。而中文文献里再次出现“新闻出版自由”一词已是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根据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新闻出版”一词出现的语境,可推知“新闻出版自由”概念的生成有两个推动因素:
第一个推动因素是“新闻自由”一词在国内的出现。1945年前后,美国在全球发动新闻自由运动,彼时正逢中国抗战胜利,国内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战时新闻出版统制的声音巨大,因此“新闻自由”概念在中国流行了起来,并逐渐取得了和“出版自由”概念几乎同等的地位,“新闻出版自由”一词作为二者的结合体也应运而生。比如,1945年抗战结束后,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许孝炎向新闻界承诺,要“根据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之原则,将现行出版法所有条规,重新加以裁废或修正”,《时事新报》报道时副标题就起为“许谈实现新闻出版自由”。
第二个推动因素对“新闻出版自由”一词的形成则更加直接。1946年9月,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向联合国提交了申请,希望联合国方面可以修订关于促进新闻出版自由的公约(a convenant toestablish worl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of thepress)。“Freedom 0f Information and of thePress”即被翻译为“新闻出版自由”。而到了1947年1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回应了美国方面的申请,正式成立了新闻出版自由小组(Subcommission。n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of the Press),“新闻出版”一词进入了联合国官方话语体系,“新闻出版”的运用由此被大大推动。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直到今天仍旧是常被混用的概念,而这样的混淆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出现。上文中提到的许孝炎承诺修订《出版法》的事件,部分报纸将“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之原则”记载为“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原则”,而联合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小组也被诸多报纸写成“新闻自由小组”,这种正式事件的新闻报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混淆,就更不用提日常使用时的混淆了。从这些词语使用的具体语境可以部分推知混用的原因:这几个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的运用,基本都是为了反抗国民党新闻出版检查、保障新闻出版界人士的权益,加上近代中国“新闻”和“出版”两个概念从未彻底泾渭分明,因此几个概念的混用也就十分正常了。联系到上文中《中国经济志》中“新闻事业”“出版事业”“新闻出版事业”混用的情况,可知“新闻出版”这个概念同时作为“出版”“新闻”的同义词,将“新闻”“出版”两个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扭结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作为行政话语的“新闻出版"
民国时期,虽然偶尔能在官方活动的记载中看到“新闻出版”字样,但总的来讲“新闻出版”还是属于习惯用语的范畴。新中国成立后,地方上跟随中央新闻总署、出版总署的设立,纷纷设立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处,“新闻出版”由此正式进入行政话语体系,尤其随着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其被推动成为新闻出版学界业界习以为常的概念。而在民国时期,我党在新闻出版管理工作上显著的集约化倾向,以及推动新闻出版自由的激进态度,都促成了“新闻出版”概念的生成与流传。
首先,民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和出版事业的管理上,已经表现出了显著的集约化倾向。从管理机构来看,曾经统领过新闻、出版的领导机构先后包括1937年复立的中央党报委员会、1939年成立的中央出版发行部及后来由此改组的中央出版局,以及1943年成立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等;从行业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曾在抗战期间为集中人力物力,将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并入华北新华日报社,使得华北新华日报社肩负着出版报纸、图书的双重任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北平之后,在文化接管委员会下设了新闻出版部,类似地,上海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也在文化管理委员会下设了新闻出版处。这几方面说明了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出版”两项事业已是深深一体同构,甚至“新闻出版”已被中国共产党作为行政机构名加以运用,这为后来新中国“新闻出版”概念运用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其次,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中国共产党是将“新闻出版自由”观念弘扬得最为激进、激烈的力量之一。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敦促国民党“立即无保留的废除一切新闻、出版、戏剧、电影及邮电等检查制度”,促成了《和平建国纲领》内相关条款的达成;解放战争时期更是有大量书籍和文章控诉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垄断和压制,例如军政大学政治部所编《现中国的两种社会》中控诉国民党当局“对于人民的文化新闻出版事业”进行“严厉的统制”,作曲家光未然的《蒋介石绞杀文化》一书更是单独拿出一整章来控诉“蒋介石绞杀新闻出版事业的真象”。对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意涵,中国共产党也结合阶级论进行了积极改造,《华商报》上一篇作者署名为“星火”的《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文章可以代表共产党的立场:“要就是适于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大众的自由,要不就是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大地主和买办资本家的自由……如果说过去存在新闻出版业的污垢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残酷的摧残与统治,由国民党政府负其全责;那么,今后在新闻出版自由开放了以后再有什么错误就由新闻从业员本身负责了。”
由此可見,今天的“新闻出版”能够成为常用概念,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基础。而近几十年中国的传媒与信息领导机构的变迁中将新闻、出版、广电等传统传媒事业不断集约化管理的趋势,显然又是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出版业管理一贯的集约化风格的延续,而这和“新闻出版”在今天成为常用语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五、总结和讨论
近代中文中“新闻出版”虽然算不上一个很常用的词,但这一概念确实在民国时期就已经生成。“新闻出版”一词所具有的鲜明的行政倾向,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显露端倪。“新闻”和“出版”在中文中最早被并列,本就是西方现代君主立宪政治学说引进中国所产生的结果,而“新闻”和“出版”合并为并列结构复合词的过程,更是深深受到了国民党文化统制的影响,同时正是民间反抗新闻出版统制、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过程,“新闻”“出版”的合流被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在宣传事业上历来有着将新闻、出版事业集约化管理的倾向,加之中国共产党深度参与到了20世纪40年代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浪潮中,加速了“新闻出版”概念的流传,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乃至近几十年把“新闻出版”设置为行政机构名,则直接使得当今“新闻出版”成为常用概念。总的来讲,“新闻出版”当今的用法和清末民初“新闻纸出版”意涵的“新闻出版”没有承继关系,但基本承继了1930年前后开始出现的并列结构四字词“新闻出版”的意涵。
“新闻出版”一词之所以成为中文语境中的特有概念,是因为中国“新闻”和“出版”两个概念历来高度合流,而这和中国从近代以来延续至今的政治体制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潘祥辉曾经根据历史学者萧功秦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划分的六个阶段,总结了相对应的六种媒介体制,其中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开始,分别经历了威权主义模式、计划主义模式和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这几种模式都强调党管传媒的重要性,都重视政府对媒体的管控,都不同程度地将媒体看作宣传工具,而报纸和图书等大众媒介在近代又长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这自然促使政府基于有限的行政资源对新闻和出版等事业进行严格的集约化而非分而治之的管理。中国语境下“新闻”和“出版”的合流,以及中文中“新闻出版”概念的生成,正得源于此。
通过对近代文献中“新闻出版”一词用法和语境的梳理,可以看到“新闻”“出版”两个概念之间的扭结,从而厘清“新闻出版”一词的概念演进历史。在此之外,或许可以为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概念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几个概念在中国语境下本就同义,在中国“新闻”“出版”两概念常常合流的情况下,是否必须要按照西方社会中新闻、出版分立的预设前提,严格地来探析各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呢?或许这是梳理“新闻”“出版”两个概念关系后可以继续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