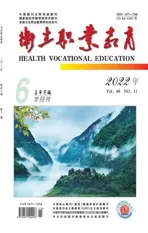情绪与社交孤独对大一新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2022-06-17蔡瑶瑶占丹玲王礼申
蔡瑶瑶,占丹玲,王礼申
(1.韶关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2.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韶关 512126)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是指个体将过多的时间消耗在网络上而产生的一种心理障碍,会对个体的生理、心理、社会功能造成不良影响[1]。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是生理、心理与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2-3],其中心理因素与个体的疏离感[4-5]、孤独感[6-7]、生命意义感[8-9]关系密切。研究显示,孤独感和生命意义感缺失是出现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原因之一,孤独感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10],生命意义感可以负向预测个体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11]。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自身存在意义和目的的主观体验,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12]。生命意义感的界定可以从目标(给予个体方向感与价值感的目标)和含义(生命意味着什么)两方面进行。Steger整合了生命意义感的目标性和含义性,认为生命意义感包括意义寻求(动机维度)和意义拥有(认知维度)两部分[13]。其中,意义寻求是指个体付诸行动实现生命目的的尝试,意义拥有指的是个体对于生命意义感的理解[14]。研究显示,生命意义感缺失与个体的疏离感[15-16]、孤独感[17-18]、网络成瘾[19]呈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个体体验到的消极情绪越强,就越难体验到生命意义感,越容易出现网络成瘾。
Davis提出了解释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20],认为个体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是生活事件(压力源)、个体易感因素与适应不良认知综合作用的结果[21-23],其中适应不良认知是核心影响因素。基于此,我们认为个体在归属感受挫(孤独)时,若寻求网络途径缓解负面情绪(意义寻求),或将网络内容带来的积极体验视为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价值(意义拥有),以补偿孤独引发的生命意义感匮乏,则会影响个体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我们认为孤独感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也可以通过意义寻求和意义拥有这两个中介变量,影响个体的孤独感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粤北地区两所高校大一新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1年6月在腾讯问卷平台进行调查,共回收问卷650份,有效问卷626份,有效回收率为96.31%。其中,男生389人(62.1%),女生 237人(37.9%);年龄 17~20岁,平均(19.21±0.72)岁。
1.2 工具
1.2.1 情绪与社交孤独量表[24]由Vincenzi等编制,包括情绪孤独与社交孤独两个维度10个题目。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分数越高则意味着孤独体验越强。本次调查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6。
1.2.2 人生意义问卷[25]由Steger等编制,王孟成等修订,包括意义拥有与意义寻求两个维度10个题目。采用李克特7级评分法,分数越高则代表生命意义感越强。本次调查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1.2.3 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26]由雷雳等编制,包括突显性、耐受性、强迫性上网、心境改变、社交抚慰、消极后果6个维度38个题目。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题目均分≥3.15分为网络成瘾群体,题目均分<3.00分为正常群体,其余为网络成瘾边缘群体。本次调查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积距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使用AMOS 23.0进行拟合度检验,中介检验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区间估计,选择95%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样本量为 5 000 次,检验水准为α=0.05(双侧)。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共12个,其中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3.84%,低于40%的临界标准,即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粤北地区大一新生情绪与社交孤独量表得分为(26.05±5.62)分,人生意义问卷得分为(49.95±9.68)分,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得分为(2.32±0.72)分。按照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界定标准,分数≥3.15为网络成瘾群体,有75人(11.98%);分数<3.00为正常群体,有502人(80.19%),3≤分数<3.15为网络成瘾边缘群体,共49人(7.83%)。
2.3 大一新生情绪与社交孤独、生命意义感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间的相关分析
Pera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粤北地区大一新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与人生意义问卷及其维度得分呈负相关关系(r=-0.104~0.437,P<0.001),与情绪与社交孤独量表及其维度得分呈正相关关系(r=0.272~0.384,P<0.001);情绪与社交孤独量表和人生意义问卷及其维度得分呈负相关关系(r=-0.482~-0.273,P<0.001,见表1)。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r值)
2.4 意义寻求与意义拥有在情绪与社交孤独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和情绪与社交孤独、生命意义感显著相关,满足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前提条件。根据我们的假设,我们尝试以情绪与社交孤独为自变量,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为因变量,以意义拥有与意义寻求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初始模型,并通过修正指数得出最终模型。最终结构模型拟合指数:χ2/df=3.077,GFI=0.938,AGFI=0.915,NFI=0.940,IFI=0.925,TLI=0.948,CFI=0.958,RMSEA=0.058,SRMR=0.061,数据显示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模型合理(见图1)。

图1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模型
中介检验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区间估计,样本量选择为5 000,并以95%CI是否包含0作为中介效应显著与否的判断依据,若95%CI包含0,则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反之则显著。数据结果表明,情绪与社交孤独→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 95%CI为(0.272~0.562),不包含 0,表明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412,占总效应的77.59%);情绪与社交孤独→意义拥有→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95%CI为(0.084~0.266),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171,占总效应的32.20%);情绪与社交孤独→意义寻求→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95%CI为(-0.100~-0.018),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53,占总效应的9.98%)。即情绪与社交孤独可以通过意义寻求间接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产生正向影响,可以通过意义拥有间接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产生负向影响(见表2)。

表2 生命意义感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n=626)
3 讨论
3.1 大一新生网络成瘾现状不容乐观
本研究显示,被调查的粤北地区大一新生群体网络成瘾检出率为 11.98%,略高于以往新生检出率(5.53%~8.86%)[7-8,27]。互联网已经融入当代青少年的生活,其对网络的使用主要受网络匿名性、便利性、逃避现实的自身特点[28]以及外界环境约束、自制力、心理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从高三高度紧张的氛围转换到大一相对轻松的氛围,最大的变化之一即为外部环境约束基本解除,此时个体内在的自制力与心理需求成为网络使用的重要影响因素。自控力不强[29]与以网络内容满足心理需要[28]会显著增加互联网的使用。加之本次调查时恰逢广东省各高校仍处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节点,“社交隔离”“非必要不外出”的管理措施也会在客观上降低个体现实中与外界接触的频率,进而影响个体的网络使用情况,导致网络成瘾检出率较高。
3.2 大一新生情绪与社交孤独负向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本研究发现,粤北地区大一新生情绪与社交孤独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情绪与社交孤独可以正向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与以往的结论一致。适应大学生活是每个新生的重要任务,良好的适应结果意味着更少的孤独感[30]与更高的自我价值,不良的适应则意味着心理与行为问题发生[31]。赵陵波等[6]通过元分析指出孤独感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存在中等相关关系,王鹏等[7]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得出孤独感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可以双向预测,郑童等则认为孤独感是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诱发因素[32]。
3.3 意义拥有与意义寻求在大一新生情绪与社交孤独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情绪与社交孤独可以通过意义寻求间接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意义拥有间接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产生负向影响。这与姚梦萍等[33]的研究结果一致,与黄时华等[8]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姚梦萍等的研究显示,无聊感会通过意义拥有对手机依赖行为产生负向影响;黄时华等的研究显示,正念水平会通过意义寻求可以负向预测网络游戏成瘾,意义拥有的中介作用则不显著。我们认为这种不一致主要是生命意义感中意义寻求和意义拥有两个维度的动态关系引起的。具体而言,意义寻求与意义拥有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生命意义感匮乏可能导致意义寻求(负相关),意义寻求也可能导致意义体验增多(正相关)[34],个体不同的生命意义感与对生活的期望状态可能起到了调节作用。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孤独感会影响个体归属与爱的需要。这种基本需求的缺乏会降低个体的生命质量,进而影响个体的生命意义感[35]。获取和维持生命意义感是个体的基本动机[12],当个体处于生命意义感匮乏状态时,会激发个体产生寻求意义的动机,引导个体寻求那些让自己可以体验到价值感和生命意义感的事情。网络的便捷性可以在疫情防控期间给个体带来即时的积极反馈,可以使个体在生活中体验到浅层的满足感与价值感。因此,这种偏向动机性质的意义寻求可以在情绪与社交孤独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间发挥中介作用,增加个体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这种过多的采用网络反馈缓解孤独感和生命意义不足的认知方式,与Davis认知—行为模型中的非适应认知内在是一致的[20]。
意义拥有是个体对于生命目的的理解和认识,属于生命意义感的认知维度,反映的是个体对自己内在价值的认识。因网络的虚拟性和工具性特点,网络使用正常群体可以客观评价其重要性与价值,不会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即孤独感导致的生命意义匮乏状态会激发个体寻找有意义的事情,但在个体的价值评价中,网络所能提供的深层价值感有限,无法从认知层面成为具有意义感的事情。因此,这种偏向认知性质的意义拥有可以在情绪与社交孤独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间发挥中介作用,减少个体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这也符合意义疗法理念[36]。
因此,对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干预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1)减少通过网络途径满足浅层次需求的发生,可以降低意义寻求在孤独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路径中的正向影响。通过增加外部环境约束(如课堂纪律、宿舍公约、互相监督等)与培养良好的自制力,减少过多的不合理的网络使用行为。(2)提高对于网络使用的理性认知可以从深层减少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发生,可提升意义体验在孤独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路径中的负向影响。认清网络的工具属性与无节制使用的危害性,从认知、情感两方面树立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增强意义体验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