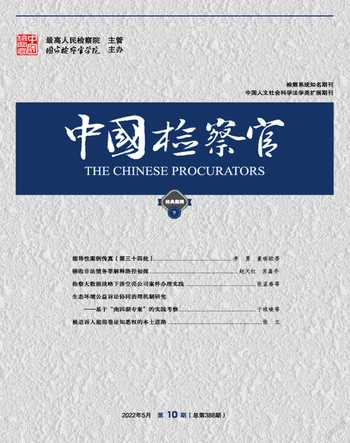被追诉人庭前卷证知悉权的本土进路
2022-06-14张立
张立
摘 要:美国布雷迪和桑切斯案肯定了检察官有义务在与被告人达成认罪答辩之前向其披露控方掌握的重要辩护证据,这对于我国保障认罪被告人的知情权具有借鉴意义。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应当积极探索运用检察机关主导下的认罪认罚具结前的证据开示制度,来构建我国的被追诉人庭前卷证知悉制度。
关键词:庭前卷证知悉权 认罪认罚 证据开示
一、问题的提出——保障被追诉人庭前卷证知悉权
相较于辩护律师的阅卷权等辩护权利保障日益完善的现实,我国的司法实践对于被告人的庭前阅卷权或称庭前卷证知悉问题关注较少。由于被告人的被追诉地位,相较于委托辩护权,其自身的当事人地位和直接行使辩护权的保障容易被忽视。事实上,保障被追诉人庭前卷证知悉权是确保公正审判、实现有效辩护的应有之义。首先,被告人的辩护权不应也难以被律师辩护权取代,只有被告人在庭前得以获悉指控的事实和依据,才更有利于实现有效辩护。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协商合作式刑事司法的本土范式,给传统的对抗式司法模式带来了深度转型和变革,也给刑事司法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确保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及认罪认罚的真实和自愿性,提升控辩协商的质效是适用的基础和前提。作为以辩诉交易作为刑事案件主要审理方式的美国,对于向被告人证据开示的问题也经历了一系列探索和变革,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具有借鉴和研究价值的样本。
二、美国刑事司法关于向被告人开示证据的判例和立法
(一)美国无罪证据强制披露制度的确立
在美国的普通法传统中,刑事被告最初并没有窥探控方证据的权利。20 世纪60年代,以布雷迪案为转折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判例法形式确立了无罪证据开示制度。[1]
[案例一:布雷迪诉马里州案[2]]1958年,被告人布雷迪(Brady)与鲍勃里特(Boblit)两人将被害人带到森林后将被害人勒死。法院对布雷迪与鲍勃里特进行了分案审理,审理焦点集中在“谁直接实施了杀害行为”。布雷迪供认他确实参与了谋杀,但辩称鲍勃里特直接实施了杀害行为。两人均被认定一级谋杀成立并判处死刑。布雷迪在被定罪后,发现检察官扣留了一份鲍勃里特承认自己才是实施杀害行为的人的书面陈述,而并没有将该陈述开示给他。布雷迪认为自己本可以在庭审中利用鲍勃里特的供述来影响陪审团做出不同的裁决,遂申请重新审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3年的判決中支持了布雷迪的主张,认为“在辩方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如果某证据对定罪或量刑有实质的重要作用,则控方隐瞒这个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就违反了正当程序,不论控方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此判例确立了“布雷迪规则”,规定了对重要辩护证据的强制性披露,即检察官基于辩护方的请求,应将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或罪轻证据向被告人进行开示,否则就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被告人可以据此申请进行重新审判。
(二)“布雷迪规则”在认罪答辩中的进一步应用
“布雷迪规则”系审判程序的产物,是否应当适用于辩诉交易程序?换言之,在被告人决定是否接受有罪答辩前,其是否有权要求控方开示辩护证据。
[案例二:桑切斯诉美国案[3]]1995年的桑切斯诉美国案中,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肯定的回应。1989年,在两名政府机密线人认定桑切斯(Sanchez)为毒贩后,联邦调查局开始对桑切斯进行调查。线人将其介绍给了伪装成富商的FBI探员卡森。经过谈判,桑切斯同意向卡森出售 24 公斤可卡因。在桑切斯等人将可卡因运送到指定地点后,卡森和洛杉矶警方逮捕了桑切斯。后桑切斯接受了认罪答辩并因贩卖毒品罪名被判处235个月的监禁。后桑切斯上诉要求撤销判决和认罪,称政府未能披露交易上家作为警方线人的身份,违反了根据布雷迪规则披露无罪信息的义务,并称如果知道上述信息,其不会接受认罪而会选择接受审判。上诉法庭在判决中肯定了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之后如果发现控方隐瞒了辩护证据,有权以有罪答辩违反自愿原则为由申请答辩无效。判决认为,通常情况下接受有罪答辩的被告人不能提出违宪的请求,但在控方违反“布雷迪规则”时应有例外。判决分析了控方隐瞒辩护证据和被告人有罪答辩自愿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如果控方隐瞒了重要的辩护证据材料,则其有罪答辩并非自愿、理智。因为被告人是否作有罪答辩的决定往往受到其对控方案件评估的影响,如果其进行有罪答辩时不知控方所隐瞒的重要证据,则放弃宪法接受审判权利的决定不能视为自愿和理智的。而且,如果被告人不能在有罪答辩之后基于“布雷迪规则”提出违宪审查申请,则检察官将来就可能故意隐瞒辩护证据以取得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所以,判决认为被告人可以援引“布雷迪规则”质疑有罪答辩的自愿性。然而,在有罪答辩程序中,如何适用“布雷迪规则”?隐瞒证据材料的重要性如何检验?上诉法庭认为,在有罪答辩之下,检验证据重要性的客观标准就在于被隐瞒证据所可能具有的说服力以及对辩护的实质重要性。“如果没有隐瞒相关的重要辩护材料,被告人就不具有作有罪答辩的合理可能性,而是会选择接受审判的话”,那么这一被隐瞒的证据就是重要的。最终,上诉法庭以线人身份不属于布雷迪证据,且对桑切斯的认罪决定并不具有决定作用为由驳回了其上诉动议。该判决事实上确立了检察官具有在与被告人达成有罪答辩之前向其披露重要辩护证据的义务,并设定了被告人有权据此申请有罪答辩无效的法律后果,阐述了重要辩护证据的判断标准。桑切斯和布雷迪案是美国证据开示制度发展中重要的判例法,也对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被告人知情权保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关于被追诉人庭前卷证知悉的域外立法趋势
除判例法外,美国各州在证据开示立法上仍然存在差异,但多年来的普遍改革趋势是迈向更早期和更全面的证据开示。最近具代表性的改革经验来自于纽约州于2019年通过的《证据开示司法改革法案》,采纳了特别早期开示论,对于占绝对多数的辩诉交易案件进行了特别规定:如果控方提出了认罪协议并设定认罪协议期限,控方必须向辩方开示其控制或持有的、且依首次开示义务应当开示的证据。[4]美国的司法实践并非孤例,逐步承认并扩大被追诉人的卷证知悉权已是趋势,否认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摒弃。目前世界范围内关于保障被追诉人证据知悉主要存在卷宗披露制度与证据开示制度的两种模式,分别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以德国为代表的阅卷模式,承认被追诉人是阅卷权的权利主体,但是将其阅卷权与辩护人阅卷权进行了区别对待。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瑞士、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刑事诉讼法均已明确承认被追诉人阅卷权。[5]无论是阅卷模式还是证据开示模式,其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被追诉人在庭前对指控证据的知悉权。
三、我国被追诉人卷证知悉权的司法现状审视
(一)被追诉人阅卷权之立法阙如
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完整的阅卷权,但并没有明确地同时赋予给被追诉人,只是间接规定了辩护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向犯罪嫌疑人“核实证据”的权利。关于该“核实证据”权利在理论和实务界存在较大分歧,虽然也存在对于律师核实证据“等于认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阅卷权”乃至“表明律师可以将案内不同证据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观点,但也遭到了许多权威学者的质疑和反对,认为“难以从现行规定中直接导出“被告人阅卷权”[6],并主张对辩护人告知的证据范围加以合理限制。[7]概言之,目前的刑事立法对于辩护人核实证据的方式和尺度并不明确,更不支持赋予刑事被告人以直接完整的阅卷权。
(二)间接阅卷的现实困境
目前借助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实现间接阅卷来满足被追诉人的知悉权仍存在诸多困境和不足。第一,相当部分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并未委托辩护人,只能指派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虽然“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12条规定了值班律师自审查起诉起可以阅卷,但明显缺少制度激励和便利。值班律师目前的工作常态是需要在短时间内为多名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且身份具有临时性,往往异化为具结见证人的角色。因此,被告人想要在决定是否认罪认罚之前通过值班律师了解案卷中的指控证据往往并不现实。第二,对于委托辩护人的案件,目前的间接阅卷机制仍有不足。根据前述,目前的立法对于辩护人“核实证据”权利的范围和尺度仍不明朗,加之违法违规的执业风险的高压之下,辩护人实际操作仍存有顾虑和障碍,犹如带着“镣铐的舞蹈”。且辩护人在阅卷后根据自身理解进行证据核实,辩护效果肯定不如辩护人和被告人在各自均充分了解卷证情况下的沟通协商。
(三)被追诉人庭前卷证知悉权的肯定
虽然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并未肯定被追诉人的直接阅卷权,但最高司法机关对于被追诉人庭前卷证知悉权的肯定态度逐渐明朗。《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第19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组织展示证据的,一般应当通知被告人到场,听取被告人意见”,明确了庭前会议展示证据时被告人具有当然的到场权。《指导意见》第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探索证据开示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及自愿性”,明确肯定了被追诉人庭前对于指控证据的知情权,相较庭前会议提前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并通过检察机关主导的证据开示予以保障。
四、认罪认罚制度语境下卷证知悉权的本土构建
(一)卷证知悉权对认罪认罚的功能补足
1.保障认罪认罚的真实和自愿性。认罪认罚的灵魂是自愿和真实性。选择认罪可视为被追诉人作出的重要決策,那么相关的证据材料便是决策的信息基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是盲目的甚至可能是为摆脱不利处境违心做出的。数据显示,1989年到2003年间美国已被平反的刑事错案中,有20%的无辜被追诉人进行辩诉交易,而证据信息不对称是其选择非自愿认罪的重要原因之一。[8] 因此,在侦查终结后允许被追诉人阅卷,实际上是向其提供作出认罪决策所依据的必要信息,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充分权衡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真正自愿的选择认罪认罚,最大限度地遏制冤错案件的发生,也能降低之后反悔和撤回的风险。
2.提升认罪认罚教育转化的质效。目前,检察机关主要通过在看守所播放认罪认罚宣传片、讯问时释明法律规定和政策精神及分析利害关系等途径开展认罪认罚的教育转化。而赋予被追诉人庭前的卷证知悉权,可以使其对指控证据体系有清楚的评估,明晰其被定罪判刑的心理预期,消除侥幸心理,敦促其尽早彻底的认罪认罚,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繁简分流和程序从简,缓解案多人少的压力。
3.提升控辩协商的实质化水平。只有充分有效的控辩协商,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控辩合意,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法官对量刑建议的信任和尊重。当前司法实践中形成和运行的量刑协商过程主要表现为检察官单向的听取意见层面,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在只载有认定罪名和建议刑期的具结书上签字捺印。现行方式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协商的交互性不强,容易流于过程缺失和无的放矢之弊,而究其实质则是被追诉方的信息壁垒和弱势地位。因此,在协商程序中嵌入卷证信息披露、展示程序,改善被追诉人的信息不对称地位,缩小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情节的认知差距,可以增强协商的交互性和针对性,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回转。
(二)证据开示制度的再引入
虽然域外对于保障被追诉人卷证知悉权的思路值得借鉴,但如何在我国现行司法语境下具体实现却非易事。嫁接被告人直接阅卷制度却可能会产生“南橘北枳”的困惑,且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并不支持赋予被追诉人直接阅卷权。相较而言,美国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主导下认罪答辩前的证据开示确实具有借鉴的价值。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提起公诉时全卷移送的规定,本使得证据开示一度淡出,但认罪认罚制度的全面铺开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再引入提供了有利契机。在目前认罪认罚制度已普遍适用的情况下,可以探索完善检察机关主导下的认罪认罚具结前的证据开示制度,来保障我国的被追诉人庭前卷证知悉权利。具体可做如下制度构建:
1.检察机关主导的依职权证据开示。检察机关主动开示证据而非依申请开示是充分发挥其刑事诉讼审前主导地位的体现。启动开示的范围是经审查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经构成犯罪的案件。开示时间应当选择在检察官对案件证据已经审查完毕之后、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前。此外,根据双向开示的原则,辩方也应当向检察机关开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而不在卷的相关证据,但相较于检察机关,辩方的开示不是必经程序,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开展。
2.以证据开示清单为载体的全面开示。开示证据可以以证据开示清单为载体,包含证据名称、证据证实的主要内容等。证据开示可以参照庭审举证的方式进行。检察机关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出示包括不利于定罪证据在内的全部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以及事关量刑情节轻重的证据。对于涉及侦查秘密、个人隐私、证人安全等不宜向犯罪嫌疑人出示的证据,可以决定不予开示或隐去相关内容后出示。
3.证据开示的流程操作。检察官开示证据时应当通知值班律师或辩护人在场。证据开示也应实行繁简分流,在犯罪嫌疑人已经主动认罪的案件中,检察官可以简要宣读、出示或交由犯罪嫌疑人自行阅读。对犯罪嫌疑人尚不认罪的案件,检察官可以重点对定罪证据进行详细具体出示如宣读同案犯供述、证言笔录、播放监控视频等视听资料、展示电子证据等。检察官可以在证据开示的同时对证据的关联性、证明作用及辩方的疑问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开示结束后将开示清单交由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签字后归档,待提起公诉时一并移送法院。
4.证据不当开示的救济。检察机关未履行证据开示义务,法院应视情况认定被告人认罪认罚不具有自愿和真实性,从而否定认罪认罚具结书和量刑建议的效力。对检察机关未履行开示证据职责的,法院可求公诉人当庭出示,开示后被告人仍无异议的可以认可原具结书的效力。对被告人提出异议或发现检察机关隐匿、伪造或歪曲证据诱导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则应当及时依法转换诉讼程序,按照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五、结语
正视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逐步扩大其诉讼权利已是世界范围的潮流。积极应对认罪认罚改革带来的协商合作型刑事司法转型,引入由检察机关主导的主动证据开示制度并辅之以本土化改造,结合辩护人的证据核实权利,来构建我国的被追诉人庭前卷证知悉制度,既是对世界潮流的回应,也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审前主导地位的有力举措,值得积极探索和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