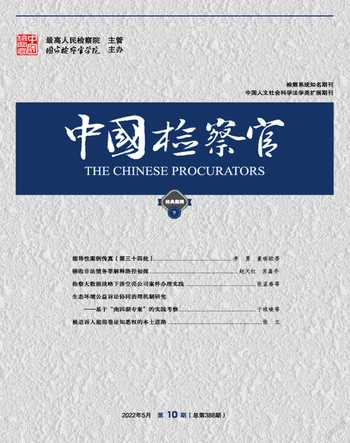仅变更罪名是否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2022-06-14张艳青
张艳青
一、基本案情
[案例一]2019年6月,杨某某以820元人民币从淘宝购买2只凤梨小太阳鹦鹉。同年10月,杨某某又以800元人民币从咸鱼平台购买2只蓝化小太阳鹦鹉。2020年3月12日,杨某某在将上述4只小太阳鹦鹉以人民币每只800元的价格出售给赵某某。经鉴定,上述4只鹦鹉均为暗色锥尾鹦鹉,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每只价值人民币10000元。2020年3月14日,杨某某因涉嫌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取保候审。2021年3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以杨某某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同月19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杨某某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7月6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判决杨某某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罚金人民币2000元。
[案例二]2021年2月18日,张某某以人民币7500元的价格向张某(另案处理)出售陆龟1只。经鉴定,该陆龟为辐纹陆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核算价值为人民币5000元。2021年7月6日,张某某因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刑事拘留。2021年9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以张某某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21年10月15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某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同月20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张某某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2000元。
二、分歧意见
行为人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41条第1款。在该款未作修正的情况下,2021年3月1日“两高”出台并施行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七)》)对该款罪名由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罪名调整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那么,对于2021年3月1日之前发生的此类犯罪行为,究竟是适用旧罪名“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还是适用新罪名“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即便在同一法院,由不同法官办理也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判决结论。
“肯定说”观点认为,罪名属于刑法规范的一部分,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各级司法机关在起诉、判决时适用司法解释明确的罪名,法律文书必须使用准确的罪名。罪名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而且,我国刑法条文中也有直接指称罪名的情形,如刑法第382条的贪污罪。因此,罪名的变更涉及刑法溯及力问题,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否定说”观点认为,罪名不属于刑法规范的一部分,对其适用只是为了方便对行为人的定罪处罚,并不直接影响行为人的处刑方式或刑期长短,罪名只不过是最高司法机关出于司法辦案方便而对刑法规范中具体犯罪罪状的高度概括,类似于具体犯罪的“代号”。罪名并不能完全包含具体犯罪罪状的全部特征。因此,单纯罪名的变化,不涉及对行为人处刑轻重的比较,不属于刑法溯及力的适用范围。
三、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否定说”的观点。罪名变更常常伴随着罪状与法定刑的变更,但罪名的确定、变更、适用具有独立的形态,不能与定罪混淆了概念。能否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关键看具体罪状与法定刑是否发生变化,而在罪状与法定刑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单纯罪名的变更本身并不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案例中,对于发生在2021年3月1日之前的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应当适用新罪名,即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一)罪名的变更与罪状、法定刑的变化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二者不能混同
从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与两高出台的关于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来看,罪名的确定、变更往往伴随着刑法修正案的颁布而出台,绝大多数罪名依附于罪状、法定刑的变化而变更,以至于很容易将罪状、法定刑变化所产生的溯及力问题误认为是罪名变更所导致的。因此,要弄清罪名的溯及力问题就必须明确罪名变更与罪状、法定刑变化的关系。笔者认为,虽然罪名变更与罪状、法定刑变化具有紧密的依附性,但二者仍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
首先,罪状、法定刑的变化并非必然导致罪名的变更。罪名是对犯罪罪状最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对罪状的描述不能做到面面俱到,罪状和罪名的关系好比内容之于标题。如果刑法修正案对一些犯罪罪状或法定刑作了重大调整,原罪名已无法涵盖现有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则有必要对原罪名作相应调整,但如果罪状、法定刑的变化并未超出罪名所囊括的范围,就没有变更罪名的必要。如《刑法修正案(十一)》调整了30个个罪的罪状及法定刑[1],与之配套的《补充规定(七)》对此变更了6个罪名,而其余24个个罪并未因罪状及法定刑的调整而变更罪名。
其次,罪名变更可单独存在。刑法修正案未对刑法分则具体罪状作出调整,但是原罪名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及时作出调整。正如两则案例中所涉及的刑法第341条第1款,《刑法修正案(十一)》并未对其作出调整,但《补充规定(七)》将该款的罪名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调整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这种情况下,罪状、法定刑没有变化,只是罪名发生了变化,罪名的变化与罪状、法定刑的变化处于分离的状态。
最后,在罪状、法定刑发生重大调整而罪名随之变更的情况下,罪名变更的本质在于罪状、法定刑的变化。此时所产生的刑法溯及力适用问题实质上是罪状、法定刑变化所引起的,因为罪状、法定刑变化会直接引起刑法处罚范围的扩张或者限缩从而影响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换句话说,不管罪名是否变更,在罪状、法定刑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产生刑法溯及力的适用问题。
(二)罪名的确定、变更、适用与定罪量刑有本质区别
长期以来,理论上之所以会将定罪与罪名的确定、适用相混淆,主要原因在于“1997年刑法颁布以前未能实现罪名的立法化,对罪名确定的探讨仅限于学理研究,而学理概括的罪名无法做到统一,使得实践中司法机关在选择适用刑法分则具体条文时还要将该条文所描述的犯罪名称予以确定”[2],从而导致“一罪多名”“多罪一名”等现象比比皆是,而定罪和罪名的确定也就混为一谈。但随着1997年刑法和有关罪名确定的司法解释的出台,罪名的确定工作逐步走向统一和完善,司法机关只需根据所适用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直接适用已确定的罪名即可,不再“创造”罪名。不可否认,罪名的确定、适用与定罪具有联系,在定罪时需要以一定的罪名适用于行为人,才能使得罪名确定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彰显,得出定罪的结论。但是罪名确定与定罪具有本质区别。从行为性质上看,罪名的确定是一种刑法解释活动,是对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罪状进行高度概括而取定具体犯罪的名称,根本不涉及对犯罪行为的认定。可以说,确定罪名的目的在于统一标准。[3]罪名一经确认即不以司法人员的意志为转移,“罪名作为对罪状的标识,不可能反映出罪状所有的要素,所以罪名不是办案的依据,不能也不应该根据罪名办案”。[4]而罪名的适用是司法机关根据具体犯罪事实所适用的刑法分则具体罪状来对应已确定的罪名,以此来方便对行为人的定罪处罚,罪名的变更本质上并不影响对行为人的实质处刑。定罪则是一种关于法律适用的刑事司法活动,是对行为是否有罪的确认,包括区分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等活动,需要司法机关对具体犯罪行为作出实质性判断,直接影响行为人的處刑。正如案例一中,昌平分局移送审查起诉、昌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以及昌平区法院作出判决均使用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这一罪名;案例二中,昌平区检察院、昌平区法院使用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这里的罪名是司法机关根据行为人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事实所选择适用的对刑法第341条第1款罪状的“代称”。就定罪而言,因为刑法条款并未发生变化,司法机关对于具体犯罪事实的实质性判断未改变,处刑亦未受影响。
(三)对“处刑轻重”的比较是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关键
我国刑法溯及力原则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即以适用旧法为原则,以适用新法为例外。从刑法第12条的规定来看,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新法,那么,“处刑”轻重则成为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关键。换句话说,从旧兼从轻原则涉及的是刑罚的有无和轻重的问题。一般而言,从旧兼从轻原则意在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强调对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即在对行为人作出处理决定时不能突破行为人的预测可能性而作出更为严厉的刑法裁判结果。这种预测可能性是行为人事先能够明确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判处何种刑罚方式以及在何种幅度内适用刑罚的问题。因此,只有涉及到“处刑轻重”的刑法规范才有刑法溯及力原则适用的空间。回归到案例中,在案件办理时,不管公检法适用的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还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并不影响行为人的处刑轻重或处刑有无的问题,自然就没有适用刑法溯及力原则的空间。
(四)罪名的功能决定了罪名的变更不适用刑法溯及力原则
罪名具有概括、评价、威慑和教育等功能。[5]其中,罪名的概括功能体现在对罪状的高度提炼[6],在罪状和法定刑不变的情况下,新罪名一般比旧罪名对罪状的描述更加准确。罪名的评价、威慑和教育功能体现在对违法犯罪行为给予的否定评价,新罪名代表的是鲜活而真实的法律对犯罪行为的现实性谴责,以罪名的形式确定的否定评价的形态和性质,适用旧罪名则代表了一种过往性评价,反映不出与现实的关联,旧罪名因为已经废除,如再适用会给人一种不合时宜的印象和错觉。[7]因此,新罪名的适用能够更加发挥罪名功能,当新的罪名出现时,不能强行违背其发展趋势,而选择适用“过时”的旧罪名。正如两则案例所涉及的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补充规定(七)》之所以修改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主要考虑到司法实践中原罪名过于复杂、繁冗。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往往伴随后续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按照原罪名,司法适用中存在数罪并罚的争论,而且对于涉及已死亡的野生动物尸体的,在罪名上究竟适用野生动物还是野生动物制品也常存在争议。概括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则简单明了,既能避免司法适用中不必要的争执,解决法律适用难题,也能充分涵括各种行为方式和保护对象。[8]因此,就上述案例来讲,适用新罪名“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能够更好地实现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的有效刑事司法保护,符合刑事立法发展及司法适用的需要。
(五)罪名变更不适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的规定
有观点认为,罪名的确定多是“两高”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规定的,因此新旧罪名适用问题本质上是刑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对于新增的罪名,根据“两高”《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2条规定,对“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新罪名;对于罪名发生变更的,因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确定了具体罪名,那么依照该《规定》第3条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对罪名予以适用,除非适用新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笔者认为,该观点只是从《规定》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忽视了《规定》条文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对于刑事司法解释溯及力原则适用的关键作用。
对《规定》第3条的理解应当建立在对第1条的基础上。《规定》第1条规定,司法解释是对司法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司法解释效力及于法律施行期间。从性质上看,刑事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司法解释的内容和生效时间均依附于刑法条文和生效时间。由于司法解释并不是一次性针对某一刑法条款作出全部的解释,而是根据具体应用有针对地予以明确,如果刑法修正案实质改变刑法具体条款的适用,在适用修正后刑法时,依附于其上的旧司法解释条文则不再适用,而新司法解释的效力可以及于刑法具体条文修正生效之时,同时,如果该新司法解释中有些条文并未涉及刑法修正,则其生效时间可以“穿透”刑法修正之时溯及到其所依附的具体条文的生效时间,进而产生新旧司法解释的比较适用问题。因此,刑事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溯及生效时间并非完全一致,而对于《规定》第3条的理解则必须依附于刑法的溯及力原则上。刑法溯及力原则适用限于对行为人“处刑”有实质性影响的条文上,那么作为依附于刑法规范具体条文的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适用上同样也不例外,只有对行为人“处刑”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司法解释才有溯及力原则适用的空间。回归到两则案例中,《补充规定(七)》(法释〔2021〕2号)虽然是“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文件,但其所规定的内容仅涉及罪名的确定,而正如上文所述,罪名只是对具体犯罪的代称,不涉及对行为人是否有利的实质判断,不会对定罪量刑产生实质性影响,罪名的确定也仅是辅助司法机关具体办案的一种规范化手段,那么,《补充规定(七)》不宜适用《规定》第3条,对于刑法第341条第1款的行为,适用新罪名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