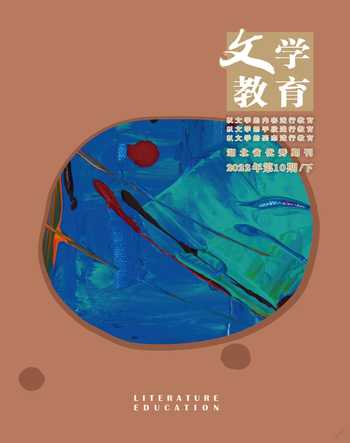时间副词“曾”和“曾经”的比较分析
2022-05-30曾惠中
曾惠中
内容摘要:“曾”和“曾经”在作时间副词时,二者的词义相近,但作句法成分以及与否定词组合时却存在差异:“曾经”可以作状语、定语、宾语、主语中心语;而“曾”只能作状语。“曾”与否定词“不”的组合能力更强。在语用层面:“曾”更多用于书面语,或者书面语色彩更浓厚的文体。
关键词:时间副词 句法分析 组合能力
“曾”和“曾经”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都很高。《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曾”的解释是“曾经”;解释“曾经”是表示从前有过某种行为或情况。《现代汉语虚词词典》认为二者一般可以换用,“曾”多用于书面。由单音节词到双音节词的发展变化是古汉语词汇向现代汉语词汇转化的特点之一,双音节词的演变研究也一直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那么从“曾”到“曾经”的转化,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以及二者在使用时又有哪些区别?本文就从句法语义层面和语用层面对“曾”和“曾经”进行对比,探究“曾”向“曾经”的转化过程以及二者在使用时的区别。
一.“曾”和“曾经”的句法和语义比较
(一)作句法成分
1.作状语
“曾”和“曾经”作状语时,修饰谓词性成分。表示在过去的某一时间点的动作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可以互换,替换后不影响句子表达效果。下面看具体例句:
(1)她曾经/曾想两三年当上副教授,于是玩命搞课题发文章。(人民日报2016年09月02日)
(2)在这里可以唤起人们的记忆,曾经/曾看过、用过、拥有过的东西,感到很亲切,是滇西北地区的一个文化缩影。(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07月16日)
“曾”和“曾经”修饰的动词也有一定的限制:不能为重叠式。
(3)a.这件事我们曾经商量过。
b.这件事我们商量商量。
c.*这件事我们曾经商量商量。
在以上三個例句中,前面两个例子都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述,而第三句的表述在现代汉语中并不成立。“曾”也是如此,不能修饰重叠式动词。
“曾经”和“曾”作为时间副词,在作状语的时候,只能采用无标记的形式,不能带“地”:
(4)*这条河流,曾经/曾地见证大上海历史风云,又目睹了一场世界文明交流的盛宴。
“曾经”作状语时还能位于句首,具有衔接篇章结构的功能。“曾”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5)曾经,“90后”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如今,我们逐渐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对将来父母的养老问题,都抱持积极的心态,精心规划并为之努力。(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1月30日)
(6)曾经,她是人们为之唏嘘的“篮球女孩”,现在,她是中国残奥游泳队的一员。(人民日报2016年09月12日)
“曾经”放于句首时,后面一般会跟有“如今”“现今”“现在”“而今”等词语用以对照,强调过去的时间,突出和“现在”的对比。
2.作定语
“曾经”作定语时,指过去的时间,相当于“过往、昔日、过去”等。此时“曾经”的修饰语可以是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以及短语。
(7)现如今观众的年龄越来越小,从曾经的70后、80后过渡到了90后甚至是00后,“IP改编”“鲜肉当道”“比拼颜值”已经成为了电视行业的口头禅,毕竟谁能抓住了年轻观众的胃口,谁就能赢得收视率。(人民日报2016年09月16日)
(8)曾经的我,想要让别人来了解自己,想要把自己全盘地托出去,快乐和难过都想要和朋友分享,那时的朋友是兄弟。(微博)
“曾经的70后、80后”以及“曾经的我”都是指在过去的特定时间点存在的人,重点强调过去的时间,与当下谈话讨论的情况并不一致,说话者有意进行一个对比。
并且注意到:“曾经”作定语后面都要加上标记词“的”,“曾经”不能独立作定语,而是加上标记词“的”构成体词性短语才能作定语。作中心语的成分也有一定的语义限制,“曾经的”修饰的名词或名词短语一般有以下几种类型:时间类名词、自然现象、衔位官职、情感态度、见解论点、作用意义和方针政策。这些词语或带有外部时间性,或能构成顺序序列,或具有语境顺序义,都可以随时间而发展变化。又因为“曾经”在表达中,总是处于动词的前面,长期的使用搭配使得“曾经”有了动态义,当与具有时间或者顺序特点的名词搭配时,认知推理过程会将这种动态联系转嫁过来。当定语位置表“过去”时间意义的词出现空缺时,时间副词“曾经”又刚好在语义上有相近的表达效果,语言使用者就会自然而然地择近选取时间副词来填补空白,这完全符合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
邵敬敏认为:两个词语之所以能够组合成一个句法结构,是因为二者在某方面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语义特征决定了句法组合的可能性,某个或某些共同的语义特征是彼此间相互选择匹配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任何结构的组合都必须遵循“语义一致性”这一基本原则。[1]“曾经”作定语,修饰时间或顺序类名词,正是遵循了“语义一致性”的原则,下面看具体例句:
(9)当人们阅读到西域的历史,总会被那里曾经的璀璨与辉煌所震撼。(齐东方《胡杨林的控诉》《人民网》2003年1月24日)
(10)三兄弟曾经的互相不谅解,最终还是在民族大义前消弭于无形,令人感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06月24日)
被修饰的成分为动词或形容词时,是指称化的“VP”。[2]也即谓词性成分不做陈述功能,不表达一个命题,而是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上述例子中“璀璨”以及“互相不谅解”经由“曾经的”修饰后都变成了体词性成分。
3.作宾语
“曾经”充当宾语时,一般情况下是有定的,有的表示“某事件已经发生过的那个时间,但不延续到说话当前”;有的表示“经历、阅历”或者是“过去的某个较为具体的指代”。
(11)比起灯红酒绿的摩天大楼,我更想要穿越古镇的曾经。(人民日报2017年09月13日)
(12)爱情就是这个样子,有些人会慢慢遗落在时光的某个角落,我们一起哭过,笑过,吵过,闹过,但再恋恋不舍也都只是曾经。(新浪微博)
“灯红酒绿的摩天大楼”与“古镇的曾经”是一组对比,这个“曾经”具体指的是与“灯红酒绿”的繁华相对立的事物。后面的例句选自新浪微博,在网络用语中出现的情况比较多。“曾经”单独作宾语的现象不常见,在正式的官方媒体中用例极少,而在语法规范要求相对没那么严格的网络用语中更有生命力。
4.作主语中心语
(13)但是此后,五里河体育场的经营状况业绩平平,它辉煌的曾经也换不来经营上的繁荣。(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4月22日)
(14)还记得我跟你表白的那个地方,过去的一点一滴都让我难以忘怀,我难以想像我居然能挺过来,虽然我已不再喜欢你,但每逢夜晚来临,我独自经过那里时,总是泪流满面,我的曾经那样美好,但友情爱情如今都不复存在了。(《华西都市报》2013年6月21日)
以上两个例句中的“曾经”都是有所指的,是发生在特定时间段的特定事态,提到这个时间点,人们就会想起与那个时间相关的事情,也就慢慢趋向于用该时间段来表述与该时间点相关的事物、景象等。并且“曾经”作主语的时候,前面离不开定语的修饰,单独的“曾经”并不能作主语。经过定语修饰后,成为了体词性的结构才能用作主语。
综上,“曾经”可以作状语,定语,宾语和主语中心语。而“曾”只能作状语。“曾经”的非状用法是在与其他词语搭配组合时转化为体词性短语,从而具有指称性,指“过去具体的某件事,某个情境,某个状态”,隐含着与说话人当下情况的对比。“曾”无法通过与其他词语的组合完成这样的转化,所以不能像“曾经”一样能灵活地充当多种句法成分。“曾经”的非狀用法虽从句法层面看不太规范,但是在语义方面能够解释得通,符合人们的言语习惯和认知模型,表达效果也形象生动,所以能被使用者接受。
(二)组合能力
1.“曾”/“曾经”+“不”
(15)曾经不会哭的女孩,后来痛痛快快地哭了10分钟。(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04月11日)
(16)为了防止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再起,国际社会曾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人民日报1997年06月14日)
“曾”和“曾经”都是作状语,“不”只是刚好在空间序列上位于“曾”和“曾经”的后面。在语义黏合上,否定词与后面的词语结合得更紧密。
2.“不”+“曾”/“曾经”
(17)考茨基不曾经是一个有点名气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人民日报1973年10月03日)
(18)请看:当年的英帝国主义不曾经是称雄一时的强国吗?它曾经霸占地球的四分之一土地,奴役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口,号称“每一个英国人拥有三十个臣民”,自夸为“日不没国”。(人民日报1966年04月04日)
“不+曾经”的组合在语料库中的例子有限,出现报刊上的例子也都比较久远,即使在网络用语中也很少看到这样的使用。且“不+曾经”这样的组合几乎都是出现在反问句中,用来加强语气。
“不+曾”的例子非常多,《现代汉语词典》甚至已经把它收录成词。“不曾”是对“曾经”的否定。既可以出现在疑问句中,也能出现在陈述句中。
(19)哪一个母亲不曾为儿子一针一线地缝补过衣物呢?(人民日报1963年04月30日)
(20)我们经讨论一致认为,沈从文从来不曾“自我放逐”过,也不是什么边缘人物,更不是自甘寂寞。(人民日报2002年12月28日)但考虑到《现代汉语词典》已经将“不曾”收录为词,所以将“不+曾”归为词法序列而不是句法序列。
此外,“曾”作为单音节词,除了与否定词“不”、“未”,组成“不曾”、“未曾”外,还能和疑问词“何”组合表疑问或反问。用于表示对过去某件时间完成情况的感慨、质疑、询问例如:
(21)这个侠骨柔情的汉子何曾不愿为自己的小家庭多操一份心?又何曾不想让自己的妻儿老母能够过上富足的日子?(人民日报2001年03月02日)
(22)千百年来,人与人何曾“一样”过;千百年后,人与人能否继续一样?(人民日报2016年07月04日)
(23)即使是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亲情又何曾变改?(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07月01日)
二.“曾”和“曾经”的语用比较
(一)适用文体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认为“曾”多用于书面,于是笔者选取了几本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对“曾”和“曾经”出现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对比。
笔者在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曹禺的话剧《雷雨》、王尔德的书信《自深深处》(译林出版社,朱纯深译本)和杨绛的散文《我们仨》中检索,发现在两本散文中,二者出现次数相差较大,“曾”的使用频率要比“曾经”高。散文的语言简洁精炼,透彻精辟。所以在散文创作中会倾向选择更加简练的“曾”而非“曾经”。而在口语色彩更浓厚的话剧和书信中,二者的使用频率相差并不明显,甚至在话剧中,“曾经”可能略胜一筹:
(24)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
(25)蘩:(笑)我怕你是胆小吧?
萍:怎么讲?
蘩:这屋子曾经闹过鬼,你忘了。(《雷雨》)
在杨绛的《我们仨》中,几乎所有能用“曾”和“曾经”的情况,杨先生都选择了“曾”,唯一一处使用“曾经”的地方还是一句口语:
(26)她扶着我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娘……娘……”(《我们仨》)
《雷雨》因为篇幅原因,“曾”和“曾经”出现的次数也不多。但也可以看到,对话中用得比较多的是“曾经”,而在旁白中更倾向于用“曾”。
(二)音节配置
作状语时,“曾”在使用中占优势,后面可以接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甚至是多音节词语,例如:“曾不止一次”“曾不可一世”“ 曾不得不”。无论是“1+1”还是“1+2”,都是符合汉语的韵律的结构规则。在一些情况下,用“曾经”来替换“曾”,可能不及原来的表达效果:
(27)a.原来,A曾是某厂的团委副书记,曾为同性恋行为入过狱,他在狱里自学了大学课程,并通过了成人考试。(王小波《东宫·西宫》)
b.*原来,A曾经是某厂的团委副书记,曾经(因)为同性恋行为入过狱,他在狱里自学了大学课程,并通过了成人考试。
替换之后,两个“曾经”连用,且后一个“曾”被替换之后,后接的“为”为了使句子自然流畅,还需要改为双音节词“因为”。整个句子会变得比较啰嗦,不够精炼。这是因为汉语的句法结构除了受句法规则的制约,还要受到韵律规则的影响。“音步必双”是汉语韵律系统的要求。单音节副词可以选择一个单音节词语作为被修饰成分,二者一起构成一个临时的音步。但如果双音节副词来修饰一个单音节词语,就可能构成一个“2+1”的不好的韵律结构。而在用作其他的句法成分时,“曾经”转换为体词性成分,可以更灵活地在运用在句子中,“曾”不能对其进行替换:
(28)a.曾经,终究变成了曾经,我只希望你可以幸福。(新浪微博)
b.*曾,终究变成了曾,我只希望你可以幸福。
双音节时间副词相对而言,语义承载量要更加丰富。“曾经”最开始连用时是表示词组,那时“经”还只是一个动词,与副词“曾”组成的是比较松散的谓词性偏正短语,表示是“曾经经历”或“曾经经过”。在使用过程中“经”的语义磨损,语素义逐渐丧失,变成了粘着语素,“曾经”也就由词组降格弱化为了词。但在今天,“曾经”一词也还有“曾经经历(的某事)”“曾经经历(的状态)”的意思,还保留着原有词组的词义,内涵随着具体语境更加丰富,使用过程中也更具生命力。
此外,双音节更具有音律平衡感。在“单音节时间副词+的+中心语”这样的结构,如果中心语为双音节词或者是多音节词时,就会出现左轻右重的情况,从语感上来说失了平衡,分量不够,不符合汉语搭配的习惯。
本文对时间副词“曾”和“曾经”进行了句法和语用层面的分析,对比了二者作句法成分以及与否定副词组合的情况。“曾经”在句子中除了可以作状语外,还可以作定语、宾语和主语中心语;而“曾”只能用作状语。“曾经”通过与其他词语组合成体词性的结构,可以在句子中灵活地充当多种句法成分,“曾”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曾经”与“不”连用时,依据句法序列否定副词一般放在“曾经”的后面。放在“曾经”前面时,一般用于反问句中,用于加强语气。“不”与“曾”的共现主要是在“不+曾”这种组合中,出现得早,而且出现频率也高,直至今日早已合并作为一个词语来使用。语用层面:“曾”主要用于书面语,“曾经”更多地用在口语中。双音节时间副词“曾经”和单音节时间副词“曾”在语义或是句法层面上的差异与音节的差异有关。双音节词的语义承载量更为丰富,内涵也能随着具体的语境变得更加具体。所以在句子中的位置会更加的灵活,哪怕是非常规用法看起来也并不突兀。而且双音节更具有音律平衡感,这使“曾经”在作定语时整个结构看起来更加平衡,读起来也比较自然,这恰恰是单音节词“曾”所不能做到的。
参考文献
[1]邵敬敏,吴立红.“副+名”组合与语义指向新品种[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6).
[2]张谊生.从“曾经”的功能扩展看汉語副词的多能性[J].汉语学习,2003,(5).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