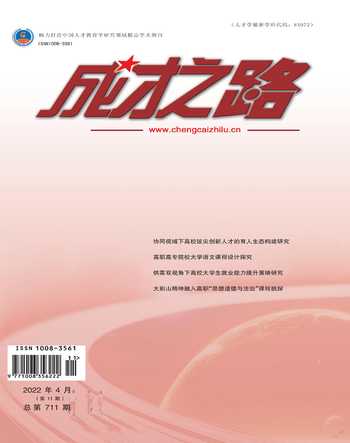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干预问题刍探
2022-05-30种文浩
种文浩
摘要:随着时代发展和社會转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日益复杂化、严重化,大学期间是精神分裂、长期抑郁等重大精神疾病的首发期和高发期,及早发现、提前预防、及时疏导成为高校心理工作中至关重要的内容。文章通过对一例精神分裂学生案例的处理与分析,探讨与反思如何应对学生的严重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为建立健全大学生心理问题干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高校心理工作,促进学生健康稳定发展打下基础。
关键词:精神分裂;大学生;心理干预;心理健康教育;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G4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3561(2022)11-0040-03
一、案例概述
Q(化名),女,19岁,就读于苏州某高等专科院校。入学一个月,她自行联系学校心理中心,要求预约咨询。因其存在幻觉、思维障碍等明显症状,且有加剧的趋势,心理中心教师遂联系其班主任、辅导员并建议就医。在医生的建议要求下,该生进行休学、住院治疗。第二年重新返校,并继续进行心理咨询。
二、案例过程
Q在进入大学后一个月,自行联系心理中心预约咨询。在第一次咨询开始时,Q反复核实笔者的咨询师身份。签订知情同意书时也犹豫再三,多次向笔者确认保密原则。Q自述“总感觉很恐慌”“莫名烦躁,胸闷”“看见人群会感到恐惧不安”。上课时Q会坐立不安,无法认真听讲,总能听到别人在叫她的名字;她惧怕人群,甚至不敢去食堂,因为食堂的人太多,她害怕别人听到自己脑袋里的想法;与同学关系疏远,总感觉有同学在背后骂她、议论她。
在咨询过程中,Q几乎每段话的声音都会越来越小,有时会陷入自言自语、嘟嘟囔囔;偶尔会出现长时间的沉默,神情游离,并发出类似沉思的“嗯……嗯……”的声音;还有很多异常的小动作,如捏眉心、揉眼睛,说感觉眼睛很痛,在整个咨询过程中常常摇头晃脑。
因其存在幻觉、思维障碍等明显症状,且有加剧的趋势,笔者便与Q讨论保密例外的原则,建议与其班主任或家长沟通,她并无异议。咨询结束后,笔者联系了Q的班主任、辅导员并建议就医,班主任及时带她去了专科医院,Q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发作期),遂休学并住院治疗。
三、案例分析
1.病情分析
笔者在与Q咨询过程中,能够明显察觉到其言行举止的异常之处。Q自述经常会听到别人骂她、议论她,并觉得其他人都能听到自己在想什么,在人群中会听到别人在说她,这是精神分裂症最突出的症状之一———感知觉障碍,以言语性幻听最为常见。精神分裂症的幻听内容有时是争论性或评论性的,也可能是命令性的。患者的幻听有时会以思维鸣响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Q存在明显的思维障碍,表现为缺乏连贯性和逻辑性的思维形式障碍,和以关系妄想为主的思维内容障碍。
2.病因分析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作为一组病因未明的严重精神疾病,多起病于青壮年,所以大学期间是这类人群患病及发作的高发期。患者常有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障碍,一般无意识及智能障碍。目前认为该病是脑功能失调的一种神经发育性障碍,复杂的遗传、生物及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该病的发生。笔者与Q的咨询主要围绕其家庭进行,所以这里主要从家庭方面来探讨Q患病的原因。
原生家庭(family-of-origin)是指个人出生后被抚养的家庭,区别于个体成年后所组建的新生家庭,是个体情感经验学习的最初场所。对于Q而言,充满不安与创伤的原生家庭对其心理健康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其一,丧失至亲。Q的亲生母亲在其七岁时突然离世,在母亲去世当年的年底,父亲就与一个年轻的阿姨再婚。后来,Q与奶奶一起生活。父亲与后妈生下弟弟后,三人搬去广东生活,留下Q在老家由奶奶照顾。在童年期丧失至亲、有创伤经历的人,很容易陷入难以言表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可能表现为分离的精神状态、身体痛苦和其他躯体感受的功能障碍等,还会对当事人的感受、认知、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产生很大影响。其二,亲属代养。一般来说,由亲属代养的孩子因为与父母的感情剥离过早,不安全感较强。代养对孩子的个性发展和心理健康会产生消极影响,容易使孩子产生自卑、不安、对人不信任的心理和性格。其三,教养方式。不良的教养方式是导致青少年心理障碍的高危因素。Q的母亲过世后,父亲对她并未投入太多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反而态度冷漠、缺乏关心。与Q一起生活的奶奶又重男轻女,经常打骂、责备她。其四,经济因素。家庭经济状况在青少年身心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外学者研究证实,家庭经济困难的个体在心理问题上具有更高的易感性。笔者建议Q就医时,Q曾询问就医需花多少钱,说自己没有钱,自述父亲“对别的事情不管不问,就好像想让我自生自灭”,入学仅一周,父亲就让她去找兼职,她上大学用的是助学贷款,即使这样,她父亲也想让她尽快找工作挣钱。
由此可见,Q在家庭中感受到的更多的不是爱和温暖,而是母亲的离世、父亲的冷漠、奶奶的责骂带给她的不安与恐惧。创伤可能是许多精神病理症状的病因之一。而精神病性特征则可能是对于童年期负性事件的反应结果,也会使个体倾向于对后期的丧失做出病理性反应。由于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当悲痛和丧失过于痛苦、难以承受,就会想方设法逃离,或是构建防御来抵挡痛苦。心理学家John Steiner(约翰·斯坦纳)形象地将这类状态称为“精神避难所”(Psychic Retreat,即“精神撤退”,是一种强大的防御系统),它可以让遭受巨大打击、承受强烈的精神痛苦的人暂避压力,获得相对的平静与保护。这些防御可能也是Q出现幻觉等症状的根本原因之一。
四、案例后续
Q休学住院治疗后,第二年重新返校,笔者主动约其会面。重返校园的Q有明显好转,不再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思维逻辑性也有很大改善,已停止药物治疗且无任何心理咨询等辅助治疗。但是Q情绪较为低落,在咨询过程中仍会清晰地讲述父亲和继母对她的冷漠,诉说自己的痛苦、茫然及疑惑,自我评价低且伴随明显无意义感。
五、案例反思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问题有加重趋势,有就医服药史、家族病史的大学生也日益增多。面对存在严重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的学生,高校心理咨询中心需具备完善的心理工作体系,心理咨询教师需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保证学校的和谐稳定。
1.对严重心理疾病的预防与干预
以本文患精神分裂症的Q为例,她在新生普测调查中就显示出预警,但其身边的教师和同学并未发现异常。这对学校的心理专业教师及学生工作一线人员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复发率较高的精神疾病,首次发作的患者中虽有75%可达到临床治愈,但反复发作或不断恶化的比例较高。受家庭及经济因素的影响,Q在康复的巩固和维持期没有坚持服药,并在复学后表现出一定的抑郁情绪。
抑郁症状可发生于精神分裂症的所有阶段,可以出现在首次发作、早期病程和精神病性症状缓解后,抑郁症也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残留症状。所以,患有严重心理疾病及精神分裂症的学生复学后,应根据自身病情定期复诊、维持治疗。对于伴有抑郁症状的精神分裂症,除了进行药物治疗外,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支持格外重要。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具有病耻感、孤独感,常常有意无意地与他人和社会保持距离,而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常常也出现问题。比如Q的家人对其缺乏理解与关心,使其无法得到足够的物质和心理支持,这有可能加重患者的抑郁情绪。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给患者安全、温暖的环境,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病情。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则越有利于缓解患者的抑郁情绪,越有利于患者的心理健康。
2.提高辅导员心理专业素养
在高校,心理健康工作并非心理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独享”。由于辅导员的角色与岗位定位非常重要,因此出现各类学生问题时他们应充分重视、积极解决。辅导员不仅需要用认真的工作态度处理纷繁琐碎的学生事务,对待学生有耐心和爱心,还需要学习一些预防和处理心理问题与精神疾患的知识。例如学习大学生心理障碍、精神疾病的鉴别与风险管理知识,了解一些处理大学生精神疾患的相关法律与伦理知识,加强心理危机干预知识的学习等。对于危险性高、攻击性强的精神疾患,如精神分裂症、抑郁或躁狂发作、物质滥用、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和边缘性)、器质性精神障碍(如癫痫性精神障碍)等较严重的病症,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发病症状、表现形式等,这样可以提高初步甄别的能力,同时对有自杀史、家族自杀史、创伤史和就医服药史的学生要加强关注,以提前发现、提早干预。
此外,学校应经常开展辅导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心理知识培训活动,定期请专家进行经验交流分享与传授,培养辅导员面对高风险心理疾病、危机事件的处理能力,如怎样做好个人防护与回避,如何在不刺激心理异常学生的前提下进行谈话,如何与学生家长进行沟通等。身处学生工作一线的辅导员,掌握更多心理危机的识别与预防、心理危机的应急程序、心理危机程度的评估等知识,就可以更好地处理突发事件、危机事件。
3.建立心理健康防护机制
(1)班级与宿舍。班级心理委员等班干部要充分发挥骨干作用,通过多种形式与班级同学加强思想和感情上的联系、沟通。班级心理委员要定期填写“学生心理健康月(周)报表”,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向班主任报告。
(2)二级学院。各二级学院辅导员、班主任及普通教师要关爱学生,密切关注学生的异常心理和行为,对学生的异常情况及时向二级学院有关领导与学校心理中心报告,并在领导和咨询师的指导下对问题快速反应、有序干预。还要在问题的干预与处理过程中,做好资料的收集与证据保留工作,包括与相关方面联系的谈话录音、录像、照片等。
(3)学校。学校应推进突发事件处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学生心理健康普查制度和危机个案干预制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应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普测,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筛查出需要主动干预的对象并采取相应措施。在心理咨询或学生工作中,一旦发现处于危机状态的学生,要及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确保学生的安全健康和学校的和谐稳定。
4.后期跟踪
因心理障碍、精神疾病而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学校除按学籍管理办法办理外,还应让其提供医院等专业机构认证的心理疾病康复证明。在学生复学后,要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让班主任、辅导员和心理委员等人在保护学生隐私的前提下对其密切关注。学校心理中心要根据二级学院提供的情况,安排咨询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所在二级学院。要保持信息畅通,最大限度地降低学生心理危机发生率。
参考文献:
[1]吴九君.积极心理干预对大学生心理和谐、抗逆力、总体幸福感及抑郁的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
[2]罗晓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对策[J].教育研究,2018(01).
[3]王健,刘书梅,张沛超,吴海艳,迟新丽.积极心理干预对抑郁症状大学生情绪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特殊教育,2016(11).
[4]關心,乔正学,邱晓惠,杨秀贤,王琳,杨艳杰.大学生抑郁心理干预效果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4(02).
[5]苟晓玲,彭玮婧,刘旭.全域视野下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素养:内涵、构成与发展路径[J].当代教育论坛,2020(04).
[6]骆莎.论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现代转型[J].思想理论教育,2020(01).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hong Wenhao
(Suzhou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uzhou 21500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The mental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serious. During the university period, it is the first and high incidence period of major mental diseases such as schizophrenia and long-term depression. Early detection, early prevention and timely counseling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psychological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treatment and analysis of a case of schizophrenic stud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reflects on how to deal with students seriou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r mental diseases,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intervention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further improving college psychological work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 words: schizophrenia;collegestudent;psychologicalintervention; mentalhealth education;case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