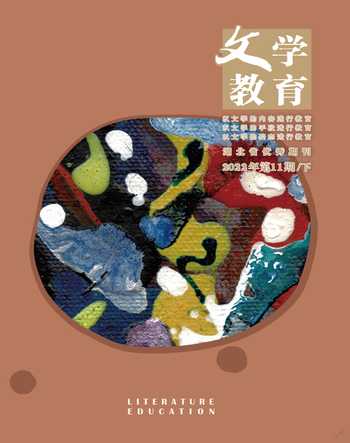论基诺族作家文学的学校教育书写
2022-05-30王贞歌
王贞歌
内容摘要:学校教育为基诺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也成为基诺族作家书写的重要对象。基诺族作家文学见证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为了解起步阶段的学校教育提供新的视角,从细微处弥补宏观调查的不足,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选择体量小、写实风格的散文和诗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诺族作家对教师的正面书写,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促使基诺族作家将目光聚焦于教师慈爱善良、无私奉献的形象特征;基于此形成了基诺族师生关系的和谐书写。基诺族作家文学作品记录和反映着民族学校教育与作家文学之间的特殊关联,是这个民族重要历史进程的再现。
关键词:基诺族 作家文学 学校教育 教师形象 师生关系
基诺族主要聚居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作为“直过民族”、“云南特有民族”、“人口较少民族”、“无文字民族”,1979年才被国务院确认为我国单一的少数民族,也是新中国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该民族的作家文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诺族作家张志华1980年开始书写新闻,1988年成为《云南经济信息报》的特约记者,同年六月,陶润珍在《民族文学》杂志发表诗歌《小鸟飞走的时候》,张鉴的诗歌《追寻》和王志祥的散文《车前草》见刊。[1]3892015年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基诺族卷》和2017年出版的《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布朗基诺族合卷》是基诺族作家文学成果的集中收录,最受基诺族作家青睐的文学体裁是散文和诗歌,小说屈指可数。张璨的《我的基诺爸爸和爱伲妈妈》显示出小说的故事性、对话特点。
学校教育为基诺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基诺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新中国成立之前,基诺族世代居住于高山密林之中,极少与外界进行交流,没有正常运行的学校,除了何贵没有人识字。故长期以来基诺族只有民间文学没有作家文学。西双版纳解放之后,基诺族开始由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1956年,学校教育在基诺族落地生根,基诺族学子得以接受汉语教育。“1956年,从景东、镇沅等地选拔了一批中学毕业生到边疆任教,并在巴亚寨和巴卡寨建起了两所小学。不久后,又在巴来寨建了一所小学。从此170多名儿童走进了学校,他们成了基诺族的第一代学生。”[2]249
将学子首次接触汉字的新奇和喜悦细腻呈现的是张云的《那时,这时》:“当我第一次翻开课本闻到了一股香味,觉得每一本书的味道都是一样,汉族的文字是说不出来的清香。”[1]2671956年至1965年培养的140多位高小毕业生,[2]249-250有的后来参与基诺族文学创作,并有作品发表;有的继续升学,成为基诺族第一代知识分子;其中有的还成长为基诺族第一代作家。如黄玲所说:“经过将近三十年的现代教育,培育起了本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才,为作家文学的出现奠定了文化基础。”[3]王志祥的《我的大学梦》就将义无反顾地走在“基诺族文学创作道路”归功于“大学梦”,反映了学校教育和作者从事文学创作的紧密联系。
学校教育对基诺族作家文学发展进程的重要推进,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基诺族作家对学校教育的反向书写。基诺族作家文学见证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史,为了解起步阶段的基诺族学校教育提供了新颖视角,从细节处弥补宏观调查的不足,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体量小、写实风格的散文和诗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作家对教师的正面书写,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促使基诺族作家目光聚焦于教师慈爱善良、无私奉献的形象特征;基于此形成了基诺族师生关系的和谐书写。
一.作家文学见证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
基诺族的学校教育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不同于学者田野调查、数据论证指向一个客观结果,作家们用诗意的個人体验,落笔于细微之处,再现了学校教育的曲折和艰难,侧面反映了基诺族学校教育七十年来的风云巨变。
学校教育最艰难的时期,往往更能激发作家的书写热情。目前,笔者未读到1956到1965年十年间的学校教育书写,作家张志华是1966年入学,70年代艰难的小学、初中生活常见于他的文学作品之中,有着“苦难书写”的意味,以个人视角再现了那个贫苦的年代和不完善的学校教育。《真情永远》以1972至1973年的小学教育为背景,那时学校刚刚发展起来,基本的教室、宿舍都是老师领着学生盖的,“学生们一边读书,一边编织草排,立起房屋木架,建盖起校舍。”“我”吃的是冷水泡山药撒上盐巴,饥饿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课程学习。[1]60
散文《一双鞋》中,张志华这样描述70年代中期的初中学校:“那时候的学校很简陋,陈旧的茅草房,破烂的竹篱笆墙,学习环境条件艰苦”。基诺族初中教育起步阶段十分艰难,学生上学要跑几十里山路不算,除了学习还要开挖山梁为扩建学校做准备。课程安排也不稳定,“学校领导安排我们的课程是半天读书,半天劳动,有时候一天只上一节课。”因学校简陋,又没有什么取暖设施,冬季还是比较寒冷。即使餐食十分简单,交生活费也成问题。[1]106-107
张云的作品《这时,那时》为基诺族1979年之后的小学教育留下了一张剪影,校园里有“排排白杨、清翠竹林”,教室是茅屋教室,桌椅都是由“两根木头左右载桩,在桩头上平放木板用铁钉扎稳……教室周围用竹片包围着,左右两侧是半墙竹笆,两根木脚架支撑的黑板”。[1]267这时的学校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教室、书桌都是就地取材,体现了八九十年代学校的生存智慧和俭朴作风。
张鉴《故乡的森林》反映了2000年左右景洪市北部的大渡岗中学的教学成果,虽然简陋,也没有大的名气,却“连续数年中考成绩名列前茅,各科成绩也在稳步上升”[1]54。此时的学校教育完全步入正轨,作家文学关注点已经由温饱、客观环境转向学生的学习成绩,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几率大大提升。
新世纪基诺族也出现了小学在读的作者,张尚卓、孙贝、车都、周雨欣等以儿童纯真的视角、稚嫩的笔触在基诺族的作家文学发展史上挥洒笔墨。车都于2011年发表的《我快乐的成长》中,基诺族民族小学是另一番面貌:“我们有四层的教学楼,每间教室既宽敞又明亮。学校还有宽阔的体育场……每年召开一次冬季运动会。”除了硬件设施的完善,教学管理制度更加成熟,班主任教学生读书写字,还教他们穿衣服、扎头发、洗衣服,带他们去食堂打饭。学校每年还召开一次冬季运动会。[1]231新世纪基诺族学校早已走上正轨,教学环境优美,硬件设施完善,师资力量不断加强,课程安排也更加科学、系统、合理。
作家的倾情书写不仅见证了基诺族学校教育的发展进程,也为了解起步阶段的学校教育提供了微观视角,从细节处弥补了宏观调查的不足,对探析特殊背景下基诺族学子的普遍心理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从“传统学术观念中的文史不分,到现代史学理性关怀下的文史分途”,[4]正如杜甫“三吏”“三别”的史料价值,基诺族的作家文学书写也似乎体现了文学与历史关系的回归。
二.教师形象的刻画
基诺族作家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往往从形式灵活、选题不限、篇幅短小的散文和诗歌入手,作品中记叙的事件、抒情的对象都有现实依据,虚构成分较少。文学体裁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诺族作家对教师的正面书写。正如朱希祥说过的“写实言情的散文、报告文学或诗歌后者居多”,这里说的后者指的是对老师“有着较为虔诚的尊重与敬爱,加以赞颂与讴歌”。[5]
基诺族的散文作品通常叙述了老师关怀学生的难忘事件以及他们的高尚品质,刻画了无私奉献、温柔慈爱、善良敬业、乐观积极的教师形象,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恩和赞美、怀念与敬重。张志华是这方面的主力,《再送一程》的温元章老师在初中两年坚持陪伴学生走过野兽可能出没的险峻曲折的小路,这一份关怀和温柔被深情的歌颂;《一双鞋》的彭崇元老师在艰难的70年代初期,细心观察到“我”因没有鞋子双脚冻僵冻裂,送我一双黑皮鞋;《真情永远》的张良品老师看“我”因家境艰难影响了学习,选择管我的午饭、晚饭,晚上还会边改作业边辅导“我”当天的课程。王志祥的《我的班主任老师》一文刻画了一个不断追求完美、认真生活的教师形象,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敬业务实的品质,良好的教风学风令人敬佩。诗歌因为篇幅限制,不能展开叙事,一般都是直接抒情,依然是歌颂教师无私敬业、乐于奉献的美好品质,如张鉴的诗歌《园丁》中主要讲教师们在偏僻贫瘠的土地上,忍受荒凉孤寂,但他们任劳任怨,笑对生活,无怨无悔地奉献一生。
基诺族作家将目光聚焦于教师慈爱善良、无私奉献的形象特征,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有关。一方面,基诺族是人口较少民族,位于边疆山区,教育基础薄弱,学校教育的初步开展实施需要克服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基诺族学子十分懂事,明白教师们从远方来到这里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更亲眼目睹了严苛的自然条件和艰难的办学条件之下,老师忍耐寂寞、任劳任怨,将青春奉献给这片土地的动人故事。正如张鉴《园丁》所倾吐的:“遥远荒芜的土地,布满杂草荆棘。崎岖坎坷的道路,绵绵延伸进大山里。等待你的是偏僻,等待你的是贫瘠……”[1]324《再送一程》提到了汉族教师遇到的语言不通、学生贪玩、环境气候不适应、生活用水不方便等问题。对于基诺族作家来说,无私奉献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词汇,其包含的丰富内涵活生生地在他们眼前。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前,基诺族的温饱还是大问题,人们处于极端贫困之中,灾年更甚。“1978年,我们乡的41个自然村1441户人家,只有5户住瓦房,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只有96.4万元,农民人均收入才106元,群众生活十分艰辛。”[6]张志华也在《挖山药的日子》《真情永远》《一双鞋》等作品中多次书写过学生们的贫困与艰难,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如《真情永远》,“每人每天一角五分的菜錢,一碗饭和少量的南瓜或冬瓜、豌豆芽汤”,寒冷刺骨的冬天,学子们也是衣单少被。[1]107正因如此,在他们眼里,教师在困境中伸出的一双手里比教授知识更为重要,他们更没有更多心思去关心老师们的性格以及其它方面的挖掘。他们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人性中最珍贵的善良,老师展现善良的一瞬是最美好最值得书写的。
三.和谐的师生关系
基诺族作家文学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有村邻之间的互帮互助、友好相处,知己的闲暇共游,亲人之间的难舍眷恋等,但师生关系的和谐书写绝不应该成为被忽视的对象。走进学校接受教育是基诺族的一件大事,也是基诺族群众生命中刻骨铭心的记忆。前线教师成为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知识的代名词,是学校、国家等重要力量的凝聚实体,同时教师也是具体的,在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下,他们无私敬业、任劳任怨的精神愈发熠熠生辉。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客观生存条件不再那么严苛,但基诺族对教师的尊敬和热爱却留在了骨子里。基诺族的作家书写中,学生信任、依赖、尊敬老师,老师关心、喜爱、帮助学生,师生共同谱写和谐的乐章。
张鉴的作品,是以老师的视角书写师生之间的美好。散文《一起走》中,老师不只是一个教导者的角色。学生的纯净心灵和“傻傻的笑”,真诚直白的依赖“我们想和老师一起走”,抚慰了成人的疲惫。[1]50真情涌动,成就了师生共走在路上,欢声笑语不断的和谐画面。《远方的约定》一文中的感情大致相似,学生对归来的老师表达想念、撒娇,老师感动不已,最后师生一起玩游戏,而未来的约定是这份美好时间上的延续,见证这个约定的大青树为整幅画面增添了难忘的色彩。诗歌《心愿》中,学生是“茁壮的小树”,有“明亮的眼睛”,怀着“纯真的期待”,而“我”是园丁,有着丰富的“知识泉水”,泉水满足了期待,这正是师生之间的完美契合,教师眼中的“绿林花海”是学生不负教诲的最好归宿,也是和谐的诗意表达。[1]320-321
不同于张鉴作品中师生的有来有往,张志华作品中的师生关系似乎是教师的给予居多,《再送一程》老师两年都陪着学生走过险路,《一双鞋》中老师赠予“我”一双黑皮鞋,《真情永远》的张良品老师管学生的午饭、晚饭,晚上还辅导当天的课程,而学生却无以为报,这样的关系似乎不太平衡。多年后学生献出深情歌颂和“平安度春秋”的祝愿,学生炽烈的感恩之情和祝愿似乎才使得局面平衡,尤其《再送一程》是对老师和初中经历四十年后的追忆,填补了前面欠下的债,最终达到平衡。而且作家对人间美好品质的歌颂,对刻骨铭心的受恩经历的回忆,在老师付出关爱那一刻,画面就无比温馨和睦,如《真情永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剪影,学生复习当天课程,老师边批改作业、备课,边辅导学生课程。煤油灯增添了满满的和谐温馨感。
新一代基诺族作家对“和谐的师生关系”的书写显然更加幸福,没有了艰苦的教育背景,学校环境优美,教室明亮宽敞,老师依然是温暖的,一切都无比和谐美好。车都的《我快乐的成长一文》,“我”热心帮助同学,不吝弯腰捡地上垃圾,老师时常夸奖。“每位老师都关心着我们,同学们团结友爱”。[1]231-232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校,都无比的和谐,充满着真情。
相比于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学校教育书写的多样,情感层次的丰富,基诺族的书写内容和思想表达或许显得较为同质化和单薄,但基诺族文学书写的重要价值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作品记录和反映着民族学校教育与作家文学之间的特殊关联,是这个民族重要历史进程的再现。同时,学校教育专题的文学探讨较为新颖,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
参考文献
[1]中国作家协会.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基诺族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2]刘怡,白忠明.基诺族文化大观[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3]黄玲.拓荒与创造——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发展历程扫描[J].边疆文学,2016,(4):61-66.
[4]黄文丽.历史与文学[D].山东大学,2015.
[5]朱希祥.一半是神,一半是……——中国文学中教师形象的塑造及文化意味[J].文艺评论,1992(06):48-55.
[6]罗宗伟,谢先斌.跨越千年,全面小康[N].春城晚报,2019-6-3(1).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教育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基诺族作家文学产生的驱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1Y702)
(作者单位:昆明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