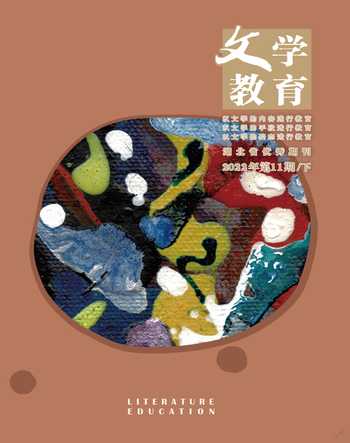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佩剑的符号变迁
2022-05-30贺嘉玚
贺嘉玚
內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士佩剑的历史进行梳理,分析剑的符号变迁。本文认为,从对抗皇权的工具之一,到皇权的授予物,再到文人精神的象征,最后成为一种艺术,直至消亡,“士佩剑”符号变迁的背后,是中央集权对分封制的摧毁、皇权的扩张及士地位的下降,以及市井生活的兴起。
关键词:中国古代 知识分子 剑 符号
中国的王朝更替频仍,但中国的统治阶层在“现在和过去,整整两千年以来,始终是士。”作为统治阶层,士的构成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点,在两千年来士佩剑的演变中可以发现。
剑在史前社会先被作为武器使用,由原始人类打磨而制成,它小巧便携,能够藏在衣服内贴身携带,“是一种防备意外的防身兵器”。而古代猎头习俗盛行,本身就有着象征胜利、证明勇气、威吓敌人的意味,而剑在猎头时能够发挥切割敌人头颅的作用,也拥有了象征的意义。
考古学家在商朝中晚期、北方草原地区的墓葬品中发现,青铜剑往往出现在青铜礼器旁边,装饰精美。剑随着青铜器一同进入祭祀当中,变得神圣化、礼制化,是祭祀规定制度化的一种象征。神话传说中,黄帝作剑、蚩尤作剑的故事和争论使得剑本身具有了象征意味,剑是“五兵”之一,孔子责骂蚩尤作剑的说法,认为蚩尤贪婪、见利忘义、六亲不认,因这些而丧命,他这种人作不出任何武器,剑已经与美德联系在一起。“在商代中晚期,剑主要被用在祭祀之中……从此,剑不但开始有了一些真正文化或统治秩序意义上的象征作用,还被更加深入地渲染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光环——玄奥可通鬼,威权缘自天。”
一.规范:区分地位和阶级
周时期的铸剑水平并不高超,剑身较短,在以战车为主要作战工具的当时,长柄武器、弓箭才是军事作战中更常用的武器,短剑只能用作近身自卫,贵族随身佩剑先是为了自保。除此之外,剑的制作工艺也十分复杂,普通人在经济上无法负担得起,再加上对贵族“文武兼修”的要求——既能精于诗书礼乐,又能统兵为帅——这种文化就为剑作为礼仪装束的流行和被认可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随后,西周“西戎献剑周穆王”的故事描画出强盛的周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武力优势,剑在其中成为外交的符号,剑具有了更高的地位。此时的中原地区贵族的墓葬频繁发现青铜剑,这显示出少数民族崇剑的习俗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剑突破了礼器和武器,成为贵族的装饰品。从这时起,剑的主要功用已经转变成了贵族身份的象征,贵族带剑之风蔚然形成了。
德国社会学家格罗塞曾说过:“在较高的文明阶段里,身体装饰已经没有它那原始的意义。但另外尽了一个范围较广也较重要的职务:那就是担任区分各种不同的地位和阶级。”剑在当时就是区分地位和阶级的符号之一。周公旦所规定的世袭制和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宗法制度规定了贵族的继承原则,贵族与平民之间、各级贵族之间有着明显的礼制规定,不可僭越。《春秋左传正义》写道:“车马、旌旗、衣服、刀剑,无不皆有法度”。剑的佩戴具有了划分阶级的色彩,只有贵族才可佩戴。《老子》中提到“服文彩,带利剑”,描绘了贵族热爱穿华服、带利剑的情形。
二.象征:品性的高洁
屈原在《楚辞》中写道:“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即剑,贵族屈原佩戴原本作为武器的剑,剑指示身份的功能之外,更暗含美德。
士将长剑看作是自己的好友,甚至是自己的象征。孟尝君的门客冯谖向孟尝君抱怨自己生活待遇低,吟唱道:
长铗归来乎!
食无鱼。
长铗归来乎!
出无车。
长铗归来乎!
无以为家。
冯谖对着自己的长剑发牢骚,实际上是在向孟尝君提要求,第三个要求被认为是非分之情,但孟尝君没有断然拒绝,而是给冯谖的老母亲送去吃食用品。一来没有破坏规矩,二来拉拢了冯谖,三来显示出他的雅量,吸引更多人才,他也得到了冯谖的效忠。在这里,冯谖随身携带的长剑是他倾诉的对象,就算冯谖生活贫困,但他依然必须有自己的佩剑,而且还无比珍重,回家也要一块儿回——剑是士高洁气质的代表。
剑指向权力与指向正义两种取向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定型,从此,剑既成为身份的象征,又寄托了文人的情怀,面对着皇权的扩张,剑的这两个方面也愈发清晰。
三.武器的权力意志
宗法制里各贵族层级递减,跌落到士——贵族最底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曾经接受过教育,在动荡的社会中也有一番抱负,是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士成为为大贵族建言献策的门客,拥有参政议政的权力。
佩剑原本是贵族的标志,在战国,旧的分封制分崩离析,新的封建制度在改革下诞生,佩剑的权力下放到平民。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七年,“令民初带剑”,能够带剑的群体大大向下延伸,主要是“士”这个阶层。秦简公面对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主动改革,把原本只由上层贵族才能享受到的特权下放,士一级的贵族拥有了更多的权力。
士佩剑拥有了与权力相抗衡的能力。按遂执剑质问楚考烈王为何犹犹豫豫不能定夺合纵之事:按剑这个动作是一种威慑。唐雎更是面对权力毫无惧色,面对秦王的愤怒及是否听过天子之怒的威慑,唐雎以士之怒回击,直接举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例子,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为回应,挺剑而起。可见在战国时,士是能够佩剑直面皇权的,且他们有着武器,有着剥夺王肉体存在的能力,因而在很多情况下是对皇权的制约。
庶人佩剑又让贵族佩剑有了更加高贵的内涵。庄子在劝说赵文王停止观看人斗剑的爱好时,讲述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的区分,他细细讲了每一级别剑的象征:天子之剑象征天子的权威,诸侯之剑象征诸侯的威势,庶人之剑则与斗鸡无异。在《庄子》的故事中,剑是不同的,天子、诸侯的剑始终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只有庶人的剑是为了个人欲望。这和钱穆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谋而合,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多以参政议政作为实现社会理想和抱负的唯一途径,能够从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中推演到超越阶级属性的政治构想来。这种对阶级的超越在战国时期最为明显:“战国知识界,虽其活动目标是上倾的,指向政治,但他们的根本动机还是社会性的,着眼于下层之全体民众。他们抱此一态度,使他们不仅为政治而政治,而且为社会而政治,为整个人文之全体性的理想而政治。”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大门的打开,知识分子得以通过政治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孔子周游列国,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等,无不显示出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政治和社会的热爱,他们着眼的,总是全体民众,而不是个人兴趣。
而后,随着皇权的集中,臣子上朝被剥夺了佩剑的权力,荆轲不得不将匕首藏在画卷中谋刺秦始皇,而殿内没有一个大臣能够救他。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销天下兵,则民间刀剑戟槊镝尽以为金人十二。意者吏尚带剑而民则莫敢有剑者矣。”民间佩剑的现象消失,佩剑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到汉代,“剑履上殿”成为皇帝表彰功臣的礼仪之一,唯有功劳巨大或权力滔天的臣子才能被皇帝特许持剑上殿。持剑上殿成为礼仪上极为贵重的符号,是皇权赐予的。
四.落寞的侠义
汉初,剑逐渐被利于砍杀的刀所取代,一些将校官吏由佩剑改为佩刀。剑作为武器的意味逐渐降低,剑被文人墨客视为气质和性格的标志,借以抒情,具有高度的审美意义。除此之外,还与舞蹈结合。
东汉,太学兴盛,士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藐视政治权力,“他们的人生,成为一件艺术品。”高尚不仕的风气让士在政治之外,成为纯粹平民式、书生式的阶级,名士之风诞生,这种传统从东汉一直延伸至南北朝,名士再加上门第,维系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在南方,东晋门阀政治治下,士族人才日趋退化,政治腐朽,玄学兴盛,名士为自我的满足而清谈;在政局动荡的北方,各门第依然为着稳定的政府而进行战争。这时的名士非常多:竹林七贤、陶渊明、鲍照、谢灵运等寄情山水,不同流俗,阮籍以剑作为诗歌中的重要意象,抒发自己在政治上不得不缄口莫言的悲愤哀怨之情,陶渊明咏诵荆轲的侠义,重点也放在他的剑上,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鲍照以剑直抒胸中悲壮激烈的情怀,慷慨而高贵。
隋唐时期,门阀势力兴盛,唐代的士多从门第而来,对政治积极合作,气度恢弘,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带有豪杰气魄;其后科举制成熟,政权向普通人开放,唐的进士们与门第分庭抗礼。唐朝的文学也阔大,诗歌走上高峰,诗人们延续魏晋南北朝的传统,用剑作为抒情扬志的意象。李白一生好酒爱剑,写下了“我家青干剑,操割有余闻”,“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抚剑夜吟啸,雄心照千里”的潇洒淋漓诗句,表达了报国立功的心声,慷慨豪迈。而当他在政治上遭遇挫折时,也是借剑来抒发,剑象征着他的政治才干:“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裙王门不称情”,剑也是李白蔑视权贵、热爱自由的象征符号:“不待金门诏,空持宝剑游”,“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杜甫在二十岁时浪迹天涯,表达自己“拔剑欲与龙虎斗”的气概;在经历了多年的流离颠簸之后,老年时发出了“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的感叹。边塞诗人岑参以剑舞入诗,剑与舞蹈结合,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表达边塞官兵浓浓的思乡之情。剑作为文学中抒发感情的重要意象流传至今,具备了凝练的审美:剑是友谊、自由、浪漫、风流、修身、神圣的象征。
舞剑则是在斗剑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较高审美情趣且呈现程式化的项目。从春秋起,舞剑就已经出现了,《孔子·家语》记载“子路戎服见孔子,仗剑而舞”,舞剑已经是君子修身的方法。秦以来,剑作为士随身佩戴的武器拥有了艺术的色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故事带有明显的军事、政治外交色彩,项庄是以“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作为舞剑的原因,说明那时已经有舞剑艺术了,且确实能够挥剑助兴,烘托场面。到了东晋时期,剑术开始遵循“重术轻击,多练少战”的理念发展,士依然随身佩剑:祖逖“闻鸡起舞”,刘琨“枕戈待旦”,为着报效祖国而练武健身,舞剑成为文人锻炼身体的方式。隋唐之后,剑舞文化达到高潮,甚至女性也可以舞剑,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描绘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舞剑具有了震撼天地的艺术色彩。剑舞从隋唐开始,走上舞台,成为表演艺术。
宋代门第不再,科举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补充,一时书院风起云涌,“一个尚武、好战、兼顾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所取代了。”文人佩剑的场景已不多见。到了南宋,剑舞基本从舞台上销声匿迹。元朝对武器管控严格,且普遍带刀不带剑,直至明清,治学风气盛行,尚武不再,士佩剑的现象从此消失。
从春秋到战国,再到秦汉大一统,佩剑的权力由贵族扩大到平民,逐渐下放,又从平民收回到统治阶级,剑从制约皇权的工具,变成皇权的授予物。从魏晋南北朝到北宋,剑由士的象征转为一种艺术,士佩剑逐渐失去其象征品格的意义,最终,士佩剑消亡在宋明清繁华的世俗生活中。
从对抗皇权的工具之一,到皇权的授予物,再到文人精神的象征,最后成为一种艺术,直至消亡,“士佩剑”符号变迁的背后,是中央集权对分封制的摧毁、皇权的扩张及士地位的下降,以及市井生活的兴起。
参考文献
[1]汤学智.台湾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韋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陈肯.挑灯看剑:混在杀戮里的浪漫情怀[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4]杨彦鹏.战国秦汉剑的凡俗化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4.
[5]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
[6]杜预,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司马迁.史记[M].上海:中华书局,1959.
[8]吉灿忠,郭强,刘帅兵.剑“文”化进程之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09):50-55.
[9]杨祥全.中国武术思想史纲要[M].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2010.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