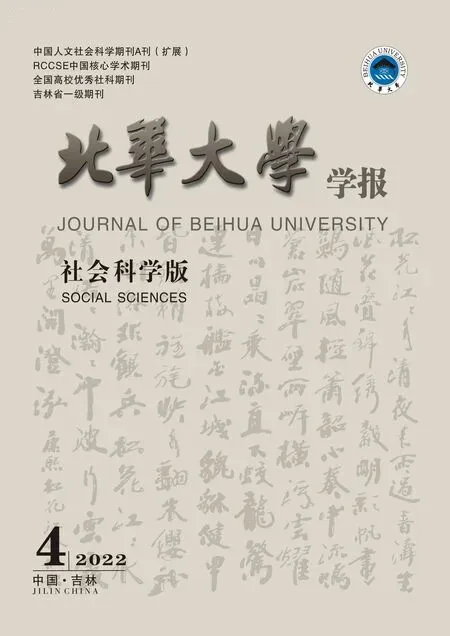壬辰战争时期朝鲜王廷对明日封贡议和的反应
——以通信使黄慎的遣出为中心
2022-04-16刘永连
刘永连 高 楠
壬辰战争研究中,封贡议和问题是学界尤为关注的话题。由于该活动是在明日双方的主导下进行,学界研究大多集中在明日之间的交涉问题,(1)李光涛《万历二十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7),对明日和谈的缘起与经过以及“封贡”政策的落实与失败进行了详细研究,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关于壬辰战争封贡议和的中文专著。然其史料限于朝鲜王朝《宣祖实录》等少数朝鲜官方史籍,忽略了朝鲜文集资料及日本史料,部分结论有待商榷。其他相关论文如杨昭全《论明代援朝御倭战争中的和议问题》(《朝鲜研究文集》(一),吉林省朝鲜研究学会,1981),张庆洲《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日和谈内幕》(《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第103—106、114页),朱亚非《明代援朝战争和议问题新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55—164页),文廷海《明代碧蹄馆之役及中日和谈考实》(《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9—13页),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和平条件的交涉及其变迁》(《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第132—143页),刘耀东《壬辰战争期间明日议和纷争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王煜焜《壬辰战争与十六世纪末的东亚世界》(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等,均是围绕明日交涉探讨问题。对于朝鲜在议和期间的反应关注不足。尽管个别学者关注到朝鲜对明日议和的态度及转变,(2)朱法武《壬辰战争中朝鲜对中日议和立场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第148—153页)。也有人论及朝鲜僧人松云大师与日军将领加藤清正之间的交涉,(3)如陈文寿《朝鲜禅僧惟政与壬辰战争及战后议和——佛教僧侣与东方外交之个案研究》(《韩国学论文集》2007年第2期第7—17页),陈尚胜《壬辰战争之际明朝与朝鲜对日外交的比较——以明朝沈惟敬与朝鲜僧侣四溟为中心》(《韩国研究论丛》2008年第1期第329—354页),刘晓东《万历壬辰战争和谈中的朝日交涉——以朝鲜义僧惟政与加藤清正的接触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02—111页)。上述成果均未涉入朝鲜派遣通信使及通信活动,因而对封贡议和阶段朝鲜层面史事的挖掘留有较大空间。但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层面需要切入,那就是朝鲜遣使问题和通信使活动,因为朝鲜遣使是封贡议和活动中直接涉及朝鲜的重大问题,而通信使活动又是反映朝鲜王廷意志的重要层面。本文即通过对这一层面的考察,剖析明日封贡议和背景下,朝鲜在遣通信使问题上的犹疑、挣扎及黄慎出使日本的种种表现,不仅揭示朝鲜对明封贡议和问题的复杂心理,亦反映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微妙变化。
一、明日议和博弈与遣使要求传出
(一)明日议和过程中的博弈
和谈期间,明廷内部就“封”“贡”问题多次掀起争论。册封与通贡是古代中国处理与藩属国关系的主要途径,“夫中国之御夷狄,顺抚逆剿,本为常经,因经行权,亦当通变”。[1]5539在明朝君臣看来,夷狄野蛮无知,但若其诚心归顺,皆可纳入华夷秩序圈中,得到明廷的册封、赏赐。基于这种传统,明朝君臣并不排斥与日议和谈判,这是壬辰战争中和平交涉能持续四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关于当时的和平条件,郑洁西曾专门著文讨论,认为明朝历经“封贡”之议,最终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与日本请封使内藤如安(小西飞)订立“三事”之约,强调“只封不贡”,对日政策实际上变得更为强硬。[2]所谓“三事”,即:“一、釜山倭众准封后,一人不敢留住朝鲜,又不留对马,速回国。一、封外不许别求贡市。一、修好朝鲜,共为属国,不得复肆侵犯。”[3]也就是说,此时明朝只准封不准贡,约定屯聚釜山的日军撤退后才进行册封。
日本方面的议和条件也有所调整。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宋应昌遣谢用梓、徐一贯出使日本,日方出示《大明日本和平条件》(4)该约具体条款为:(1)明公主下嫁日本天皇;(2)两国复开勘合贸易;(3)明日高官誓约通好;(4)割朝鲜南部四道予日本;(5)朝鲜王子及大臣渡日为质;(6)交还被俘朝鲜王子陪臣;(7)朝鲜永誓不叛日本。转引自郑洁西《十六世纪末的东亚和平构建——以日本侵略朝鲜战争期间明朝的外交集团及其活动为中心》(《韩国研究论丛》2012年第1期第283—308页)。[4],提出和亲、通贡、朝鲜王子大臣入质等七项议和条件。随着战事的发展及与明交涉过程中对明朝议和底线的试探,二十三年(1595)五月,日方又提出《大明朝鲜日本和平条目》(5)该朱印状原以“大明日本和亲议条”为题,但以“谕朝鲜差军将小西摄津守、寺泽志摩守大明朝鲜与日本和平之条目”开篇,故此朱印状一般被称为《大明朝鲜日本和平条目》。因小西和寺泽两家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败亡,该朱印状原件下落不明,但有誊文录于《江岳和尚对马随笔并云崖和尚续集》(简称《江云随笔》)。《江云随笔》原藏建仁寺大中院,东京都立大学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均藏有复印本。本文所用文本为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复印本。调整后的议和条件为:“一、沈游击到朝鲜熊川,自大明之条目演说之云云,依大明钧命,朝鲜国于令恕宥者。朝鲜王子一人渡于日本,可侍大阁幕下,然则朝鲜八道之中四道者可属日本者,前年虽述命意,王子到本朝近侍,则可付与之。朝鲜大臣两人为轮番,可副王子之事;一、沈游击与朝鲜王子同车马至熊川,则自日本所筑之军营十五城之中十城即可破之事;一、依大明皇帝恳求朝鲜国和平赦之,然则为礼仪赍诏书,大明敕使可渡于日本。自今以往,大明、日本官船、商舶于往来者,互以金印勘合,可为照验事。” 转引自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和平条件的交涉及其变迁》(《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第132—143页)。[2],主要集中到三点:以朝鲜遣王子为质代替割地要求;沈惟敬与朝鲜王子至熊川倭营后销毁倭营;册封后明日通贡。郑洁西指出,明廷表示只封不贡后丰臣秀吉仍提及通贡一事,很可能是小西行长在向丰臣秀吉汇报明神宗册封敕谕时回避了“一封之外,不许别求贡市”一条,使得丰臣秀吉认为恢复“贡市”尚有转圜余地,要求小西行长和寺泽正成在事后争取到“贡市”权利。[2]无论如何,日方的议和条件明显减少,将重点放在朝鲜遣王子、大臣入质上。
在后来的交涉中,双方态度和举措仍有变化。起初,日方提出朝鲜王子、大臣入质方可撤屯。(6)《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其中一条称:“四道者既返投之,然则朝鲜王子并大臣一两员为质,可有渡海事。”转引自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和平条件的交涉及其变迁》(《学术研究》2017第9期第132—143页)。然而朝鲜始终未答应遣出王子,日军还是撤回部分军队,焚毁多处倭营以示诚意。万历二十三年(1595)六月,行长从日本带来消息称:“关白已许撤兵,且差二将官,一管烧营,一管迎接。”[5]516七月,沈惟敬查探金海、德桥等处倭营,“则栅子望楼,尽已撤毁,旁屋则尚留一半,而亦皆撤去墙壁,以示必撤之意。”[6]但按照前约,准封后釜山倭众应数撤退,册封使才可渡海。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月,小西行长赴日向丰臣秀吉报告沈惟敬已到釜山的消息,临行前亦与沈氏约定,“请天使老爷,暂驻王京。如清正执拗不去,断不请天使进营。”[7]可在实际的议和交涉中,日本一再变卦。本来册封副使杨方亨等留住居昌县,准备待日军焚栅渡海后至釜山倭营,日方提出副使入营加藤清正才撤军。杨方亨至釜山后,日本又要求两使同入倭营后清正撤兵渡海。[8]可见,日本以撤兵为由不断提出新要求。同年十一月,正、副两天使均已身处釜山倭营,但直至次年五月日军都未撤尽。据黄慎状启:“清正已撤阵,而卒倭尚有三分之二;安骨、加德等处,则各其主将先入,而其余倭众待运粮讫,当过海。”[9]709朝鲜曾上奏明廷,力陈倭情之反复:“釜山、竹岛、加德、安骨四处倭兵,尚无渡海之期,倭将清正移据头毛,气势颇盛。”[1]5573可见急于促成议和的沈惟敬等人罔顾釜山等地还有大量日军的事实,多次奏报倭情无异,朝中大臣赵志皋、石星等人亦坚信日本志在册封,议和被继续推进。直至册封使一行发船渡海,釜山等处倭营仍留屯日军。
总之,围绕封贡议和问题,明日双方不断博弈。日军虽确有撤兵焚营之举以示议和诚意,但其以撤兵为筹码不断向明廷、朝鲜提出新的要求。虽然明廷决定“只封不贡”,对日议和条件更为强硬,但在推进议和的谈判中,实际上变得更为被动。此时的朝鲜,处在明日交涉的夹缝中,一直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探听消息,始终对日本的议和诚意表示怀疑,对议和前景充满疑虑与担忧。
(二)遣使要求的传出
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月,朝鲜国王于南别宫(7)按:“南别宫”,又称“小公主宅”,此前明朝使者至朝鲜都城,馆于崇礼门内太平馆,壬辰战争时,太平馆毁于战乱,朝鲜改由南别宫接待明朝来使。宣祖于此接待过刘綎、骆尚志、戚金等明军将领。接见沈惟敬,沈氏称兵部尚书石星令朝鲜差陪臣一员,随其至倭营宣谕日军撤屯渡海。[10]478朝鲜权衡后差出黄慎与之同行。然日本撤军一事进展并不顺利,朝鲜对遣使大有疑虑。四月,都元帅权慄驰启:“且天朝有人通谕于行长曰:‘天使往时,朝鲜通信使,亦当送之。’”[10]487朝鲜有人质询辽东都司谭宗仁,谭氏当即辟谣:“我与玄苏、行长、调信等,相对议定,而不及朝鲜使臣入去之事。如此等语,决不可信也。”[5]506明朝并无此说,但朝鲜君臣还是对此事予以关注。君臣议论时,郑经世及李德馨强烈反对,认为朝鲜同倭贼乃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遣使之理;而朝鲜国王等则担忧明廷要求朝鲜遣使:“通信使,或礼部题本、圣旨,或兵部,迫胁入送,至于降敕,则何以为之?”[5]507可见,朝鲜君臣虽有断然拒绝日本的魄力与勇气,却对明廷若要求遣使心存忌惮。
在朝鲜国王等人忧虑重重时,身处釜山倭营的黄慎也面临考验。日僧玄苏表示,平调信自日本返回后,朝鲜通信使当渡海通信,且应择官尊位高者遣之,这遭到黄慎等人的严词拒绝。[11]616同年十二月,平调信从日本带来据说是出自关白之口的议和条件:“但关白欲得朝鲜陪臣通信,勿论大小陪臣,要一介跟天使到日本。”[11]619这一说辞与此前《大明朝鲜日本和平条目》明显不同。丰臣秀吉所要求的遣王子、大臣被平调信转述为“遣陪臣通信”。联系平调信自日本回釜山后曾先于釜山众倭将终日密议,又至沈惟敬处谈话良久之举,[11]619很可能平调信从行长等人口中了解到朝鲜对遣王子的反对态度,故小西行长、平调信等人退而求其次,将其要求调整为朝鲜派遣陪臣赴日修好。(8)按:黄慎《日本往还日记》亦记载,当通信使一行返程至大浦时,小西行长曾言:“当初关白放还两王子之时,意谓朝鲜必差王子中一人来谢,而厥后竟不为来谢。我曾对沈游击言之。而游击曰:‘我要一个陪臣,亦不肯许,况肯差遣王子乎?尔勿复言’云。我又禀杨天使。天使但曰唯唯,不肯说出。我辈亦以为只此使臣之行,亦足完了事,故不为强请耳。”参见黄慎《日本往还日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3页)。[12]193同月,沈惟敬移咨朝鲜,正式对朝鲜提出遣使要求:“天朝为贵国解纷,允其封事,乃遣开国带砺元勋及倚重大臣,远涉海岛。揆之理势,不必关白欲烦陪臣同行,而贵国亦应遣二三陪臣,追随天使东渡,亦礼也,义也。况彼又有是意乎!”[11]619此后,朝鲜遣使通信作为明日议和的附加条件开始正式被频频提起。
通过与朝鲜官员接触,沈惟敬等人深知朝鲜对议和不满,更不要说日本又有遣使要求,故而在劝说黄慎时,沈惟敬不断强调遣使对促成和议的关键作用,“陪臣若不去,则两国终不得宁息”,“若令一陪臣跟去,则大事可就。不须大官,只妆出一武官,将就送去亦足矣”。[11]619尽管如此,遣使一事还是在朝鲜朝堂引起轩然大波。
二、朝鲜王廷对日本遣使要求的反应
对朝鲜而言,主动与侵略者日本遣使通好无疑是对其国家尊严的挑战。闻知日本要求遣使,朝鲜君臣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可随着明日议和交涉的进行,无论明朝册封使臣,还是留驻朝鲜的日军将领,都开始向朝鲜施加压力,积极劝诱朝鲜遣使。朝鲜君臣的心理经历了长久的挣扎,最终在现实压力前动摇,开始倾向于遣使赴日和议。
(一)义理与尊严的坚持:拒不遣使
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初三日,就沈惟敬移咨问题,朝鲜二品以上大臣献议,在实录中留下了40多位大臣七千多字的议论。备边司对其内容总结道:
沈游击移咨,以大臣所议观之,则沈守庆以为:“陪臣起送,实是无名之举。”柳成龙以为:“今此咨文,若以直辞拒之,则正坠于游击作弄之中,不可于一言之间轻为许与不许,使难收拾。以更査彼中情形,与册使商确定夺之意回咨,观其答如何而处之。”崔兴源以为:“今若轻许,而他日之请不止于此,则前头难处之患,恐有甚于今日。”尹斗寿以为:“册使则不与较,而游击中间弄坏至此,宜以严辞婉意修咨。”金应南以为:“不可轻信游击之言,遽从其请。宜具奏以闻,以待天朝处分。”郑琢以为:“绎以王律,则宜犯私交之罪。非有皇朝钦差,不可冒行。”诸宰臣所议,虽有异同,而其不欲通使之议,则大概如一。惟权征、李希得以为:“姑从其言。”朴忠侃、权慄以为:“不称信使,差官跟随天使而送。”此乃国之大事,议论间有不同如此,未知何者为长。[13]
从朝鲜廷议情况看,除极少数人认为不以通信之名则可遣使送之,多数大臣从义理及现实利害出发对此事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明朝天子、兵部、册封使均未有朝鲜遣通信使的指示,若遣使通好,则犯私交之罪,且今日若轻易答应日本条件,则他日欲壑难填。基于此,朝臣建议以“不可从”之意回咨沈惟敬,且将此事告知明使,上奏明廷。
册封使久不渡海,明廷流言四起,明神宗大怒,责问石星封事进展,明廷诸多官员因此革职,故石星连忙差人至册封使寓所,再次敦促渡海册封之事。[14]随后,千总刘朝臣赍正使李宗城咨文通知朝鲜国王:“为今日计,陪臣似当从权遣发,跟同使节过海,而证此盟约,永尔辑睦,彼此不许相犯,庶两国生灵,有息肩之日。”[15]在石星、沈惟敬及小西行长等多方劝说及压力下,李宗城亦开始要求朝鲜遣使。
万历二十四年(1596)四月,发生正使李宗城出逃一事,各方惊动,促使册封议和的进程明显加快。恐丰臣秀吉闻此不满,釜山倭将急急派人回日本通报:“上天使逃出,不过病心所致,而讹言所惑,脱身独出耳,别无他意。”[16]688同时,平调信等则对朝鲜威逼利诱:“关白若闻上天使不即入来之说,则必增疑虑,发送兵马之后,则势难停寝矣。上天使差出之间,朝鲜通信使,上副中一员,先送釜山,与副天使同在,则关白必信无疑。”[16]688副使杨方亨也一改其最初“没有所干”“不欲带去”的态度,开始积极劝说黄慎等人促成朝鲜方面遣使。
(二)现实压力下的动摇:遣出“陪臣”
正使出逃、明廷催促册封使赴日,这一系列变故使朝鲜君臣态度松动。万历二十四年(1596)五月二十八日,明朝册封副使杨方亨差备通事朴义俭呈书于朝鲜王廷,再提遣使问题:“副使谓义俭曰:‘过海陪臣,观事势,不可不给。岂必以通信为名?只随我往还可矣。给则速给;不给则亦当永绝,毋使彼更望。然,不给则恐必不利也。’”[9]714六月一日,承政院提议:“今副使以此屡为揭帖,至于委遣通事朴义俭,使之面达。今若不从,则后日处置,恐益难于今日。故以跟随陪臣许送事回答,而差出其人,随后发送宜当。但以信使为名,则难处之端益多,又必有国书、礼物等。今但依副使杨方亨前后所言,只谓跟随以送,此后虽有他言,一切紧拒,不可听从也。”[17]1总之,朝鲜朝堂内,同意遣使的声音越来越多。
六月三日,朝鲜国王要求从二品以上官员就遣使一事献议,在《朝鲜宣祖实录》留下三千七百多字记录。[17]4-5其中,行判中枢府事尹斗寿议:“我国摧败不振,凡所以缉补收复之策,皆仰天朝,而天使若索跟从,至于再三,在我无辞可拒,势不可免焉者。但以跟随为名,从天使而行,恐为无妨。”行领中枢府事沈守庆议:“陪臣往日本事,名之为信使,则不可为之。依副使之言,陪伴使臣而行,则似是无妨。”商山君臣朴忠侃议:“臣之愚意,天使前使译官周旋,涤去通信之号,以天使跟随称号入送,于理不甚无谓。”以此次群议观之,则朝臣皆认为危迫之际,应作变通之举,不妨以天使“跟随陪臣”称号派出使臣,解决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兵部差官詹永祥等传来明廷指示,“本部题奉圣旨,已升杨老爷为正使,沈老爷为副使,诰勑、章服,随后出来”[17]7,议和继续被推进。杨方亨等恐再生变,在日军并未尽数撤退的情况下先行渡海。[17]16就遣陪臣一事,兵部回咨朝鲜国王:“至于陪臣随册使渡海一节,该国不敢擅许,请命天朝,具见恭顺之义。但以要致为名,则不可轻遣;如果释憾修好,则不宜峻绝。一听彼国君臣相机而行。”[18]此时朝鲜君臣如坐针毡,既面临日本催促遣使的直接压力,又担心若议和不成,朝鲜拒不遣使会成为日本嫁祸朝鲜的理由。朝鲜国王与朝臣商议决定,以敦宁府都正黄慎、掌乐院正朴弘长分别为正、副使,以跟随陪臣为名入送日本。[19]23
朝鲜确定遣使后,日将要时罗、平调信又进一步提出礼币之请。[17]21此番得寸进尺之举,激起朝鲜的愤怒。七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之间,司宪府、司谏院数次合启,极陈倭贼变诈,通信、书币不可为之事。[19]30-33但如备边司所言:“大抵论事易,处事难,自古有是言矣。台谏在论事之任,故惟务直截而不顾他事,臣等在处事之地,故千思百度,而未免委曲。”[19]28最终,在考量义理与利害关系之后,朝鲜国王答复“廷议已定,更无可为”,做出坚持遣使且送出书币的决定。[19]33万历二十四年(1596)八月初二日,朴弘长携国王准备的贺关白书及礼物抵达釜山。八月四日,黄慎一行终于与调信等人同行,发船渡海。
李光涛先生曾指出,“跟随陪臣”四字,自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始见之,既无前例,亦无后继,是在东封史事中专用名称。[20]事实上,朝鲜君臣深知,所谓跟随陪臣,不过为给自己保留一份体面的掩耳盗铃之举。此前朝臣议定以跟随陪臣为名遣使时,政院就直言:“‘称以跟随则无妨云。’此一句话,足以捧腹。昔有一人,盗钟而恶其声,遂自掩其耳。今日所议之事,是乎。”[17]5一般来说,朝鲜通信使团的使命,主要是两国官方的一般外交礼节性的交往,保持彼此商贸的畅通,互相交换情报。[21]此次遣出的使团,即以“修好”“睦邻”为目的,虽无通信之名,但日方以通信为号,使团又书、币俱全,其性质与通信使无异。朝鲜之所以如此,实是自视“小中华”的朝鲜在面对眼中的“蛮夷”日本时,坚持保留自身文化的一份优越感而已。
三、黄慎出使与议和失败后朝鲜王廷的反应
迫于压力,朝鲜遣出熟知倭情的黄慎出使日本,但朝鲜君臣反对议和的态度却贯穿通信使整个出使过程。黄慎拒绝了日方提出所有的要求,并竭力探听消息。议和失败后,朝鲜君臣根据黄慎等带回的消息对倭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也由此为应对日本的二次进攻做出准备。
(一)黄慎出使
万历二十四年(1596)闰八月十八日,明和朝鲜使臣抵达日本堺港。二十八日,日方通报丰臣秀吉将于九月初一日接见明使。次日,小西行长等人突然带来关白恼怒朝鲜的消息:“当初我欲通中国而朝鲜遏,不为通情。反至动兵之后,沈游击欲调戢两国,而朝鲜上本极陈其不可。且以沈游击为与日本同心,每每恶之。李天使之出去,亦因朝鲜之人恐动。册使既渡海,而朝鲜不肯差官跟来,今始缓缓来到,且不遣王子来,事事轻我甚矣。今不可许见来使,我当先见天使后,姑留朝鲜使臣,禀帖兵部,审其来迟之故,然后方为许见。”[12]177平调信、要时罗劝说黄慎等及时将此情况报告沈惟敬,使其尽力措辞,平息丰臣秀吉怒气。但黄慎称:“我离釜山时,已决三条计,事体若快则竣事即返,一计也。事体或变,欲为拘留则任留一年十年,一计也。事体大不顺,则虽加凶害亦所不辞,一计也。”[12]178可见,黄慎出使日本,一开始就抱定不对日本做任何妥协的决心。
丰臣秀吉怒而不见通信使,但册封一事还在推进。九月初三日,丰臣秀吉受封,诸倭将40人具冠带受官。[12]179封事已成,可回自大阪城的沈惟敬又一次带来关白恼恨朝鲜的消息,其说辞与此前平调信所言几乎无差。(9)按:按沈惟敬说法,丰臣秀吉在其面前表示怒朝鲜之意,原因为:“我四五年受苦,当初我托朝鲜转奏求封,而朝鲜不肯;又欲借道通贡,而朝鲜不许。是朝鲜慢我甚矣,故至于动兵。然此则已往之事,不须提起。厥后老爷往来讲好,而朝鲜极力坏之。小西飞入奏之日,朝鲜上本请兵,只管厮杀。天使已到,而朝鲜不肯通信,既不跟老爷来,又不跟杨老爷来。今始来到。且我曾放还两王子。大王子虽不得来,小王子可以来谢,而朝鲜终不肯遣。我甚老,朝鲜今不须见,来使任其去留。” 参见黄慎《日本往还日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12]179据二人说法,此时丰臣秀吉对朝鲜发怒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日本欲通贡明朝而朝鲜不为之通情;二是朝鲜不遣王子且通信使姗姗来迟;三是明朝与日本讲和而朝鲜从中屡屡作梗。大事垂成,又生波澜,日本矛头直指朝鲜,这究竟是小西行长与沈惟敬勾结祸水东引,还是丰臣秀吉的真实想法?初五日,“沈老爷贻书关白,且使正成、行长等往议撤兵。通信等事,明日竿后当回话矣”[12]180,这让丰臣秀吉的怒火迅速升级。据平调信描述:“今日行长等持沈天使书往见关白,关白大怒,曰:‘天朝则既已遣使册封,我姑忍耐。而朝鲜则无礼至此,今不可许和。我方再要厮杀,况可议撤兵之事乎?天使亦不须久留,明日便请上船。朝鲜使臣,亦令出去可也。我当一面调兵,趁今冬往朝鲜’云云。”[12]180传教士刘易斯·弗洛伊斯(Luís Fróis)的《日本报告书》对此也有记载:
使者(明朝册封副使沈惟敬)给太阁写了一封信,提了如下的希求:“请将朝鲜的倭营全部毁弃,撤回全部在朝鲜的驻军。大明皇帝前年以慈悲原谅了朝鲜人,请您也同样地宽恕朝鲜人的过错。他们或许应该受到惩罚,但是,即使惩罚了他们,您也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啊!”……太阁读到尽毁倭营这段要求时,非常愤怒,内心好似被一个恶魔的军团给占据了,他大声叱骂,汗出如涌,头上好似冒起一股蒸汽。……[4]
可见,沈惟敬提出日本撤兵、通好朝鲜,使丰臣秀吉怒火彻底被点燃。无论是《大明日本和平条件》,还是删改后的《大明朝鲜日本和平条目》,丰臣秀吉始终表现出胁控朝鲜、凌驾于朝鲜之上的意图。闻知使臣抵日本,丰臣秀吉还未与使臣相见,就表现出对朝鲜是否遣王子的强烈关注。可实际的议和交涉与其预期相差悬殊。未能与明朝通商,连不堪一击的朝鲜都能拒不遣王子,藐视其尊严,沈惟敬又于此时提出撤兵、通信要求,日本对朝鲜仅有的军事胁控都将失去,这是丰臣秀吉不能接受的结果。秀吉怒不可遏,决定再次发兵朝鲜,封贡议和宣告失败。
九月初九日,在杨方亨及沈惟敬的劝说下,通信使一行无可奈何地踏上返航船只。值得注意的是,使臣临行之际,平调信等人仍旧不放弃议和的最后一丝可能,希望使臣便宜从事,先应下送出王子的要求;又提议若关白见使臣,则使臣便宜许之以“或每年遣使,或间一年遣使,且定礼币之数,为以恒式”[12]182。总之,黄慎虽未能见到丰臣秀吉就被迫回程,但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所有要求。黄慎此行是朝鲜与日交涉的代表,其绝不对日妥协的态度代表着朝鲜王廷反对与日议和、通信日本的立场。同时,在黄慎看来,明朝册封使杨方亨、沈惟敬的表现显然有失天朝“体面”。初闻关白怒朝鲜,平调信等人有意使沈惟敬周旋,但沈惟敬“连日对关白不敢一言及之”,引得平调信等人都连连感慨“天朝不忒软,怕关白如此,可恨可恨”。[12]179当黄慎询问如何应对议和失败问题时,沈惟敬无可奈何地表示:“人在井上,方救井中之人。今自家方在井中,安能救人耶?”[12]182册封使的种种表现,深深触动着朝鲜使臣。
(二)议和失败后朝鲜王廷的反应
黄慎等人归国后,在宣祖面前作了详实汇报。君臣议论间反复提及的内容,往往是朝鲜关切所在,也最能体现朝鲜此时的复杂心理。
在东亚诸国,自从蒙元时代即13—14世纪以后,各国的“自国中心思潮”崛起,构起一种涉及国家尊严的文化比赛。[21]如宋希璟、李景稷、金诚一、金世濂等,均曾在名分与礼仪等方面与日方较量高低,且表露出朝鲜文明高于日本的心理。(10)按:宋希璟(1420年出使日本)、李景稷(1617年出使日本)均曾因国书书写问题与日本产生争论。金诚一(1590年出使日本)、金世濂(1639年出使日本)均曾因礼仪问题与日本产生纠纷。宋希璟《老松日本行录》,李景稷《李石门扶桑录》,金诚一《海槎录》,金世濂《海槎录》均可见于《海行总载》(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重印本,1985)。这种文化较量绝不单纯是使臣个人意志的表现,更加折射出朝鲜王长期存在的文化优越心理。每当与日交使,朝鲜王廷往往就通信使人选颇费心思,“必选一时之人材”[22];使臣回国复命,朝鲜君臣又往往询问日本衣冠、风俗、待使之道,以此审其高下。
黄慎一行复命,宣祖同样反复问及日本接待明使的仪仗、饯慰,还有册封仪式的举行及日本谢恩使、谢恩表文的送出等事。黄慎有意强调:“封王时,贼将四十余人,皆以唐服行礼,独关白不为衣冠矣”[23]93,“而拜礼则或云为之,或云不为矣”[24]134。在儒文化圈中,礼仪往往传达着政治秩序的权威,也维系这种秩序下的尊严。日本是否严格按照仪礼接受册封,在朝鲜看来是其诚心与否的表现。同时,“衣冠”常被作为文明象征,而“大明衣冠”则被朝鲜视作华夏正统在本国延续的象征。(11)按:明清鼎革之后,东国士大夫以固守“大明衣冠”来表示其对“中华”文明的坚持与传承。中国的元明易代 (1368),与朝鲜半岛的丽鲜更迭 (1392) 近乎同时,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作为文化象征的衣冠,在明丽新宗藩关系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丽末士大夫屡屡通过“请冠服”这一举动 来表示对华夏文明、进而是对自称接续中国“正统”的明王朝的认同;而站在华夏中心主义立场上的明王朝,也乐于通过颁赐冠服的形式 来显示对藩属国在文化上的接纳。“大明衣冠”在丽末鲜初的行废,与明朝和朝鲜半岛关系的起落相同步;在明初的东亚国家关系里,衣冠成为构建政治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参见张佳《衣冠与认同:明初朝鲜半岛袭用“大明衣冠”历程初探》(《史林》2017年第1期第96—107、74、220页)。[25]在这种观念驱使下,丰臣秀吉在受封仪式中不著唐服,显然被朝鲜君臣视为尚未开化的蛮夷行为。还有谢恩使问题,丰臣秀吉面对册封强调“必先通朝鲜后,次可遣使天朝”[24]134,终无遣使谢恩之举。后来“有倭僧三人,是关白所亲近掌书记者,来议回谢表文”[12]180,再后“复令正成赍表来,无印信,天使不受。”[24]134日方这些行为,在朝鲜君臣看来无疑是无礼、不恭之举。
朝鲜有意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26]当文明参照物由中国换成日本时,它便充满优越感乃至傲慢。黄慎对日本待使之道大加批评:“倭国无礼义,故别无仪仗,而只以金牛运行。有时以简慢之礼待之,则一枝筇竹,徒步来见。”[24]134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日军挺进朝鲜半岛很快就使得朝鲜三都尽失,朝鲜君臣仍有日本军制、器械战备皆不及朝鲜的自信。黄慎称:“弓矢非不持去,而点火弛张,必难得宜,故不为用力于弓矢。至于舟楫,倭子之所尝操习,而只知轻捷之爱,不知完厚之为可恃,故我国船制,不知学得矣。大砲则无之,每以鸟铳放之。”[24]134关于日本军制,黄慎认为:“关白使行长等将兵,而各治兵治食以自给,不如我国或出兵力,或运粮糗矣。”[24]134
这种单纯的文化优越心理并不能抵御现实中蓄势待发的日军。议和不成,秀吉欲再次发兵,这是直接关系朝鲜生死存亡的问题。黄慎等带来日军动向的最新消息:“关白,使清正、长政、吉盛、行长等四将先去,此四人当为先锋。清正则今冬当先渡,长政、吉盛则冬末春和当出去。清正等虽先去,只屯据旧垒而已,大军则二月间出去。”[24]133危急之下,朝鲜迅速做出再次请兵明朝的决定,“为今日计,要须尽力措备,而告急于天朝,速请天兵出镇平壤”[23]95。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南兵擅长水战且军纪较好,多次在对日作战中取胜,给朝鲜君臣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故宣祖及多位大臣都提出,要请南兵,“必请南兵,辽军则无能为已”[23]95;“须告经略处,速请天朝得南兵,留屯南方某处,则人心有恃,贼亦畏忌也”[23]95。但朝鲜李元翼等人也深刻意识到,不可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明朝兵马,除了请兵天朝,还从水陆两方面制定迎击日本的策略:“陆地则当据险坚壁,以挫其锐,清野以绝粮道,水路则以舟师出没于釜山以南,邀截贼势,幸而得胜,则贼必有后顾之忧,而不敢恣意深入。”[23]103
事实上,在此前的议和交涉过程中,明廷在撤兵问题、遣使问题上均对日本做出妥协,朝鲜对此十分不满。封事结束后,杨方亨和沈惟敬试图欺瞒明廷,其发向明朝的禀帖中极言秀吉受封之恭敬、对明廷之感恩,只字不提秀吉拒不撤兵、欲再启兵衅之态度,更是让朝鲜大失所望。[24]127议和失败的消息传至朝鲜,领议政李恒福评价:“天朝之人,急于功利,殊不知信义之为何事。……今此东封一事,天朝非不知苟且,而犹强而行之者,意必有在。善揆度彼我,称量轻重,不得已而为之。……今贼酋,既受封于天朝,加兵于我国,则当初天朝拯济我国之意,已无有所在,只是无故而捐百万之金,封化外之国也,外有封倭之名,内无封倭之实也。”[23]109然直面凶悍、强大的日本时,朝鲜对明朝军事上的依赖远远超过其心理上对封贡议和的不满,朝鲜君臣一致决定再次请兵明朝,又可见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务实心理。
通过对朝鲜王廷在议和和通信问题上系列反应的梳理,可以看出三国复杂的关系。而在此背后,也折射出这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微妙演进。首先,随着战事进展,日方深知拿下朝鲜、攻取明朝并非易事,故其索求目标转向朝鲜对日本的臣服,希望以朝鲜王子入质日本或驻兵于朝鲜半岛,达到胁控朝鲜的目的。在两者希望都落空的情况下,丰臣秀吉再次兴兵侵朝,掀起带有明显报复性、残忍性特点的丁酉再乱。其次,朝鲜看待封贡议和,对日本撤兵、朝鲜遣使问题尤其关切。朝鲜君臣对明朝议和政策不满,对册封使行径更是不耻,但其无力独自抗衡日本,只能依违明朝,消极地参与议和。面对日本,朝鲜军事上屡屡受挫,却处处强调自身文化上的优越。
在近世华夷秩序扩大化的过程中,朝鲜、日本皆有意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秩序圈,这势必与其“事大之礼”产生冲突。事实上,朝鲜经常从自身国、家利益考量而做出有违“人臣”本分的行为,外交政策具有明显的务实性特点。而日本接受明朝册封,不过是想借“封”通“贡”,获得实利。壬辰战后,明朝和日本断绝交往,朝鲜却很快恢复与日交邻关系。如此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朝鲜对明廷失望、不满所导致离心倾向加大的表现。总之,在此背景下,若明朝还试图以“怀柔远人”的传统羁縻政策息事宁人,带来的只能是表面的和平与秩序的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