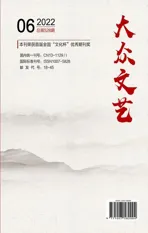女性私语化写作的审美研究
——以《私人生活》为例
2022-04-11林芷含
林芷含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000)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诞生推动着个人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在这一时期私语化写作潮流的背景下,女性身体欲望逐渐得到重视,聚焦于女性个体经验的私人写作进入到大众视野之中。郭春林教授指出,“私人写作”指的是“摆脱了宏大叙事的个体关怀,是私人拥有的远离了社会和政治中心的生存空间,是对个体的生存体验的沉静反观和谛听。”
而陈染1995年创作的《私人生活》文如其名,具有鲜明的私语化色彩,进一步将女性私语化写作推上高峰。
《私人生活》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以女性为主体的书写,也正因如此,本书的情致抒发才如此深邃而真挚。作者有意识地描绘着倪拗拗成长成熟路上的微末细节,用诗意的、充满幻想的笔致抒发了感伤与浪漫的情愫。
一、身体美学——女性对于自我的关注
(一)身体感知的层叠递进
主角倪拗拗对自我身体的体认,是在对于两性关系和身体欲望的感知与探索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文中第一次直接谈及“身体”,是从T先生令人窒息的猥亵中开始的,这样扭曲的性体验给儿时的倪拗拗留下了一定的阴影;此后,禾寡妇的爱抚对倪拗拗进行了进一步的启蒙;夏日里,拗拗渐渐发觉自己的身体变化,如胸部日渐丰满等,这是生理上成熟的标志;在随后的成长过程中,拗拗在缺乏对性的充分认知的状态下面对了多次猝不及防的身体体验,如目睹伊秋与表哥发生关系的经历,再遇T老师的纠缠的经历等等;最终,极力摆脱过去,摆脱恋父情结的拗拗遇到了初恋尹楠,并在尹楠离开、母亲去世之后迈向孤独,达到真正的精神上的丰满与成熟。作者在其意识流的写作中,细致地描绘着主角倪拗拗面对自身身体的所思、所感、所想,并不断向内探索,剖析解构其成因。小说全程使用倪拗拗的第一人称视角,用细腻的浪漫主义情调描绘着女性青春时期曲折的、非常态的身体认知,展现了时代情感对青春的表达。陈染这种个例性的、摒弃他者视角的书写,是私语化女性写作的特点之一。
倪拗拗,这个孤傲的、看似思维古怪的女孩,她的懵懂、隐忍和沉默的根源来自畸形的环境——亲情和友情的缺失,也来自父权制社会中的性抑制等权威的压迫。
(二)自我探索的身体美学
全文的最后一章,成年后的倪拗拗躺在浴缸中,看到镜中的自己,思绪游走开,展开了“白日梦”的幻想。这段情节充分地展现了陈染对于潜意识流露的敏感性,以及其意识流的写作风格。
“我从来不知道躺着的时候,倦怠和柔软会使人如此美丽和动心。”此时,倪拗拗被自己身体雕塑般的美感所感动,透露出某种“自恋”的特质,通过镜像的躯体体验,倪拗拗完成了对于自我的身体的体认。这种通过掌控身体以获得精神上的独立的叙事手法,展示出写作中女性化的身体美学特征。
同时,此处的环境,即不大的浴室和狭长的浴缸,其封闭性与包裹性的特征有着多重隐喻的意味。
首先,是自倪拗拗儿时起,父爱的缺失和父权的压迫就使她缺乏安全感,而倪拗拗蜷在浴缸中这样仿佛回归子宫的姿势和行为,正暗示着这一点;其次,外部世界的喧嚣使拗拗不堪其扰,因而她试图躲起来、封闭自己,逃离世俗的纷扰和重压;此外,性的意味也不可避免地在这个封闭、隐秘的小空间里默默弥漫开来,倪拗拗在她的绮丽的性的幻想中,通过与他者交融的方式来探索她自己,而透过一切她所经历过的她者,她成了现在的自己。
此处在拗拗对于自己身体展开了一番探索之后,她开始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展开哲学性的思考,这里笔者将会在后文进一步进行阐述。
二、母亲与姐妹——对于同性关系的审视
《私人生活》全书主要描绘了两类同性关系——母女情谊和姐妹情谊。两类关系相互关联但也有所区别。而可以肯定的是,作者笔下的女性与女性是相互共情的、是站在统一战线的。
(一)母女情谊
在小说的母女情境中,倪拗拗与母亲共同生活在父亲高压的强权之下:“我们对父亲们说‘是’,我们对生活说‘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在相似的压迫之下,倪拗拗与母亲一样是“遍体伤口”、一样地痛苦挣扎,因而无意识地建立了一种共生共存、循环映照的关系。母亲的命运,透视到倪拗拗的身上,使读者仿若看到倪拗拗的另一种结局——如果没有选择孤独,她将成为下一个“母亲”。
而倪拗拗与禾寡妇之间,更多存在的似乎是一种禁忌的爱恋。文中,禾寡妇散发着“一股‘母亲’的气息,这气息一直令我十分迷恋”。
暂且不提精神分析学所阐述的“恋父情结”,倪拗拗身上的“恋母情结”实际上是更加深刻和鲜明的,因此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中生长的倪拗拗把对母亲的依恋移情到了禾寡妇身上——她们有着相似的孤独、相似的感伤与恐惧。陈染笔下,倪拗拗与禾寡妇惺惺相惜,女人间也可以相濡以沫、心心相印,在她的多个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
同时,母亲、禾寡妇与倪拗拗之间的情谊,既可以视为充满张力与隐秘愿望的女性情谊,又可视为女性自我的双重投射。因为在倪拗拗通过外部世界来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她需要找到一个参照,而母亲和禾寡妇正好成了倪拗拗特定阶段的理想自我形象,由此,倪拗拗在“母女情谊”中找到了自己身份的镜像。
(二)姐妹情谊
《私人生活》中的姐妹情谊即体现于倪拗拗与伊秋的友情。但情节中两人的友情其实并不牢固,而只是建立在某种被迫的“共情”上的。
如文中所说,倪拗拗是“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而瘸腿的少女伊秋与拗拗同属于人群中的异类,被群体所排外,由此才建立起友情。但不同的是,伊秋是被迫疏离人群,而拗拗则是主动选择去疏离人群的,因此拗拗和伊秋短暂的做伴,并不能使她们互同款曲,两人的精神上仍然存在着隔膜。但即便如此,伊秋的出现还是对倪拗拗影响颇深。
伊秋在拗拗成长过程中影响她最多的,在于青春期少女对于性的关注和对于生命的认知的方面——倪拗拗在审视同性关系的过程中,也逐渐丰富了自己对于自身的体认。在同性身份的镜像中,倪拗拗看到了不同层面的身体体认,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将自己与对方相区分。
母女情谊和姐妹情谊两方面的书写,透露出陈染写作中对于同性情谊界限的暧昧态度,体现了她丰沛的情感质性和对于性别秩序的试探和挣扎。戴锦华老师讲到,由于真切的个人经历与体验,陈染认为,“与同性朋友的感情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力量”,其情谊的疆界的微妙与脆弱十分耐人寻味。
三、从对抗到和解——对于父权与异性关系的审视
(一)恋父情结与弑父情结的对抗
陈染的叙事中的恋父与弑父情结是共存的,故事中,是父权的压迫、父爱的缺失使主角对于具有父亲特征的这类角色既爱又恨。例如,T先生作为倪拗拗的老师,与倪拗拗的父亲一般,有着相似的蛮横和相似的权威,这个角色实际上就是倪拗拗父亲的变体。而倪拗拗在与T先生对抗的过程中,却不得不一步步地被其所谓的“爱”所引诱,这种结果正是源于倪拗拗的恋父情结,源于T先生弥补了拗拗对于父爱的渴望。同时,在渴望着一个“父亲”的角色的同时,倪拗拗也憎恶着“父亲”这类角色的粗暴和蛮横。例如,倪拗拗曾多次在想象世界中对T先生展开愤怒的反击;此外,某次在内心深处的某种冲动的驱使下,倪拗拗用剪刀剪破了父亲的裤子,这透露出她潜意识中的恨意,即潜意识的“弑父”情结。
(二)对于父权的审视
“许多男人就是这么一种矛盾、暴烈、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作者借由倪拗拗成长途中对于不同男人的审视,描绘了父权制社会下部分男性的蛮横与残酷,憎恶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在父权的强权面前,拗拗在性的层面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这种憎恶退居幕后化为隐性。
倪拗拗面对父亲和与父亲相像的T先生的态度,始终是隐忍的——她虽然厌恶T先生,但却不得不屈服于父权的强势。在长久的性的压制下,倪拗拗无力反抗从而不得不屈服,她不得不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房思琪一般,即使对于侵犯本能地回避与憎恨,但为了使自己好过,产生了将诱奸行为下意识地美化的心理。面对父权的性剥削,她太无力了,因此只能退让,在想象中试图获得真正的爱,在想象中征服对方,并且将放弃抵抗侵犯姑且视作自己对于对方的“怜悯”。
(三)与异性间关系的和解
温情而青涩的尹楠,他对倪拗拗来说或许是个例外。在尹楠身上,拗拗最终达到了自己对“弑父”和“恋父”情结的和解,认可了两人的关系。即使这种和解并没有解决倪拗拗身上的全部困境,但或多或少是一种精神上的有利慰藉。陈染关于异性关系的书写是个人化、私语化的,且在某种程度上带着强烈的主观个性。她肯定着离不开身体体认、但同时也超越了身体体认的两性关系,并指出其中的种种问题——她的写作中,异性情谊与同性情谊的内核同时充斥着文化症候,而主角则不断在不同的关系中寻求着出路。
四、“孤独的人不是无耻的”——孤独感、异己感的书写
(一)死亡美学的书写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的倪拗拗曾多次提到死亡、多次幻想死,这除了是源自其童真的好奇之外,也在预示着之后母亲和禾的相继去世将会对倪拗拗造成深重 的隐痛,渗透着倪拗拗对于生命的哲学思考。母亲和禾相继去世后,本就孤独的倪拗拗此刻更加孑然一身,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隔离的孤岛”了,这样的经历使倪拗拗越发“孤独”。或许陈染如此安排情节的目的,除了是为了通过自叙手法书写和表达从而获得自身心灵的治愈之外,更加为了使倪拗拗彻底性地走向独立、走向成熟。“我听到死像一件最刺耳的乐器,仿佛是尖厉的玻璃或者金属发出的声音,房门合着它的拍子,“嘭”的一声关闭起来,我被外部世界排除在外。”——这是倪拗拗对于生命的深邃感叹,将生死相隔用带有异己感的死亡美学演绎得深入灵魂。
(二)孤独美学的书写
最后一章中,倪拗拗对《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首1994年的老歌进行剖析,以“为什么孤独可耻”的问题,步步引出了、直视了自己身上长久以来的异己感。
“拗拗”名字的含义或许就意味着执拗、反叛、离群。首先,倪拗拗“瘦弱”“不合群的别扭天性”的背景就铺陈了“孤独”的审美底色——她注定远离人群;其次,被父权控制的焦虑、生命中重要角色(如母亲和禾寡妇)的离世,则造就了她对于社会的失望与憎恶,造就了她对于生命的偏悲观认识;再次,时代的轻浮使她主动选择远离这样一味地狂欢。
终章的倪拗拗除却拥有了对于死亡的深度认知之外,更是在反思许久过后,对于“自己本身是怎样的”以及“自己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问题形成了无比清醒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抉择。
“我对自己说:你是无耻的,你多么地无耻啊!”倪拗拗以反讽的感叹回应了狂欢的集体主义社会:世界说她疯了,非要她摆脱“孤独”,她便装作妥协以得空追求内心真正的自由。时代的背景逼迫倪拗拗被迫地妥协于时代情感,但这种妥协是表面的,她绝不会从心底去认可它,也不打算附庸这种时代主流。倪拗拗本质上是反叛的。
后来,倪拗拗漫不经心地给医治她的精神科医院写了封信,乔装成“已经回归正常”的模样,但同时深知“其实,一味地欢乐是一种残缺,正如同一味的悲绝。”“这座城市正在由于日益的膨胀而愚蠢麻木。”倪拗拗憎恨狂欢而浮华的“世纪末的流行病”,与享乐主义的现代生活相比,她实际上更加适应着孤独,渴望着孤独状态下的宁静。倪拗拗的内心在呐喊:“孤独的人不是无耻的!”
在这里,陈染回应了小说开头就已抛出的结论:“性,从来不成为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在别处——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
这两个“残缺”的形容,透露着不同的信息。“残缺的时代”一指拒绝孤独的享乐主义现代生活场景:它是残缺的,不包容的;二指畸形的父权性别压制使社会残破不堪,挤压了女性的生存资源、生存环境。而在这“残缺的时代”生存的倪拗拗又怎能是完整的呢?因此,倪拗拗自嘲地描述自己为“残缺的人”。
“残缺”这个严酷、刻毒的词首次用在倪拗拗身上,是来自T先生的恶毒嘲讽。而“残缺”的标签,恰恰是T先生在那个原本完整的拗拗身上留下的无情的创伤和烙印。或许是源于这永久的伤痕,抑或是源于对社会的反讽,此后的倪拗拗常常用“残缺”一词来形容自己的异己感,并将此视作自己本身携带的“问题”。
事实上,陈染认为,女性真正缺乏的并非欲望的缺失——当代女性已经开始敢于承认欲望,但脱身于“孤独”之境、迈向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仍旧困难重重。《私人生活》这整部小说实际上是一次对于“残缺”的寻回与再读,是对女性私语化的清晰认识。这种“残缺”虽然看似荒诞,但它意指那些独立于主流的异己感的特质,是小众的、独属于倪拗拗的孤独美学。而这种孤独美学在终章的前几章,倪拗拗的回忆中也表现了出来:倪拗拗的孤独是“有气节”的孤独,是为到达自由和独立的另辟路径。
结尾处,倪拗拗凝视着龟背竹,再度去审视自己的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而其实现实中的作者已然坚定地做出了她的选择:
“日子一天天过去,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小说的终章结尾与序章呼应,对全书中倪拗拗的身体体验做了概述性的描写:主角的孤独感源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时代的冲突对立;成长过程中曲折而隐秘的身体探索终结出果实;最终,恋父、恋母情结收束,成为欲望的自我表达,陈染用一种平静的、微暖的笔触,描绘、升华、释放了一场自我欲望的洗礼。
在这里,倪拗拗自渎的情节被描绘得隐秘、委婉、唯美、细腻,甚至可以称作神圣。
镜中的倪拗拗在浴缸中自渎,她沉浸于“上半身被(母性的)女人抚摸,下半身被(去父权的)男人抚摸”的幻想之中。此时倪拗拗对禾和尹楠的复杂情感碰撞交织,象征着作者对于同性关系和异性关系中性别视点的总结——回归女性本体后,女性的身体仍属于自己,而女人最终依恋的仍是女人,并在性关系上同男人得到和解。
回顾整篇小说,作者在前后映照的闭环叙事中,将孤独感、异己感所带来的各类美与丑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时还透露出独属于陈染的、充满幻想和感性的神秘主义审美倾向,将女性深层次的心理活动,如幻想和追忆,书写得细腻而透彻。
结语
整个《私人生活》的叙事呈现为一幅感伤而执拗的自画像。它是作者的一次追忆、一个澄清、一场表态,全文充溢着私语化、自叙传色彩。作者大胆描绘了身体欲望,将同性情谊和异性情谊的交织描绘地细腻而意蕴丰富,同时构建了意识流的,具有独特异己感和神秘主义审美的女性话语风格,具备着女性化的身体美学、死亡美学和孤独美学,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写作提供了新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