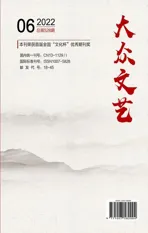王度庐悲剧侠情小说的叙事艺术分析
2022-04-11王远润
王远润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199)
王度庐以他的悲剧侠情小说书写了一代代江湖人的真诚与不易,他的武侠言情小说中,折射一个大时代的无情变迁。王氏武侠貌似漫不经心,实则苦心孤诣地为读者呈现了一出出有厚度的大戏。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的“现代特征”确在不断发展,不断有新的元素注入,但总有某些根本“基因”的相似。“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因而发掘、研究王度庐悲剧侠情小说中的“现代性特质”有利于更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谱系与脉络,发掘民国武侠小说的现代性。
王度庐擅于将西方小说的叙事艺术技巧融纳于传统叙事模式中,具有很强的超前性与创新性。王度庐悲剧侠情小说在叙事艺术上仍有很大的可探讨空间。具体分析王氏武侠的叙事策略,探讨在叙事层面体现出的悲剧意识能够完善对于王氏武侠的“类型”研究,更好地梳理现当代言情武侠小说的发展谱系,理解当下的文学生态。有利于读者审视并反思现实生活,对命运拥有更多理解之同情,关注普通小人物的悲喜人生。
一、灵活转换的叙事视点与悲剧意识
王度庐的悲剧侠情小说创造性地运用了“封套结构”与“双重非全知视角”,他对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使得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更类似于品鉴者对老照片的观看以及观众对老电影的重温。拉开一定时空距离的审美静观使得时移世易、物是人非的苍凉氛围更加浓厚。“叙事视角是一篇小说构思和布局的基石。”王度庐在其武侠故事的讲述中主要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视点。这种叙事视点也是我国古典小说最常选用的叙述角度。王度庐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继承了第三人称叙述的传统,又自觉融合了具有突破性的叙事视角与结构方式,在叙事视点的灵活转换中显现其独特的悲剧意识。
(一)封套结构的运用
叙事视点的灵活转换在王度庐“鹤-铁”系列之后的悲剧侠情小说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绣带银镖》中王度庐成功实现了在多种叙述视角间自由流畅地切换。小说开头,叙述者以自然的第一人称视角“我”向读者描述当时的社会,“保镖”行业逐渐受到冷遇,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存在于过去的名词。叙述者以画外音的叙述方式拉开了读者与文本间的审美距离,为悲剧效果的产生做出铺垫。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向读者介绍主人公刘得飞。在正式进入叙述后,第一人称叙述者退场,转而由第三人称“他者”视角介绍刘得飞与许小芳、卢宝娥两个女子之间的爱恨纠葛。小说结尾,叙述者以拉开距离回望历史的视角交代了刘得飞晚年的生活境遇,与小说开头的印子部分首尾呼应,带给读者“物是人非”的叹惋之感。从而使小说的头尾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封套”或“镜框”,将故事嵌入当中,构成巧妙的小说结构。
因此对于小说文本的阅读就变得与欣赏“镜框”中的黑白老照片相似,时空距离的间隔使得属于旧时代底层人的挣扎更具辛酸悲凉的美,增加小说的悲剧感。“封套结构”的存在是一种王氏武侠在叙事艺术上的独特创新,巧妙地体现作者独到的悲剧眼光、悲剧意识。在《紫凤镖》中,叙述者以同样的“封套结构”进行叙事。小说开头回溯到清代光绪年间,由保镖行业的兴盛引出曾经威震一方的“紫凤镖”,随后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向读者介绍了“紫凤镖”的威力。当小说进入到对柳梦龙和陶凤儿凄美爱情故事的叙述时,“我”的视角随之隐退,第三人称的客观叙事视角登场。至第七回结尾处,作者重新认同叙述者“我”的视角,向读者补充介绍陶凤儿死后柳梦龙的境遇与生活状况,首尾呼应成完整的叙事“封套”,使读者沉浸在陶凤儿短暂却传奇的悲剧人生中,回味无穷。作者在对叙事视点的灵活运用中,随心穿梭于不同的人称与视角,在一波三折的叙事节奏中收放自如,向读者娓娓道来他的悲剧武侠世界。
(二)双重非全知视角
除了在叙事中注重视角的自由切换,王度庐在其悲剧侠情小说中还成功尝试了“双重非全知”视角的运用。“鹤-铁”系列中《铁骑银瓶》的故事成功实践了“双重非全知”视角。在小说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和作者一样都是“无所不知”的,对小说第一回玉娇龙在岁末风雪中于张腋城来安店产子,后被方二太太调包的故事了然于心。而随着讲述过程的推进,讲述者和“假想读者”被当成了“非全知者”对待。他们与小说中的主人公玉娇龙、韩铁芳、春雪瓶以及次要角色绣香、萧千总等处于同一观看境地,同呼吸,共悲欢。小说中大部分情节推进主要选取主人公韩铁芳的视点。他聆听了养父情绪激动的追忆后更加坚定了西去寻母的决心,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落入黑山熊之手的方二太太。与病侠玉娇龙的相遇、同行,叙述者细腻地展现出韩铁芳内心对病侠的“莫名亲切感”。他护送病侠出玉门关,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亲手埋葬玉娇龙,于无意中尽了人子的孝道。在韩铁芳追随春雪瓶赴迪化城、路遇罗小虎、勇斗吴元猛的过程中,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整个叙事过程中,故事的真相与始末得到“抽丝剥茧”式的还原,向读者传递出人类在命运戏弄下的徒劳、悲戚、辛酸与无奈。巧合的设置,故事的推进显示出王度庐的叙事功力。对故事“全知”的读者,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非全知”的人物上演痛苦的悲剧,那些对局内人来说解释不清的举动,无法言明的举动为拥有双重视角的读者昭示了“直觉”无法言说清楚的意义。在“双重非全知”的观看视角下,读者因拉开了一定的审美距离而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也更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玉娇龙纵横大漠,威风凛凛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夫离子散、骨肉分离的痛苦与悲哀。在审美静观的过程中,母爱、父爱的高尚与感人得以更强烈地展现出来,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因而玉娇龙的大漠埋骨、罗小虎的雪山葬身更加具有悲剧的震撼力和崇高之美,其中透露出的辛酸况味耐人寻味。在“双重非全知视角”下,人物一次次与真相擦肩使“全知的”读者得以直观感受到命运的无可奈何。笼罩在作品之上的悲悯感也由此而更加强烈。在叙事视点的灵活运用中,王度庐悲剧侠情小说的深刻性得以显现。作品的悲剧意识、现代精神也得以更深层次地展示。
二、富有悲剧感的色彩隐喻
王度庐武侠小说中对于色彩有极为巧妙独特的处理方式,善于运用明快的暖色与柔和的中性色调表现悲戚诡魅,在强烈的反差中显露悲剧张力。“色彩不仅是视觉上的知觉手段,也与社会文化、人文心理相契合。”从颜色隐喻的角度来讲,颜色的使用频率对于不同作家是个体化、差异化的,不同作者会对不同色调形成心理倾向。由此,颜色隐喻主要是作者以其独特的手段表达感受的叙事技巧。
(一)色彩隐喻与悲剧人物的内在一致性
王度庐悲剧侠情小说对于“紫色”的运用体现着作者独特的倾向。众多色彩中,紫色是一种特殊的颜色,首先因为它在自然界中的提取相当复杂,物以稀为贵,因而紫色从古至今就被赋予了一种神秘而高贵的含义,它暗示权力与财富,是特权阶级使用的色彩。同时,作为红蓝双色的混合,紫色带上了飘忽不定,捉摸不透的性质;同时也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代表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反抗精神。“鹤-铁”系列之后,王度庐的创作模式更加成熟,对于色彩象征意义的运用也更为精妙。
《紫凤镖》与《金刚玉宝剑》中,作者对“紫色”的运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陶凤儿是一只凤,然而她终究不是“金凤”却是“紫凤”,她身上很好地凸显了一种“紫色气质”。《紫凤镖》中,“紫色”是出现次数最多的颜色,绣着十分精细的紫凤的“紫凤镖”是作品中第一个出现于读者阅读视野下的物件,这镖旗上的紫凤取的是女主人公陶凤儿随身携带的紫绒凤,只要有“紫凤镖”所保的镖车,无论是多少辆,准保万无一失,“紫凤镖”在江湖上的权力与地位隐喻着它的主人陶凤儿的江湖威望。凤儿是一个具有紫色气质和现代性色彩的悲剧女性。她为江湖恶霸所惧怕而又行踪神秘,和紫色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她武艺高强,与柳梦龙大战众多回合而精神益奋,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她家产丰厚,田产众多,帮助“三霸天”改邪归正,是权力和财富的掌握者;她逃离耿家,摆脱耿二员外,拥有对霸权的反抗精神。这些都与紫色的象征意义巧妙吻合,具有内在一致性。
《金刚玉宝剑》中,王度庐同样探讨了一个与紫色相关的悲情女子:吴卿怜。作者对吴卿怜所居崇楼的外观进行了三次细致入微的描写,因为吴卿怜所居的崇楼处于和珅府内,这“紫色的绸帘”“紫色的绫子”恰到好处地凸显着这座楼宇的华贵和楼宇女主人在府中的权利与地位,这冰炸梅窗格上紫色灯光的亮浅又象征着它主人的受宠程度和生命力。叙述者以伍宏超的视角窥探了这“紫色”灯光三次,灯光由“很亮”到“淡紫色”再到“黑得厉害”,明暗变化暗示着吴卿怜由受宠到失宠的过程,也隐喻她生存境况的恶化。但生存境况恶化却激发了她的反抗性,可是她的反抗终究是不彻底的,她将未来再次交给了一个并不能护自己周全的男性,最终落得失足坠楼的下场。这微微染着的淡紫色的灯光成了吴卿怜悲剧命运的隐喻,暗示着作者对他笔下女性前途和命运的隐忧。
(二)反差强烈的色彩对悲剧感的营造
王度庐尤为擅长使用“红”“金”等明艳华丽的颜色词表达诡魅、凄惨、悲凉的意蕴,营造强烈的悲剧张力。“红色”原本代表旺盛的生命力与喜悦。在王度庐的作品中,这个原本充满热情的色彩,却被赋予了凄惨哀艳的寓意,彰显了作者对这种色彩的特殊印记。作者写“明艳的红色”却表达的是“血红色”的诡魅。
在《鹤惊昆仑》中作者细致地刻画了鲍阿鸾与纪广杰成婚的场面:“墙上和两扇屋门都贴上了红喜字,窗子上也遮住了红布窗帘。”此时的纪广杰是“戴着没有顶子的红缨帽”,此时的洞房是满屋的“红”与“金”,极为华丽,但是成婚的鲍阿鸾却是芳容暗淡,“两只眼睛哭的红肿”,这满屋的“明红”使人能够不自觉地联想到鲍阿鸾深山失踪后遗失在荒野暗夜中的一只红绣鞋。而荒野深村中艳丽的红绣鞋却透露出诡魅的意味,隐喻着阿鸾凄惨哀艳的命运。可见,阿鸾夹在“人伦”与“天性”之间挣扎的痛苦是血红色的,就像她引剑自刎后胸口涌出的鲜血。暗夜的阴森惨淡与明丽华艳的明红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刺激着读者的感官。在颜色词的本意与情景意中强烈的反差构成巨大的戏剧张力,其隐喻意义耐人寻味。
“红色”在王度庐的作品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在《卧虎藏龙》中,作者同样细致地刻画了玉娇龙在鲁宅中的“新房”。“外屋陈设得颇为华丽庄严。墙上还贴着双喜字,挂着喜屏,朱色艳然。”只是屋中的窗户全都“挂着红色的布帘……堂屋还摆着神龛,供着‘伏魔大帝’‘观音老母’,佛灯下还压着种种灵符”,屋中的陈设与新房的红色配在一起,多了神秘幽暗的意味。这种陈设是鲁玉两宅为掩人耳目而自欺欺人的道具,是古老的、东方的婚姻中蕴含的门第观念和礼教规训的象征。而此时的玉娇龙是被囚入笼中的鸟,被禁锢在这神秘幽暗的红色所隐喻的“门第为重”的观念里。从对“红色”的把握与运用中,能够看到王度庐对色彩的敏感。将人物的悲惨际遇透过色彩的晕染表达出来,在加强视觉冲击力的同时,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意识。
除红色在王度庐的作品中蕴含丰富而深刻的内蕴意味与悲剧性意义之外,“金黄色”“黑色”“白色”等同样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悲剧意识,起到很强的渲染悲剧氛围的作用。在《铁骑银瓶》中,侠女玉娇龙的落幕显得格外悲壮,而这种悲壮的效果却主要是通过“金黄色”与“血红”的强烈对比传达出来。“他披散头发,脸有如金纸一般黄而发光,……血色惊人,冲得胸上的沙子直往下落;脸上发上都沾着吐出来的鲜血”这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将一代女侠玉娇龙的形象推向完满,展示出了一种悲壮的崇高性。
“金纸一般发光”的脸凸显出玉娇龙患病之重,但同时也隐喻着她作为一代奇侠,一生的伟大与传奇,此时的玉娇龙是带着光晕的。而与这金黄色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冲得胸上的沙子直往下落”的鲜血,急而多的血红色与金黄色糅合在一起,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令人对病侠产生出强烈的痛心与惋惜。但由此,玉娇龙的形象得到了极大的丰满。读者可以想见,玉娇龙拼命挣扎想要说出口的话无外乎与铁芳的母子相认。她对铁芳有极度的牵挂与不舍,虽然最后始终没有机会说出,但玉娇龙生命的后期,“母亲”这一身份被着重强调,尤其在“死亡”这一场景中,她完全就是一位母亲,一位散发慈母光辉的平凡却伟大的母亲。明艳的色彩本身带有的刺眼光晕与悲戚惨淡的寓意结合,极大地增加了文本的冲击力与悲剧性。
一生游走江湖,渴望获得自由,骄傲狠辣的侠女终因“母亲”的身份而变得温暖柔软。养育与寻亲的过程虽磨难重重,但她的生命终因成为母亲而圆满。作者在此将玉娇龙最终还原成了一个普通的女性,一个普通的母亲,一个普通的“人”。
此外,《铁骑银瓶》中黑龙潭沙漠绵延不断的黑沙丘、白龙堆沙漠中天地的昏黄、祁连山石洞外皑皑的白雪坚冰,这些色彩无一例外地渲染着作品如史诗般的悲壮氛围,增添着作品的悲剧性意味。王度庐于细微处注入悲剧色彩,增强作品的悲剧性。这种敏锐而又细腻的悲剧意识透露出作者对悲剧出神入化的巧妙运用能力,反映出一种现代性精神。王度庐对色彩的选择、调配与把握可谓是现代武侠小说创作史上一次有益的尝试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