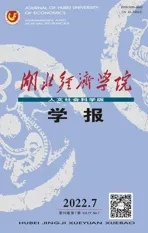论外宣翻译中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性
2022-03-25曹韵之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南宁530000
曹韵之(广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一、引言
“对话”始自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际。 对话是古老的交流方式, 远古先民主要是通过对话来传递信息、表达思想、交流感情。 中国的先贤孔子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通过对话传授知识。 广义的对话是万物之间的互动。 巴赫金借用音乐中的复调提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对话概念。对话体现的是主体间性,自我的存在就是与他者的对话。
孙文宪教授分析了萨义德的“东方学”观点,指出“东方”实际上是一个用西方话语建构起来的语言现象[1]。 中国对西方而言则是一个被建构的他者的形象,受西方意识形态塑造与操控。 在西方的视域下,中国的他者形象历经几重变化,从清朝时期在国际地位上的失语到抗美援朝的胜利,标志着夺回话语权再到现今由被动转向主动,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愈发密切,而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也需要推陈出新。
翻译活动也就意味着对话活动, 是主体间的交流,是自我与他者的互动。 “如何通过各种类型的翻译输出并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一个全新的、崛起的中华民族形象, 已经成为翻译实践者和研究者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2]。
以下主要从“自我与他者的相约、自我与他者的竞争、自我与他者的言欢”来探讨外宣翻译中,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认知思维模式、以及话语体系等层面的对话性。
二、自我与他者的相约
随着中国的经济、科技等迅速发展,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屹立在世界舞台, 世界各地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更多的国家希望了解关于中国的政策走向、外交趋势、科技发展与文化内涵。 在“一带一路”倡议语境下,大量的外宣翻译(传统文化、典籍、新闻语篇、外交话语等的对外翻译)目的是以期达到与他者文化实现有效沟通与对接的效果, 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助推中国文化远洋,翻译义不容辞。
(一)走出去更要走进去
现今, 有不少外宣翻译走出自家国门的成功案例,但是也面临着难以走进他者国门的问题,许多效果差强人意。如翻译的成品在国外接受度不高,甚至被排斥与误读。
1. 主要原因
其一,我们没有亲近他者的认知思维模式,在翻译时更多的从自身的视角用他者语言去再述中国文化,但是没有做到再现中国文化。语言差异是需要攻克的难关, 翻译过程中常见中外文中没有对应的术语的情况发生, 普遍认为译者是戴着脚镣的文本奴仆, 一边试图再现原文内涵, 一边努力满足译文受众,左右为难。
其二, 对中国文化术语的精神内涵缺乏深刻了解。 翻译家黄友义指出,“几乎每一条术语背后都是几千年的文化史。”何况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无所不包,丰富多彩,对其理解不易,翻译则更加不易。翻译对于助推外宣话语远洋功不可没, 通顺且表意正确的外宣翻译十分有助于中国声音的传播,反之亦然。
其三,对于外宣工作而言,需要紧跟时代脉搏,与时俱进。 不同时期外宣话语中所传达的政治动向不同,聚焦重点也不同,故而需要译者常学常新,多多阅读与思考。
2. 解决方法
其一,坚持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最初由费孝通先生提出, 文化自觉着重强调译者除了对他者文化的了解之外,更应该对本国文化底蕴烂熟于心,并对源语与译入语文化持客观态度。罗选民教授指出,“翻译中的文化自觉应包括对源语文化的自觉、目的语文化的自觉和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文化自觉,这要求译者不仅要谙熟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同时还需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 文化自觉不仅适用于典籍外译, 在其他类型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也应作为基本前提。 ”[3]
其二,研究西方汉学家的译作,如宇文所安的作品《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其中收录了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等著作。中国的文论术语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凝练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气节,是耐人寻味的宝库。研究西方汉学家的作品相当于研究西方学者的认知思维模式, 深入了解西方逻辑与理性, 贴近他者思维,有利于外宣翻译作品更好地为西方受众所接受。
其三,多与他国受众交流,了解他们的阅读需求与关注重点,以及寻找异同,进而通过译文激发他者的认同感。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认真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价值理念, 努力发现彼此不同的思维方式及其存在的分歧,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最合适的方式来解读和翻译最合适的典籍材料,从而达到消解分歧,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极大地满足西方受众阅读中国典籍的需要”[4]。
(二)引进来更要批判吸收
我们认为除了走进去的问题需要努力解决之外,关于中国文化传下去与引进来的问题也十分值得思考。 自我是与他者相对应的概念,是密不可分的。 在寻求走进去的突破口时,引进来的任务也不能落下。 作为西方视域下的他者,中国文化、政治话语与对外传播都极富魅力。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他者视域下的自我。正如巴柔所言,“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 ”[5](转引自孟华,2001)
中国文化走出去,走进他者文化之中,自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但不应鄙弃他者,不可忽视他者文化之长处, 在翻译过程中还须引进他者文化, 要对他者文化进行风险评估, 不可盲目引进, 要做到有的放矢, 要批判吸收他者中的优秀成分,吸收他者文化中的精华。 在引进时,要进行科学甄别,理性地去判断真伪,以批判的态度吸取他者营养。 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引进他者的优秀成分绝非同化自我,自我是独立的存在。 尤其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的翻译绝不能因为引进他者而异化自我, 我们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明以及民族话语体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三、自我与他者的竞争
除了以上讨论的要打破文化上的壁垒外, 在外宣翻译中,还存在语言之间、话语体系之间的竞争。具体是源语vs 译入语、作者话语vs 译者话语、译文话语vs 受众话语。 这三个层面的竞争分别与语言风格、文化介入、话语形象建构及意识形态有关。
(一)源语与译入语
源语与译入语是两套语言体系, 有语码形式差异,语法构式差异,特别是两种语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难以找到对应词的情况,或是语义内涵不对应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语言结构的差异性越大,其对世界的概念化方式就会越不相同。 在翻译的时候,就会存在源语与译入语之争。 对待源语与译入语,译者应报何种态度? 以源语为取向还是以译入语为取向? 此时译者应该考虑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和文化因素。 语言结构差异很大,则应以译入语为取向,表达上尽量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尽管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源语的个性,但有利于译入语受众喜闻乐见。若是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较大,则应以源语为取向,翻译时可以采用直译加注或音译加注,做到忠实与易懂。
1. 作者话语与译者话语
在德里达、福柯、巴特等解构主义者眼里,作者是被否定的对象,作者死了,但我们不能完全无视作者的存在。作者有时是隐身的言说者,有其特定的话语方式。 翻译中,要么作者话语同化译者话语,要么译者话语同化作者话语。二者最好达成某种默契,否则翻译就无法完成。
在翻译过程中, 作者的思想与意图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译者所改写。 这时作者的权力和译者的自由就会发生碰撞,产生摩擦。译者作为重生的作者有权利进行再创作与一定程度上的偏离和改写源文本。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指出翻译即改写,改写必然受到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者的操控。同时取决于翻译的目的,正所谓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根据场依存性,主体的认知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而做出一系列行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方面解构作者的话语方式,另一方面又是在建构自我的话语。译者话语的建构无疑会受到自我与他者文化介入的影响,同样地也会受到自我与他者意识形态的影响。
2. 译文话语与受众话语
必须指出的是译文话语不等同于译者话语。 译文话语可能是译者的母语、第二语言,也可能是译者的中介语。译文话语与受众话语同样处于竞争之中。译文话语要为受众所接受, 译文话语也需要与受众话语达成默契。 将外宣话语思想融入他者的语言体系中,译者需要考量的因素有许多,但以读者感受为主。Holliday 认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把他者视作自我主体形象构建的关键要素;但由于人们对“他异性”缺乏正面认识和沟通欲望,常对他者产生臆想和偏见,以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优越感[6][7]。 (转引自黄勤、谢攀,2019)
翻译推动着中国话语的传播, 其中外宣翻译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助推力。外宣话语是国家形象的表征,其中政治话语代表了国家话语权。 自“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出后,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对于中国话语感兴趣的西方受众也从原来单一的学者圈辐射到西方社会各个领域。 故而外宣翻译话语的建构则更须考虑受众话语方式、表述习惯,使得外宣翻译话语能够为广大西方受众乐于接受。
四、自我与他者的言欢
自我与他者是难以拆分的。 “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 我也以某种方式同时说出了围绕着我的世界。 他者形象如同一种次要语言,它平行于我所说的语言,与其共存,又在某种意义上复制了它,以说出其他的东西”[5]。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 实际上自我与他者作为一个完整的共同体而存在。 尤其在外宣翻译中,自我与他者不应该彼此拒斥,而应是彼此包容,互相取长补短。 只有二者达成默契,翻译话语才是和谐话语, 才具有协调性, 翻译是言和与言欢,绝不是拒斥与抛弃。
因此,在翻译中针对他者文化、他者话语体系和他者形象,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巴柔(Pageaux)认为他者文化态度有三种基本倾向:憎恶、狂热和亲善[6]。 (转引自黄勤、谢攀,2019)
(一)对他者的迷恋及憎恶
在此,我们将巴柔的他者文化态度“憎恶、狂热和亲善”进行诠释。自我的迷失常常导致对他者的迷恋,形成对他者“狂热”的态度。当译者把他者文化视为优于自我文化、本土文化时,译者就会认为自我文化是低级的文化,进而故步自封。他者便凌驾于自我之上。从古至今,对他者文化持有狂热态度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其结果都是损尊折威,得不偿失。 另外一种对待他者的态度就是憎恶, 尤其是欧美主义对待他者文化、他者意识形态、他者话语体系等常报憎恶的态度, 这种非理性的否定态度认为自我文化是先进文化而他者文化则是落后文化, 不能够客观地对待与学习他者的优点,是一种骄横自恋的态度,这是文化不自觉的表现。
(二)对他者的亲善
在外宣翻译中对他者的迷恋及憎恶都是非理性的,更不可取的。 译者应该如何对待自我与他者? 那就是“亲善”。 “亲善”的态度才是可取、长久之道。 亲善之说也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不谋而合。譬如,儒家主张“仁,中庸之道”。 道家主张“上善若水”。 在传统文化的陶冶下,中国始终以亲善的姿态与各国交好。
译者不仅需要突出外宣话语的中心思想, 同时在翻译中还要保留文化异质性。 在全球化文化趋同的形势下,如何保留文化的异质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吴永认为坚持以中国为本位,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反对用异质文化改变中国文化。 正所谓“不与夷狄主中国,不与夷狄执中国”,以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8][9]。
在保持本土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之外, 还应该秉持亲善与包容的态度。 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费孝通先生认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0]。 为了助推中国文化远洋,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向世界展现一个亲和、友善、踏实的国家形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人人一家亲,需要外宣翻译。 外宣翻译中的自我与他者对话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建议作用。最后,笔者认为中国这片汪洋容得下世界上任何一只文化小船。
五、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语境下,中华民族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为此就要建立良好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对西方而言则是一个被建构的他者的形象, 受西方意识形态塑造与操控,中国文化遭受西方社会打压。当今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强盛,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国文化不仅要走出去, 而且要走进去, 更要传下去。另一方面,还要引进来,以了解他者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认同感。 做到知己知彼,方能使中国文化、中华思想精髓走进去并传下去。 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对话,以亲善包容的态度构建中国国际形象。通过外宣翻译,根据新时代特点构建国家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福柯指出“人类话语实践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与实践性”[11][12](转引自魏向清、 杨平,2019),因此,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树立良好的国家话语形象显得尤为重要。 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国文化的走出去、走进去与传下去,获得国际社会一致认同,并与他者文化和谐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