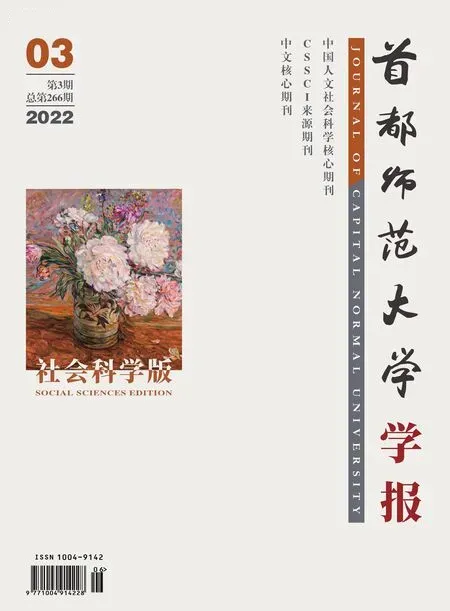论教育学-现象学视频分析的理论基础
2022-03-18彭杰
彭 杰
关于现象学的基本认识构成了教育学-现象学视频分析的认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阐述现象学导向的经验理论,即经验的时间结构、意向性、主动性和被动性交织等成为理解教育经验比如课堂中的消极经验、注意经验等的依据。在此意义上,现象学可视为通向事物自身和经验的生产性、开放性、怀疑-批判性的路径。那么如何尽可能贴近事物或经验本身?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如何坚守现象学的旨趣——回到事物本身?现象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方法论,而理论性的方法论如何引导具体的研究实践?如何能使不可见事物可见?在此需要一种操作化实践:现象学的还原(Reduktion)、描述(Deskription)和变更(Variation)。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在系统介绍教育学-现象学视频分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视频分析以及由柏林洪堡大学普通教育学系研究团队发展的教育学-现象学的视频分析的实践过程。
一、现象学作为通向事物本身及经验的生产性路径
与以演绎思维和归纳思维为基础的研究不同,现象学研究遵循“溯因式”(abduktiv)①Charles S.Peirce,Schriften zum Pragmatismus und Pragmatizismus,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6.Jo Reichertz,Die Abduktion in der qualitativen Sozialforschung.Über die Entdeckung des Neu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3.思维方式。作为第三种思考和认识路径,现象学研究既不遵循从普遍法则到特殊事件的演绎逻辑,也不完全遵循从特殊事件到一般法则的归纳逻辑,而是从被看见、被展示物以及自身显现物出发,将可能的意义或解释“嵌入”(einlegen)②Eugen Fink,Grundfragen der systematischen Pädagogik,Freiburg:Rombach,1978,p.13.到这些事物之中。这是以教育经验为核心主题的教育学-现象学研究的重要认识论基础。对教育经验的现象学理解建立在现象学的经验理论之上,其中经验的“显著差异”(Signifikative Differenz)③Bernhard Waldenfels,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e,München:Fink,1992.即经验的“时间结构”是其他一切结构特征的基础。
(一)现象学的基本思维方式
如上所述,溯因式的思维方式作为现象学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不同。演绎式研究始于既定的普遍规则、法则、定理和理论,并尝试从因果关系的层面解释(erklären)某一现象或事物的原因,因而被观察或研究的事物和现象可诉诸那些纯粹客观的法则、规则和理论,演绎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确定的普遍法则的应用,并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径;演绎的研究范式可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必然性的思维方式,“演绎实际是去证明某物必然如是”④Charles S.Peirce,Schriften zum Pragmatismus und Pragmatizismus,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6,p.171.。与此相反,归纳式研究遵循自下而上、从特殊到普遍的路径,从大量的特殊事件归纳式地界定某一法则和理论,或者“挖掘”(auslegen)⑤Malte Brinkmann,“Verstehen,Auslegen und Beschreiben zwischen Hermeneutik und Phänomenologie.Zum Verhältnis und zur Differenz hermeneutischer Rekonstruktion und phänomenologischer Deskription am Beispiel von Günther Bucks Hermeneutik der Erfahrung,”in Sabrina Schenk,Torben Pauls,ed.,Aus Erfahrung lernen.Anschlüsse an Günther Buck,Paderborn:Schöningh,2014,pp.199-222.隐藏在事物与现象背后的既存意义,归纳的目的不在于从因果关系的层面证明、解释现象与事物,而在于阐释(Interpretieren)和理解。解释学遵循归纳的思维方式,并将“理解”(Verstehen)作为其核心概念,解释学的理解指向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既定的意义世界,⑥Malte Brinkmann,“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ologie und Empire in der Pädagogik.Ein systematischer Entwurf für die Rekonstruktion pädagogischer Erfahrungen,”In Malte Brinkmann,Richard Kubac&Severin Sales Rödel(hrsg.).Pädagogische Erfahrung,Theoretische und empir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5,pp.33-59.在此意义上,解释学可被视为一种“解释的艺术”(Auslegungskunst)和“解释理论”(Theorie der Auslegung)⑦Helmut Danner,Method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r Pädagogik,München,Basel:Reinhardt,1998,p.32.,即“意义挖掘的艺术”;在解释学看来,某一实践、事物、文本和所言说之物的背后存在某种隐含的、潜在的意义,它们借助于“解释”、阐释或重构而浮现并被理解,因而解释学旨在对某一实践、事物、现象的“理解”⑧Dieter Lenzen,Pädagogische Grundbegriffe,Reinbek:Rowohlts Enzyklopädie,2001,p.1198.,并因此而“偏离事物本身”⑨Helmut Danner,Method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r Pädagogik,München,Basel:Reinhardt,1998,p.32.。在狄尔泰看来,研究者的“理解”可视为对隐含的意义视域的重构、“对过往意义的重建”[10]Malte Brinkmann,“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ologie und Empire in der Pädagogik.Ein systematischer Entwurf für die Rekonstruktion pädagogischer Erfahrungen,”in Malte Brinkmann,Richard Kubac&Severin Sales Rödel,ed.,Pädagogische Erfahrung,Theoretisch e und empir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5,pp.33-59.或意义挖掘的过程。因此,理解意味着将某物理解为某物(etwas als etwas),但解释学并未进一步区分感知与理解之间的时间性差异,即对表层事物的感官知觉和对事物背后意义世界的理性理解之间的差异。
现象学的研究路径与以上两种推理方式不同,它更多地遵循或类似于第三种思维路径:溯因。与其他重复和再生的推理方式不同,溯因推理属于创新性的推理模式,因为它既不属于形式逻辑,也不遵循既定的操作化步骤;①Jo Reichertz,“Abduktives Schlussfo”lgern und Typen(re)konstruktion.Abgesang auf eine liebgewonnene Hoffnung,”in T.Jung und S.Müller-Doohm,ed.,Wirklichkeit“im Deutungsprozess:Verstehen und Methoden in den Kultur-und Sozialwissenschaft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3,pp.258-282.既不致力于从因果关系层面解释某一事件,也不致力于理解和挖掘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意义或将某一事件纳入既定的理论和秩序,而旨在对被感知物、自我呈现物的某些可能的、非因果性的解释,旨在生成可能的意义和发现新的解释可能性。因此,溯因可被理解为一种“猜想式”的思维方式,具有开放性并蕴含多种可能性,正如Peirce所言,“溯因表明可能之事物”②Charles S.Peirce,Schriften zum Pragmatismus und Pragmatizismus,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6,p.171.,因而并不具有确定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证明力,只具有有限的说服力。但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和有限性,才使得意义和视角的多元化、认识和理解视域的拓展、经验的新维度的生成成为可能。因而,现象学作为一种溯因的思维和研究风格可被理解为通向现象和经验的生产性路径。
但现象学的研究路径首先并不在于可能之意义或解释模式的内置或嵌入,而是将自身显现物的显现置于中心。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Phänomen)意味着“自身显现者(das,was sich zeigt,das Sichzeigende)、敞开者(das Offenbare)”③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Niemeyer,2006,p.28.以及“表面物(das Oberflächliche)和就其自身显现自身者(das Sich-an ihm-selbst-zeigende)……诸现象即那些自身处于光亮之中或被引入光明之中的事物的总和”④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Niemeyer,2006,p.28.。因此,现象并非直接给定的,而是在与自身显现物的相遇中构造的。海德尔格对“现象”的界定意味着“在现象学的现象背后本质上并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东西”⑤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Niemeyer,2006,p.36.,这种对现象的基本态度或假设是意义嵌入以及以现象学取向的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区分现象学与解释学的重要维度,因为解释学假定:在表面物或现象背后存在隐藏的意义、本质、实在、实质,存在着某些隐蔽的、符号性的或象征性的东西。
现象学作为一种思考和研究的“态度和风格”⑥Maurice Merleau-Ponty,Phänomenologie der Wahrnehmung,Berlin:de Gruyter,1966,p.4.,实际上是一种回到事物本身(Zurück zur Sache selbst)的、开放的态度。作为现象学的首要口号“回到事物本身”首先意味着“拒绝科学”,但拒绝科学在此并不是对科学的敌视,而只是表明生活世界的经验应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起点,“因为科学自身源自于生活世界”⑦Severin Sales Rödel,Negative Erfahrungen und Scheitern im schulischen Lernen.Phänomenologische und videograph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21.,“科学的世界作为整体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要在严格意义上思考科学本身、准确地衡量其意义和影响范围,就要首先回到对世界的经验之中”⑧Maurice Merleau-Ponty,Phänomenologie der Wahrnehmung,Berlin:de Gruyter,1966,p.4.。因此,回到事物本身并不是回到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实或绝对客观性,而是“回到所有认识赖以存在的世界”⑨Maurice Merleau-Ponty,Phänomenologie der Wahrnehmung,Berlin:de Gruyter,1966,p.5.、回到前述谓的经验、回到那些自身向我们显现者,即对事物自身的尊重。另外,现象学的这种回到事物本身的态度以及诉求基于以下这种基本观点:对差异的敏感性、对世界和他者(物)以及对在感知和思考中遭遇到的陌生者(物)的开放和敞现,在此基础上,可将同一个现象或事物感知为其他不同的事物。由此,现象学的生产性和反思性在逻辑上就变得可理解。因此,现象学作为一种认识和研究风格、作为一种回到事物本身和开放性的态度,为以经验和经验现象为对象的质性-实证教育研究以及理解教育理论(Theorie)、经验(Empirie)和实践(Praxis)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可能性。
教育科学作为“理论-实证分支学科”和“经验科学”[10]Malte Brinkmann,“Allgemeine Erziehungswissenschaft als Erfahrungswissenschaft.Versuch einer sozialtheoretischen Bestimmung als theoretisch-empirische Teildisziplin,”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ädagogik,2016(2),pp.215-231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理论—实证(经验)—实践”之间的关系,并将“经验(Erfahrung)的概念和现象置于中心地位”。①Johannes Bellmann,“Jenseits von Reflexionstheorie und Sozialtechnologie.Forschungsperspektiven Allgemein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in Bellmann,J./Müller,T.,ed,Wissen,waswirkt:Kritik evidenzbasierter Pädagogik,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11,pp.197-214.在广义上,经验(Empirie)等同于经验(Erfahrung);在狭义上,经验(Empirie)是实证经验(empirische Erfahrung),是对他者和陌生者经验的重构,而这些陌生经验将成为教育质性研究的对象,它们不仅通过质性研究被观察、描述和阐释,还能开启新的视域。②Malte Brinkmann,“Verkörperung und Aufmerksamkeit in pädagogischer Relation.Der Beittrag phänomenologischer Unterrichtsforschung für die qualitative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in Robert Kreitz,Christine Demmer,Thorsten Fuchs und Christine Wiezorek,ed.,Das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qualitativer Forschung,Leverkusen:Budrich,2019,pp.17-38.因而,经验(Empirie)可被视为关于他者和陌生者经验的研究实践,它一方面诉诸特定的理论,另一方面借助于实证材料对既定理论进行批判、补充、再述或生成新的理论。理论与经验(Empirie)因而处于一种螺旋式的关系之中,二者相互依赖、互为根基。在此基础上,教育实践(Praxis)可被理解为“被经验的实践”(erfahrene Praxis)③Malte Brinkmann,“Pädagogische Empirie.Phänomenologische und methodologische Bemerkungen zum Verhältnis von Theorie,Empirie und Praxis,”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2015-61(4):527-545.、基于经验的实践,因而教育实践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由行动主体(师生)所进行、经历、体验和遭遇的实践,由研究者观察、参与、反思、阐述以及向研究者呈现的实践。在现象学看来,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并非始终确定不变:二者既非彼此对立,亦非单方面的理论指导实践、理论源自实践。相反,二者处于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中,教育经验(Erfahrung)被视为重要的连接。由于教育经验(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和陌生的经验)在理论-经验(Empirie)-实践关系中的基础性和连接性作用,需要一种现象学取向的经验理论,以更好地描述、认识和把握教育实践以及与其相关的教育经验。因此,在描述、解释、重构行动者的经验之前,必须首先思考:某物如何被经验以及人们如何经验这一问题。
(二)现象学取向的经验理论
现象学分析始于对某一现象或事物的感知。当人感知某物或某人时,总是将其感知为某一特定的物或人(etwas als etwaswahrnehmen),其中蕴含着感知或基于感知的经验的基本结构和特征:时间性、意向性、主动性和被动性等。
经验与经验表达之间的“显著差异”蕴含着经验的时间结构。正如胡塞尔所言:“在感知与对感知的符号性设想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本质区别。”④Edmund Husserl,Husserliana.GesammelteWerke.Band 3,in Herman Van Breda,Samuel Ljsseling,Rudolph Bernet,ed.,Den Haag:Nijoff,1950-2004,p.79.这种居于鲜活的经验与对鲜活经验的语言表达之间不可化约的区别,根植于身体的、缄默的、前反思的、前述谓的主体经验与事后的符号化表达(语言化和文本化)在时间上的差异。切身体验总是先于其事后的表达,因为人是“身体的存在,而非具有身体”⑤Helmuth Plessner,“Lachen und Weinen,”in H.Plessner,ed.,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Frankfurt am Main:Fischer,1970,pp.11-171.,他首先必须借助或通过身体(Leib)⑥在现象学领域,身体通常作为自身与世界之间交互的媒介(Hua IV,S.286)以及作为感知、行动、思考的存在基础。因此,人不仅是理性的、思考的和行动的主体,更是身体存在的主体(Meyer-Drawe 2001)。身体不再是无生命的、物性的感知客体。正如Polanyi所言:“我们的身体(Körper)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常从不会称之为对象的东西,而是将其作为世界来体验。”在此他并非区分身体和肉体,而是在身体的意义上使用肉身这个概念。但梅洛-庞蒂和Plessner却十分注重身体存在(Leib-Sein)和拥有肉身(Körper-Haben)的差异,强调身体在人的在世存在中的重要性,以此试图克服心灵与身体、精神与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及心灵对身体的蔑视。在感知、行动、思考中,意向性或对某物的指向性都以身体为基础。去感知和经验某物,之后才能谈论和描述他所经验的、引其注意以及向其显现的东西,由此可见,对经验的语言表达和符号性呈现以具身化⑦Plessner将具身化(Verkörperung)描述为人对自身肉体的行为,并从角色承担的层面出发,区分了三种具身化模式:初级的、表征的和功能性的模式。Brinkmann将具身化视为一种身体的或交互身体的表达和应答形式,通过具身化经验或实践的不可言说的、缄默的维度得以描述,不可见的或尚未可见的事物(如注意经验和消极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见。的经验为前提,因而具有滞后性。在经验的时间结构中蕴含着某种“抽离特征”:首先,我们通过远离自身、通过由我们自身指向他者(物)和陌生者(物)的方式,去感知自我显现物,因为人是“离(中)心”(exzentrisch)①Helmuth Plessner,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Berlin:de Gruyter,1975,p.328.存在并总是在行动中远离自身。我们不仅以自我远离的方式感知自我显现物,而且在感知中也远离了感知活动本身,比如我们在观看的时候并不能看到“观看”活动本身,当我们学习时,我们遗忘了自身,也遗忘了学习活动。因而,这些切身经验只能在事后被把握,就如同学习只能在事后被意识到。其次,当我们事后借助于语言去表达和阐释亲历经验时,亲历经验自身已经远离了对亲历经验的表达,因此对经验事后的语言的、符号的描述很难完全契合地表达和再现亲历的、缄默的、前反思的经验,只能尽可能地接近这些经验。这对以学习和教育过程中的“教育经验”为对象的质性教育研究而言意味着什么?研究者只能尽可能地从不同维度(身体、交互身体、语言、空间等维度以及这些维度之间的关联)去观察、描述、分析和重构具体教育情境下的鲜活的主体经验,这正是教育现象学研究以及教育学-现象学视频分析的首要旨趣。那么如何尽可能贴近经验自身呢?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如何处理其自身经验呢?对此,现象学发展出了其自身的方法论(详见第二部分)。
感知总是对某物的感知,因而具有意向性和指向性。在早期胡塞尔看来,感知和经验是意识的意向活动,是主体的成就,即经验和感知由主动的、作为主体的“人”所主导,并赋予被感知物和经验物以某种意义和内涵。因此,经验和感知可被理解为主动的意义建构(Sinnbildung)。海德格尔批判了这种以主体为中心的意向性概念,强调“被感知/经验物”在感知和经验活动中的主动性:我将自我显现物、吸引我注意的事物感知/经验为某物。在我主动地感知和经验某物之前,已经发生了某种被动的生成,即我已经被自身显现物所唤醒和吸引;在感知和经验活动中,不仅是主动的“我”(Ich)将某物体验为某物或者某物被我体验;同时,自我显现物作为某物由其自身出发向“我”(Mir)显现。因此,行动主体就具有某种主动的被动性,而自我显现物也具有某种被动的主动性,感知/经验活动是主动感知和被动感知的交织。在此,“主动自我之有意向的意义建构与被动的意义给予(Sinngebung)相遇,即与能赋予意义的他者、事、物和世界相遇”②Malte Brinkmann,“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ologie und Empire in der Pädagogik.Ein systematischer Entwurf für die Rekonstruktion pädagogischer Erfahrungen,”In Malte Brinkmann,Richard Kubac&Severin Sales Rödel(hrsg.).Pädagogische Erfahrung.Theoretische und empir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5,pp.33-59.。因而,意义并非由主动的、活动着的主体所重构,而是在意义建构与意义给予的交织中被构造。被动性意味着向与我们相遇的他者(物)和陌生者(物)的开放。③Malte Brinkmann,“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ologie und Empire in der Pädagogik.Ein systematischer Entwurf für die Rekonstruktion pädagogischer Erfahrungen,”in Malte Brinkmann,Richard Kubac&Severin Sales Rödel,ed.,Pädagogische Erfahrung.Theoretische und empir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5,pp.33-59.借助经验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的交织,主客二元对立以及以主体为中心的思维被打破,这为认识具体的教育经验(如学习)以及基于经验的质性教育研究开启了新的可能:通常认为学习作为经验是个体性的、主动的与他人、世界、事物交互的过程,学习必须由自身发起,而不能被强迫;但其也有被动性的一维,主要体现在“某些事情只是这样发生在我们身上,它映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从自身所处的视角去‘看’它……学习并非总是积极主动的过程,所要认识和学习的事物、他者以及世界首先充盈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身体遭遇,才为我们所见、所听、所学、所感知、所认识”。④彭杰:《现象学视角下的学习:一种新的面向和可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在经验活动中,主动建构意义和被动给予意义均与经验自身的“作为-结构”(Als-Struktur)不可分割。这种Als-Struktur则与经验方式以及自我显现物的显现方式相关。相对于将某物经验为某物、某物作为某物向我们显现而言,自我显现物作为某物向我们显现的方式,我们将某物经验为某物的方式更为重要。在将某物经验为某物的经验活动中Als-Struktur首先将经验对象和经验内容联系起立,并蕴含某种方法论的差异,即经验活动和经验内容之间的差异。我们所见之物与事物自我显现的方式以及与我们观看的方式密切相关。自我显现物并非简单地作为某物显现,而是作为某物向“我们”显现。另外,此结构也表明:自我显现物绝不会完全地向我们显现,而总是伪装或遮蔽地向我们显现。当经验对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向我们显现其某一方面时,当我们从某一视角或在某视域内将其视为某物时,它的其他方面在当下就淡出视野,成为不可见或尚未可见之物。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感知、描述、阐释某一现象,并为其他可能的观察方式和阐释留有余地。因此,我们只能尽可能地贴近某一现象或经验,现象的自我遮蔽式显现成为现象学开放性和生产性的重要认识论前提。
二、通向事物自身的方法论操作
现象学的经验理论表明,由于经验的时间结构和自我显现物的自我遮蔽式的显现方式,即某物在显现自身的同时,也遮蔽了其自身(的某些层面),我们只能尽可能地贴近、描述和把握经验,只能尽可能地回到事物本身。作为研究者如何尽可能地贴近他人的经验和回到事物本身?如何处理自身的经验?如何处理现象的不可见维度或如何使不可见和尚未可见的事物可见化?现象学发展了其独特的方法论,并具体化为以下操作:现象学的描述、还原和变更。
(一)现象学的描述(Deskription)
现象学的描述和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差异紧密相关,并基于以下观点:事物的表面之下和之后并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东西。①Malte Brinkmann,“Verstehen und Beschreiben.Zur phänoemnologischen Deskription in der qualitativen Empirie,”in J.F.Schwarz und V.Symeonides,ed.,Erfahrungen verstehen—(Nicht-)Verstehen erfahren,Innsbruck:Studien Verlag.2020a,pp.29-46.因此,现象学的描述性首先集中在可见的、可体验的和可描述的东西上。这种可见的、可体验的和可描述的东西就是身体和交互身体的表达:面部表情、手势、目光和目光方向、姿势、身体张力、身体运动以及笑、哭和微笑中的一些表达等。与此相反,行动者的动机、意图以及他们的内心感受和心理过程是不可见的,它们只能借助行为的可见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被把握。但不可见性并不限于以上内在的过程,现象的遮蔽式自我呈现以及研究者已有的偏见、经验和理论认识也会导致自我显现物的不可见(层面)。为了使尚未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可见,就需要方法的保障,而这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描述以及伴随其发生的还原和变更来实现。在此意义上,现象学的描述可被视为“让看见”的实践。在现象学描述中,不仅要对自我显现物进行还原式的、内容丰富的描写,而且要描写其显现方式,即不仅描述发生了什么,而且要描述如何发生,人如何对其所遭遇的他者(物)或陌生者(物)的要求做出回应。所以,现象学的描述首先既不致力于隐含意义的挖掘,也不致力于可能意义的嵌入,既不致力于阐释,也不致力于因果性解释,而旨在描述经验的初级的、可见的层面,旨在看见和描述表面的事物和可见的事物。
此外,现象学的描述也是对切身、前述谓和前反思的经验在语言或文本层面上的符号化。在文本化和语言化过程中许多东西超出了语言和语法的范畴,因而是缄默的、不可说的,很难借由语言的媒介将其完全转化。为了尽可能地接近前语言和前反思性经验,现象学描述需要对语言有特殊的敏感性。比如,要为所描述的行为选择恰当的动词和非评价性、非推断性的形容词,尽量避免使用因果句、目的句以及隐喻等。
(二)现象学的还原(Reduktion)
“现象学分析并不始于观察和释义,而始于对感知内容和潜意识解释的还原。”②Malte Brinkmann und Severin Sales Rödel,“Pädagogisch-phänomenologische Videographie.Zeigen,Aufmerken,Interattentionalität,”in Christine Moritz und Michael Corsten,ed.,Handbuch Qualitative Videoanalyse.Method(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en-forschungsprakt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8,pp.521-548.在胡塞尔看来,悬置(Epoché)意味着暂时终止或推迟判断。在还原中研究者将已有的关于所观察现象的经验、认识、偏见以及理论和科学的解释模式暂时地加括弧、尽可能地悬置和批判性地反思;基于这些被悬置的个体经验和理论模式之上的判断、解释、评价也应该暂时中止。虽然所要悬置的东西是感知和认识的基石,但同时也限制甚至阻碍了研究者对于事物的认识和认识的可能性。通过还原,关于所要感知和体验之物的判断和预先理解失去其效用,以使那些由于预先理解和判断而被掩盖的事物和事物的某些方面、那些尚未可见的以及未被看到的东西、那些以遮蔽的方式自我显现的东西如其所是地显现或可见,以丰富和拓展观看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感知对象的认识,因而还原的目的并非是追求一种纯粹中立的、不做任何判断的认识。现象学的还原并非一种实际可见的操作,而是指向对现象和事物的认识的一种反思-怀疑的态度,一种使现象或熟悉的事物陌生化、自身视角陌生化以更贴近事物自身的过程;缺少了现象学的还原,现象学的描述和变更则无从谈起。在现象学还原中,研究者不仅要悬置和反思自身已有的经验、理解和理论,还要反思其观察、感知和体验事物的方式、角度和过程,因为其所能体验和感知的事物与这些方式和视角密不可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存在百分之百的还原和悬置,如同无法完全将前反思、前语言的身体经验转化为语言表达。
(三)现象学的变更(Variation)
在接下来的变更实践中,先前被悬置的经验、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解和判断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正是由于现象自身的遮蔽式显现、现象学的溯因式思维以及与此相关的向世界的敞现和开放态度,研究者才可以从另一视角考察现象,并将其设想和解释为与它开始呈现于我们的不同的事物,对此需要研究者具有相当的想象力以及与其他研究者之间交互主体的交流。借此,关于某一现象和事件的观点、视角、意义得以丰富和多元化。借助于溯因,那些可能的说明与意义被纳入感知对象之中,并由此生成关于经验的新的认识以及新的理论。
但在现象学的分析路径中,三种具体操作并非依次发生,而是彼此交织,并可能同时被用于某些具体的分析阶段。借助于反思-怀疑的还原、还原式的描述以及基于想象的变更,才可能更加接近经验和事物本身,补充旧有的认识,并从中溯因式地生成某些新的东西。
三、视频分析及现象学视频分析
现象学-教育科学在内容、方法论、学科层面上都将经验概念置于中心,并借助于现象学方法论尝试重构教育领域中的经验即主体经验。但由于教育实践的复杂性,教育与学习过程中的主体经验并非直接可见、可描述和可把握,身体作为自身与世界、他者关系的媒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被视为经验的载体。因此,个体的主体经验可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在应答过程中借助于身体或具身化得以被观察、描写。但如何从不同视角充分和准确地描述、把握教-学过程中稍纵即逝的经验、身体表达和应答过程?视频分析,确切地说,现象学的视频分析,借助于其自身优势在质性-实证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视频分析简论
在介绍教育科学领域中现象学视频分析及其过程之前,需要先简要介绍一般意义上的视频分析。严格来讲,视频分析出现于20世纪末,因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还是一种相对新的研究方法。但基于视听数据的方法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一方面可追溯至183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聚焦于人类行为观察和互动过程的图片和影视分析;另一方面可追溯至1890年代在人类学中致力于重构和解释异文化或原始文化的行为方式和社会文化结构的民族志电影。①RenéTuma and Bernt Schnettler,Hubert Knoblauch,Videographie.Einführung in die Video-Analyse sozialer Situationen,Wiesbaden:Spinger VS,2012,p.24.
与其他类型的数据相比,视频数据能够为质性-实证研究带来什么?与其他的研究方法,如主要基于文本和言说资料且致力于意义或秩序重构的客观解释学和对话分析相比,视频分析开启什么新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视频其实是人类眼睛的延伸、记忆的底片,也是对现实,更确切地说是对视频所构造的真实性的保存,因为视频总是在特定框架、视角和研究目的下被录制,因而可能只呈现了其自身所构造的真实或有限真实。
视频不仅捕捉和呈现静态、瞬时的情景,也记录动态事件和过程;不仅记录发生于特定情境下的交流与互动中的言说层面,而且展现言说的语气、语调、语速等,呈现特定时空情境下人与人或人与物之间应答过程的非语言的、身体的、不可言说但可展示的方面。因而通过课堂实录的视频,不仅可以准确地观察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应答,也可以观察人(师生)与学习材料或物品之间的应答。在此意义上,视频作为一种媒介能够鲜活地记录、呈现和保存具体情境中的教育互动和应答之语言的、身体的、物质的、空间的和时间的维度。在某些课堂互动和应答中,语言自身有时是枯燥的、贫乏的,并不能够充分表达双方的意图或者所要表达的事物是不可或不能言说的,因此需要借助身体去传达与交流;有些互动和应答本身是无声的、静默的,只通过身体的表达(如眼神接触、手势等)去实现;即使在以言说为主的互动和应答中,也必然伴随着某些其他的身体表达。身体的表达有时先于言说自身,其所呈现的东西有时远多于言说,“我们所知的远多于所能言说的”①Michael Polanyi,Implizites Wiss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5,p.25.。因此,视频分析借助于视频数据的多维性能够呈现和把握教育互动和应答的复杂性和多模态性。
除了视频资料的多维性,借助于视频不仅可以观察同时性的互动,也可以观察课堂互动与应答的不同维度之间的交织和相互关联,比如言说与(身体)展示、言说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因此,通过视频不仅可以观察在特定时刻或时间段中互动与应答的某一或某些维度,如语言的要求与应答、表情、手势、身体姿态和身体的活动等,更能观察这些维度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如“手-眼协调”。视频分析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由于视频资料的多维性、对课堂互动与应答的同时性和动态性记录以及对这些互动与应答的不同维度之间交织关系的呈现,能够为观察、描述和把握课堂互动和应答开启新的可能,对质性-实在研究以及教-学过程中经验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视频可以永久地保存其中所记录的情景,因而研究者可以反复观看,可以更加详细、全面地观察所要研究的情景,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改进、修正、检验关于这一情景的描写文本,以更加准确地描写、贴近情景本身。通过反复观看可以“陌生化”、反思自己对某视频所记录之情景的最初视角和观点,并获得新的认识。其中,除了反复观看,观看方式即视频的播放模式(常速、慢速、加速,或有声、无声)也扮演着重要作用。借助于以上视频播放技术,视频分析不仅使更加详尽具体地观察成为可能,而且使得对课堂互动与应答复杂性的描述成为可能。另外,从现象学的视角看,也使得尽可能地贴近所要研究的情景以及互动性和应答性的经验成为可能,使得关于情景的新的观察视角、认识和理解成为可能。
但是每一种方法都有其边界。视频资料并不能直接向我们呈现隐藏于可见的行动和互动背后的(人的)目的、意图、动机、感觉、情感和抽象概念(如注意、消极性、爱、自由等等)。这些通常只能从可见的具身行为、对他者或陌生者的交互主体性应答中部分地推测。通过视频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不同模式和视角下身体和语言的表达,那些缄默的、不可言说的或很难言明但却可展示的东西,即那些表层之物,也正是现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另外,视频本身并不能直接呈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实际关系,不能(完全)呈现在没有摄像机介入下的、日常课堂生活的样态以及师生的行为习惯等。而这只能通过前期的田野工作或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来弥补和平衡,由此尽可能地了解视频所不能直接呈现于我们的东西。视频以及其他的数据类型(田野笔记、深描、访谈、教学材料以及其他物品)是后续研究的对象和材料,但它们并不只是分析的对象和客体,其自身会对应答者提出要求并期待研究者对此的应答和回应,研究者在观看、阅读这些研究素材时会对其产生身体的、情感的、非意向性的应答。
(二)教育学-现象学视频分析的实践性操作
与课堂教学研究中其他取向的视频分析相比,现象学取向的质性-实证视频分析遵循现象学方法论的基本操作,建立在现象学基本认识和经验理论之上。它并不局限于互动过程的语言层面,因而,并不致力于课堂意义的重构,也不致力于重构超个体的、制度化的、普遍的教学秩序和结构。相反,它特别强调互动过程中身体、身体间、情境和物质的层面,因而,教-学过程中个体性、独特、主体以及交互主体的经验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被观察、描述和把握,由此,尽可能地接近主体经验本身。柏林洪堡大学普通教育学系在批判性地接受其他视频分析理论以及反思性地遵循现象学基本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教育学-现象学的视频分析”①Severin Sales Rödel,Negative Erfahrungen und Scheitern im schulischen Lernen.Phänomenologische und videograph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252.。
如教育科学领域中的现象学研究一样,现象学取向的视频研究将教育经验置于中心,并尝试重构在教育互动中以及在与他者、物体和材料交互中主体和交互主体的经验。教育学-现象学视频分析遵循现象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基本思维方式和开放性态度:在现象背后并不存在隐含的意义、本质、实质,现象即自我显现物,现象学旨在让事物显现;以溯因的方式看待和思考教育现象和教育经验;对所研究的现象和情景持开放的态度。因此,教育学-现象学视频分析并不致力于挖掘和解释经验的意义,而在于嵌入可能的意义和解释。另外,在分析具体视频时,尤其是在观察、描写、解释过程中,运用现象学的还原、描述和变更。教育领域中的现象学视频分析并不仅关注视频中所描绘的教育情景和事件,而且关注在单独或集体观看视频时研究者对视频自身以及对视频所呈现之事件的应答,这种应答以响应性和非意向性为特征,既非某一原因(线性-因果)的结果,亦非对某一刺激的机械性反应,②Malte Brinkmann and Severin Sales Rödel,“ Pädagogisch-phänomenologische Videographie.Zeigen,Aufmerken,Interattentionalität,”in Christine Moritz und Michael Corsten,ed.,Handbuch Qualitative Videoanalyse.Method(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en-forschungsprakt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8,pp.521-548.而是身体的、情感的响应,因而可借助现象学方法论的操作被描述,并作为研究者的经验或参与式经验对后续关于视频所描绘事件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③Severin Sales Rödel,Negative Erfahrungen und Scheitern im schulischen Lernen.Phänomenologische und videograph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253.最后,教育学-现象学视频分析很难由某一位研究者独立完成,需要与其他研究者交流与碰撞,尤其是在对视频的描述和解释阶段。在与其他研究者交互主体的交流中,对视频的深度描写被讨论、理解、质疑、改进,使描写事件的视角得以丰富和多样化,而对事件的解释也被交互主体性检验,事件和经验的意义因而变得多元,自身关于事件的观点被反思和陌生化。
如前所述,在视频录制之前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田野工作或参与式观察,是为了搜集其他数据资料以及参与经验,使研究的问题更加聚焦并确定视频录制的时间等。通过田野工作和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可以更好地了解所观察学校、班级、教师和学生的概况,对课堂氛围、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习惯等形成初步的认识,也让师生能够习惯于“观察者”的在场,以减少研究者的在场对教学、学习和师生互动产生的影响。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此处的田野工作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约为一个月。而在课堂观察过程中,研究者已经对所观察的情景、教-学互动等做出了某种身体-情感的回应,在此意义上,研究者并非“冷漠”的观察者或旁观者,而是作为“体验者”,他总是处于所观察的课堂之中,成为整体情景的一部分并体验着所观察的课堂情景。
在课堂观察时,观察和体验的引人注意的情景被深度描写,不仅要描写课堂互动和应答的语言层面,也描述身体或身体间的表达。在此阶段,已经使用了现象学的还原和变更。现象学的描写其实是对前反思经验的书面记述、符号化、语言化和文本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只需描写其所见、所经验之事物,自我显现物及其显现方式,需要悬置研究者先前关于学校、学习等的经验、偏见、预设、想象以及相关的教育教学理论等等,此阶段所需要做的不是解释和判断,而是呈现实际的课堂情况:课堂互动以及应答、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发生等等,进而形成关于某一课堂情景的深度的、系统的、可读的文本。这些深描文本需要与其他研究者讨论:为何选择描写这一情景及其与研究主题的关系如何?此文本或文本中的某些句子想要表达什么?其他在场者对同一情景是如何描述的?通过讨论,研究者自身的经验得以交流和扩展,所描绘的情景更加清晰,其他可能对此情景的理解和解释角度也随之而来,文本自身也可进一步被完善和加工,其他研究者对文本以及文本所描绘的事件的应答被搜集,接下来研究的问题也进一步被聚焦。
视频录制时需要两台固定但可旋转的摄像机从(前后)相对的视角对课堂教学进行录制,以捕捉师生在某一互动过程中的同时行为。①Malte Brinkmann and Severin Sales Rödel,“ Pädagogisch-phänomenologische Videographie.Zeigen,Aufmerken,Interattentionalität,”in Christine Moritz und Michael Corsten,ed.,Handbuch Qualitative Videoanalyse.Method(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en-forschungsprakt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8,pp.521-548.在感知性观看时,尤其关注研究者对视频以及视频所描述情景、事件及其要求的情感与身体表达,而这种身体和情感的应答可被视为一种理解方式。另外,在对课堂视频进行“感知性观看”时,师生的身体表达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学生在课堂中的行为表现,他们在做什么,尤其在课堂对话中如何回应教师和第三者(其他同学)的(语言的、身体的)要求,如何对他们的应答进行回应等等。其中师生的身体表达作为具身行为(目光、眼神、面部表情、身体姿态、手势等等)、作为对他者(物)的应答在一定意义上能表明:其注意是否被唤醒和维持,其是否专注以及专注于什么,他者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等等。
在感知性观看之后,结合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选取和剪切接下来要详细分析的不同视频片段(1~5分钟)。所选取的视频将与其相关的其他材料(对该视频片段的文字转录、深描文本,视频片段所在的课时的教学流程表、所用教-学材料)在资料分析会或其他形式的交流中被观看、讨论,其中现象学的还原、描述以及变化在此阶段被同时使用。另外,视频选取应遵循以下原则:被选取的教育情景对师生而言应是常态化的、典型的而非一次性或偶发的情景;所选取的视频片段应与研究主题和问题密切相关;由于现象学视频分析尤其关注身体的、缄默的表达和经验,所选取的教育情境应包含相对丰富的身体互动和应答。如此看来,视频片段的选择其实是基于对视频所描绘的教育情景的“初步理解”②Severin Sales Rödel,Negative Erfahrungen und Scheitern im schulischen Lernen.Phänomenologische und videograph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257.。在资料分析会或者其他交流形式中,在观看视频片段以及阅读对视频片段的深度描述时,研究者关于视频片段及其描述的“初步理解”或“响应经验”被表达、搜集和批判性交流,在交流过程中,自身的经验、视频与文本描述为他者所理解,对视频和文本中所描述的教育情景的不同理解或不同理解角度也在此浮现。
在接下来的现象学分析阶段,主要使用到现象学的还原和变更。首先,在还原阶段尽可能悬置或搁置研究者主体的已有经验、设想、理解以及研究者所具有和习得的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和洞见,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其目的不在于实现认识和理解的绝对“中立性”,而在于使研究者已有的经验和理论模式暂时地失效或失灵,以此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观察和贴近事物本身,尽可能地让教育现象按其自身呈现于人的方式显现或被看见。加括弧或悬置并不等于排斥和消解,而且个体已有的经验和理论作为认识的基础也不可能被完全悬置。在变更阶段,那些被悬置的东西尤其是理论方面再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发挥作用,一方面还原过程中对事物和现象的理解可追溯或归于相应的理论模式,所研究的教育现象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或在不同的理论模式下被说明和解释,在此过程中再次实现了意义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存在这种情况:已有理论并不能契合或解释实际的实证经验,由此那些作为理论之镜被使用和嵌入的既存理论被批判、反思、重述、补充,并结合实证经验生成某种新的理论。在此阶段,不再仅仅关注对视频所呈现的教育现象和事件的身体的、情感的、响应式和前反思的应答和应答经验,而是转向反思的、有条理的观看、判断、评价、分类以及理论再生。③Severin Sales Rödel,Negative Erfahrungen und Scheitern im schulischen Lernen.Phänomenologische und videograph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9,p.258.
在完成对某一视频片段的现象学分析后,还可将其与其他视频片段进行比较,这些视频片段可来自于同一课堂录像,也可取自其他教师、其他学科、其他学校甚至另一文化背景下的课堂视频。通过比较,一方面可以探寻不同文化和社会环境下的共性和差异,另一个方面可以将教育实践(如课堂展示和注意)进行分类,“这些类型并不是从诸多材料和资料中归纳而来,而是从反思和还原的操作中以溯因的方式获得的;类型并非被建构或重构的,这些共性或共有物作为典型的事物以一种意义生产的方式被嵌入”①Malte Brinkmann and Severin Sales Rödel,“ Pädagogisch-phänomenologische Videographie.Zeigen,Aufmerken,Interattentionalität,”in Christine Moritz und Michael Corsten,ed.,Handbuch Qualitative Videoanalyse.Method(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en-forschungsprakt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8,pp.521-548.。
最后是视频分析软件Feldpartitur的使用。“借助于此软件的乐谱式标注,它不仅能描绘视频的历时特征和序列逻辑,而且基于共时性视角考虑教育情境的复杂性。在视频转录中使用图像符号(Symbole)而非语符(sprachliche Signifikanten),从而实现了(由语言向符号的)符号化的转换。符号在意义(Sinn)和含义(Bedeutung)上更具开放性,使人较少地依赖于语法规则。”②Malte Brinkmann and Severin Sales Rödel,“ Pädagogisch-phänomenologische Videographie.Zeigen,Aufmerken,Interattentionalität,”in Christine Moritz und Michael Corsten,ed.,Handbuch Qualitative Videoanalyse.Method(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en-forschungspraktische Perspektiven,Wiesbaden:Springer VS,2018,pp.521-548.尽管借助于Feldpartitur研究者可以将诸多事物和现象符号化,并从不同维度历时地观看它们,但此视频分析软件并非自动解析视频,不能将视频中的某些事物符号化并赋予其意义,研究者在使用视频分析软件之前必须事先确定分析的维度和类型、所使用的相应符号,并赋予这些符号特定的含义,在软件中观看视频片段时,将被赋予意义的符号添加至视频中相应的位置。总体而言,在教育科学研究中,这一视频分析软件其实是研究结果外化、可视化、直观化和符号化表达的媒介和工具,如对情感、视线、手势、身体姿态类型的符号性转换与表达。
四、结语
基于现象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教育学-现象学视频分析是一种反思、怀疑、批判、开放和生产性的质性-实证研究路径,从教-学过程中具体的教育经验和经验现象出发,首先聚焦于教育现象和互动的可见方面,以呈现教育互动和现象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借助现象学的还原操作以及视频观看模式使教育现象中尚未被看到的方面以及由研究者理论的、个人的、文化的、历史的视域所遮蔽的方面尽可能地显现,并将“可能的意义”嵌入到所研究的教育现象以及现象的诸多可见的方面之中,进而实现意义的丰盈和多元化:“意义”在此并非指隐含于教育现象和经验背后的、已经存在的意义,因而意义的多元化并非通过研究者的重构、挖掘和再生产来实现,即并非完全归于主体的成就和意志;相反,“意义”指向可能的、潜在的意义,借助于“嵌入”而实现,借此强调了具体教育现象(即质性研究对象)作为自我显现物在意义生成中的重要作用,重新认识作为研究者以及行动者的人的被动性或“主动的被动性”,即向教育经验和现象的开放,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对作为一切活动之起源和发端的主体的过度强调、对作为被动承受者客体的轻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