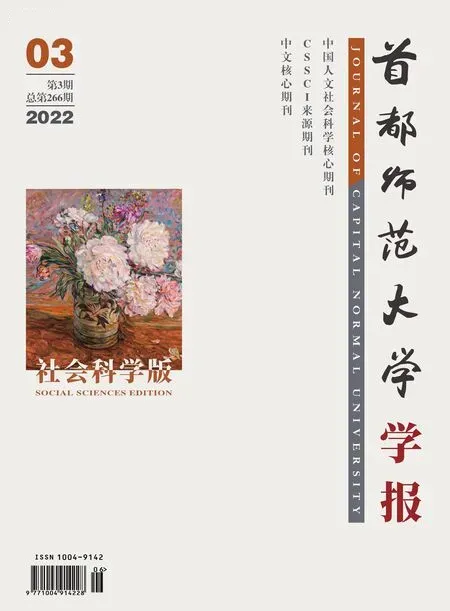中西美育精神的比较阐释及“游艺”范式的当代转化
2022-03-18柏奕旻
柏奕旻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授的回信中指出:“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①《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强调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人民日报》2018年8月31日第1版。“中华美育精神”作为时代命题由此凸显,美育研究亟待再出发,尤其应在中西文明互鉴的视域中,通过再问题化加深学科自觉,通过再脉络化予以理论重构①近年有代表性的成果,参见杜卫:《美育三义》,《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冯学勤:《中华美育话语的现代建构与当代发展》,《美术研究》2019年第4期。。
中华现代美育思想的萌发与演进,一度以日本为中介,深受西方现代美育思潮的启发。在西学东渐的理论旅行中,“美育”的历史语义生产始终隐现着话语权力关系的变动,与中国现代性工程的展开、文化认同的塑造息息相关②柏奕旻:《走向“世界美学空间”的“美育”——一个“明治—五四”的概念史考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追求人性完整、人格自由是东西方美育的共通旨归,近四十年来的美育研究也充分阐明了这一点。
值得追问的是:以美育人,需要哪种“完整”?什么“自由”?以席勒为重要代表的西方美育精神脱胎于其“社会的道德与习俗”,把“时代的需要和风尚”当作义务③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适应着“新教-市民社会”的欧式现代性状况。比较而言,无论是文明传统的生成,还是习俗风尚的延续,中国的现代性模式皆与之迥异。
中华美育精神的范式特征是什么?其存在论依据为何?探索一条会通古今中西、适应当代生活的美育新路如何可能?本文尝试将中华美育精神的核心概括为以“学-习”为体的“游艺”范式,区别于西方美育精神以“教”为本的“游戏”范式,进而探究“游艺”范式的当代转化路径,彰显当代美育介入生活、共享生活的创造性价值。
一、游戏与鉴赏:审美现代性的形上取径
在西方美学史上,特别是在康德以后,“游戏”(Spiel)成了一个重要的审美概念。早在“前批判时期”,康德就把审美活动的理想状态视为一种“游戏”状态,“当我们不以思想来工作时——在工作时我们的思想必须有一个目的——我们就以思想来游戏”,因而广义上“诗的艺术”是思想的一种游戏,它“把心灵中的一切机能和动力置于游戏之中”④康德:《美,以及美的反思:康德美学全集》,曹俊峰译,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193页。。进入“批判哲学时期”,康德针对诸项认识能力提出,仅有知性能够提供先天的建构性认识原则,理性唯有就欲求能力而言包含先天原则,判断力构成了知性和理性的中介环节。进而,他将判断力划分为审美的判断力和目的论的判断力,通过超越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宣告知性的立法与理性的立法在审美领域获得最终的联结。此时,康德主义美学已经成型,他把“艺术”作为制作的产品与“自然”区别开来,作为人为的技巧与“科学”区别开来,作为自由的游戏与“手艺”区别开来⑤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317页。,指出美的艺术以愉快的情感为直接意图,它不同于纯然以享受为目的的适意的艺术,是一种真正天才的艺术。
在此,康德把“审美判断力”具体化为“鉴赏判断”、把“游戏”等同于“思想的游戏”这一事实更值得注意。对康德而言,尽管判断力的原则不是从先天概念中推导出来,也不属于知性能力而仅仅关涉知性的运用,它却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同样处于一种“我们的认识能力的秩序中”⑥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78页。。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前言中强调,对于鉴赏能力的研究不是以陶冶和培养鉴赏为目的,而纯粹是在先验意图中进行。因此,康德美学指称的主体是先验的主体,这一主体具有的审美鉴赏力虽然是纯粹无目的的,与道德欲望无涉,却能够不受外在限制保持自身的尺度,成为道德的象征,又基于共感原则而保证普遍有效。在这一意义上,康德开启了美学研究中一个充满张力的基本范式:当哲学家宣布美的艺术为天才的艺术时,“天才”是指艺术创作者;当他指认一项艺术为“美”时,身兼鉴赏者的哲学家自身才是“天才”的真正所指。艺术制作本身的物质性、具身性最终被排除在外,哲学家因为发明了审美的游戏规则,成为美和艺术的立法者。
康德美学有关创作者与立法者的张力,在席勒学说中得到了更富问题性的呈现。席勒充分吸取了康德的思想,又对其观点作了关键改造。一方面,在席勒看来,康德对美的概念是否客观存在持怀疑态度,并未提出美的概念。席勒则力图超越康德,推导出美的定义。席勒认为,美既是感性的,又是客观的,“美就是一种不要求说明的形式”,“美是人为中的自然”①席勒:《卡里亚斯,或论美》,《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2、56页。。另一方面,席勒最终取消了纯粹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张力。康德定义纯粹理性时着力区分感性与知性,承认一切知识始于经验,并同时指出,需要一种独立于一切感官印象的知识②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席勒虽将美学研究视为知性活动,但在实际描述审美活动的过程中,他却统合了知性与感性,把来自人的物质存在或感性天性的冲动直接称作感性冲动。在这一前提下,席勒提出,游戏冲动具有连接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桥梁意义。因此,席勒关于审美教育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席勒相信,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这是因为人们只有通过美才可以走向自由。这样一来,审美问题本身成为需要关注的中心和亟待应对的难题。康德意义上遵循先天原则的审美判断被席勒实在化了,康德意义上的实现手段则在席勒这里成了目的。
席勒力图证明审美作为纯粹游戏的合法性。“我们不能一谈到游戏,就想到现实生活中进行的、通常只是以非常物质性的对象为目标的那些游戏”③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在美的观照中,心情处在法则与需要之间的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位置,正因为它分身于二者之间,所以它既脱开了法则的强迫,也脱开了需要的强迫”④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所以,席勒断言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这种审美的游戏始终是一种头脑的、心灵的游戏,一种回避物质性的精神游戏。实际上,强调文艺和审美的自律性,既与席勒受到康德的启发相关,也离不开席勒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转变。席勒一度将文艺看作批判社会和道德教育的手段,并为此创作了《阴谋与爱情》等作品。法国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后,席勒不再寄望通过实际的政治变革实现自由,不再规定文艺具有实现外在目的的功用。“现在是心灵提供了游戏美”⑤席勒:《论秀美与尊严》,《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1页。,席勒开始在精神领域中探寻温和改良、争取自由的契机。这一阶段,席勒对审美问题的探讨多立足鉴赏视角。在谈论文学创作时,席勒仅指出作家必须努力克服语言表达的抽象性和被表现对象的感性本性之间的矛盾,却没有解决这一矛盾。在谈及雕刻家、画家、演员的创作时,席勒也仅根据自身的审美理念分析作品、评论艺术,展现出鲜明的鉴赏姿态⑥在后人通常认为的席勒专攻美学研究、倡导美育的时期(1787—1796年前后),席勒几乎没有进行文学创作,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重心灵游戏而轻身体实践,强调鉴赏者而忽略制作者,根本上尊奉哲学话语的权威性,这是康德、席勒所开创的审美研究的内在倾向,也是对静观知识、贬抑实践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刻继承。柏拉图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明,爱智慧者追求“知识”而非“意见”,但在当时的城邦中,政治家、诗人、手艺人等的见解都局限在特定领域,他们对真正的智慧一无所知⑦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32页。。《理想国》宣称,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应被视为“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他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治理良好的城邦拒绝他们的进入⑧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6页。。在《法律篇》中,真正的诗人应该是能把握自然法律的立法者:“我们是像你们一样的诗人,构成同一种类型,你们的作曲家、艺术家,以及在最好的戏剧中的演员,只有真正的法律才具有自然的力量使其‘产生’并臻于完善(这一点我们是十分自信的)。”⑨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孙增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另一方面,把游戏的状态看作一种自由状态,用游戏的方法了解孩童天性并教育孩童,这在古希腊城邦中被当作一个重要任务。鼓励游戏又非一味迁就玩乐,古希腊思想深刻地规定了游戏的本体论意义。到了德国古典美学中,游戏的意义和审美现代性紧密相连。美的艺术本身被视为游戏,这为后来的思考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对话前提。由于游戏通常追求某些外在目的,格罗塞在游戏与艺术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尽管如此,他仍将游戏视为实际活动和审美活动的过渡形式,并承认游戏与审美活动都包含愉快的情感因素①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8页。。伽达默尔立足本体论阐释,把游戏界定为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②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在他看来,游戏具有相对于游戏者及其意识的优先性,艺术乃至广义的人类文化都可以在游戏中找到起源。麦克卢汉则指出,游戏是人的延伸,是集体的通俗艺术形式,是神奇游戏和古老仪式的文明替代品③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93页。。当现代西方学者以“游戏”来命名其哲学观念时,诸如海德格尔的“世界游戏”、罗兰·巴特的“解读游戏”、德里达的“解构游戏”、伊瑟尔的“文本游戏”、利奥塔的“公正游戏”等,这些“游戏”概念隐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特定承续性。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或后现代哲学家通过重构、拓展游戏规则,进一步护持了其艺术立法者的身份。
二、修养与技能:西方美育论的实践难题
“教育”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古希腊城邦中,教育“正是一切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④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孙增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在宗教社会学的视域中,韦伯试图澄清学术工作在世俗时代不再承担引导通神道路的重任,他严正廓清了教师不是领袖或生命导师这一观点⑤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I》,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他的看法从反面确证了教育与教师在西方文明传统中具有持续而关键的作用。
席勒“审美教育”的精神也需要在这一语境中考察。根本而言,席勒倡导美育旨在追求神性的复归,其教育内涵关乎而不限于古希腊语源中本就包含的游戏意义⑥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页。,更在于传达对神性存在的信念。席勒承认,他关于美育的思考最终意在回到神性概念这一出发点上⑦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按照他的推论,无限的存在是绝对的、永恒的、必然的,人格虽然也具有神性的倾向,但人既有理性,又有感性,因而必须通过审美的游戏状态才能真正调和这两者。席勒美育学说的核心精神在于“归还”和“恢复”。他宣布人性只有在审美状态中才能完整地、纯洁地表现出来,只有通过审美生活才能把自由归还给人,才能使人本来的天性得到恢复。席勒实际要说的是:相较于神性,人性是分裂的、破碎的,所以人必须成为接受教育的对象。
进一步,席勒阐扬美育旨在回应现代性(modernity)引发的社会与主体的困局。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世俗性指涉了宗教信仰及其实践的失落。对“宗教”的理解,关键在于抓住“超越”与“内在”这一区分⑧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等译,徐志跃、张容南审校,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0-21页。。在现代性的世俗时代,人取代神成为万物的主宰,人试图运用科学和技术掌控自然。由于信仰权威被启蒙理性予以祛魅,私人领域和个体价值的膨胀使人类面临新的危机:客观上,人的社会生活逐渐失范;主观上,人的精神世界陷入分裂。如何从“自在”走向“自由”,如何在“天真的”宗教信仰已然终结的时代追寻一种完满(fullness)的体验,构成了关乎社会和人性双重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审美教育来塑造“完整的人”,这不仅显现为一个神学隐喻,更表征着席勒在世俗时代对社会与主体双重同一性的追求。在对古希腊往昔整体生活的追忆中,席勒揭示了个体的撕裂如何与集体的分裂相互作用,甚而强化了公共社会中的裂隙;恢复人的完整性则有望治愈社会的弊病。神性复归、主体游戏、社会救治,共同构成了席勒美育方案的三个要旨。
那么,意旨如此遥深的美育,究竟该如何落实?是理论教育,还是实践教育?是鉴赏教育,还是创作教育?是培养主体修养,还是培养创作技能?现代性脉络中的审美教育一般重前者,轻后者。纯艺术或美的艺术在长时间内被现代美学家看成天才灵感迸发之作,但已被不少研究揭露为一个神话。一直到17世纪末,艺术(Art)的含义都与技术不可分,并作为自然(Nature)的对比。“艺术”是指人类技能作用下的产物,广泛包括中世纪大学课程中的“七艺”和后来的人文学科等不同技术①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页。。中世纪的作坊隶属于行会,只有基督教徒能够成为匠人。在法律、宗教信仰及共同体仪式的保证下,特定教育仪式实现了技艺的传承,师傅不仅口传心授,更重要的是面对面、手把手带领学徒掌握技能。反复模仿有利于学徒领悟权威的奥义。学徒在历时漫长的模仿、考核、见习后,最终用“高级杰出作品”赢得取代师傅的资格。因循守旧未必由于匠人自身创造力不足,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最早都是匠人,他们并非骤然出现,也很少独自工作②理查德·桑内特:《匠人》,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伴随个人主义的兴起、世俗时代的到来、艺术市场的出现,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家(artist)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凭借不可言传的天才与讲求技术纯熟、注重实际效用的手工艺者(artisan)区别开来③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页。。随着“艺术”从“技术”中脱离,身体劳作也不再必要。艺术家的工作被界定为纯粹精神性质,艺术创作的原理被神秘化,艺术的知识对大众变得隐秘且难以习得。于是,艺术鉴赏开始进入了教育领域。在文艺复兴艺术家最初登场的时期,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引人注目。“原创性”的定义掌握在权贵手中,艺术家的自主性颇为有限,这说明艺术鉴赏标准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布尔迪厄指出,这种社会性、历史性更复杂之处在于,文化资本的传承逻辑和学校教育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共谋关系。学校教育并不能赋予个体以艺术才能,甚至不提供艺术教育,艺术教育主要由家庭的文化传承来保证,但学校教育却能通过知识配置与认可赋予艺术鉴赏能力以合法性④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2页。。
席勒将“美”描述为“事物对它的技艺性的自愿认同”⑤席勒:《卡里亚斯,或论美》,《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0页。,但“技艺性”概念仅被抽象指认,“美”根本上仍是自由观赏或曰反思的产物。相比席勒,康德在思想与生活之间的张力显得更加意味深长:“除了军队进行曲之外他讨厌所有的音乐,这一点确实众所周知,同样众所周知的还有他对视觉艺术也毫不在意——他只有一幅版画,是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卢梭的肖像。”⑥罗杰·斯克鲁顿:《康德》,刘华文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康德喜爱诗歌,却对音乐和美术兴趣阙然。维特根斯坦的经历也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这位犹太富有家族的子嗣继承了家族的高超艺术修养,甚至发明“语言游戏”概念并引入哲学研究。20世纪20年代,维特根斯坦致力于为他的姐姐设计、建造一座楼房。他把哲学理论运用到建筑领域,意在使该作品完美实现“囊括所有可能性”的理念。楼房的形式、比例贯彻了设计方案,室内用具精美至极。然而,维特根斯坦后来成为这一作品最严厉的批评者。他称它缺乏健康和自然的生活气息,并且终身未再涉足建筑业。相较而言,他的友人、建筑家路斯(Adolf Loos)在同时期的建筑作品却成功得多。受财力所限,并为了兼顾美观与实用,路斯采取了和维特根斯坦迥乎不同的“创作”路径。
针对上述事例,值得追问的是:作为立法者的美学家是否等于好的鉴赏者?有修养的鉴赏者能否成为好的创作者?进一步,审美教育究竟应如何把握理论知识、鉴赏修养、创作技能这三者的关系呢?桑内特试图重新强调匠艺、手法、技巧等创作技能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维特根斯坦与路斯之别展现了判定匠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即优秀的匠人总能合理克制自己的痴迷情绪,他们尽管明白理论方案的重要性,却也重视偶然因素、避免钻牛角尖、不固执于完美、懂得适可而止⑦理查德·桑内特:《匠人》,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26-327页。。桑内特力图证明“人人皆可为匠人”,依其界定,匠人需要亲自从事创作实践,必须通过身体活动熟练掌握一项技能,匠人的劳作产品应当是具体的物质现实。实际上,西方思想却常常警惕匠艺及物质制作,如担忧原子弹或机器人作为技术产品会反噬自身。尽管桑内特认为矛盾根源“就是(西方文化长久以来)自然和文化的对立”①理查德·桑内特:《匠人》,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66页。,然而只要跳出桑内特旨在申辩的匠人情怀与匠艺立场,不难发现:在理论知识、鉴赏修养、创作技能之外,伦理意涵已若隐若现。审美教育的难题,在教育领域或许不仅仅是从鉴赏修养走向创作技能可简单解决,还需进一步关注创作技能的伦理意涵。这对于那些把席勒的美育理想寄托于创作技能教育的民主主义者来说,仍是亟须应对的实践难题。
三、学习与游艺:中华美育观的存在内涵
韦伯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现代西方的独有特征,这源于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理性思维形式和文艺复兴发展而来的技术经验。理性与技术,共同形塑了西方现代艺术特征: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经验技能和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功名追求②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旨在通过东西比较凸显基督教文明的独异之处。他洞悉儒家要求一种俗世伦理,儒家精神与西方新教伦理那种既崇尚禁欲主义又遵奉职业伦理的世界观大异其趣。在他看来,官僚制度和考试制度决定了中国历来把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中国的士人阶层是基于书写知识和文献知识的“活书库”,他们欠缺手工艺为基础的经验技能,难以养成自然科学思维及职业伦理,进而导致在中国难以发展出资本主义。
西方本位的价值取向阻碍了韦伯真正进入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论语》开篇并非“教”,而是“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许慎《说文解字》与班固《白虎通》都将“学”训为“觉悟”③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页。。钱穆解释:“孔子一生主在教,孔子之教主在学。孔子之教人以学,主在学为人之道”;“孔子之学,皆由真修实践来,学者无此真修实践,即无由明其义蕴也”④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3页。。钱穆认为,编者将“学”列为《论语》篇首饱含务本的深意,他明言孔子的事业并非居高临下地“教”人知识,而根本在于传授“学”做人的道理。子安宣邦也给出过相通的解释。他认为,现代学者把“教”直接理解成“教育”,将孔子视为信奉平等主义的教育家,都是现代主义的谬误,“教育”作为Education和Erziehung的现代译词,是伴随现代国家的成立、平等理念的确立而问世,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现代色彩⑤子安宣邦:《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读〈论语〉》,吴燕译,吴素兰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 30、34页。。子安宣邦指出,《论语》中除了寥寥数语几乎不谈“教”或“教育”,因为真正要紧的问题是“学”。孔子的身份首先是一位“学”人,他营造了鼓励“学”及“志于学”的氛围。通过这种学问,每个人都获得了扩充一己、实现人性向善的可能。
“学”的内涵远比韦伯所谓文献书写知识更丰富、更生动,它具有文化实践论的意义,涉及对先觉著述的诵读领会和对道理知识的躬行实践(“习”),其首要目的在于“为己”或“己欲立”,这一手段和目的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学-习”实质上还与文明的存在论关联紧密。白川静将“儒”解释成祈雨仪式中被用作牺牲的巫祝(Shaman)⑥白川静:《孔子》,韩文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3-54页。。据他推论,孔子曾长期生活在巫祝社会的底层,通过参加各地的丧礼仪式,孔子从贫贱的巫祝者那里习得丧葬祭典的知识并加以运用。白川静强调,孔子作为圣人的伟大之处不在言语,而是由言行来展示。李泽厚则将中国文明的特征提炼为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和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⑦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页。。李泽厚指出,巫术礼仪注重活动而非静观,强调激情而非理性⑧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政教合一、天人合一、礼法交融、情理交融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结构与生命世界,这区别于西方文化基于神人殊异、灵肉两分的超越性结构。因此,中西文明的存在论结构有根本差异。中华文明是“一个世界”,人与神和光同尘,始终没有形成绝对的、全知全能的、远超世俗生活经验之上的神。西方文明则是“两个世界”,人或依归上帝、从属上帝,或取代上帝、置换上帝。依此,“学-习”作为文化实践,深深扎根于“一个世界”的文明存在论结构。
中华文明传统善于应物、造物而又倡导忠恕、爱人,“学-习”正是中国士人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核心方法,具有深刻的存在论意义,涉及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华美育精神诞生于“一个世界”,以“学-习”为体,与人为善,与物为春。西方美育精神则依托于“两个世界”,以“教”为本,人神区隔,主客对立,身心分离。中华美育精神具有独特的存在论特征、实践性意义、伦理化价值,既重视道法自然,又追求日新开物,更兼顾立人达人。如李泽厚所言,中华文明既包含外在物质文明(人文),也包含内在精神文明(人性)①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页。。“度本体”和“情本体”构成了中华文明处理“天道”与“人道”关系的核心范畴:“度本体”是强调“掌握技术、恰到好处”、“技术或艺术,技近乎道”的“社会-工艺”本体,“情本体”则是主张“道由情生”、“经由历史洗礼和文化积淀的情感形式”的“文化-心理”本体。“度”与“情”成为了中华美学精神的两个关键支点,“度”源于技术而又超越技术,“情”脱胎感性而不滞于感性。“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与由技术(手工业)和理性(功名心)形塑的西方现代艺术显出了存在论的差异,同时也是美育论的差异。如果说中华文明传统的存在论是“一个世界”及“学-习”,那么中华美学精神的支点就是“度本体”和“情本体”,中华美育精神则有待召唤“游艺”范式。
“游艺”语出《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历来被看作孔门学习的纲目。“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蓺”“藝”二字虽未见于《说文》,作为字源的“”字却与农业息息相关。段玉裁认为,儒家之“六艺”可比农者之树艺②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这足见“艺”有树人、立人之意。“游”则彰显了传统中国士人的身心感受、情理结构。《礼记·学记》将“游于艺”解释为“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③引自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7页。,意谓好学、乐学与兴艺、游艺相辅相成,君子品格由此成就。庄子在《逍遥游》中也阐发了无所待、游无穷的自然德性,在《养生主》中又通过庖丁解牛的事例,描绘了道进乎技、游刃有余的技法同心性的有机结合。郭象指明这反映了庄周崇尚任物之性、称事之能、各当其分、各安其分的“自得”境界④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1页。。儒道的交融互补奠定了后世士人“游目”“游心”“游世”的思想根基,刘宝楠称之“不迫遽”⑤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7页。,钱穆则曰“泳也”⑥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60页。。
概言之,“游艺”范式源自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是指在早期中国“礼乐文明”这一存在论结构中,士人君子经由沉浸式、具身性的礼仪文化学习,达到一种人格自立的自由境界。较之“游戏”,“游艺”隐现了中华美育精神的独特内涵:“游”是悠游从容的自由境界,“艺”则兼顾理论知识的掌握、鉴赏修养的培育、实践技能的操演。“游艺”包含了理论、鉴赏、实践、自由的四重意涵:即理,及物,上手,从心。较之西方的天才或匠艺,士人君子不一定从事实际生产劳动,也未必都是天赋异禀,但能通过“礼乐文明”的长期训练,达到掌握知识、提升修养、得心应手的境界。巫鸿将早期中国称为“礼制艺术的时代”,他对“礼”的解释是“既是世俗性也是宗教性的人类关系和交往的原则与形式”⑦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并认为“中华文明的历史也就是‘礼’或‘祭’产生与完善的过程”⑧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据此,士人君子以“礼”为方法,不单要在知识上了解相关礼仪、器物,而且要身体力行于实践,甚至能够熟练自如,呈现出一种礼仪活动的审美自由感、“祭如在”般身心一致的道德尊严感。所以,“游艺”范式融知识、道德、审美于一体,就性质而言,是达成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礼制之外,“游艺”范式还可视为儒家讲求“人化的自然”与道家崇尚“人的自然化”融通的结果。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人的自然性必须符合和渗透社会性才能成人,道家的“天人合一”则要求人彻底舍弃社会性来实现与自然的重新合一①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儒道看似南辕北辙,但在“度”和“情”的意义上,两家分享了对感性生命的肯定态度,在“自然-人文”合一的存在论取向上殊途同归。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儒道相参,儒道互补,“游艺”范式孕育自中华文明传统,又体现了中华美育精神。
四、生活与共育:游艺当代化的创造潜能
激活中华传统美育资源,博采世界经典美育学说,赋义当代现实美育经验,构成当前开展美育学建构工作的必要环节。考掘中华美育精神的“游艺”范式进而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临着“当代化”问题。“当代”(Contemporary),就是“既与自己同构,也与自己同时”,跳出从过去到未来的编年框架来定向自身的时间②阿兰·巴迪欧、让-吕克·南希:《德国哲学谈话录》,扬·沃尔克编,蓝江译,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版,第75页。。“当代性”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历史意识,旨在反思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建立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③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论友爱》,刘耀辉、尉光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开展“当代化”工作,意味着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想象乃至现实地开启别具可能的当下时刻。鉴此,“游艺当代化”,既不是简化“游艺”概念、止步口号操演,也不是僵化“游艺”形式、抒发怀旧情结,而是立足“游艺”范式及其文明存在论意义,重新理解被现代化、城市化进程遮蔽的存在状态,重新彰显被现代性教育制度忽略的育人环节。同时,通过“游艺当代化”,中华美育精神也将寻找契机重新深度介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通过“美育的生活化”和“美育的共育化”致力于“美丽中国”的现实构建与社会实践。
“美育的生活化”涉及“审美”与“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得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寻求对它的解答,则构成了21世纪前后“美学的复兴”的内在动力④高建平:《“美学的复兴”与新的做美学的方式——兼论新中国60年美学的发展与未来》,《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围绕“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议题,学界展开了热烈争鸣,进而召唤“生活美学”,反思精英主义传统范式,倡导美学介入日常生活⑤王德胜、李雷:《“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相关研究援引韦尔施对于消费主义时代“美学膨胀”的诊断,借鉴费瑟斯通关于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分析,直面中国城市化进程迅猛、消费文化急剧扩张等问题⑥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大致上,这些研究共享了某种问题预设,即中国与西方在社会进程、文化氛围、生活经验上日渐趋同。因此,就“审美”与“生活”而言,学者们多聚焦“重构美学”,但问题在于,中国与西方的“生活”质地也许并不相同,更迫切的应该是“重构生活”。
“美育的生活化”,意指对中华美育精神进行古典的现代化、精英的大众化、仪礼的日常化的创造性转化。“生活”对于有着“一个世界”存在论的中国人具有安身立命的意义。值得注意,“生活”迥异于“生命”。“生命”是现代与后现代西方美育精神的一个关键词,尼采的生命美学、福柯的生存美学、德勒兹的生成美学,都把自我保存作为生命本能,把个体生命价值作为核心旨归。其生命观根本上是由“两个世界”存在论所决定。西方美学探讨人性时离不开人和上帝的关系这一预设,“自然人”的“生命”乃至“裸命”就构成了相关讨论的自明前提。与之有别,中国人的“生活”则是“过日子”,包括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老、送终、年老、寿终等一系列环节,亦即一个人一辈子的过程⑦吴飞:《论“过日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在“一个世界”中“过日子”才是中国人的生活常态,既不是赤裸裸的生命状态,也不是神性和罪性相结合的自然状态。
同时,“生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概念也有差别。卢卡奇开启了日常维度的思考范式,列斐伏尔主张日常生活是反抗资本主义的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赫勒则吁求走向一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他们着力批判资本主义导致了人的异化,试图通过思考“日常生活”来克服现代性危机,塑造“总体的人”。诸种探索虽饱含关切却不乏浪漫色彩,“日常生活”作为实现“总体”目标的手段得以凸显,而“日常生活”与“总体性”仍处于“两个世界”的存在论结构之中。作为对照,中国人的“生活”就是“日常”“日子”,无需将“日常”(everyday)作为定语附着在“生活”(life)上,来显示其同“生命”(life)的语义差别。中国人的“生活”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展开,家庭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基本单位,同时作为“修齐治平”的内在组成,更是中国人的意义感与价值感的重要来源。在“一个世界”中生活的中国人,往往以家庭为核心来看待人,“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绝不将人视为私人化的、原子化的个体。在传统中国,“游艺”范式体现为士人君子沉浸礼乐文明的自我涵育过程。在当代中国,“游艺”的实践主体则应涵盖普通人民群众,“学-习”也从庙堂书斋扩展至生活方方面面。简言之,生活就是“学-习”。“美育的生活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会过日子”,即人在生活中待人、接物、处世皆显出行止有度、通情达理的分寸感和人格魅力。进一步说,“游艺当代化”的核心旨趣,并非单单追求“完整的人”,而是将“完整的人”“完整的生活”“完整的世界”融于一体。
据此,“美育的共育化”就构成了中华美育精神创新性发展的另一要旨。相对于精英个体式的“完整”,中华美育精神更注重民众共同体的“完整”。中国人的“生活”既然深深扎根于家庭生活,“美育”就必然蕴藉着“共同美育”亦即“共育”的意涵。费孝通以“差序格局”定义中国乡土社会的组织逻辑,并指出亲属伦常组合形成的“家”是其中的基本社群。现代以降,尽管中国人的家族制度、家庭规范相较传统中国发生较大变化,基本理念却一以贯之,即以家庭为核心、在“一起过日子”的背景中理解自己的人生①吴飞:《论“过日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在公与私、情与理、立己与立人、独善与兼济、庙堂与江湖的生活结构中,中国人“学-习”的过程始终处于一种“共”(com-)的关系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与家人“共”,与他者“共”,与万物“共”,与世界“共”。“游艺当代化”的另一旨趣,并非追求原子个体主义的主体性自由,而是致力于共同体文明传统的主体间性自由。一言以蔽之,“当代美育”即“共育”。
“美育的共育化”,意即中华美育精神创新性发展的历史潜能是使中国老百姓共同过上有意义、有尊严、有滋味的美好生活。“美育的共育化”旨在强调“共同性”(community)。“共同性”不是西方美学重视的精英化“公共性”(publicity),它表征着中国人生活中血脉相连的社会关系纽带,支撑着中国人从身体、物质、情感等多维度建立“和而不同”“感同身受”的共通感,倡导推己及人、共同富裕、立人达人的“好日子”,彰显独特“审美-伦理”境界及文明价值的“小康美学”②罗成:《“风味”的精神——“小康美学”及文明意义》,《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注重“游艺”范式的当代转化,开展“美育的生活化”和“美育的共育化”,正回应了新时代对中华美育精神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吁求。
这是一个美学复兴的时代,更是一个美育复兴的新时代。“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要以美启真,也要以美储善,更要以美致“共-同”,将“共-同”设定为当代美育的学理价值与实践方向,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游戏”走向“游艺”,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完整的人”迈向“完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