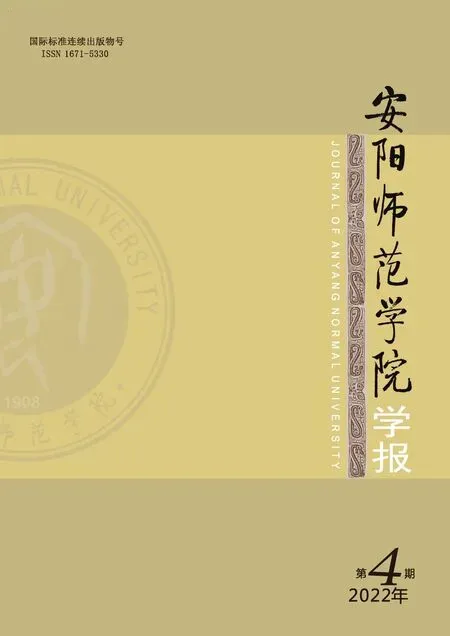传播史论的国际化视野
——基于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的解读
2022-03-18杨临端
杨临端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以下简称《传播纵横》)是李金铨教授历时十多年完成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了他的多篇论文与演讲稿。其名为纵横,英文名crisscrossing,即十字交叉,表现了作者对于时间的历史脉络和空间的全球视野的学术取向,同时也有在学科上力求打破学科边界、渴望跨学科交流的学术视野。
李金铨教授在《传播纵横》一书中展现了他的雄心壮志,既是既往,也是开来,他总结了传播学史(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史和美国式的国际传播学史)以及近代的中国报刊史,批判了一直以来的范式流弊,提出了自己独特而宏大的学术视野、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该作反映了李金铨本人学术生涯的研究重点,即国际传播和近代民国报刊。尽管由于篇幅所限和作者的文风问题,每篇作品在宏大开头之后总有“希冀来者”云云而不免意犹未尽。但是在每个命题背后,总能看出作者敏感的学术思维和广阔不羁的学术视野。同时,站在中西传播的前沿阵地,加上李金铨教授本身多年在两岸三地及北美的科研经历,他敏锐地提出了中国(或华人社会)在传播时应该具有的姿态是从特殊到普遍,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理论,而非作为西方传播的注脚。
李金铨教授《传播纵横》一书是论文集,在论述中虽有一些重复,但思想脉络基本是统一的。2019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后,虽较繁体版少了第三编访谈录的部分,但仍基本展现了作者的学术脉络,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浙江大学吴飞教授等从历史与比较视野对其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解读[1],华东师范大学唐小兵教授从跨界研究着手,以更宏大的场域介绍了李金铨教授的学术贡献[2],但总体而言,对李金铨教授《传播纵横》及其思想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试从传播史视域下的国际化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一、包容性思想与独立性意识
《传播纵横》对于国际传播背景下中西文化如何融合贯通、个案研究与宏大思考都有深入的思考与探究[3]。李金铨教授宏大的研究视野和严谨的研究路径在第一章就有比较充分的体现, 作者在开篇就站位很高,直接比较了中国偏直觉的文化传统和重概念、逻辑、证据的社会科学。和一般现代社会科学学者对中国文化传统重直觉而少逻辑的轻视态度不同,李金铨教授虽然也批判了直觉思维过于抽象的“全称命题”,并在其后对美国主流传播范式批判时也多有涉及,但对其朦胧清新的话语之美也有所推崇,这也体现了李金铨教授包容调和的思想。与我们熟知的各种思想学派的激烈冲突有所不同,如后现代思想对主客二元的批判,又或者五四以来现代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交锋,而包容调和思想能使我们站在更加客观的角度去面对矛盾冲突。包容调和并不是“好好先生”,而是一种开放平等的对话与理解。
同时,作者的正—反—合思维也是贯穿始终。李金铨教授的研究法既充满了中国传统式的从看山是山(肯定),到看山不是山(否定),再到看山还是山(合),又有着黑格尔辩证法的知性。如第一章的从一般直觉到深刻直觉,再如后面第二章论述我们与西方对话的态度应有从learn、unlearn到relearn的变化,都体现了作者正—反—合的综合辩证思想。这种思想其实和上述的包容调和有所呼应,即作者始终强调的对绝对的批判和对条件性的重视,任何事物的分析都要注意它存在的条件性,而不能用规律来预设。
李金铨教授还围绕《题西林壁》提出了三个想法。第一,社会真实是多重复杂而非绝对的,作者强调要进行“互为主观”的观察,在后面章节可以看到这种思想来自于作者对韦伯方法论的推崇,即“容许不同的诠释社群建构不同的现实”[4](P97)。第二是局内人与局外人观点的各自利弊,该观点引自默顿,这点除了是为唤醒中西方学者“同情理解”的学术心态外,我感觉更像是李金铨教授这个对美国式传播学和中国传播都穿梭得游刃有余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自表。李金铨教授作为华人传播学者,相对于美国主流传播界更像是洞若观火的局外人,但同时又在北美学术圈中得到日常的观察经验,因而更有“同情理解”之优势。第三,即最能体现李金铨教授学术思想的“常与变、同与异”。他批判了线性思维的历史观,正如后面章节批判现代化理论一样,认为要用“对位阅读”“意义交涉”等方法来对历史进行多角度切片和互为主观的观察。空间上,不赞成只强调化约的同和第一世界采取的树立他者的异,而提倡“允执厥中”的态度,这里除了体现了李金铨教授的包容调和思想之外,也反映了他对于社会整体的宏观结构思考,认为社会应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并与微观互动(正如他更乐意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媒介社会学)。在学术具体表现上,他提倡要考虑具体条件解释同与异,在具体语境中考虑结构与能动者(结构与能动者也随语境不断变换主体)的复杂互动,而不能过度抽象、过早预设,这里他又一次批判了“目的论”和“全称命题”。
李金铨教授最终的人文关怀仍然是对华人社会传播的观照,提出应有的立场是平等对话、“境界共融”。在分析自身问题时,要考虑历史脉络和国际视野,不要陷入西方国际传播(或美国式)的桎梏之中。这种历史视野和人文关怀李金铨自称受米尔斯的影响很大[4](P93),即把个人关怀联系到公共问题,同时把重大问题放到时空背景。李金铨教授认为,如果缺乏宏观的视野与对社会现实的观照,那做出的东西就是“精致的平庸”。
李金铨教授对哈贝马斯热和“公共领域”风行的评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金铨教授发现,现在华人学界很多年轻学者,动辄声称要研究新媒体的公共领域,但往往就只是断章取义地借用概念,然后急切地在本土现象中找对应参照,就如李金铨教授在书中反复提到的,拿了个西方理论的锤子,恨不得走到哪里都要敲敲打打(美国传播学者同样在犯类似错误,才会形成理论内眷化),却不考察理论生成的场域不同,不考虑在地经验,到最后只能沦为西方理论的翻版或者注脚。
二、对美国传播内眷化的历史脉络分析
在上编《国际传播:中华与世界接轨》中,李金铨教授深刻且不乏激烈地批判了美国主流传播的内眷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际传播的“学术殖民思想”,并由此,希冀构建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中国传播体系。
李金铨教授梳理了从芝加哥到哥伦比亚,从施拉姆到查菲等第二代学者的美国传播学发展过程,尖锐地提出美国传播学已经陷入到区域自闭、视野狭窄、理论贫乏的内眷化,变成了精致的平庸。需要说明的是,李金铨教授将involution翻译为“内眷化”而非通译的“内卷化”,是因为他认为美国传播学术圈现在只向内求索问题和理论资源,而不外顾,因此取“向内眷顾”之“眷”。
李金铨教授虽然也认为早期传播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很多问题,但更推崇他们宏大的学术视野和人文关怀,比如芝加哥学派将城市当成实验室,注重学术与社会、政治的联系,以及施拉姆不遗余力地从跨学科引进理论与视野。李金铨教授分析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内眷化,是哥伦比亚学派范式取代芝加哥学派以后逐渐形成的。其外部原因主要是因为美国战后的学术潮流主要由研究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变革变成了如何维系社会稳定,同时由于学术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和资本家,所以就尽量回避讨论社会结构的合理性,转为研究媒介效果。而在内部原因上,李金铨教授认为是长期以来传播学的学科焦虑形成的。因为传播学早期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开创的,但当时主要是以社会分析为主,而各地零散的新闻系也大多是英文系的分支,只培养新闻实务人才。后来施拉姆的野心很大,想将传播学建设成为统摄性的传播科学,这也是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统一科学”运动下的产物。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集结了奥斯古都、香农、韦弗等各领域的学者,又在斯坦福创立了传播研究所,可都只是激起短暂的火花。而施拉姆的学生查菲以及第二代学者们,认为传播学科已经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而不必假其他社会学理论,从他们合编的传播科学手册即可看出。因此,视野不断狭窄、理论不断贫瘠也就在所难免。李金铨教授在第一章就引用库恩一个观点,即“须先做传统者,才能做创新者”,就是要在之前的范式里不断学习、操练才能发现破绽,显然,李金铨教授认为第二代学者缺乏这样的意识,因此虽然范式转移,但是并没有超越原有范式,反而不断内化、狭隘。可见,在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中,以及在施拉姆与第二代学派之中,李金铨教授都更赞同前者。其原因不只是因为其学术开放性,能够主动去学习引用别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更在于他们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精神,而不是视社会结构为应有之物。此外,李金铨教授也认为芝加哥学派虽已被哥伦比亚大学的范式取代,但仍暗流涌动,而且其关心的媒介与权力的互动关系以及米德的“象征互动论”,可以与政治经济学和欧陆的现象学展开对话,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所没有的优势。
在美国主流传播学范式的具体缺陷上,李金铨教授总结现代美国传播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派的影响下具有两种真空:历史真空与国际真空。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不同的就是他们不太承认历史与现在的联系,陷入到米尔斯所谓的“抽象的经验主义”,不去讨论时间维度上的常与变。而国际真空就是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为理所当然之物,原因前面已经做过阐明。因而,其缺乏政治经济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所具有的权力分析,忽视意识形态问题,所以不止是在国内分析传播问题时不断走向内眷,在国际传播上也漠视了在地经验,反而以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加以统摄。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美国传播学的视野和理论日益内眷,并受到了媒介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英国文化研究和萨义德东方主义的挑战。
而在学科上,李金铨教授更认同凯瑞和培斯理的说法,即传播学更像是横向学科而非社会学、心理学一样的纵向学科,它是一个链接不同学科的领域或者是表现各种社会动态斗争的场域,即媒介社会学。
三、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传播的批判
受到美国国内传播研究主流的影响,国际传播研究也发轫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范式之中。典型的就是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施拉姆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以及李金铨老师罗杰斯的“创新扩散”。他们的相同点在于都是植根于现代化理论,认为媒介是第三世界进入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这里,李金铨教授敏锐地发现了吊诡之处,即在美国国内,他们认为媒介效果的有限论,认为媒介只能强化固有立场,而在国际上,媒介却还像魔弹论一样具有强大效果。由于西方在现代学术的开创和领先地位,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以来对此观点深信不疑,凡是与西方不符的理论都成为了例外。李金铨教授认为,这就如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是一种学术师徒共构的意识形态。第三世界也希望用这种化约的简单手段来解决问题,因而长期受害。
李金铨教授并没有就学科而论学科,而是像他所推崇的对位阅读者或芝加哥学派学人一样,主动去寻找政治、社会及阅读主体的历史脉络。他分析了国际传播盛行时期的“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土壤,发现拉丁美洲的依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经常针锋相对。但在传播学领域,由于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冲击过大,现代化理论仍然大行其道。而在冷战后美国建立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现代化理论仍然充当了马前卒的作用。但是李金铨教授也并没有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中迷失对微观的受众解读。在此他加入了长久以来研究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辩论(他的学术生涯也是由其博士论文《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而发端),罗列了政治经济学、文化分析等各个学派大家的辩论。李金铨教授提出,不能过度夸大资本对读者的影响,也应该从读者解码本身进行分析。这也表现了李金铨教授从小到大、从特殊到普遍的思考路径以及允执厥中不偏不倚的学术态度。
对于目前研究的现状,李金铨教授认为,在国际传播中一定要摆脱哥伦比亚大学范式下美国国际传播的桎梏,力求平等对话。李金铨教授推崇韦伯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力主打破哥伦比亚大学的实证主义范畴,不能简单化约,强调互为主观,以不同社群诠释多重真实。在具体操作上,李金铨教授借用了兰克的观点,认为应该从特殊性到普遍性,而非从普遍到特殊。他推崇韦伯式的研究路径,即了解在地知识之后,用学术概念类型化(概念、逻辑、理论架构),深入生活肌理,再提取理论,寻找和西方理论的“抽象阶梯”,勾连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点。李金铨教授在抨击对西方亦步亦趋现象的同时,也提出要警惕“学术义和团”的民族主义,不能否定一切西方理论,就如萨义德也是以启蒙、解放为主旨,而非排外。
通过《传播纵横》一书,我们能够受到启迪的不只是在研究方法上,在学术素养的积累上李金铨教授认为也应遵循渐变的规律,先要在范式内完成充分学习、操练,才能找到破绽完成创新,即库恩所谓的“须先做传统者,才能做创新者”。只有如此,方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就如李金铨教授在第四章推崇的王国维和陈寅恪,他们都是首先让自己成为贯通中西的大家,然后才能自觉使用西方理论工具分析,而不受其约束。其实,李金铨教授本人也是如此,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学术培养,使得李金铨教授能够摆脱五四以降学术普遍的“世界之中国”(梁启超语)的倾向。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很容易走向两种误区,一种是拿来主义,凡是一种新奇流行的理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直接照搬到本土经验上;另一种就是急于求新求变,否定原有一切范式而不遵循科学规律(如学术义和团)。李金铨教授的治学态度,也如一种浮躁学风下的镇定剂,让我们面对复杂的国际传播局势与崭新的本土研究问题时,做到“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