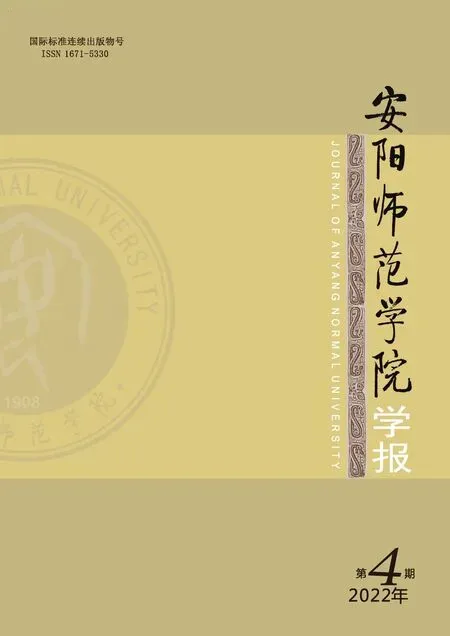严复翻译实践中“训诂”与“界说”的会通机制
2022-03-18张德让
李 东,张德让
(1.皖南医学院 公共基础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2.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3.安徽师范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严复称名词为译事之权舆,可见名词的翻译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转述,阐发并澄清概念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近年来,关于严复翻译的本土话语研究拓展了严复译学的研究思路。其中,关于严复译学中“儒者之学”和“文章之学”的探讨都比较多,而对严复翻译理论及实践中“训诂”“界说”等释名问题却鲜有提及。宋代理学家程颐曾总结文章学、训诂学和儒学为“今之学”[1](P187),严复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条说》中便开宗明义,提出了翻译的四大宗旨,“敦崇朴学”[2](P125)为其中之一,这一要旨体现了严复的“实证精神和会通宗旨”[3](P104)。
严复所言“朴学”,又称考据学或考证学,重点在于文字的训诂和考订,要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4](P5)。这一朴学实践传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孔子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5](P82)孟子云:“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6](P261)《礼记》云:“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7](P24)南宋陆九渊继承孔孟朴学传统,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8](P399)。清代乾嘉学派提出“训经明道”,魏源、康有为等人更是重视“经世致用”精神,强调学贯中西、广征博引。严复继承了传统朴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精神,在译学实践中对概念进行正音训声、明义辨义,又援引以西方逻辑学为基础的“界说”手法,对概念加以古今理训、中西多证,从而对中国传统朴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严复翻译中“训诂”与“界说”会通的本质:互为体用的“训”与“界”
严复通过翻译带来新知的同时也未忘故识,他频用“训诂”之法探西学之微,又巧借“界说”之长补“训诂”之短,通过“界说”保证西学概念输入正确性的同时,又发展了传统训诂方法,最终形成了“训诂”“界说”互为体用的会通范式。
1.训诂
在《英文汉解》中,严复指出:“以言其义训,则文字之于人意有各当之异用……乃至本原流变,则其义愈繁,往往初义与引申者绝异,而其用于文辞也,往往有所分合而其遂殊。”[2](P348)该段论述体现了严复对“义训”的看法,文字之“义”因“训”者而生“异用”,“初义”与“引申”故而有别,不训义,义难明,训其义,义多释。因此,“训诂”不可望形生训,而当顺义以训。夏曾佑论曰:“主宰前定之义,原于宗教,而达于政治,凡在皆然也。周之制,凡天下之学,能为语言文字所持载者,无不集于史。”[9](P10)训诂之实在于“史”,因天下学问集于史,而其路径在于“至宗法,达政治”。
2.界说
严复在谈论西方“界说”时,作出如下表述:“西人类别群分,区之为八九类,不若中国之但以虚实云也。”[2](P348)对于概念的界定和描述,西学以事物的本质为抓手,反映概念的内涵外延,因此以“类别群分”见长。
而严复的《义界五例》则在西方“界说”的基础上,明确了“界说”的规则,并融入了中国话语:
界说必尽其物之德,违此者其失混。界说不得用所界之字,违此者其失环。界说必括取名之物,违此者其失漏。界说不得用诂训不明之字,犯此者其失荧[10](P118)。
严复以“德”为譬,喻指事物的本质,指出界说重在穷尽事物本质,界定概念边界,力避概念混淆。界说不可以“界字”论“界”,以避免循环论证。界说因囊括相关联的事物,以避免概念对象的缺失。界说不可用表意模糊或有歧义的语词,否则会导致概念表述不清。
由此可见,严复十分重视“义界”的精确性、全面性和深刻性。正如曾克耑在严复《评点<老子>》“叙”中所指出:“识不能东西万里,学不足综上下千古,其何足以言道术之全之真之微哉。”[9](P13)因此,对知识的理解,既要讲求东西视野,也要关注历史沿革,基于此才能看出学问之“全、真、微”。“道术之全”即考察学问之全面,“道术之真”即探索学问之真确,“道术之微”即探究学问之精微。
兹举严复对“宪法”的训诂一例试论之:
按宪法二字连用,古所无有。以吾国训诂言仲尼宪章文武,注家云宪章者近守具法。可知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今日新名词,由日本稗贩而以来,每多此病。如立宪,其立名较为无疵,质而解之,即同立法。吾国近年以来,朝野之间,知与不知,皆谈立宪[2](P281)。
严复从构词规则的角度,认为“宪”“法”互训,后对“宪法”一词的由来做了介绍,并指出该词的误用现象严重。以“宪”为核心,他又以“立宪”被误用的例子加以说明“宪”实非人人所言之“法”:“立宪即同立法,则自五帝三王至于今日,骤听其说,一若从无法有法,必待往欧美考察而归,然后为有法度也者,此虽五尺之童,皆知其言之缪妄矣。是知立宪、宪法诸名词,其所谓法者,别有所指。”他接着对“宪法”实为“国制”进行分析,并对译名的“词法”误用举证辨伪:“新学家之意,其法乃吾国所旧无,而为西人道国之制,吾今学步取而立之。然究竟词法,吾国旧日为无为有,或古用而今废,或名异而实同,凡此皆待讨论思辨而后可决。故其名为立宪,而不能再加分别者,以词穷也。”在充分分析了“宪法”“立宪”译名的使用差缪后,严复按照“词性分析-构词分析-源语语义-语义范畴-译语语义-语义范畴”的顺序对“Constitution”和“宪法”分别做了义训:“宪法西文曰Constitution,此为悬意名物字,由云谓字Constitute而来。其义本为建立合成之事,故不独国家可以言之,即一切动植物体,乃至局社官司,凡有体段形干可言者,皆有Constitution。今译文宪法二字,可用于国家之法制,至于官司局社尚可用之,独至人身草木,言其形干,必不能犹称宪法。”通过推勘,严复总结为“即见原译此名,不为精审。译事之难,即在此等”,即在说明因为中西构词和语义范畴的差异,翻译往往无法做到绝对对等。最后,严复加以点评,提出自己对译名是否继续使用的观点,他认为:“其名自输入以来,流传已广,且屡见朝廷诏书,殆无由改,只得沿而用之。异日于他处遇此等字,再行别译新名而已。”[2](P281)
综上所述,严复在朴学实践上并非墨守成规,而是在传统训诂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朴学传统的增益。他完成了从音形到义理的多层次训诂,又将训诂发展到古今理训、中西互训相结合的境地,从而实现了训诂和界说的体用结合。
二、严复翻译中“训诂”与“界说”的会通范式:正音训声,训义界义
训诂一般分为音训、形训和义训三种,鉴于中西语言文字在形态上的差异性,严复翻译实践中对训诂传统的承袭并无形训方面的内容,而多见于音训和义训。又考虑到英汉发音的较大差异,严复往往为英文单词正音,通过汉语尽量还原源语词汇的发音,并因声求义,即采用声训法。义训方面,严复在传统义训范式的基础上,增设界说,对概念流变过程及其内涵加以阐发说明,力求概念描述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1. 正音训声
正音训声,在于“规范发音”和“因声求义”。因晚清西学概念和西洋专名繁多,其译名实难音义两全,故多用音译,而音译译名虽大体相似,却无固理,因此变化较多,严复便不得不厘清古今各音,聊以释惑。如《法意》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一章严复的案语:“ 梵字。魏、晋时音读如婆,所称梵种,即婆罗门最贵种也,故薄伽梵亦作薄伽婆。”[11](P479)又如:“而国家常政,王乃别选具臣,为其侍从,此于古曰孤理亚,今音转曰孤尔德(译言朝廷),常在王之左右备任使。”[12](P453)
至于声训,在传统训诂中,因声求义早已有之,即以或音同或音近的词语释义,推及其源。声训者往往通过物象(如形状、属性等特征)推陈义理,遂有主观臆断之嫌,但从翻译的角度看,每每能做到音义对等,不失为翻译妙法。如严复在《法意》第十四卷第二章中,将“Fibres of the body”译为“肋糸”,注释谓“糸音密,至细之丝也,与系异”[11](P247)。“纤维”是一种连续或不连续的物质,本由细丝组成,严复便通过声训,巧用“糸”字,既似其音又通其义。
2. 训义界义
训义界义,在于“训”与“界”的会通融合。严复的训义观是对中国义训传统的继承,旨在求其“真源”,主要是通过对源语概念的追根溯源,明确词语在源语语境中的意义。如:
But there is, likewise, a danger in specialization; and a man who uses the microscope only, loses the treasures revealed by the telescope.[13](P4)
严译:
虽然,吾往者不既云乎,学之为道,有通有微,通者,瞭远之璇玑也;微者,显微之测验也。通之失在肤,微之失在狭……[12](P363)
原文中“microscope”和“telescope”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较为陌生,严复以“通者”“微者”构词,首先还原其构词的形态特征,即“-者”对等“-scope”。其次在原文基础上说明了“microscope”和“telescope”为何物。“通者”为“瞭远之璇玑”,而“微者”为“显微之测验”,终明二者之真义。
又如下例:
吾英古谚有云:“英民之狱,毗尔听之。”(按:毗尔,字有二义,一曰平等同类,一曰有爵贵人。)[12](P442)
该例中“peer”一词,有数种含义,其一为同龄人,其二为英国贵族成员,严复于此明义,旨在对音译“毗尔”之理本奥衍做出诠释。
再如“liberty”的译名“自繇”之训义界义:
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须以为恶,即欲为善,亦须自繇。……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12](P245)。
首先,严复介绍“自繇”的原意为“放诞、恣睢、无忌惮”等贬义概念,尔后便脱离贬义。认为为善为恶,皆需“自繇”,由此认定其为中性词。其次,严复从个体和集体的角度,界定“自繇”,认为个体无论“善恶”,皆出于“本身起义”,而集体“自繇”以他人之“自繇”为界。又以儒学为其古训,即以“絜矩之道”引申出道德规范。
综上所述,严复的训诂从音、义两个范畴“以见古今之异言”[14](P38),却较训诂家更为严谨广博,因借鉴了“论名、论词不论界说,则于义不全”[14](P107)的西方界说精髓,因此严复对训诂释义之词以界说为其重要补充,以求深论,并达“求全求真求微”之旨。
三、严复翻译中“训诂”与“界说”的会通方法:古今理训,中西多证
如上文所述,严复的朴学实践以训诂为主,会通界说,表征为音训和义训。一方面,因传统训诂不求深论,如“鲸、鲲、鳟、鳇非鱼也,而从鱼矣。石炭不可以名煤,汞养不可以名砂。诸如此者,不胜偻指。然此犹为中国所前有者耳”[14](P38)。另一方面,晚清西学渐入,需立译名,但受困于时局,译名往往繁芜纷杂,“智各囿于耳目之所及”[14](P38)。以至于以讹传讹,失诂、浑诂、偏诂、误诂等问题频现,如严复所述“海通以来,遐方之物,诡用异体,充牣于市”[14](P38),“几无名而不谬”[14](P38)。
1.两种情况
严复视正名为要务,一方面诉诸探寻西源,刨根问底;另一方面以古会今,释名疏正,以“训”见道,以“界”明道。“训”嵌其表,“道”裹于里。严复又根据名无可译和名有可议两种情况,区别训义。
名无可译,即西有中无之物(理),必须按本求源,如:
蛮獠相聚,如群羊耳,此以云部落,尚未叶也。盖部落虽不必为种人,亦不必不为种人,而常有其部勒者,则又非初民地位也[12](P367)。
名有可议,即中西皆有之物(理),严复则借题发挥,借中西本源阐发探微,如:
孟氏之所以云然者,盖法民革命以前,欧人旧法,国君虽暴,可废而不可诛,即有叛乱,其身可亡,而其统不可废[11](P146)。
2.四种方法
根据时空关系,严复“训诂”大致可分为古今理训和中西多证二法,继而形成四种具体方法:理古汉训、理今汉训、理古西训和理今西训。
(1)理古汉训,即以中国传统义理诠释西名。如《穆勒名学》中,严复在“论自然公例”一章中,诠释了“自然公例”后,加入案语:
此段所指之自然公例,即道家所谓道,儒先所谓理,《易》之太极,释子所谓不二法门[14](P217)。
“自然公例”在原文中被定义为“最易最简之法门,得此而世界万化,相随发现者也”,或“自然公例非他,乃极少数之公论,得此而一切世界之常然,皆可执外籀而推知之”。其中,严复紧扣“最简最易之数”这一核心概念,将传统道家之“道”、儒家之“理”、“《易》”中“太极”、释子之“不二法门”以训西学之“自然公例”。
(2)理今汉训,即以中国现有之物或义理诠释西名。如《法意》中,严复对一系列司法概念进行义训:
西人所谓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11](P10)。
本例以“礼典”义训西人之法,以“礼、刑”义训“法典”,以“《周礼》《通典》及《大清会典》《皇朝通典》”义训“劳士”,以“上谕”义训“西国议院所议定颁行令申”“中央政府立法”。
(3)理古西训,即从西学概念的传统出发,探本溯源。如:
古希腊政家之论治制也,大体分为二宗,曰独治,曰公治而已[11](P63)。
严复以西学传统为训,寻“治制”之西源,从古希腊政治家论“独治”和“公治”二宗出发,分别论述了“独治”的利弊,并从“独治”的弊端出发,以显亚里士多德所言“公治”的优势,亦说明了“公治”的缘由。
(4)理今西训,即理从西学,阐发西名当下的含义。如《法意》中,严复在介绍“沁涅特”(Senate)时,对上议院当下的概念做了义训:
沁涅特者,公治最尊之国会也,可谓政府,可谓内阁,可谓元老院,可谓上议院[11](P18)。
严复在该例中对“Senate”的各种译名进行罗列,对其性质、地位、权责及其组成成员进行介绍,较为全面地展示了“Senate”在当时的构成、功能和地位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严复的朴学实践承继孔孟以来儒家朴学传统又有所创新,皆源于严复察中西文字之异,求道术之全。在会通训诂与界说理念的引领下,严复之“训”不分畛域,以正音训声、明义辨义为范,而得法于理训古今、中西多证。因此,严复的“义训”兼有中国传统训诂和西方界说之长,打破了古今中西之藩篱,这其中的“道”与“术”值得日后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