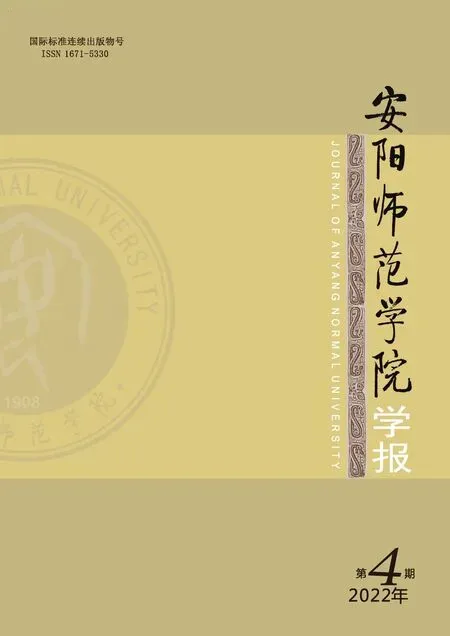五四新女性作家的母女书写
——以冯沅君、庐隐、冰心等作品为例
2022-03-18任钰镯
任钰镯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关于五四时期女作家笔下母女关系研究,学界已有相关论述,学者普遍将研究重心放在解读母亲形象上,认可五四女作家以现代女性的立场书写处于历史弱者地位的母亲形象,同时赞美母女之间真挚的情感。然而,针对母女关系问题还应该关注的是:首先,关于母女之间冲突问题的作品可以用研究“问题小说”的方式来解读。母女之间的问题是文学的母题之一,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特殊性。这些女作家敏锐地察觉到、甚至集体地提出了独属于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女性问题,那就是热烈地宣扬女性解放,是否有实质性的突破?女性是否能够走出家庭,或言之,走出家庭是否真正意味着解放?女性能否通过解读母亲认识自己?其次,五四时期女作家经常以母亲的名义书写女性,她们不直接反思女性、歌颂女性,转而以母女之间的关系、母女之间的身份转化来隐晦地表现女性的身份处境与价值追求。在为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五四女作家女性意识觉醒而欢呼的同时,又要警惕这觉醒是借“母亲”身份来言说女性。说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尚未破除传统观念的局限(将女性限制在“母性”“家庭”“牺牲”“奉献”框架中的局限)。另外,时代环境确实对人有深刻的影响。但是,在如此重视伦理关系的民族文化中,不能忽视母女之间的代际关联与女性身份言说的关系。
一、母亲的“反叛者”或新式“烈女”
冯沅君小说《隔绝》《隔绝之后》发表于1923年,小说中的女儿们因为婚恋问题与母亲产生强烈冲突。在此之前已有研究者从解读“母亲”的形象角度出发,阐释母女之间冲突的原因,“她们无法将母爱与母亲所坚持的封建父权的立场区别对待,于是陷入了要么辜负慈母,要么向父权妥协的两难境地中。”[1]最终走投无路的女儿选择自杀。由于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所导致的自杀风气并不是女作家冯沅君臆想出来的,这是新文化运动早期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市22岁的新娘赵五贞在花轿内用剃刀割断喉管,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一事件轰动全城并影响全国。赵五贞经父母包办许配给开古董店的31岁的老板吴凤林作续弦,她对此婚姻不满,多次向父母抗争遭到拒绝而走投无路,只得以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表示对封建婚姻的反抗[2]。
由于婚恋问题引发的极端性事件,揭示了当时在青年女性中盛行的自杀风气。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早期,青年女性群体中盛行这种自杀风气?
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将妇女从夫之奴隶的境遇中解放出来,还原其“人”的地位(1)1915年陈独秀《敬告青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之后翻译《妇人观》《欧洲七女杰》等。从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宣扬女性解放的努力,还处于思想传播阶段,陈独秀将西方妇女解放的观念移植到中国,这对冲击传统封建思想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也有“拿来主义”的思想倾向,他没有结合中国女性所面临的实际性问题而进行深刻的思想剖析,他对女性解放的阐释是为“人”解放观念而服务的。之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等在《新青年》探讨女贞、女性工作、教育等具体问题(2)《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女性问题的文章:陈独秀《一九一六》(1916)、陈钱爱琛《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1917)、梁华兰《女子教育》(1917)、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1917)、高曼《结婚与恋爱》(1917)、郑佩昂《说青年早婚之害》(1917)、 胡适《贞操问题》(1918)、唐俟《我之节烈观》(1918)、夬庵《一个贞烈的女孩子》(1920)、陶履恭《女子问题》、陈独秀《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1920)等。。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女性解放问题仅限于新旧思想交锋,知识分子理论讨论的层次,放眼于民国初建时期的历史状况,这只是其中一种社会舆论,关于女性解放具体的实施策略尚未生成。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才颁布相应法律,而传统思维与社会结构的改变则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于是,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第一批走出旧家庭的“娜拉”,作家笔下的“女性死者”成为了新旧思想博弈过程中的“试验品”甚至是“牺牲品”。也就是说,在这场文化运动的早期,有一种惯性的波动征兆:社会舆论与新思想的传播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这与思想解放所要求达到的社会发展高度相比,显然是错位的。舆论的力量没有动摇根本的社会结构,这就缺乏解放所需要的社会物质和制度准备。“如我们所料,受难者是烈妇们——平添了一种新的混乱:解放和妇女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妇女,而社会结构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于是这些发现自己找不到具体的手段去实现自身的解放,发现自己遭到周围人的无谓反对,于是失望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3](P101-102)。回溯到前文提出的自杀风气问题,以及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中国妇女问题,不论赵五贞还是冯沅君笔下的人物,从行为看,她们是母亲的反叛者,在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力的情况下,精神上不能自我肯定的状态下,她们对旧思想的反抗仍然是无效的,借死神来解决问题仿佛回到了为爱殉情的古典反抗方式以及“节烈”的思维模式。这种自杀的“女性死者”与其说是母亲的反叛者不如说是一种新式“烈女”。
由于婚恋问题所引发的母女之间的冲突和极端性自杀事件,反映出这些青年女性受女性解放思想影响,认为自由恋爱是女性反抗父权的唯一途径。不能成功便以身殉情或者“节烈”。加上社会结构的固化,使遇到旧家庭的阻碍,没有物质保障,精神尚且不能独立的女儿们,在反抗之时“激增的紧张破坏了一个人的(思想)平衡”[3](P101),她们的生命走向了毁灭然而并未看到新生,“一旦她们离开父子对立的特定语境面对自己,便会发现,所谓女人仅仅是有史以来那个被奴役、被统治者——弱势群体”[4](P21),也说明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女人仍然有一种弱者的自觉,以死亡与毁灭的方式与暴力抗争。即便是顺从女性解放的思想潮流,也难以从本质上改变女性的集体无意识,难以逃离现实困境和历史处境。
总之,由新旧观念的冲突所引发的母女之间的冲突,昭示出五四女青年欲反抗父权却又依恋母亲、走不出旧家庭的矛盾心理,呈现出五四时期女儿们在新旧观念之间,在家庭的牵绊与实现自我之间的痛苦与挣扎。
二、被建构的“母爱”与女儿自我的救赎
前文谈及母女之间的激烈冲突问题,那么针对母女关系书写的第二个问题是母女之间的联结问题。母女之间天然情感联结对女儿也就是青年女性的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以冰心为代表的女作家不直接讴歌女性,转而以感恩和赞美母爱的方式来隐晦地表达出来,那么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女作家们常常借母爱的名义来言说女性呢?又是如何书写的呢?
冰心早期的诗歌反映母女之爱,亲子之爱的主题更多,在她笔下的世界里母女之间的情感和谐而自然,几乎没有冲突。这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女作家作品中是独树一帜的。她笔下的母女亲情更多表现的是女儿对母亲的倾诉,女儿对母亲的想象。在诗歌当中母亲对女儿的态度显然处于被遮蔽状态,缺少了这一环节的母亲形象、或言之母爱地表达便不是完整的,真实的,而是被建构的。冰心在诗歌当中营造了一种“母爱”的乌托邦,即由女儿来诉说母爱,以母爱来建构女性。这种“被建构的母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它展现出女性第一次冲出历史阐释的罅隙,以女性的视角言说母亲,将女性爱与美的精神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值得反思的是这种“被建构的母爱”是由女儿想象出来的,与其说是想象不如说是一种心理需求。在新旧观念交替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外部的危机,女儿更渴望保持一种在母爱的温暖中生长的状态,躲避现实的困苦,获得情感与精神的宽慰。诚如戴锦华所言她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女儿”[4](P71),离不开母亲便难以离开家庭真正独面社会,更不会触及两性之间的关系。那么“长不大的女儿”则是处在幼年中的“静态的女儿”,而非从女儿过渡到女性的动态表达。这也是冰心早期创作略显局限的一面。另外,她将母亲限制在“母爱”的情感属性当中,那么母亲的形象便是单一的。以母爱来言说女性,仍然没有走出传统观念将女性锁定在母性、家庭、牺牲、奉献的框架中,对女性的认识与理解仍然是有局限的。
将庐隐与冰心对比,庐隐在小说中影射自己的身世经历,在她的作品中女儿与母亲冲突不断,母亲甚至有自私、愚蠢的一面。然而,仔细分析《庐隐自传》会发现她反复言说母女之间的关系,一个对母亲失望的女儿,也在诉说与母亲之间割舍不断的爱,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儿对母爱的渴望,以及有限的母爱所给予她的精神慰籍。《庐隐自传》中母亲临去世前展现出慈母的一面“母亲脸上露出不忍离别的热情,和声说到:‘差五六天就到新年了,你一去不是不能在家过年了吗’”[5](P56)。母亲去世之后,“在儿时我虽不被母亲所爱,但是几年以后,为了我的努力,母亲渐渐对我慈和,同时我是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所以对母亲仍然有着极深的眷恋”[5](P56)。庐隐没有理性地认识到,她与母亲之间不和是因新旧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裂隙。她认为母亲的态度逐渐和缓是因自己的努力获取的,她出于情感的角度所讲述的“母爱”,显然也是被建构的。她认为这种骨肉亲情需要她用后天的努力去获得,以抚平她幼年时遗留的心灵创伤,“她既不会对母亲进行批判,也不会在母亲面前屈服,只是通过在母亲面前展现自己努力的成果来接近母亲,借此来降低对母亲的恨意也只是她在不知不觉中寻找到的一种自我精神救赎的方法。”[6](P56)
由于二人身世经历的差异,庐隐与冰心笔下“被建构的母爱”有不同之处。冰心笔下母亲对女儿的爱是与生俱来的,而庐隐相反,母亲的爱是她后天努力所获得的。显然,冰心将母爱上升到爱的哲学层次,这种爱在无形当中化为了与父权抗争的精神动力,这种爱的救赎是敞开式的,对女儿的成长有积极的价值;而庐隐笔下后天努力获得的母爱、不完整的母爱反而成为了她一生的痛,希望以孝的方式去弥补心灵创伤,以寻求精神救赎。前者因爱的救赎获得了精神的圆满,而后者一生都会处于一种爱的匮乏与寻求的状态。
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女作家常借母爱来书写女性的情感体验,因女作家的身世经历,性格特点不同,她们笔下“被建构的母爱”被赋予了多重的、更深刻的时代精神内涵,一方面,以女性经验书写母亲,将母女之间隐秘的情感体验公之于众,展现了一个非男性的世界。在一个女性解放没有取得实质性进步的时代,她们将爱的哲学本身作为女性区别于男性的、立身于历史的文化依据,这是女作家的突出贡献。而另一方面,以母爱的名义言说女性,还是停留在精神层面,难以摘掉社会制度所赋予的“母性”的假面。女性的真实出路还需要后代作家继续探索。
三、母女之间代际关联与女性身份言说
女作家笔下的女儿们虽然受女性解放思潮影响,但母女之间天然的代际关联,往往是母女冲突与联结的源泉。那么母女之间的代际关联是如何影响女性身份言说的?
母女之间的代际关联,即从女儿到母亲,是天然的生命代序,也是女性集体无意识的传承。实际上,它更为复杂。这与女性身体的特殊性、社会分工结构赋予女性的性别职能以及两性文化价值符号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女性从呱呱坠地的一刻起,便延续着前代女性的肉体生命、社会职能与文化符号。正因如此,女儿既是母亲的复制品,又是母女共同体。“在妇女身上一直保持生产别人同时又产自别人的力量,在她身上有母体和扶育者;她自己既像母亲又像孩子一样,是给予者,她是他自己的姐妹加女儿”[7](P2)。然而,父权体系的“聪明之处”在于利用了女性“代际关联”的特殊性,把代际的关联与传统文化结构联合,将女性钳制在崇尚“生育职能”的父权体系当中,女性注定成为母亲,并将这一职能无限复制下去。周而复始形成了女性的集体无意识。这种受代际关联影响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女性一直有弱者的自觉和维持家庭、哺育子女的职能。它一直影响着女性的身份言说。
结合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历史情景。一方面,相较于父子主体间的冲突来讲,处于弱者地位的母女联结性更强。缺乏主体性的母女以互相依赖的方式结成了弱者同盟,即便是宣扬种种女性解放思想也难以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女作家借母亲的角色言说女性的精神极乐与精神负担。
苏雪林《棘心》中的女儿看到母亲亲手安置的家后感慨到“这才使我们的脑海里浮上一个清晰的‘家’的概念,这些都是母亲隔日为我们安排好的”。女儿对家庭的认知、与周围其他人的关联,乃至对家以外社会理解,都来依赖于母亲。冰心更是将母女共同体“神圣化”。“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明月的大海里”[8](P86)。从诗歌结构上看,大海里的小船,小船中的母亲,以及母亲怀里的我,一代孕育着一代,形成母女之间代际相传的时空象喻。冰心诗歌中常现女儿在母亲怀里躲避风雨的意象,这是母女共同体意识的自觉表达,也显现出女儿对母亲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引向积极的方向,便使女儿敢于面对自己,走向社会人生。但往往会参杂消极的影响。比如庐隐笔下的纫青,苏雪林笔下的醒秋,因婚恋问题与母亲发生冲突,一个想要自残,一个想要母亲早点去世。女儿难以走出母亲的影子,母亲也不能控制自己的占有欲,更有甚者对女儿百般挑剔又恶语相加。这不能不使接受新思想的女儿产生警惕与抵触,想要并摆脱母亲的束缚,于是冲突便引发了。甚至母女之间相互憎恨,性格与心理扭曲,衍生出种种病态的母女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母女身份的转换,女儿在家庭生活中不知不觉复制了母亲的职能。走出旧家庭的“娜拉”来到丈夫的家庭却依然重复母亲的角色,那么还算是新女性吗?庐隐《海滨故人》中,宗莹取得了自由恋爱的胜利,走进了丈夫的家庭,然而还是堕入了世俗的圈子,新女性与旧女性无异。这说明即便社会思想松动,在男性主导的文化结构中,女性承担的职能与性别符号都难以动摇。
与女作家敏感于母女代际关联引发女性问题不同,男作家也注意到了青春女性的陨落,但鲁迅与老舍反思的是社会与家庭对女性的压抑。那么,女作家创作的价值在于透过社会的表像,权利与欲望的网罗,揭露以前由男性遮蔽的女性隐秘经验。从根底的文化结构和女性心理反思女性,即便有种种的解放运动,也难以根除千百年来生长于文化体制中的集体无意识,以及母女之间由代际关联引发的矛盾冲突。这二者是伴随女性一生的文化与精神枷锁。
四、结论
本文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史料结合,重新阐释文本,探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女作家笔下的母女关系问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冯沅君、庐隐、冰心、苏雪林、陈衡哲、凌叔华、石评梅等女作家敏感于新旧观念交替之际女性的现实困境,借书写母亲来认识自己,形成一代文学的主题。鲁迅曾以“历史的中间物”来形容五四这一代人,这是空前解放的一代,也是最迷茫的一代。走出旧家庭的“娜拉”,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碰撞中,演绎一幕幕人生悲剧。女性对自身幸福的追寻以及精神成长之路的血泪教训,说明这些女性还不具备新女性的素质,女性意识还尚未成熟。从女儿到女人的心路,仍需后代女性继续书写。
母女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冲突与联结”的方式来解读,但联结与冲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说明母女之间的关系实则更为复杂,冲突中有联结,联结中又突显冲突。越是理解就越是抵触,越是抵触反而越是紧密。女儿如同复制了母亲的人生,如此的相似又如此的不同,那么女性到底是谁?是母亲还是自己?这是借母亲书写女性最核心的问题。只有女性深入审视母亲,探究女性的隐秘经验,真正认识母亲,才能重新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