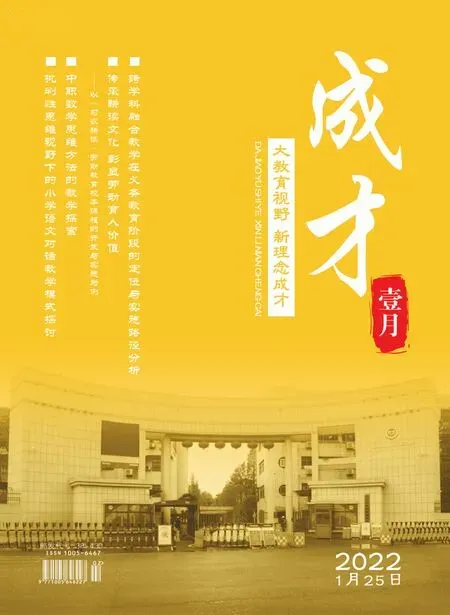高校劳动育人获得感的内涵与生成
2022-03-18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钱 玲
一、劳动育人获得感的内涵
劳动育人获得感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界定。借鉴劳动教育与获得感的相关研究,可以深化对该概念的认识。
(一)劳动教育的历史脉络与时代内涵
劳动与教育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劳动观均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劳动教育的过程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二是教育与劳动实践的结合。苏联教育思想家苏霍姆林斯基主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有机结合,注重创造良好的劳动教育环境,提倡劳动实践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方针的更迭,呈现出与时代特征结合的劳动形态(孙会平等,2020),从“工具理性”逐渐走向“价值理性”,经历了五个时期的劳动教育的理念导向和实践形态的转变:借助苏联模式,初步建构系统的生产劳动技术教育体系;绝对去西方化时期,拔高劳动教育的政治意义;探索自身路径时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逐步开辟中国模式,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成有信,1982);随着时代的变革,新时代下的劳动教育被赋予了“以劳动托起中国梦”的崇高地位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目标指向,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更强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价值”(陈理宣等,2017)。目前关于劳动育人要素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劳动认知类、劳动情感类、劳动行为类要素。劳动育人的本质是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统一,包含劳动价值观和劳动素养养成。劳动价值观是所有教育内容中最核心、最深层的要素(陈好敏等,2020)。
(二)获得感的内涵
学术界对“获得感”一词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目前尚无一致性的定义。当前思政课教育改革以学生的获得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王玉荣(2019)指出获得感是指对“客观获得”的主观感受,黄冬霞(2017)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的深度融合的主张。阎国华(2018)认为高校思政课的获得感主要源于知识及信仰的实际获得和积极的主观体验。现有的研究,把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落脚在“得”和“感”上。梅运彬等(2018)提出只有准确把握大学生的发展需求和期待,才是提升获得感的关键。国外尚无“获得感”的概念,与之相近的是“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特拉(1997)认为幸福感是个体从主观感受出发,依据自定的标准对整体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所作出的总体评价,是个体一种独特的心理感受。D.M.约翰逊(1978)最早提出“生活满意度”的概念: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和认知评价。之后,学者一直沿用和采纳约翰逊提出的生活满意度的定义。“获得感”的提出,既是对“满意度”进一步的深化,也是将“幸福感”具体化和实际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劳动育人获得感定义为教育对象在参与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中因心理和行为上的收获体验而产生的积极正向主观感受。心理层面获得感包括以下几点:
(1)认知层面:大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包括大学生劳动观念、劳动认知,树立正确思想认识、形成价值认同,这是大学生劳动育人获得感的起点和基础。
(2)情感层面:大学生对劳动实践、劳动事迹的情感、态度体验。
(3)意志层面:大学生自觉地确定目的,调节支配自身的行动,克服困难,去实现预定劳动目标。行为层面获得感包括:大学生劳动行为、习惯、能力,通过劳动行为实现大学生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
二、劳动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实践路径研究
李珂等(2008)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党中央在理念上对劳动教育的方针定位进行了慎重的调整,在实践中加强了劳动教育的系统化建构,加大了推进力度,但受各种内外部因素影响,劳动教育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新时代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大中小学学生的劳动教育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青少年的劳动教育现状不容乐观。劳动教育缺乏良性运行的长效机制。实践路径研究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劳动教育内在价值的培养研究。周婕等(2019)指出劳动教育存在边缘化、狭隘化、形式化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劳动观念的缺失。刘向兵(2018)认为加强劳动教育,就要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李珂等(2008)以劳动教育的生命之树为喻,构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劳动教育体系。毕文健等(2020)提出劳动教育植入乐学思想。
第二,劳动教育与各领域的融合研究。贾鲁音(2012)从就业的视角对学生劳动教育路径进行了研究,劳动教育与现行的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课程或创业基础课程、创新活动进行融合。把劳动教育融入高校教育教学各环节: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健体、以劳塑美(徐长发,2018;孙会平等,2020;郭长义,2019)。
第三,新形态劳动教育的构建研究。檀传宝(2018)指出当代社会劳动形态不仅包含更多脑力劳动,许多复合的崭新的劳动形态,特别是存在于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领域的新兴劳动形态正不断涌现,需要构建适应新时代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以及生活生产方式特征的一体化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三、劳动育人获得感的生成路径
(一)劳动价值观培育中自我价值感的生成
当前,学校劳动教育存在被淡化、弱化的趋势,少数大学生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呈现出劳动价值观的缺失。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的内涵,即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新时代劳动育人的核心在于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即确立正确的劳动观点、积极的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等(陈好敏,2020)。劳动价值观只有与个人价值相互融入,从过去注重工具性价值的劳动教育向具有综合性、独有性价值的劳动教育转变,才能真正取得培育的实效。自我价值感是指对自身价值的体验和判断,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以对社会的贡献为基础,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从马克思的劳动思想维度出发,劳动育人与立德树人的共同价值归宿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价值及意义,其根本目的是要确保人获得一种自我存在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从而实现对“全面发展的人”的塑造。基于培养全面发展人的目标,通过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认劳动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从职业体验与公益劳动等角度实现其自我价值,转化成劳动信仰和信心。
(二)劳动实践中个人积极主观体验的激发
青年群体本身具有冲动、情绪化的特点,运用非理性因素,引发情绪共振和共情体验是激发积极主观体验的有效路径。一是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激发:马卡连柯指出创造性劳动和集体劳动是让劳动获得教育意义的重要条件。创造性劳动体现了个体的个性和才能,个体在集体劳动中收获和他人的关系。在集体劳动关系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二是期望满足感的激发:研究表明,获得感来源于需求与预期的满足,遵循“期望—参与—满足—认同”的生成路径。由此,引入“以生为本”教育理念,将大学生的角色界定为主体角色,充分认识大学生劳动实践活动中的感性需求,激发学生劳动的内在需求和动力,同时建立劳动育人评价机制也是激励的重要途径,满足学生对目标的追求期待。三是愉悦情绪的激发。“00后”大学生具有更强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性,更加注重感性体验(李焱等2019)。以感人的劳动人物、动人的劳动故事、触动的劳动实践体验,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感染、激励和引导受教育者自觉仿效正面典型。
(三)劳动素养培育中自我发展的实现
劳动素养,即形成劳动习惯、有一定劳动知识与技能、有能力开展创造性劳动等。自我发展指个体不断更新,进步变化的过程。通过组织化的劳动与全面发展教育相结合的劳动、创造性的劳动以及多方合作劳动来开展劳动教育,在劳动素养培育中实现自我发展。构建“家校社”一体化劳动共育生态。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在劳动育人过程中的参与机制和互动机制,真正落实日常生活劳动教育、生产性劳动教育和服务性劳动教育三大任务,形成“渐进式、交互式”的一体化劳动共育生态。家庭生活劳动教育:家庭生活劳动重在习惯的养成。在传统的家务劳动基础上,融入野外生存劳动、家装劳动等更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活动,提高学生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学校劳动教育:随着劳动新形态的出现,特别是随着新技术、新方法、新知识和新工艺在劳动中的广泛应用。紧密结合产业新业态、劳动新形态,灵活多样的设计劳动育人的方法和内容。围绕创新创业开展实习实训、专业服务、社会实践、勤工俭学等活动,精心设计项目载体。例如,通过完成问题导向的项目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劳动教育:研究在重大疫情、灾害面前,如何引导学生主动作为,参与公共服务,培养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