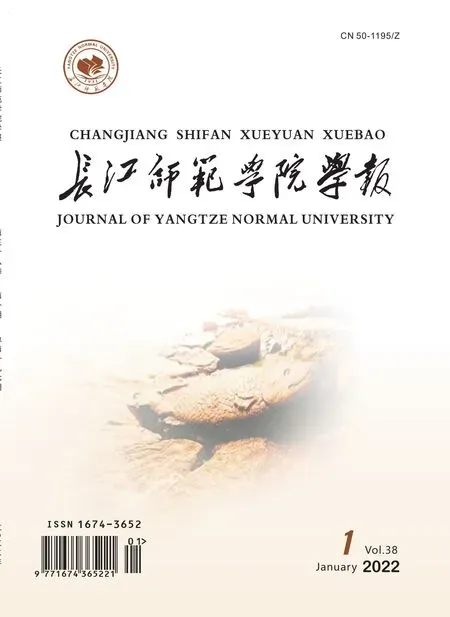灵魂不灭:排瑶人灵观的死亡人类学解读
2022-03-17周靖凯
周靖凯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一、引言
古今中外,死亡往往伴随着一定的仪式。人类学对于死亡的关注成型于赫兹(Hertz)有关“二次葬”的研究[1]。赫兹认为死亡仪式(殉葬仪式)在原始民族中是普遍存在的。不论个人还是社会,都致力于在情感维度接受某种“善终”(Good Death),在这期间,仪式就充当了转换器的作用,将难以接受的死亡转变为可以接受的道别。在仪式的展演中交织着个体有关死亡的情绪、感知、记忆与肉身的触觉,也是社会象征秩序构建的载体,其本身也处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之中。在有关死亡的人类学研究中,仪式,或言葬礼,成为其关注的核心议题。“葬礼”所关联的丰富的理论源流,使其可以连通两个看似遥远的领域:一方面是对微观且多样的个体情绪感知的解读。另一方面是宏观的社会结构下的集体表征。
本文所记述案例属遭遇研究。我在2020年11月前往广东省连南县油岭村,进行有关当地排瑶“歌堂”文化的田野调查,却遭遇了排瑶族民的“安堂”葬礼。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会首先解释排瑶的人灵观,引出排瑶观念中独特的灵与肉的关联,借着葬礼中展示的仪式行为,解释“灵魂不灭”的观念,分析死亡如何勾连着个体以及其与社会集体表征的意涵。
二、人与“缅”:排瑶的人灵观
瑶族是中国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我国56个民族中人口数居第13位,并且分布十分广泛,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地的山岳地带。瑶族同胞由于在历史上频繁迁徙,大分散,小聚居,以及与周围民族不断互动,形成了多个不同的支系,出现了细微的文化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瑶族分支。八排瑶属瑶族的一个独特的分支,集中分布在广东省西北部的连南瑶族自治县,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八排瑶独特的文化信仰。
传统的排瑶信仰属万物有灵观。早期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科学观念匮乏,人们对未知的自然的解释归因于神秘的灵力。世间万物皆有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灵力与意志,也就是西方所称的玛纳观(Mana)。人类与其他玛纳都是世间的一部分,族人不可随便触及或干扰其他玛纳,并且这种灵力有持续存在的能力,不随着肉体(物理性质)的消亡而消逝。排瑶认为,无论肉体生或死,人类身上的灵魂永不灭。我国早期对于排瑶的人灵观研究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为出发点,依据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原始社会民族存在“灵魂不灭”进行分析[2],将此种人灵观视作原始民族发展相对落后的表现[3-5]。
灵魂不灭的人灵观形成了瑶民对祖先以及灵魂的崇拜。瑶民认为,当人死后,附着在肉身上的灵魂将离开,变成“鬼”,瑶语称之为“缅”[mian]24。其实用“鬼”来代指瑶民的“缅”是不准确的。一般而言,“鬼”所指皆是作恶、捣乱或者恐吓的意涵,与“神”是作为反向的对立概念。然而在排瑶的观念中,“缅”并不对“鬼”与“神”或“仙”作出明确的划分,而是他们的统称。江应樑指出:“在任何多神教或一神教的民族中,神与鬼的划分都是很严格的,普遍认为神是有权威的,应受人敬奉的,而鬼则是漂泊的,生人只应避而远之的,且神皆为统治者而鬼则为被统治者,两者不容混杂,但瑶人对于神与鬼的观念,却似乎不是很清楚。[6]”故与其说排瑶存在人鬼观、鬼神观,不如称之为“人灵观”。
排瑶的“缅”无神鬼之分,但有善恶和大小两种维度的划分。这种划分与人生前的造化以及是否遭遇横祸有关。一般而言,生前经常做好事,有助于村民的人死后会转化为善灵,而生前无恶不作、破坏村内和谐的村民死后则变为恶灵。此外,有些人尽管生前多行善事,可并非正常死亡,而是遭遇横祸,其灵可能饱含怨气,便会变成恶灵作祟。大“缅”则是指瑶民的祖先神,如盘王,或者生前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做了大事,令人铭记之人,其中有善灵也有恶灵。小“缅”则是各房分支的祖先公,或者其他影响力相对较小者的灵。
丧葬仪式是打开阴阳与人灵界限的转换器。排瑶十分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在其特有的人灵观之下,族民的种种重大节日、盖房乔迁、生老婚丧仪式都需要进行仪式的展演,解开人与先灵之间的界限,与彼岸产生联系,让祖先也参与到仪式之中。死亡仪式(葬礼)在人灵转换中有其独特性。除了死亡仪式,排瑶其他仪式多是打开人灵的界限,邀请先灵返回阳间,最后再将其送回阴界,是一种开放纳“缅”的过程,如婚姻仪式是为了让先人认识新加入家族的女性,乔迁仪式则是让先人识得新的神堂,熟悉新家。而死亡仪式是个特殊的存在,整个过程主要是“送”,是一个从社会中排除逝者到“缅”的过程。换言之,死亡仪式是使身边刚刚去世的族人完成从阳向阴的彻底转变。
三、“灵魂不灭”:排瑶的死亡认知与丧葬仪式
对人类文明而言,一个人身体机能的停止并不是真正的死亡,不同的文明对死亡有不同的定义。排瑶认为:于个体而言,死亡是指“缅”离开消逝的肉身;于社会而言,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善终”不仅包含生者对逝者肉体(尸体)的妥善处理,尸体如何安放,有关逝者的记忆如何被重塑更是重中之重[7]。逝者在断气瞬间,灵魂离开肉体,与生者产生互动。生者在埋葬逝者之前要做各种准备,与逝者的灵魂道别。死亡仪式的意义在于让人的死亡从个体的身体走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别离。Hallam和Hockey认为死亡仪式的意义是“记忆塑造”(figuring memory):体现物质性死亡如何超脱于身体(body,或者说“尸体”),引发人群间集体纪念活动[8]。
(一)“缅”与肉:排瑶的死亡认知
排瑶相信死亡只是肉体的消失,灵魂与之分离却永不消逝。瑶民语:“人死黄泉不转生,人生死去难扶起。”灵魂脱离身体不会进入生死轮回的体系,而是永远存在,并且可能附着在其他人的身体上,可能行善,也可能作恶。为此,瑶民需要妥善处理逝者的灵魂。
瑶民不对“缅”作出神鬼划分,人与“缅”可以和睦相处,并且“缅”也像阳间的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在阴界也有自己的衣食住行,也会在彼岸生产与劳作。因而,瑶民在给逝者的陪葬品中会有逝者生前穿过的衣服和鞋子,并且会附上一些种子,让逝者在彼岸继续耕作与生产。由于两个世界是彼此稳定且和谐的体系,一般瑶民面对尸体(正常死亡)不会产生特定的恐惧,尸体(逝者)不一定就变为恶灵。面对不同的逝者,有不同的处理身体(尸体)的方式。
死亡仪式的开展与逝者的“缅”密切相关。死亡仪式的开展是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人与“缅”之间的互动。前文所述的“灵魂不灭”是对已经具有“缅”的人而言,“缅”是人生前“气”的凝聚,个体在不断累积的过程中体现所具有的灵力。刚刚出生未满月的婴儿,因尚未完全形成人样,灵力还未凝聚,因此不会形成“缅”,所以婴儿死后不会举行正式的死亡仪式,只会将尸体埋葬在产妇的床下,意图留住胎气,引导下一任婴儿的到来。一岁左右的婴儿初具人形,但在死亡后因灵力不足依旧无“缅”。在排瑶看来,未经历过成年礼的儿童(一般为男9岁,女12岁),其灵力尚未凝聚,不会形成“缅”,因而不需要举行正式的葬礼,只需对尸体进行简单的沐浴梳洗,换上干净的衣服,以白布裹起,埋葬于山冈之中。
(二)与“缅”道别:排瑶的丧葬仪式
排瑶有自己独特的殉葬文化,逝者要经历两次葬礼。赫兹认为“二次葬”普遍存在,具有体现社会集体表征的意涵。[1]排瑶文化中,第一次入土是将刚刚辞世的逝者的肉身立马埋葬起来,并不做烦琐的法事,仅仅是“安身”。第二次入土是将逝者从阳间排除出去,让其融入阴界的生活,可称之为“安魂”。瑶民将前者称为“假葬”,将后者称为“真葬”。可见,对于一个人来说,“缅”比起肉身更加重要,主宰着瑶民对生命的认识。在假葬中,排瑶存在特殊的“坐尸”习俗,其依旧与灵魂不灭相关;而真葬,称为“安堂礼”,也是为了处理无处安放的不灭亡灵。“灵魂不灭”观从接下来的葬礼实录可得以窥见。
1.假葬:坐尸礼
瑶民信奉灵魂不灭,逝者的“缅”要进入阴府继续生活。在那里,逝者宛如重生,同样要耕田种地和婚育,开启新的生活。因此葬礼上处理逝者身体时要将其以活体姿势呈现。排瑶文化将尸体以“坐尸”的形态放置,仿佛逝者依旧活生生地坐在座椅上。民族考古学资料显示,对于尸体进行活体拟制的丧葬习俗并不罕见,“坐尸”的形态包括蹲坐式、屈卧式等[9-10]。这种对尸体姿态的特殊处置,其用意为希望逝者保持在世的姿态,在阴间可以按照生前的方式生活,灵在阴间得以安抚,不会返回阳间作祟。
在排瑶文化里,当人断气时,便立即把逝者挪到床沿,将背后垫起,双腿下垂,作安坐状,以便出殡时易于放在“灵轿”(一种专供抬死人用的靠背木椅)之上。然后,逝者家属将情况报告给舅家。做好一切丧事准备后,便鸣三响火铳报丧。
听到报丧声后,族人们自觉前来帮忙料理后事。用温水为逝者净身的人,从中得到主家放在洗澡水里的硬币(当地称为“洗屎钱”)。洗好后,再为逝者穿上寿衣和寿裤,还有新鞋新袜,在头上佩戴画有神像的纸质“相冠”。每位帮忙给逝者穿衣戴帽的亲属或者乡亲会得到一件新衣服作为犒劳。穿戴整齐后,人们将逝者搬到木制的“仙椅”上,用红布及草绳固定成坐姿,逝者儿女往逝者嘴里塞进一枚硬币,称作“断命钱”。紧接着,人们将端坐在“仙椅”上的逝者移到房屋的一角,接受亲戚和左邻右舍的吊唁。
出殡时,由舅家人把逝者抬出家门,年轻力壮的后生将绑在“仙椅”上的逝者用手抬至“扎杠”(把树条绑在仙椅上以便抬)的地方。扎好杠后,在逝者头顶安置,或者由他人撑起一把黑色油纸伞,以防止逝者面露青天。“仙椅”由儿孙抬前面,女婿抬后面,在长子、先生公以及手持竹幡的女儿们引领下走向埋葬地点,队伍宛如“过九州”。
一路上,甚至在下葬以前,都严令禁止前面领路的子嗣回头看死去的亲人。如果回头看了,逝者的“缅”就会萌动,留恋家人,可能留在阳间,回家折腾在世的亲人。最后,由儿子背逝者进入墓地,然后撒上尘土,意味着初葬结束。
2.真葬:安堂礼
排瑶对于逝者的身体与灵的态度十分复杂。油岭瑶民认为,把逝者抬上山埋葬,只不过是为了防腐防臭,不让生者难为情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称为“假葬”。“安堂”这天才算是逝者真正的下葬之日,也是新坟正式使用的日子,意为禀报逝者新房已经建造完毕,可以安家落户。
在逝者入土后的第三日,亲戚邀请先生公,对照几本经书择日进行安堂礼,避开与逝者生辰八字相悖相杀的“大拜”“收死”“红杀”“罗阎时”等日子及时辰,择取与逝者生辰八字相生相宜的吉日吉时,于葬后的第七天,即建造新坟前的最后一日,由同房老者在坟地当众宣布。
按照先生公择定的吉日吉时,坟主家属将饭菜和酒肉提前送到坟地。亲友也来到坟地给逝者上香,敬奉猪肉、米饭、酒、纸钱等物品。
三声土铳炮过后,先生公走到坟前插上两炷香,摆上一碗肉、一碗酒、一碗水和一叠纸钱,为新坟“收耗”以禀明逝者。然后端起一碗水,边念诵经书“平神煞”,边“呸、呸、呸”地口吐生水,以驱逐外家的恶鬼。接着,先生公念诵“解神煞”,以清除一切障碍,为逝者平安通往“天堂”铺平道路。其后,先生公轮换到坟前坟后,举行“下契”和“下葬”仪式,坟主将锄头及一吊纸钱交给先生公,两人行半跪礼互拜三拜。之后,先生公边念诵瑶经,边在坟的前后各挖一个小坑,埋入“旺滕”(瑶民用于代替粉香的一种树藤),高呼一声后,抓起泥土往空中抛出,这时,男女老少聚在坟的四周,张开衣襟接泥土,随着先生公的吟诵又将泥土倒在坟上,意为众人挑来新土为逝者“造坟”建屋。
造坟后,先生公将纸钱分别放在两个小坑里。祭祀时,女性分为嫁入团(受妻团,包括媳妇、儿媳等)和嫁出团(给妻团,包括女儿、姑姑等)分别在前后两个小坑内送饭。嫁入团的女性着传统民族服饰的盛装的红色头饰;嫁出团则着平装,带深色发捆,这划分出了不同女性群体的身份。此外还要宰杀公鸡祭祖,先生公口念“阳人得阳钱,阴人得阴钱”等咒语焚烧纸钱,用锄头把小洞耙平,再与坟主行半跪礼,先生公把锄头交还给主家,而这时主家则把“香钱”(约120元)交给先生公。接下来又在坟前进行“安公”,杀鸡祭祖,将鸡血滴在孝男孝女们奉送在坟前的纸钱上。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在坟后进行“安龙”,即摆正神位接好龙脉。至此,“安堂”完毕。“安堂”后,众人燃放鞭炮,然后在坟前坟后喝酒聚餐,让阴阳两界共同悼念逝者。
四、死亡:从个体走向集体表征
回到本文的开篇,通过回顾排瑶的葬礼,本文尝试作出死亡人类学的解读。如果逝者的尸体应该被分解,对于逝者记忆的抹除或重塑,理解尸体如何埋葬则至关重要。
(一)如何处理死亡:“尸体就在那里”
排瑶文化中,逝者要立马入葬,以防止尸体腐烂,以及避免亲属产生悲伤的情感。身体物理性质的消亡不可避免,同时在文化上,附着“缅”的尸体也是瑶民难以面对的存在。Verdery 强调“尸体就在那里”(indisputably there)[11]27,它们的存在就是沉重的象征(heavy symbol)[11]32。尸体就在那里,“缅”则处于阴与阳两个世界的边界,由于尚未进行正式的仪式,灵魂无法进入阴间,然而留在阳间则会被视作纠缠不清的客人,会给族人带来麻烦。尸体这种模糊的状态会给生者施加一种既恐惧又怜悯的复杂情感。因此,瑶民选择立马入葬,先将模糊之物从物理空间上移除,之后再举行仪式,从社会层面进行人“缅”告别。
人类学有关“尸体”(body)研究的核心词是腐烂(corpse)。人们如何理解尸体腐烂、如何应对腐烂是人类学关注的重中之重。腐烂带来的是原本身体彻底的转变,在生物学看来,是一种从有机物向无机物分解的过程;从文化角度解读,则是人形的消逝,使人转变为非人的状态的过程。人类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转变体现着民族独特的生死观与对世界的理解。
“二次葬”是应对尸体“腐烂”的产物。这种特殊的殉葬仪式脱身于不同的死亡理解。这种特殊的殉葬礼节并非个别民族所特有,而是广泛存在的[1]17-18。这种仪式的内核是要处理身体的不稳定状态——腐烂。道格拉斯为我们描绘的洁净与危险的世界,依托于稳定的秩序边界[12];而不断腐烂的尸体则呈现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在不断分解、消逝,呈现出一种危险的性质。
许多民族研究资料表明,二次葬的初次与第二次的间隔便是要将肉身不断恶化的状态剔除,提取纯净的灵魂[1]。换言之,就是要待肉体(fresh)完全腐烂,不再散发腐臭,留下干瘪的白骨,呈现出一种稳定的状态,这样才可以达成灵魂从此世到彼岸的转移。换言之,彻底的腐烂标志着更多洁净,更少危险。
(二)灵魂何以延续:集体表征的转换
排瑶安堂礼的展演是为了安抚不灭的灵魂,死亡仪式的举行致力于生命完成某种延续。排瑶独特的人灵观下,倘若“缅”未能得到很好的安置,便会干扰人的阳间生活。逝者入土后并不能马上适应新的生活,他可能还会返回阳间来觅食。因此,刚刚入土的逝者的女性亲属要连续给他送一周饭,善待他的“缅”。并且在初葬三年内,每年族人还要不断地重返墓地,去给逝者送饭。这是生者向逝者表达挂念,安抚在彼岸的逝者,让其可以安稳地生活下去。
死亡仪式的开展是为了强调生与死的界限,划分人与“缅”的差异,形塑集体表征层面的死亡。墓地之所以成为墓地,不是因为其物理构造,而是在于特定的纪念仪式与其背后的社会记忆。传统的瑶族墓地里埋葬的是逝者确切的肉身,而肉体会随时间消逝,即墓地之下可能并不存在某一个体。在火葬推广后,肉身并不一定可以得到保留,因而瑶民在举行“坐尸”时可能要用稻草人代替肉身,墓地之下埋葬的甚至没有实际的尸体(肉身),只有骨灰。不过人们还是会前往特定的地点聚集,进行纪念。因此,瑶民纪念的不是某一个体的肉身(尸体),而是社会中集体记忆里的某个人,以及贯穿此人生死的“缅”。
举办葬礼是为了记住逝者,更是为了忘记逝者。个体机能的停止是生物人的死亡,社会集体记忆的转变是社会人的“死亡”。在死亡仪式的种种习俗中,逝者的灵魂虽然不灭,阳间的人尽量将逝者包装为活人姿态,如“坐尸”、以作物种子陪葬、祭祀时送饭的习俗,但种种习俗背后所传达的意涵却是阴与阳的区隔,种种仪式的开展是为了强调生与死的差异。
排瑶死亡仪式的开展从集体符号层面完成逝者身份的转变。以视觉符号回顾“坐尸”,虽然人们将逝者以拟人态(坐姿)呈现,可是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唯独逝者是静态的,而所有送葬队伍都在运动的状态之中;只有逝者身着红色法衣,标志着他与生者的区分,送葬队伍穿过村落,“过九州”,实际上是一种向当地社会宣告的过程——此人(逝者)与我们(生者)不同,这个过程是一种身体区分的展示。
“安堂”阶段则是一种灵魂区别的转换。姓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代号(符号),排瑶族人一生要起三个名字:初次降生、结婚生子、死后(法名)。每次姓名符号的转变都意味着一种新社会身份的赋予。在安堂礼上,逝者正式启用法名,标着其社会身份的转变,代表着对逝者此个体的社会集体记忆转变。“法名”的启用实际上是一种死亡宣告。
死亡仪式联结着社会结构。在祭拜仪式上,有一个重要环节是祭祀者要向逝者禀告自己与其社会关系。由于排瑶分布相对集中,并且主要聚集在山区,人口流动性相对较小,族内通婚现象明显,因此,一村之内的瑶族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一家或者一房的葬礼,往往会吸引整个村落的人前来悼念。当集体面临冲突的力量,如死亡,需要仪式的力量将冲突化解,重塑社会稳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原本遁形的社会结构复现,如祭祀者要向逝者禀告自己与其社会关系、对女性作出嫁出团和嫁入团的划分。这是对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深层结构的再次确认,逝者不是简单的一个生物人,而是整个社会网络中的一个点,是我们的朋友、父亲(母亲)、姐妹(兄弟)等。死亡这个沉重的符号,通过社会关系的转喻而确立。这种结构的确认凝聚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形塑着稳定的社会结构。
五、结语
在死亡人类学的讨论中,死亡本身被从本体上剥离。韦伯的志业是为世界带去祛魅(disenchantment)的力量[13]。在他的论述中,神迹都可以被计量,科学取代了魔法。当现代性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科学话语之外,死亡仪式脱嵌于特定的文化脉络,不同民族对于死亡的哀痛成了低俗之物(pornographic)[14]。
有关死亡独特的“魅”力被现代话语强有力地切除,有关死亡的探讨被现代话语形塑。死亡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Death)并不聚焦死亡本身,而是其牵扯到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国家权力或者其他一些议题的渗透[15-17]。这可能与人类学自诞生之初自我标榜的“科学性”密切相关。人类学家要获取“本地人的视野”(native’s point of view)[18],经过严格培训的研究者可以得到科学实验般统一的答案,这需要扎实田野调查工作,体现了人类学实证主义传统[19]。然而我们没法超越死亡去理解死亡,如此一来,死亡通过实证话语去重新建构。
死亡可以通过科学话语去解释,可生命并不是被动地屈服于自然规律。死亡是向外弥散性的,从肉体某个器官的枯竭,扩大到身体机能的终结,再到向整个社会集体的宣告。对于排瑶而言,死亡是“缅”逐渐离开肉身、离开阳间社会的过程。
不同民族对于灵与肉有本体论上的区分,不同的民族的宇宙观之下,死亡有不同的弥散方式。在现代性的观点下,排瑶的死亡仪式是伪科学、迷信力量的呈现。但是,一系列大型死亡仪式的展演所带来的感官刺激、人灵之间的叙事构建,以及“安身”与“安魂”,种种要素相聚合,无疑不仅可让参与者表达苦楚和对逝者的留念,以及更好地别离,还可以重新确认民族凝聚力。这种有关死亡的想象与建构自有其难以否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