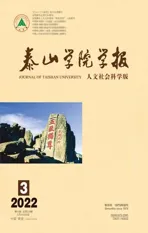明清时期河南浚县碧霞元君信仰的载体及其功能
2022-03-17张可佳
张可佳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引言
河南浚县浮丘山自明嘉靖年间修建碧霞元君行宫以来,吸纳了众多信众,成为豫北一处重要的碧霞信仰空间,名扬四方。
碧霞元君为著名的泰山女神。国内碧霞元君信仰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等以妙峰山庙会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富于创见性的认识(1)顾颉刚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容肇祖从情感发泄与心理安慰的角度分析了妙峰山香客的心理。参见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11-119、132-141.。20世纪80年代,碧霞元君信仰研究重新迎来热潮,多聚焦于碧霞元君形象、香会组织及与民间宗教的联系等方面,特别是对于北京及泰山二个信仰地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参见刘守华.碧霞元君形象的演化及其文化内涵[J].文史知识,1995(11):76-90.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52-379.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52.叶涛.泰山香社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7-116.以上仅选取一些论著,并非是碧霞元君研究的全貌。。关于浚县碧霞元君信仰的研究尚薄弱,目前仅见4篇专题论文,其中柴俊青对浚县碧霞元君行宫修建、信仰兴起以及香会组织着墨甚多(3)柴俊青.道教背景下的民间信仰——明清民国时期浮丘山碧霞元君信仰[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3):58-62.;刘炳强等将碧霞元君信仰与浚县正月庙会联系(4)刘炳强,等.碧霞元君信仰与浚县正月庙会[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5-11.;李亚东以浚县碧霞元君行宫的建筑布局为主,揭示了行宫的文化内涵(5)李亚东.河南浚县碧霞宫的形制布局与文化艺术内涵[J].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第二十届学术年会论文特辑(2017):124-129.;宋旭景以碧霞元君信仰为主,将明清时期浮丘山上各信仰的兴衰略作概说(6)宋旭景.明清时期河南浚县的碧霞元君信仰[J].寻根,2018(1):27-30.。今笔者不揣浅陋,现拟就碧霞元君行宫、信众与信仰空间为切入点,探讨明清时期浚县碧霞元君信仰的形成、发展及其与社会文化的联系。
一、庙宇:碧霞元君信仰的载体
碧霞元君又被称为“泰山娘娘”、“泰山圣母”等,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神之一。其前身为泰山玉女,至迟到汉代就已经出现,汉代道教文献《茅君九锡玉册文》中提及“玉童玉女,个四十人”(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469.。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曾到泰山封禅,并崇祀玉女神像(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庚申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2:765.,这使得碧霞元君信仰不断扩大,到了明代又发展到新高度。明人王世贞对泰山碧霞祠庙信仰之盛作过这样描述,“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即华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趣焉。祠宇颇瑰伟,而岁所入香缗以万计,用供县官匪颁”(9)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二游山记[A].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28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30-231.。从中可见明代人们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炽热程度。在元君信仰的影响下,泰山以外的地区也不断设置行宫加以奉祀。洪武至成化年间,各地兴建的碧霞元君庙尚不多见,但到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行宫已普及中国北方,直隶、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地均有设置(10)田承军.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J].史学月刊,2004(4):80-87.。如河北省新城县《泰山行宫记》云:“嘉靖己未春,适京人有造元君像送献泰山者,道经本邑南关,若有不欲然者,其人遂礼神留祀,惟时未有祠也,于是乡人马朝用、翟相等荒度土功,鸠集财用,遒于邑城南门外易善地二区,创庙三楹内省金神三尊……南北各房三间,以居守庙僧尼,时启闭奉香火也。(11)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37辑[A].民国新城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521-522.”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浚县也开始兴建碧霞元君行宫,以满足本地进香需要。嘉靖《重修碧霞元君行宫记》中还记载浚县地区之所以修建行宫,有去泰山祈福,但路途不便之意,“天下民士无不敬礼,应显尤多,山西东,河南北岁时道路不绝于行。如不及走登,则建为行宫,遍郡邑闾里矣!”(12)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76、176、179.行宫的修建满足了道路不便地区人们的供奉需要。
碧霞元君祠的前身是二郎庙,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碧霞元君行宫记》载:“先是,浚县城之南为城隍祠,祠之左有二郎庙焉,时久颓毁,乡民更为碧霞宫。”(13)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76、176、179.道士李实于嘉靖十九年(1540)在原二郎庙基址上修建为娘娘庙,将神主二郎改成碧霞元君。两年后,浚县知县蒋宗鲁捐俸并将其移建至浮丘山顶,并正式更名为“碧霞元君祠”,也即“碧霞元君行宫”。蒋宗鲁(1521—1588),字道父,号虹泉,应天府溧阳人。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进士,直至嘉靖十九年(1540)才出任浚县知县,之后曾在云南、河南、苏州、四川等地任职,著有《嘉靖普安州志序》、《碧云洞》等。关于蒋宗鲁修建碧霞行宫,有这样的趣事:在他任官浚县期间,其子蒋思孝患病三年,遍访名医却没有治愈,反而日加沉重,有人建议蒋宗鲁向碧霞元君祈告,果然一祷而验,不到十日,蒋思孝病即痊愈。这样的人神交易故事中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相信碧霞元君且供奉她,她将给有需求的人带来回报。蒋宗鲁修建碧霞元君行宫是供奉碧霞元君的体现,而元君女神回报给他的是儿子病情的痊愈。其实,除去知县蒋宗鲁的个人情感因素外,早在碧霞元君行宫修建之前,碧霞女神的信仰便已开始并根植在浚县及周围地区信众的心中,“明季因道多梗,遂于浮丘山建元君祠,数年告成。向之东游者,今皆趋浮丘,元君之神其足以保人心如此”。(14)清顺治六年《浮丘山元君殿碑记》,现存于浚县浮丘山寝宫楼西陪楼前。浮丘山上的碧霞元君行宫建立之后,原来东游至泰山的信众纷纷来此进香。
自浚县碧霞行宫修建之后,上山祈福的民众络绎不绝,“泰山碧霞元君之神,历宋元以来,威灵烜赫,遍及寰宇,远近之民除岁谒登。告外仍所在设建行宫以伺神游驻跸。矧浚去泰山甚为密迩,民亦崇信尤至。旧在城隍庙侧有祀一楹,凡民间祈请、控诉、有祷,辄应”(15)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76、176、179.。自碧霞元君行宫修建以来,行宫屡次得到修缮,现存的明清时期的碑刻中共记录有十五次修缮,分别为隆庆、万历、天启、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时期。在以上的诸次修缮中,以道光、咸丰、同治时期的修缮规模大(16)详见清道光元年《代父自序修工记》,碑存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元君行宫大门西侧;清咸丰二年《重修碧霞元君行宫备记》,碑存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元君行宫中院东廊前;清同治九年《重修浮丘山碧霞宫碑记》,碑存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元君行宫中院东廊前;清同治十二年《重修碧霞宫碑记》,碑存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元君行宫中院东廊前。。在诸次修缮之后,碧霞元君行宫的规模逐渐形成,浚县地区也逐渐成为碧霞元君信仰的中心。
浚县之庙宇作为碧霞元君信仰的载体,在吸纳信众方面影响卓著。日本学者森正夫曾经提出颇具影响力的“地域社会论”,他认为“地域社会是贯穿于固有的社会秩序的地域性的场,是包含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地域性的场。”(17)(日)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角——“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地域社会与指导者’”主题报告[A].(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中国的思维世界[M].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499-524.换言之即是将一个地区整合起来考量,将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信仰等意识形态等视为一个交互作用的统合体。其实也可以将碧霞元君行宫视为一个小的地域社会,其内部的石刻、佛像与建筑物等无不传达着宗教信息。“我天仙圣母殿实居其巅,庙貌巍峨,宫墙俊丽。身其际者如入蓬莱仙境,觉此中別一洞天,恒依依不忍去。而又窃见夫东西朔南朝山进香者,微特缙绅、士大夫心焉敬之,即囗(字迹模糊,不识)妇人女子亦无不知敬者”(18)清康熙五十年《大名府滑县梁村集居住公建天仙圣母神庙碑记》,碑存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西廊。。来此进香或游览的信众,一入碧霞行宫便觉得如入蓬莱仙境,让人心生向往,“大伾之西有浮丘山,鼎建泰山行宫,走海内人如鹜,几与岱宗爭长,盖山灵之奇也”;(19)清康熙四十三年《泰山圣母碧霞元君一十二年圆满碑记》,碑存于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西廊。“元君名于山之巅,不惟灵于浚之区,且燕、韩、赵、魏、郑、宋、邹、陈诸士夫、黔黎、黃童、白叟与夫冠嬴望族,蚁聚蜂屯,络绎不绝。每不啻亿万,皆祷祝于斯”。(20)清顺治十三年《浚县善信进香题名碑记》,碑存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西廊。众多香客营营逐逐,甚至还出现了堪与泰山进香相比的壮观景象,可见其庙祀的繁盛程度。
二、求子与祈福:碧霞元君信仰的主要功能
碧霞元君信仰符合中国民间宗教信仰讲求实用性的特点,服务于广大信众的现世需要。从碧霞元君信仰具体需求来看,又以求子为信仰的重要诉求。古代的中国以农耕为主,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社会。农耕社会下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强调了男性生产的主体地位。在这样的现实环境的影响下,重男轻女以及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社会环境与生育观念的双重作用的影响下,碧霞元君信仰的求子功能也应运产生,其中碧霞元君女神所司职掌的功能便折射出了信众渴求子嗣的心理。
元君掌管子嗣一事,自天子到庶民均有灵验,所以得到了人们的供奉,连统治者也不曾禁止求子的民间宗教行为,“泰岳有神曰娘娘,然不知其所出也。或谓送子娘娘者是也。司人间育婴,含灵吐异,恩泽遍于天下,古今之祀典最为钜然。故海内士庶尊崇瞻仰,咸乞子嗣,则民间之禋祀,亦王者所不禁”(21)清光绪二十二年《重修大伾山送子娘娘庙碑记》,碑存浚县大伾山霞隐山庄南门东侧。。不仅统治者不禁止求子行为,反而参与其中,嘉靖十一年(1532),皇太后曾遣太子太保到泰山为嘉靖皇帝求子,御祝文云:“皇帝临御海宇,十有二载,皇储未见,国本尚虚,百臣万民,无不仰望。兹特遣官敬诣祠下,祗陈醮礼,洁修禋祀,仰祈神贶,默运化机,俾子孙发育,早锡元良,实宗社无疆之庆,无任垦悃之至。”(22)马铭初,严澄非.岱史校注[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149.这或是证明了碧霞元君职掌子嗣的权力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浚县地区的碧霞行宫承担了该地区的人们对于子嗣的渴求,“尝闻:‘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碧霞元君殿东廊首一词,正子孙词”。(23)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82.又清顺治十三年(1656)《浚县善信进香题名碑记》“元君者,主掌坤元生生之道,故在东方泰岱,居山之祖,为神之宗。经历百代,自天子及庶人,靡不钦仰崇奉,神之格之亦无不照临”。(24)清顺治十三年《浚县善信进香题名碑记》,碑存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西廊。碑刻上灵验事迹的记载宣扬了碧霞元君女神保佑得子的能力,同时也助长了求子的信仰行为。明嘉靖年间浚县司训撰写的《浮丘山神灵应记》是最早记载于碧霞元君行宫求子并得到应验的事件,“(嘉靖)丙辰岁(1556)春二月,司训谢载偕僚友曙林登眺于上。载以平生乏嗣一事默祷于神,且抱一泥像童儿于宅,以图后应。不意月余孕即胚胎诞,弥十月,果生一子。感应之速,信不可诬”。(25)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 0 0 6:1 7 5、1 7 6.从谢载的事迹中能看出祷告,再加上抱泥儿塑像于后院的特殊求祷行为,似乎增强了事情的灵验度。然而记载这类求子的行为事迹似乎并不是唯一的,《重修大伾山送子娘娘庙碑记》中还记载浚县士女以剪纸焚帛的求子方式得到了灵验,“山之中迤南有庙一楹,即泰岳之尊神娘娘庙也。浚之士女尝来庙乞嗣,剪纸焚帛,以冀神之灵佑,而神即应。日久岁逝,则神之灵昭焉。庚寅春,余守卫郡,闻神之灵,家人道余以孙嗣乞祝于神,余从焉。越三载而得两孙,由是益信神之有灵矣”(26)清光绪二十二年《重修大伾山送子娘娘庙碑记》,碑存浚县大伾山霞隐山庄南门东侧。。浚县士女通过“剪纸焚帛”的行为表示自己的虔诚,继而求得子嗣的事迹传开后,引起了其他人的效仿,“浚邑城外浮丘山碧霞元君行宫,更远近闻名,香烟尤盛”(27)清咸丰二年《重修浮丘山碧霞元君行宫碑记》,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廊。。浚县及其周围地区的人们慕名前来,从而使得碧霞元君庙的香火更加繁盛。
虽然祈求子嗣在民间信仰行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最为常见的信仰需求则是祈福避祸。《正统道藏》中的《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谓碧霞元君最初的职责为惩处人间善恶,是一位普渡众生的女神,“泰山岱岳,奠靖坤元,中有元君,号曰天仙”,“受命玉帝,证位天仙,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28)陆国强.道藏·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一卷(第34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4:744-746.。民间宗教利用写有备述泰山娘娘灵迹的《泰山宝卷》的形式将元君的职能广为传播。在这个流传的过程中,碧霞元君女神的职能也在不断演变,并最终成为一个集安民护国、警世敦元、辅忠助孝、翼正扶贤、保生益算、延嗣绵绵、消灾化难、度厄除愆、驱瘟摄毒、剪祟和冤等职责于一身的女神(29)申飞雪.白云山诸神[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372-373.。
碧霞元君职能众多,但基本职能可概括为祈福这一大类。或祈求自己身体健康,或祈求粮食丰登,如清顺治六年(1649)《浮丘山元君殿碑记》中,“‘我愿祝康宁,修来世因’,功即在是;曰‘我愿祈谷’,功即在是”(30)清顺治六年《浮丘山元君殿碑记》,碑存于浚县浮丘山寝宫楼西陪楼前。。或为域内百姓祈福,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浮丘山岳神灵应祀》中所记载浚县司训为驱除瘟疫而向神君祷告,“至(嘉靖)戊午岁(1558)十一月,痘疹时行。载复祷于祠下,果获安全”(31)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 0 0 6:1 7 5、1 7 6.。又如清咸丰十年(1860)所立《奖施灯油香火碑记》中载“以故福我子孙,圣泽与河流而俱长;保彼黎民,神功偕山势而并重。”虽不乏对碧霞元君的溢美之词,但进香的信众实质上是希望域内百姓能够得到女神的庇佑。或得病后请求碧霞元君的神力以助自己早日恢复健康,日后以修缮庙宇或日行好事作为自己对女神庇护的回馈,如“自嘉庆二十年(1815)春月,有宜沟南镇车玉,因身患病来山跪祷,叩乞神佑,病痊,情愿募化四方,助修庙宇。回家不日而愈,所有布施,陆续送交与工人朱文喜收存,以便修工。(32)清道光四年《重修寝宫楼记》,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大门内东侧。”车玉的叩拜得到了神迹显现,身体痊愈后甘愿为碧霞元君行宫的修缮工作而四处募款。
不论是求子还是祈福,都是人们对于自己所不能掌控事情的寄托,继而祈求外力的帮助来解决棘手的问题。碑刻中大多记载这类辄求辄应的灵验事件即是如此,“病者痊,祸者福,求子者屡应,非聪明正直默有以佑乎?”(33)清康熙四十七年《仁育万物碑》,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东廊。清顺治十三年《浚县善信进香题名碑记》,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西廊。这些灵验事件既是他们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坚信,同时也是其被外在不可控因素支配的无奈之举,故而希冀虔诚的信念能得到女神的垂爱,“正所谓意念真诚,神必享佐,赐之五福,降之百祥,人人遂愿,户户获宁,皆神之所赐也”(34)清顺治十三年《浚县善信进香题名碑记》,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西廊。。这正反映了他们对于自己崇祀元君行为的认知,他们坚信心诚则灵,而女神最终也会被其诚心所感动,继而将幸福与吉祥洒满千家万户。
三、香会:碧霞元君崇信者的基石
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信仰朝拜圈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信众群体的庞大。其信众按组织规模划分,可划分为个体信众和群体信众,也即香会组织。由于记载个体香客的资料匮乏,拟以群体香客作为考察对象。就浚县浮丘山上现存明清时期的碑刻中记载有关会社的组织规模来说,可知其有会社有组织成员多、坚持进香年份时间长和女性参与度高三个特点。正是清代的进香组织规模大,会社组织成员众多,碧霞元君行宫也得以在会众进香朝拜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修缮。
碧霞元君香会组织规模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大体上遵循从明代到清代,其香会组织规模成稳步增长的趋势。现存的明朝碑刻资料中尚未发现有香会组织,其原因可能与统治者政策导向和碧霞元君信仰发育不成熟有关。明初对于民间祭祀信仰管控严格,将未获得朝廷认可的神庙,一律归入“淫祀”之列(35)按《大明会典》中记载:“洪武初,天下郡县皆祭三皇,后罢,止令有司各立坛庙,祭社稷、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孔子、旗纛及厉,庶人祭里社、乡厉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余俱禁止。”见于(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八一祭祀通例,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34.。严格意义上来说,碧霞元君信仰当属被禁淫祀之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执行的宗教政策逐渐放宽。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刑部尚书喻茂坚等曾上奏世宗,民间到泰山进香者,“毋令聚至二十人以上。”(36)明世宗实录卷三四〇“嘉靖二十七年九月癸酉条”[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6192-6193.可见至嘉靖年间,地方政府以20人为限,允许泰山信众小规模的进香活动。虽然放宽了香会的人数限度,但明代浚县地区碧霞元君行宫的香客规模发展得却十分缓慢,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新置碧霞元君神道碑记》中记信众接近百人(37)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81、181、188、192、200.,但是未提及香会组织情况。清顺治八年(1651)《碧霞宫完社记》碑中最早提及香会情况的记载,载“间有邑之魏氏善耄社众,资斧逾八载,处洁沐盛德汪洋而志蚁诚,展亿万之涓埃,合大众姓氏垂载碑阴,以悠久云。”(38)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81、181、188、192、200.此会社接连朝拜八年之久,是香会群体中连年进香时间较长的。连续十几年进香的香会倒也不在少数,如顺治年间《善信进香题名碑记》中“十有余载,不替”(39)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81、181、188、192、200.;康熙年间《泰山圣母碧霞元君一十二年圆满碑记》载“会聚男女,每岁赴浚县登山进香已十二年于兹矣”(40)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81、181、188、192、200.等,进香时间最长的当属乾隆年间的《东明王廷禄等进香碑记》中记王文亮率众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乾隆元年连续进香,未尝中断,而后其子继承他的事业,“朝历三君,家历两世,而精绝之意一脉相承,虽久不懈。”(41)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81、181、188、192、200.像这样父子相承、祖孙相继的香会组织不是孤例,《十王圣会四年完满碑记》中记载张耀东等人的香会也是如此,且相沿几十年(42)清乾隆二年《十王圣会四年完满碑记》,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东廊。。
清代的香会不仅进香时间长,其成员人数也众多。顺治年间《浚县善信进香题名碑记》中郭氏“携众进香”(43)清康熙四十七年《仁育万物碑》,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东廊。清顺治十三年《浚县善信进香题名碑记》,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西廊。,虽然并未说明具体人数,但大致可推测为人数很多。又顺治十三年(1656)《常香会善信提名碑记》中记载林氏组织的香会“二百余众”(44)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 0 0 6:1 8 6、1 9 2、1 7 4.的进香队伍;又清康熙年间《泰山圣母碧霞元君一十二年圆满碑记》中载会首刘自行、刘国祚组织香会,而村民“一呼百应”(45)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 0 0 6:1 8 6、1 9 2、1 7 4.;再又乾隆十六年(1751)《朝山进香碑记》中记载魏县及临近的村庄的村民自行结成香会的情况,“闻风入会,后先继香,男妇百十余人,相沿百有余岁”(46)清乾隆十六年《朝山进香碑记》,碑存浚县大伾山天宁寺大雄殿西侧。。由上述碑刻资料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清代的香会不仅数目多,其香会的人数也众多。不过,浮丘山上现存碑刻中也有仅署名会首与副会首,对香会的情况没有过多介绍的,笔者推测某些香会上山进香时采取会首代表会众的形式进行,故而没有留下过多关于其香会情况的记载。
女性在碧霞元君信众参与进香的活动中参与度高是清代香会组织的另一特点。顺治十三年(1656)《浚县常香会善信题名碑记》中记载“浚县南关内韩应龙母姓林氏者,性秉懿微,乐蠲好善,约闺阃淑媛二百余众,于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神庙点常香会,继十余年而未有已也”(47)清顺治十三年《浚县常香会善信题名碑记》,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东廊。。林氏组织二百余众善女于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神庙进香,连续十年不曾中缀。又“茲者本乡申养德母郭氏,携众进香,捐资助工,攒粮继饷,劳力供厨,十有余载,不替初心”(48)清顺之十三年《浚县善信进香题名碑记》,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西廊。。此外在《浚县善信进香题名碑记》中还可见“总领会首申养德母郭氏、会首邓守信母杨氏、会首刘天就母王氏、会首李一成妻卢氏、会首李三秋母屠氏、会首李从云母毛氏”(49)清顺之十三年《浚县善信进香题名碑记》,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西廊。。除以上罗列女性之外,浚县浮丘山中的碧霞元君的信仰空间中还常见女性身影(50)根据现存于浚县浮丘山上的有关清代香会组织的碑刻资料中,共有21块石碑记载了香会朝拜碧霞元君,其中女性参与朝拜的石碑共有9块,约占总数的43%,据此可知,清代女性参与香会朝拜之盛。。笔者以为女性在碧霞信仰活动中频繁出现的原因与民间宗教信仰中碧霞元君主管子嗣与祈福等神职有关,此外也与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承担的角色有直接关系。
香会组织和香客群是碧霞元君行宫得以时常修缮的主体力量,特别是香会组织出力甚多,对于碧霞元君信仰得以绵延祭祀所发挥的作用巨大。有香会捐资塑神像,清顺治六年(1649)《浮丘山元君殿碑记》中云:“余乡善人郑连等结会三年,赍香缗往拜其下者凡三。又各捐资财、金神像五尊。(51)清顺治六年《浮丘山元君殿碑记》,碑存浚县浮丘山寝宫楼西陪楼前。”有香会修理道路,装点碧霞元君行宫,“修理碧霞宫一座,重修山左甬道一条。创修山右甬道一条,重修灵官庙一座,施柏树二百三十株,金装两廊神像”(52)清道光元年《代父自序修工记》,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大门外西侧。。咸丰二年(1852)《重修浮丘山碧霞元君行宫碑记》,碑额题首注明“继往开来”,即是点出了信众们出于崇信碧霞元君信仰的初心而自发、自愿地接续修缮之事业,“逮及国朝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屡有重修碑记,亦历历可考无须多赘。惟自嘉庆癸酉患遭兵燹之后,历道光至咸丰元年,经四十载之久,不无风摧雨折,雀啄鼠穿。邑之太学生沈健、信士张元魁、付连仲等睹此情形,触目伤心,即命住持道人李祥钰,敦请诸位会首捐资募化,重加修理。自元年辛亥夏月开工,先修戏楼,次由大门、二门、钟鼓二楼及大殿神像,陪廊神像、角楼垣墙、砖路,皆焕然改旧为新”(53)清咸丰二年《重修浮丘山碧霞元君行宫碑记》,碑存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东廊。。
可知,自嘉靖年间迁建浮丘山上始,碧霞元君行宫虽然遭受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而衰败,但屡屡得到其信众的修缮。除士绅主体的修缮活动外,现存碑刻中还有其对于信众行为的约束记载。明嘉靖《直隶大名府浚县为施舍基地基事》中保证了碧霞元君行宫的占地(54)浚县文物旅游局.天书地字·大伾文化(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2 0 0 6:1 8 6、1 9 2、1 7 4.,清康熙《康熙五十二年告示》中规定地租用于庙宇修缮,禁止霸占行为(55)清康熙五十二年《康熙五十二年告示》,碑存于浚县浮丘山寝宫楼前西陪楼内。,清嘉庆《严禁作践庙宇告示碑》中禁止占据月台、两廊,强搭铺面的行为(56)清嘉靖十六年《严禁作践庙宇告示碑》,碑存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宫大门外东侧。。不论是修缮活动还是禁止性的规定,均由士绅为代表的地方上层人士主导,这反映世俗权力对于民间宗教信仰空间的渗入与管理。
结语
兴起于泰山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传入河南后,获得了浚县民众的认同与崇拜。浚县碧霞元君行宫自明朝嘉靖年间修建以来,屡被修缮,规格逐渐完备,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浮丘山为中心的碧霞元君信仰空间。碧霞元君信仰原有的求子嗣延续、富贵平安、寿考康健等主题,均在浚县庙祀中得到传承与发展。浚县浮丘山上现存的碑刻中记载了大量碧霞元君灵迹显现的事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众对于碧霞元君的信仰与崇拜。浚县碧霞元君信仰以求子和祈福两大主题为主,这与明清时期的时代背景相呼应,也与民众现实生活最迫切的期待相衔接。
与泰山信仰不同的是,浚县碧霞信仰仅受到了地方官员士绅阶层的推动,未能走入明清最高统治者的视野,其影响范围也仅限于河南北部。在碧霞元君信仰的影响下,明清时期浮丘山上的碧霞香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且有专由女性构成的香会。香会组织在修缮行宫与传播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其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坚定,才使得碧霞元君信仰得以薪火相传。浚县浮丘山上现存碑刻对于浚县碧霞宫庙的种种印记,展示了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的民众诉求和社会生活的一斑,可以视为碧霞元君信仰在各地的传播状况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