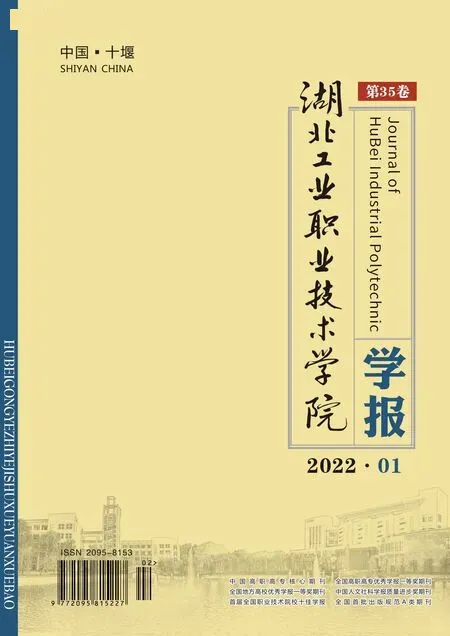韩江小说《素食者》中的身体书写
2022-03-17唐雪
唐 雪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1)
韩江是韩国新生代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素食者》于2016年获得了布克国际文学奖,她也成为了亚洲首位获得该奖的作家,该书还入选了《纽约时报》15本重塑新世纪的女性小说。《素食者》是由《素食者》、《胎记》和《树火》三个短篇故事集结而成,作家是基于英慧、丈夫、姐夫和仁惠等多个叙事视角来谋篇布局,它们即可单独成篇,同时又可联结成篇,即多视角交叉表述英慧的故事,英慧是贯穿小说文本的人物。小说讲述她因“梦”,开始拒绝食肉,面对亲人的暴力威逼,以自杀方式进行反抗。在被亲人送进精神病院后,她开始拒绝人类的主体身份,甚至自认为植物,只需阳光和水即可。小说结尾之处,熊熊燃烧的“树火”是英慧发出的呐喊,是对这虚伪文明的控诉。
《素食者》精炼短小,但内涵丰富,其中充斥着强烈的性别不平等和魔幻色彩。目前已有从生态女性主义和德勒兹的生成理论去分析韩江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境遇及其“生成植物”的延伸意义,或者直接去研究植物意象的隐喻内涵,总的而言,主要集中于对女性现代性绝望的揭露,女性主义、生成理论与身体主体密不可分。文学是人的文学,人物的身体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维度;传统的男性创作文本中,女性身体是男性欲望的对象,是污名化和被放逐的,但《素食者》中的身体叙事是被遮蔽的。“身体是主体性的辐射和理解世界的工具”[1],身体是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是意义的出发点。人与社会、文化等关系通过身体媒介来传达,生活中的一切话语都将在身体上留下痕迹,“身体成为了象征的源泉和意义的集结点。[2]”纵观《素食者》全文,身体是串联梦、植物、胎记、肉和素食等元素的中心点,身体是英慧现实受困之体现,同时也是她反抗的武器。
一、“受难的身体”与女性之“囚”
“受难的身体”,不单纯指小说中英慧被围困的身体,同时道出了中西方传统中“失落”的身体,它作为精神、灵魂的载体,它甚至阻碍主体把握真理的绊脚石。身体与女性有着同样的遭遇,都是作为客体和他者存在,都是逻格斯二元对立哲学逻辑统治下的产物,两者之间是交叠性,拥有“同病相怜”,也是嵌入性关系。身体是主体的物质性存在,身体连接着主体生存所需之食物、空间、衣服等物质形态,身体一种是揭示女性被压迫机制的重要切入点。
女性在历史长河中常被神话和圣母化,认为女性就是温顺的,是第二性的,是应该为家庭付出一切的,只能在社会中接受一个既定的位置。女性经常被“囚禁”在私人领域,每天机械地重复着琐碎的工作。英慧作为一位传统的妇女,她每天的工作集中于照顾丈夫和料理家务,“六点起床准备有汤、有饭、有鱼的早餐”[3]3,从丈夫的视角叙述了从结婚至今,英慧每天都在照料和目送丈夫上班。作为男性主场的公共领域,她只是其中的兼职员,并非是其主场,女性被锁在家庭的私人空间中。
女性除了繁重的家务活动外,她们也是男性暴力对象。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空间中有着隐性的等级观念,男性(尤其是父亲)在家庭中是绝对权威。英慧从小是父亲家暴的对象,她的身体见证了父亲的暴力。“姐妹俩轮番被性情暴躁的父亲扇耳光”[3]132,导致了英慧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姐姐和母亲摆脱了父亲的魔掌,而胆小懦弱的英慧成为父亲家暴的对象。丈夫“据说,妻子被这样的父亲大小腿肚一直打到十八岁。”[3]28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身体是精神病症外在体现,也就是现在常用科学术语创伤应激反应综合症。往昔的创伤在相似的情境中,会产生不受控的生理反应,精神创伤记忆在身体上形成了记忆;甚至某些身体症状和表现,可能是连主体都未曾留意到的精神伤疤之后遗症,如英慧绝食行为与童年的父亲虐狗事件的关联不言而喻。
英慧嫁作人妇后,丈夫早上气急败坏的催促和英慧手慌脚乱成为生活常态。面对妻子被割伤的手指,她的丈夫只是一味地吼骂“妈的,你想害死我吗?”[3]17。除了完全被困在家庭内部和经常常受到丈夫语言的暴力,遭受其性暴力,但施行暴力的男人还沾沾自喜,“当我按住她拼命反抗的胳膊,扒下她的裤子时,竟然感受到了莫名的快感”[3]29,正如作家张爱玲曾讲述,婚姻犹如长期“卖淫”,女性不仅要承担保姆的职责,更是要履行其他的不合理的“义务”。而文本中丈夫仅用平凡的、不起眼的、无魅力的等词来介绍她,英慧在他的心中是被忽视的,从未觉得她是特别的存在,“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她轻松地胜任了平凡的妻子的角色。[3]3”英慧曾尝试着与丈夫交流,她用“梦”里的荒诞性内容,试图引起丈夫的关注,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丈夫只会重复很无聊。作者多次重复“没有”和“从未”等否定性的词来强调丈夫的冷漠,凑合性夫妻关系。在妻子行为怪异后,他只会重复“她这是疯了,彻底疯了”[3]9,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疯癫化表述,是男权结构控制女性身体的战略。丈夫仍在自言自语强调,绝不会送英慧去看心理医生,这是丢脸的事情,竭力顾全“男人颜面”等极度自私的行为。丈夫是随即给亲人打电话,但家人的反馈信息皆是安抚丈夫的语言,指责英慧行为的不合理性,未有只言片语是追问英慧异常之因。
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中也受限制,比如在服饰妆扮层面。丈夫眼中“妻子只有一点跟其他人不同,那就是她不喜欢穿胸罩”[3]4。而一个不穿内衣的女性,会被社会看成是“怪物”,看成是不守妇道,淫秽的化身。历史文明中对女性身体的污名化和摧残数不胜举,如非洲的割礼、中国的裹脚、欧洲文艺复兴后贵族的束腰等桩桩对女性的罪行。但人类可从初生的婴儿和原始文明历史性表述中,窥见其实人类赤裸裸地来,后来才被赋予身上一切,不过是服装,是一种文化修饰。福柯的身体观认为,身体是权力的被动的对象,进入社会后身体是被驯服的身体,身体受到知识话语、文化标准、规则秩序等等的规训。身体是可变的,而且是被动地变化的,是受权力的管理、控制和改造的。“女人把她们自己的身体禁锢起来,置于如此狭小的内衣之中”[4]27,面对丈夫和家人质疑的时候,英慧一直强调内衣勒得难受。从东西方历史看,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前,女性的身体几乎是不加束缚的,直到17世纪,出现了“束衣”,女性身体的折磨史开启了。内衣是西方的舶来品,现代女性的内衣被消费主义赋予了时尚都市的内涵,延续着内衣是一种身份的标识,但内衣的设计者是否有对女性身体经验的体认经验?
社会对女性的规定,不仅在衣饰层面。在饮食方面,英慧也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身边所有人都逼迫食肉,残暴的父亲又“开启”灌食的行为,就因其不合群,成为一个怪物般的存在,英慧母亲所说,“你现在不吃肉,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吃掉你,[3]48”道出了社会性暴力的结果。作者通过女性受难的身体讲述了女性与世界、社会深层关系:她与施暴者的关系,与家庭、社会集体的关系等。但食肉何时成为了世界的唯一标准?在服饰穿着上,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境,为何女性就一定要穿内衣?衣服原是为了取暖和装饰之用,在原始社会早期,女性有如此要求吗?所谓的文明社会究竟是解放了人类身体还是更加框定了身体的自由度呢?女性社会层面的诸多选择,都是被男性文化提前设计,再通过文化的暗示,使得女性在身体、记忆和机能等层面强化,长此以往,一种文化性标准被操演成一种女性的自然的特性,形成系列所谓的女性气质。人类主体常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界定世界万物,身体在男女生理上的差异,被赋予文化内涵,导致它有着不同的社会处境,身体是女性苦难的集结点,是女性之“囚”的真实写照。
二、“逃逸的身体”与女性之“疯”
那么英慧针对社会和家人给予的围困,采取何种方式来突围的呢?家人对英慧的强行喂食,浅层上身体生存之需,深层是一种心灵的压迫,是一种暴力性的体现。强迫进食意味着一种不考虑主体身体生理线索的进食,食物具备了额外的内涵,已失去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关联。文本中肉除了作为人类之食材,同时是具有隐喻性的,如英慧拒绝丈夫的亲近是因其身体上充满肉味,暗指一种暴力性元素。从指涉缺席和符号学角度看,隐喻式的语言中的“肉”与女性经常是互相指涉,故而女性的身体经常被看作是肉体,具有动物和自然的特性,而不是完整的主体性的。根据生态女性主义亚当斯的观点,“食肉行为是男性统治形式的组成部分,食素行为在父权文化中是疾病的标志”[5],食物即可成为统治武器,同时它也是一种力量的源泉,故而英慧拒绝食肉是一种战斗的力量。在父亲强行喂食的时候,英慧采用自杀方式来进行反抗,这是英慧第一次用身体行动发声,食素行为是对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制度的反抗。文中的英慧形象是平庸的,异于现代都市文学中时尚女性,唯一的特别之处就是不穿胸罩,且作者在文本中多次重复该情节,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皆有表述,她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那半禁锢、半放纵的魅力乳房,它们正在竭尽全力摆脱束缚,为自由而抗争”[4]27。以西方的夏娃为例,在未偷吃禁果之前,她是赤身裸体的,是未有羞耻感的。禁果在某种程度上说,文明的分野点,文明出现以后,文化开始教化人类,让他们要有羞耻感,首要的表现,就是给原始的御寒之服饰赋予文化标签,界定某些行为是不文明的,是不符合规范的。若你不遵守,就会被世人唾骂和蔑视。英慧在丈夫的多次唠叨之下,直接在家裸露上半身,以示其态度。作者甚至直接用英慧口吻说“不”,“我的乳房变得锋利,是为了刺穿什么吗?[3]33”,这应是无数正在受困于各种规范下的女性之声。
英慧除了实际行动上的抗争,她还做荒诞性的梦,文本中的英慧的梦的内容随着身体受难的程度逐渐发生变化。首次作梦,是因丈夫忽视自我的受伤的身体,一直不停地在谩骂,面对此情此景,她的心理状态是“毫不吃惊,反而更加的冷静”[3]17,暗示了丈夫该行为的日常性。作者删减有度,直接把故事情节的高潮部分呈现给读者,然后用暗示性的时间概念交代此种生活状态的时长。梦中的英慧独自行走于四下无人的森林中,“我的脸和胳膊都被划破了,怎么也找不到出口,身上的白衣被鲜血侵染”[3]10,梦中情节与现实生活有着一定的相似点,身体受伤,丈夫之不理睬,使得英慧迷失方向。丈夫在向英慧的家人诉说痛苦后,英慧收到家人一致责骂;她又一次作了梦,梦中一切陌生,“我仿佛置身在某种东西的背面,像是被关在了一扇没有把手的门后。[3]27”家是温暖的港湾,而留给英慧的只有一望无际的黑暗。最后英慧不堪重负,直接在梦中杀人,杀的对象未有明确的指代,从小说中英慧所受到的压迫,人是作为指代符号,是所有对其施暴者。梦是潜意识的外在表现,弗洛伊德认为梦并非是无意义的,甚至是荒谬的,荒诞的梦是一种理智活动的表达,他认为梦是一种改装,是不被社会现实和伦理所认可的潜意识行为的表达。英慧的梦中杀人情节,是其抗争意识的外在表现。
每个刚出生的女性都是一个“完整的人”,在其社会化之旅中,渐次被“阉割”,成为“疯癫者”,甚至直接异化为“非人类”,这种阉割是社会性的。女性是通过男性的想象,来探索世界和辩识自己的命运的。英慧所采用的反抗行动,被笼统地概括为疯癫。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采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疯”的内涵和外延作了历史性梳理,他强调“疯癫”是权力话语界定的结果,是是游离于理性社会的行为和思维模式。“疯癫总是伴随着其对立面理性,理性在疯癫的行迹中如影随形”[6]。《素食者》小说文本中的英慧重复的“噩梦”以及食素、裸体等违背常识或文明的行为,是福柯所说的“疯癫”内涵的构成要素。女性之“疯癫”,一方面表现了女性因被压迫而“疯”的现实现状,它象征着父权制和社会施加给女性的社会、经济、心理上的暴力和控制。另一方面则是,英慧的食素、幻觉、裸体等行为,其种种行为已经违背了父权制社会规定的女性行为,已超出了男性所能控制的程度,社会关系濒临失序。
女性并非“疯”,只是女性反抗之始,女性突然一改往昔文化规范内的温顺,开始表达自身的需求,让男性猝不及防,故而只能像文本中的丈夫,给女性贴上“她疯了”的标签,以给男性反压女性寻找合理性。“从理性的观点看,身体一直都是非理性的源头,是对个人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威胁”[2]265。但个体通过自己的身体来表达个人的诉求,女性通过身体发出呐喊。女性的肉体本身就是猎物而存在,英慧蓄意食素,厌恶一切与肉体有关的物体,并采用摧毁肉体极端方式,为她的自由而战。
三、“异化的身体”与女性之“救”
作者韩江有东方的“卡夫卡”之称,她早在《植物妻子》中讲述了一个在阳台上化为一株植物的故事,该故事是贯穿《素食者》的核心线索,《素食者》中的英慧从心理层面妄想自己的身体成为一株植物。英慧并非不想活下去,单纯不想像我们一样苟且地活下去。英慧出嫁前,因性格内向,是父亲经常家暴的对象;成婚后,丈夫也会对其进行家庭的冷暴力导致她作“梦”,“梦”里血淋淋的场景,实则是她前半生生活的写照。小说中英慧处于持续反抗的状态,在被亲人亲手送进精神病院后,她逐渐生成植物,强调“姐,我倒立的时候,身上会长出叶子,手掌会生出树根”[3]130。在《树火》篇中的叙述者是姐姐仁慧,从仁慧口中可得知,英慧幼时曾有过如此行为,作者通过把英慧期望逃向深山与姐姐口中家暴的父亲情节并置,这不难获悉家暴与身体异化之间的关联性,英慧反抗的种子已深种心里,家人集体性逼迫使得英慧彻底绝望,割裂人类的肉身,以期植物化的身体寻找和救赎自我。英慧强调她的身体只需要水和阳光,就能活着。阳光和水象征着纯洁和希望,是纯天然的自然状态,是未经人类文明染指的主体,英慧通过生成植物来净化身体及其创伤,从而获得新生和救赎。
这里会联想到德勒兹的生成论,德勒兹通过“生成”的动态性以及差异性消解传统的同一化和中心化倾向,他的理论是对传统的一种抵抗和逃逸,同时是主体一种自我救赎方式,德勒兹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认为《变形记》中主人公异化的身体是另一种重生,是逃出压迫,走向自由天空的出口。英慧在生活中的遭遇与格里高利极为相似,但《素食者》中的英慧与《变形记》中格里高利略有不同,他从身体上生成动物,但英慧是心理上生成植物,但其身体并未生成植物,故而英慧的生成是失败的,同时也暗示了女性自我救赎之途坎坷,英慧生成植物的动态过程及其怪异行为之因,触人深思。英慧的食素、裸体和梦等系列的反抗行为,最终的结局导向是破碎的婚嫁和家庭,被亲人亲自送进精神病院。深山中的医院中,英慧仅是其中之一,医院中的患者与英慧的遭际相同,皆是最为紧密之人亲手送来。但英慧与他们不同,英慧在反抗医院的强制行为,如逃跑、拒食、倒立等行为,而医院的其他患者都把脸贴在玻璃门上,用着空洞的眼神望着窗外,犹如行尸走肉,无自由可言。
不可否认的是英慧生成植物的过程是对主流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一种控诉,那么为何又说英慧生成植物的反抗行为究竟为何是失败的?《变形记》中的主人公之死,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抹除的过程,象征重生和解脱,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的救赎;但英慧是求生不能,而求死也不允许,医生通过现代化仪器对拒食的她进行强行灌食,此次行为比父亲的灌食不同,英慧尚有“突围”的可能,但仪器直接插入胃部,把食物送达,让英慧逃无可逃。正如仁慧所说“你之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是你能唯一所做之事,可是现在,你连这也做不到了。[3]182”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复制了性别之间的等级关系,她真的控制了自己的身体了吗?并没有,她把她的身体交出来让他人进行控制,实质上她失去了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力或能力。
四、结语
“西苏的‘用身体书写’并非直接用一种身体语言或姿态去表达或诠释意义,而是指用一种关于身体的语言,去表达女性整体的、对抗罗格斯中心主义的全部体验,超越男人的束缚”[7]。通过阴性书写去撕裂阳性书写对女性主体的各种遮蔽性和偏碱性,开创一种新的反叛写作,把男性被放逐身体,重新拉回现实,让世人倾听自我身体的呼吸和言论,从而建构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韩江在《素食者》中直接用女性的身体语言来反抗父权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她借助身体所形成的场域,把生命、性别、文化、权力等元素综合在一起,以自然的身体形态去反抗文明尺度规训中的身体面貌。传统的文明把女性限定在狭隘的家庭空间,是男性的附属品,是肉体性存在,是性欲的对象,女性的一切都在社会的“全景监视”之下,如衣着服饰、身体姿态、饮食习惯等都有各种繁复的规范体系,一旦越轨,就会被划定为“女巫”或“坏女孩”等范畴中。自由的获得需身体之外的体验,女性对身上文化枷锁的僭越行为,是其反抗之始。“肉”、“内衣”、“暗黑的森林”等意象象征英慧之“囚”;而“梦”、“素食”和“植物”是英慧之抗争和自我救赎的方式。身体是小说中各种元素的集结点,英慧的裸体、素食、乳房、梦、植物化等身体行为揭开了文明的虚伪面具,撕裂了男权统治的伪装面具。
但韩江小说文本中的身体书写,并非只停留女性身体表述上,有男性、动物和植物的表述,通过虐狗事件以及英慧通过生成植物情节,她超越了西苏所说的“阴性书写”,她的女性书写是建立在对男性叙事的遮蔽之上,未跨越性属间界限。《素食者》中书写的女性形象都是受害者,但同时某些女性也是男权社会的帮凶;另外文本的中男性既是女性之伤的施压者,他们也是整个社会系统机制的受害者,只是男性的生命体验在小说中所占的篇幅较少,韩江某种程度上突破了逻格斯中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形成相对中立的叙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