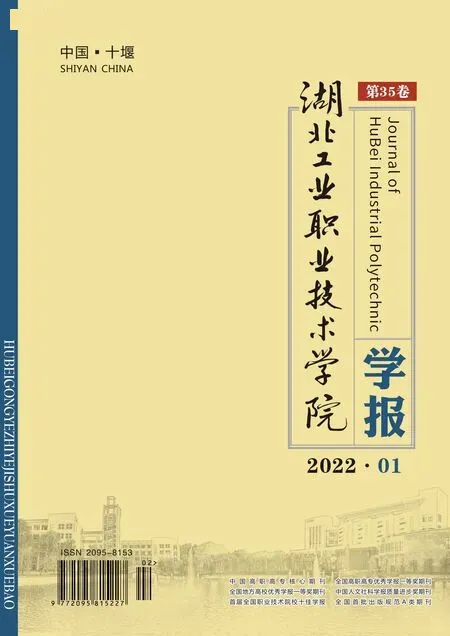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之“体”
2022-03-17董方伯谭子玮
董方伯,谭子玮
(1.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2.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230039)
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于1932年出版,述及的作家是1911年至1930年文坛的活跃人物。由于钱基博对“新文学”持谨慎的态度,也并不贬斥“旧文学”,引起新文学家们的不满,在出版当时就招来了各方的批评。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数十年间,除胡先啸、陈灨一等人做出正面评价之外,大多处于受到忽视的状况,甚至于遭到讽刺、反对。直到80年代中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提出、人们对于“主流”文学史叙事的反思,钱基博此著渐渐得到关注,被认为是借以反思的良好视角,但仍然被视为“旧文学”的“顽固”代表。
进入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此书写作的具体背景,以及背后所蕴藏的更多的价值。近十年间,这个浪潮似乎空前高涨,颇有翻案重评的意味。2008年周远斌《钱基博的文学史建构理论及其实践》、2010年姜晓云《谈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2012年魏泉《从钱基博的<集部之学>到<文学史>》、2019年李向阳《钱基博的文学史观与新文学观——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化解读为中心》等文章均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作出了积极的评价。
钱基博此部著作及学术旨归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与探讨,其评价也在逐步上升。前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强调“不以西方文学观念来剪裁中国文学”的独特价值,以及立足于“新旧”文学冲突与融会的角度去观察其书写方式,即钱基博所提出的文学史建构方法。笔者认为,在讨论其文学史建构时,著书之“体”实际上是更为具体的一个话题。作为今所谓“旧文人”,钱基博极为重视文学之“体”。《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卷首序文,作为研究此书非常重要的文献,“聊疏纂例,以当发凡”[1]4,就是在谈创作此书的“体”问题。且此书的目录设置、行文结构、段落章节之衔接等,无一不为其匠心所在,不仅是其文学史建构的方法,更是属于“体”的问题。因此,不妨从这样一个具体的名词切入,尝试分析钱基博都在文学史建构中或说旧、新文学的嬗变中起到了何种的作用。此外个人认为,其建构方式有在序文中明言者,亦有未言者。试一一辨析之。
一、两《汉书·儒林传》之体
《现代中国文学史·序》(以下简称《序》)开篇明义:“余读班、范两《汉书·儒林传》,分经叙次,一经之中,又叙其流别,如《易》之分施、孟、梁丘,《书》之分欧阳、大小夏侯其徒从各以类此,昭明师法,穷原竞委,足称良史。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略仿《儒林》分经叙次之意……”[1]4
“两《汉书·儒林传》”,指的是班固《汉书·儒林传》、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这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最为基本的体例。钱基博十分重视对《儒林传》的仿照。
其一,“分经叙次、叙其流别”。《汉书·儒林传》:“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2]”经书的名目为最高一级的分类。一经之中,又根据师承关系进行附录,以《易》而言,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以下则附录丁宽传。丁宽又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以下则附录施雠、孟喜、梁丘贺传,因此分施、孟、梁丘三家《易》学。梁丘贺又曾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学。以下则有京房传。其“叙其流别”,诸如此类。
以《现代中国文学史》目录观之,“古文学”“今文学”是最高一级的分类。古文学分文、诗、词、曲,新文学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古文学之中,文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诗之别。即是“分经叙次”的应用。
在正文叙述中,则仿《儒林传》“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以“文”中的“魏晋文”一目为例,钱基博所取的三位大师为王闿运、章炳麟、苏玄瑛。关于此等大师钱基博的记述甚为详细,章炳麟一节,不仅详尽记述了被目为“真疯子”的生平、与各色人之间的种种纠葛,还记录了他对于一些时论,例如对于崇党锢、薄程朱、蔑道德奖革命、慕共和称代议、兴学校废科举等的反对看法。谈到其文学主张,则大篇幅引用《文学论略》以作说明。而章炳麟的弟子黄侃附于其后,除录其《梦谒母坟图题记》外,关于生平仅寥寥数笔。使用这样的编纂体式,钱基博以近三十位重要作家为枢纽,采用宗派师承、各家争鸣的视角,将晚清至民国的文学史过渡有序地呈现出来,明确文学发展的脉络。
其二,“明以原委”。《序》曰:“又按《汉书·儒林》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如班书叙《易》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书之必称前书是也。[1]4”此方法在钱著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对于“逻辑文”的追溯。
“自衡政操论者习为梁启超排比堆砌之新民体,读者既稍稍厌之矣;于斯时也,有异军突起,而痛刮磨湔洗,不与超为同者,长沙章士钊也。大抵启超之文,辞气滂沛,而丰于情感。而士钊之作,则文理密察,而衷以逻辑。逻辑者,侯官严复译曰‘名学’者也。惟士钊为人,达于西洋之逻辑,抒以中国之古文;绩溪胡适字之曰‘欧化的古文’;而于是民国初元之论坛顿为改观焉。然中国言逻辑者,始于严复,而士钊逻辑古文之导前路于严复,犹之梁启超新民文体之开先河自康有为也;故叙章士钊者宜先严复,犹之叙梁启超者必溯康有为。然而康有为、梁启超之视严复、章士钊,其文章有不同而同者;籀其体气,要皆出于八股。八股之文,于宋、元之经义,盛于明、清之科举,朝廷以之取士者逾六百年。”[1]459钱基博认为严复等人的文章是“假欧学以为论衡之绳墨”,八股文随科举废除之后,其影响并未马上断绝,而是分散于各家文章之中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学。这一论断极具洞察力,也体现出钱基博对《儒林传》“明以原委”的充分继承。
但是,著文学史毕竟不能完全仿照两《汉书·儒林传》,这也就要求钱基博根据时代要求和著述内容有所调整。因此,在继承的同时又有相异之处,这正是钱基博会通古今的证明,而不是所谓“旧文学顽固派”或曰照搬古代文学传统这样简单。时代迥异,《儒林传》以经学为中心,自然以经书为纲,以儒生为目,“五经”是一个不必多加探讨的分类。若要借鉴《儒林传》体例,将它运用到文学史的写作,须自拟文学之分体。正所谓“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钱基博如此重视文学之“文体”,不仅出于“旧文学家”对“体”的认识,也是他在著此书之前,必须先对将要叙述的这段文学史之文体有所辨别,才能拟出这样的纲目。辨体之学源自魏晋,《文心雕龙》《文选》为“辨体”的重要基础。《文心雕龙·序志》:“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定势》:“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3]”
值得注意的是,钱基博对于古文学大的分类,即“文、诗、词、曲”并举,处于一个平行的位置,已经不完全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相同,受到了后起学术的影响。正如钱著本身在“曲”一章所介绍的,王国维、吴梅等人的研究和努力,把以曲词为主、有科白、有故事情节、可以上演的称为“剧曲”、“杂剧”,归于戏剧的范畴。钱著在叙述王国维的学术主张时,引用其《宋元戏曲史》的观点:“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1]351”将此类通俗文学,拉高到与“诗文”可以并举的地位,这是不能忽视的编排体例。自然说明钱基博已吸收新近讨论文学的观点,并且把它们连接到与古代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谱系,书写到了现代文学史中,而并不认为新旧之间就一定存在矛盾乃至不可容。
从西方引进的“文体”(体裁),与中国文学之“体”,并非同一概念。仔细观察钱著对“新文学”的分体,“新民体”“逻辑文”等的类目,内涵其实更接近于《文心雕龙》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谈的“体”,既包括形式的规定,又包括内容、风格乃至感情色彩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在辨体之学的视野下,如果一种文体进入了叙述的视野,那么也就意味着已经具有了应用的范围和典范的意义,得到了“体统”的承认。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白话文”也作为一种“体”而见书于钱著,就彰显出白话文已经被纳入到文学谱系之中,并且也自然不否认白话文可能会有新的发展,开启新的时代。论者多关注钱著对白话文的褒扬不足、记述篇幅较短等,据此断定钱基博的“守旧”。如若放在真正“守旧”的辨体学视野下观之,那么钱基博的这一步实际上非常重要,甚至可称“激进”。
此外,相较于两《汉书》的史笔简略,钱基博加以“长编”“比类”体。《序》曰:“然史笔贵能简要,而长编不厌求详。”《序》引章学诚言:“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1]4”而实际上,《现代中国文学史》最初就是以《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之名付梓。
“长编”一体,本是撰写编年史前,先行搜集资料,按次排列的初稿。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之前,即先用此体做准备,并且精确地揭示过长编的体制特点,“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4],尽可能地详尽收集和编次材料。长编最初是为编写编年体史书所做准备而使用的,但后世学者也有所活用,例如陈寅恪用长编考异之法,并非是为年谱或编年做准备。钱著同样如此,虽然体例上更接近于纪传体史书,却使用“长编”之法。他之所以倾心长编体,是因为认为“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为求叙事可信、立言有本,因此尽可能地详尽罗列材料,接近历史的真相。进一步而言,这里面已经有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竭泽而渔”的文献材料意识。正如钱基博辨析的那般,“文学史”是独立的现代学科,所关注的对象是“文学史”本身,“长编”的材料最终是作为文学史材料呈现的。钱基博批判胡适的文学史,其理由就在于欠翔实:“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何也?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1]10”
二、《史记》、《晋书》之体
《史记》也是钱基博重点效仿的对象。最为明显的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列传之“铺叙履历”。这并未在《序》中明确提及,而是涉及到《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部分讨论“文学史”的定义过程中,钱基博对范晔《后汉书·文苑传》的看法。《汉书》有《儒林传》而无《文苑传》,范晔《后汉书》创此体例,后世因之。在钱基博看来,中国古代史书的《文苑传》无疑是最接近“文学史”的概念,但又不能完全等同。学者已经意识到“文苑传”是讨论此著作的一大关键词,王炜《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一文详细分析了钱基博对“文苑传”与“文学史”之区别的辨析[5]。这一点不再赘述,总之钱基博对《文苑传》是持不满态度的,认为《文苑传》只“铺叙履历”,对文章得失不予评论,不能作为合格的文学史。
但是反观《现代中国文学史》,史传的“铺叙履历”是钱基博始终没有放弃的方式。钱著所录作家尤其是他所拎出的宗派大师,不仅叙述其文学创作,还涉及其文学批评,以及他们文学活动以外的各项活动或言论,并且后者的体量非常大。在中国古代的史传文学中,并不刻意区分文人的经学活动、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因政治活动本就是古代文人的根本追求,而经学与文学的概念是相通的。乃至于某些文人的书法成就,都在这部文学史中得到提及。如叙郑孝胥:“孝胥诗文之外,喜作书,笔力挺秀,而瘦硬特甚;盖原本苏轼而参以变化者”[1]307;叙康有为:“有为论书绝精,顾强不知以为知,夸诞其词,所作又不能称是;而转折多圆笔,六朝转笔无圆者……”[1]380因此,钱基博仍然是以史传的铺叙方式去写作这部文学史的。以其自言概括,《史记》之“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1]12,是本书坚持的一大特点。
其二,《史记》互见法。《序》曰:“抑史家有激射隐显之法,其义昉于太史公。”[1]4即今之所谓互见法。钱基博在《序》举例道,“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详见康有为、梁启超篇,而戊戌党人之不餍人意,则见义于章炳麟篇,借章氏之论以畅发之。”此外书中还有一些应用互见法的地方。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叙梁启超的一节,有对其师康有为的互见,在梁启超传中,交代康有为做学术有时候很武断,并且好引用纬书,用神秘性讲孔子,梁启超并不认同。
有对胡适以及白话文运动的互见。“少年有绩溪胡适者,新自美洲毕所学而归,都讲京师,倡为白话文,风靡一时;意气之盛,与启超早年入湘主时务学堂差相埒也。启超则大喜,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以视民国初元,启超日本归来之好以诗古文词与林纾、陈衍诸老相周旋者,其趣向又一变矣。顾启超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诸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诸少年排诋孔子,以‘专打孔家店’为揭帜;而启超则终以孔子大中至正,模楷人伦,不可毁也。诸少年斥古文学以为死文学;为骈文乎,则斥曰选学妖孽;倘散文乎,又谥以桐城谬种;无一而可。而启超则治古文学,以为不可尽废,死而有不尽死者也。[1]451”从这段对于梁启超的叙述中,不难体会钱基博对白话文运动有不满之处,借梁启超之行径,以及“诸少年噪曰”等史笔叙述之法,表达出对于白话文运动部分主张的担忧。
在记录人物时,重视网罗轶闻的倾向则是来源于《晋书》。《序》曰:“征文,则扬、马侈陈词赋,《汉书》之成规也;叙事,则王谢详征轶闻,《晋书》之前例也。”[1]4前者是说长篇大段地引用作家的作品,是史书的成例。而后者,则说明了钱基博认为在此书中广泛记录轶闻,是对《晋书》的继承。《晋书》此例,早有褒贬,刘知几《史通·采撰》:“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6]。较为早期的史学家,对于《晋书》这种做法是持鄙薄态度的。然而北宋《册府元龟》则称:“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遗逸,芟夷芜蔓,举其精要……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传记而附益之,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记。[7]”钱基博则是接受《册府元龟》以及以后的赵翼等人的观点,肯定其正面意义,认为搜罗轶闻是史料的良好补充,从而用以建构现代文学史。
通观全书,钱著收集不少作家轶事,也确实起到了补充史料的作用。此法在叙樊增祥时较为明显。“父燮,承袭一等轻年都尉,历官湖南水州镇总兵,酣饮不事事。巡抚骆秉章将劾之。湘阴左宗棠方以在籍举人,佐秉章,主其军政。燮恐,谒求解,伏地拜。宗棠不答,又诟让燮。燮负武官至红顶矣,亦惭怒相诟唾而出也。遂以剥饷乘轿被劾,罢官归;谓增祥曰:‘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增祥天性聪颖,七岁读唐诗;燮曰:‘汝能对「开帘见月」否?’则应声曰:‘闭户读书。’燮心喜之而故诃曰:‘书可对月耶!’时架上所有,自太白、香山、放翁、青丘而外,惟袁、蒋、赵三家诗;增祥不喜蒋而嗜袁、赵,放言高咏,动数百言;长老皆奇赏之。既而燮被议,则课增祥为举业,日坐斋中教督;属文,每数行,必取阅;阅必数数诃骂。”“之洞适自蜀还京,与增祥别且久,相见叹曰:‘子其终为文人乎?’事有其大且远者,而日以风雅自命,辜吾望矣!’增祥皇然请业,尽屏所为词章之学,非有用之书不观。之洞与增祥故皆好谈,至是谈益剧,达昼夜不止,相与上下千古,举凡时政得失之由,中外强弱之形,人才消长之数;每举一事,必往复再三,穷其原始,究其终极。所著《广雅堂问答》一卷,即当日疏记者也。[1]232”这些轶事的记录,对于说明樊增祥为何出身武人世家却从文,以及生平创作志趣的转向,如写作《前后彩云曲》其中对家国的关怀,有着很强的解释说明的功能。
类似于此的还有“王树枏”一节。“树枏少善骈偶之文。吴汝纶之知冀州也,延主州之信都书院,索观其文,笑曰:‘此非晋卿之文也。’树枏始不服,已取《太史公书》以下治之数月,试操笔为之,以示汝纶。乃曰:‘此真晋卿之文矣。’于是尽屏骈偶之文不为;益浸淫于两汉,而出入于昌黎、半山之间。[1]168”说明其创作由骈偶文向古文的志趣转变。
三、其他诸体
在两《汉书·儒林传》,《史记》《晋书》等史传之外,钱基博还采纳了一些其他方式去书写这部文学史。《序》曰:“而古文学之中,文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诗之别,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至诗之魏晋,其渊源实出王闿运、章炳麟。[1]4”
“其渊源实出……”这样的表述,对于文学渊源的关注,则近于钟嵘《诗品》。《诗品》评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评班婕妤:“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8]诸如此类。即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9]”。虽然两《汉书·儒林传》同样强调昭明师法,并且已被钱著充分继承,但《诗品》所揭示的师承渊源,更接近于今“纯文学”的范围。这也是钱基博自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强调的,要对“文章得失兴废”有所点评和结论。因此,对于“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钱基博来说,《诗品》等“诗文评类”著作,自然是著书体例的源头之一。
谈及词学大师朱祖谋,介绍其词学成就之后,钱基博又以“入能品”评价其作品。“品”一词无疑承自魏晋品藻人物,而钟嵘《诗品》应用到诗评,分上中下讨论五言诗。此后,“神品”“逸品”“妙品”“能品”等词汇,广泛应用于对书画和文学作品的评点。至于对作家的文学成就与特色的评点,在钱著中更是俯仰皆是。如谈到姚永朴《萧先生传》,“其文随手起落,不为张黄,坦迤平直中,自然感激顿挫;不如并世诸公之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气,硬断硬接;而我用我法,余味全包;此真姚鼐血脉也。[1]120”这类评点是十分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特色的而独有的。
《序》曰:“而闿运、炳麟已前见文篇,则详次其论诗于文篇,以明宗旨,而互著其姓名于诗篇,以昭流别,亦史家详略互见之法应尔也。[1]4”“互著”一词,揭示出钱基博对目录学的考虑。其实钱著与目录之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言,“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文学史本就著录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将目录之体吸纳进去。然而,《序》中又特拈出“互著”一词,需要进行辨析。章学诚言《校雠通义》:“西汉刘歆《七略》中有‘互著’之法。著录时一书分属两类者为‘互著’,即互见之法,或附加著录。如石经《周易》,既著录于经部,又可著录于金石,故可分属两类。”本是目录著作对图书进行著录时采取的一种手段,因为同一部书可能符合多个类目的著录条件,则应当不避重复进行著录,以保证对此书认识的全面性。在这里,关于文学作品的“互著”与史传的“互见”有所含混,二者的意义较为趋近,但是仍有些许不同。史传的“互见法”,包含传主的生平各个方面,钱基博所自举的例子,戊戌政变的正面情况与反对情况,互见于《康有为》《梁启超》篇和《章炳麟》篇。而此处所谓“互著”,更集中于说明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也许不止于一种文体,则取其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体进行主要的介绍,而其他成就,则在介绍其他文体的代表作家时,使用“互著”法顺带提及。
此法在钱著中大量使用。晚清民国时期的作家创作很难局限于单种文体,这也是钱基博用史传体的同时,为适应此段文学史所做出的调整。以当时著名的文人王闿运而言,经学、史学、文学都颇有成就,在文学之中,诗、文、诗选均名重一时。全书提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湘潭王闿运,称之“文章老宿”,将他推为“魏晋文”的宗师。在“魏晋文”章节下叙述王闿运生平,笔墨极为丰富,并且举《秋醒词序》《录祺祥故事》《到广州与妇书》等说明其文章成就。以下也述及王闿运的七言近体、七言古体成就。此为列传之体,铺叙履历。不过,由于王闿运对于晚清文学的影响太大,在论诗时不得不又将他捧出。从名目上看,钱基博将这一段古文学的“诗”分为“中晚唐诗”和“宋诗”进行叙述,但实际上还有一派“魏晋诗”,钱基博称:“近来诗派大别为三宗:清季王闿运崛起湘潭,与武冈邓辅倡为古体,每有作皆五言,力追魏晋,上窥《风》《骚》,不取宋唐歌行近体。……闿运自谓学二陆,至陶、谢已无阶可登。[1]230”而“魏晋诗”在钱著中未能详细展开,恐怕由于篇幅所限,前文既已明“魏晋文”的状况,在此处用“互著”法,也可减省赘述。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部分的末尾,即《古文学·曲·吴梅》的结语处,钱基博又言此处是“谨爰《明史·文苑传》附纪复社、几社之例,附于末”。其文称:“梅为南社社员之一。而南社者,创始于让清光绪乙酉,为南革命诸巨子所组合;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岁汇所著,出《南社丛刊》两巨帙,分诗文词选三种,已刊至二十余集。其中多愤世嫉时,慷慨悲歌之作。与少陵诗史相近也。它如善化黄兴克强、桃源宋教仁渔父、三原于右任、广东汪兆铭精卫之徒,皆一时政雄,而隶籍南社,焜耀斯世焉。[1]370”
《明史·文苑传》:“(张溥)崇祯元年以选贡生入都,采方成进士,两人名彻都下。已而采官临川。溥归,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社。[10]”
复社是明末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社。钱基博仿此例,可见其感时忧国的情绪,以及对政治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解。
此外,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钱基博也并非时时恪守传统的史传体例,而是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乙某人附在甲某人传记之后的情况。首先观察全书目录,以“宋诗”下为例,“陈三立(附:张之洞、范当世、及子衡恪 方恪)”。古纪传体史书通例,某人之兄弟、子嗣往往直接附于此人传后,但陈三立之子陈衡恪、陈方恪却没有直接承接其父,而是在张之洞、范当世之后被提及。可见钱基博在此还是考虑以文学史的脉络为主轴,更为重视展示文学演进的过程。其次,在附录某人时,也经常不按照史书“另起一事”的定式进行附录,而是根据行文的文意,穿插附录。如叙“魏晋文”王闿运,后附其宗派者廖平为“另起一事”,但在叙廖平中间,谈及其弟子的言论,“其弟子蒙文通著《议蜀学》以褒大其师曰:‘……六国之后,未易比拟。呜呼伟矣!’文通,名尔达,以字行,又作闻通;四川盐亭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经学导言》,亦以阐明师说;盖平弟子之尤稚齿者也。[1]76”以下又拉回到“平不屑意为词章……”的叙述中。此类附著,虽无标注,但个人认为更接近于诸如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体。复次,在同一文体的各人物传记之间,往往有一段承上启下的说明议论。如“王国维”与“吴梅”之间,则称:“特是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列;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云。[1]355”此类承接的笔法比比皆是。这种做法也在史传中罕见,能够体现出钱基博希望理清文学发展脉络,著一部真正的“文学史”的想法。
虽然《现代中国文学史》被学者视为在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主要受西学影响而起,在理论和写作上均离不开西方文学史的模式的情况下,坚持复古、保守的代表,但实际上钱基博自有创见。他的创见也许来自于传统,正如此书的体例有数个明言或未言的源头,但体例的“杂糅”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并且在依靠传统体例的同时,虽然钱基博有意跳脱出白话、文言之争,但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讲,这部书实际上绕不开“文学”的定义、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等问题,也承认了白话文作为一种“体”的存在,可为一代之文学,因此也就帮助建构了“现代性”。
文学之“体”在钱基博心目中的地位无以复加。在提及王闿运《八代文粹》时,强调“类分仍夫《萧选》,正副略仿《李钞》,要以截断众流,归之淳雅”[1]51。钱基博评论刘师培时称:“凡所持论,见《文说》、《广文言说》、《文笔诗笔词笔考》。盖融合昭明《文选》、子玄《史通》以迄阮元、章学诚,兼纵博涉,而以自成一家言者也。于是仪征阮氏之《文言》学,得师培而门户益张,壁垒益固。论小学为文章之始基,以骈文实文体之正宗,本于阮元者也。论文章流别同于诸子,推诗赋根源本于纵横,出之章学诚者也。阮氏之学,本衍《文选》。章氏薪向,乃在《史通》。而师培融裁萧、刘,出入章、阮,旁推交勘以观会通。[1]141”如果我们以类似的视角去看待钱基博这部著作本身,亦或多或少可以窥见他融合众体、以观会通的尝试和努力。本文所列,自然难以尽之,只能聊作略观此书的一个思路。